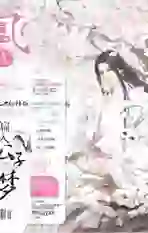可怜美人落梁家
2014-10-15天真无邪
天真无邪

梁净从嫁给崔恕的第一天起就清楚他看不起自己,也可能更早一点,早在她讥笑太子苠之胖得像头猪的时候,一席之隔的崔恕冷冷看去,眼中从那一刻开始有了讥讽的意思。
讥讽她的胆大无脑还是愚不可及,从来不是她要关心的事。她的父亲是苠国丞相,这已经足够说明一切问题。
梁净面带冷笑,微扬首,回以同样针锋相对的眼刀。
一、
崔恕并不是梁丞相意料中女婿的人选,他谋划着将梁净嫁给太子,胖得像头猪的太子,小时候梁净见他第一次回去就做了一夜被苠之吃掉的噩梦,听说父亲这想法后好似晴天霹雳,又哭又闹,从六岁闹到了十六岁,梁丞相非但没有一点退却的意思,还以苠之瘦身非常成功来试图劝她接受,她冷冷笑:“猪就是猪,瘦下来还能冒充鹿?”
她的口无遮拦很大一部分来自父亲的纵容,梁丞相在一旁抚膝苦笑,爱怜得任她胡闹。所有子女中他最看重梁净,倒不仅仅因为她是自己唯一的嫡女,而是她惊人的容貌,是真漂亮,就连最不对盘的言官都不得不叹一句,可怜美人落梁家。
美人被父亲逼着嫁给胖似一头猪的苠之,她却在他俩见面当晚碰见崔恕,以外貌闻名京城新科状元郎。酒酣之际,人少之地,他的眼睛仍旧亮得不可思议,他推开了梁净试图靠过去的身体,笑得礼貌又疏离:“姑娘自重。”
她很自重,否则她会在第一次见面就佯装自己被非礼,然后逼他娶自己,这应该是双方熟悉后才能干的事情。之后她频繁约见崔恕,崔恕频繁以各种理由回绝,久等无回应的梁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堵在苠国宫城外,这是崔恕上朝归来必要走的一条道。他骑马独行,闻声抬头,正对掀帘之后一双美目,美目的主人单手支颐,五指豆蔻有艳若丹霞的色泽,漫不经心拨弄窗下一把流苏,红色丝线缠绕在她白如明玉的指间,崔恕恨恨地腹诽:妖精。
她轻笑,眼线随之上调,划出一道异常旖旎的线条:“崔公子,有空吗?”
她不叫他大人,却称他公子,青楼女子揽客的招数,可崔恕并不清楚。她问:“公子能赏光跟小女子喝杯茶吗?”
崔恕要是清楚这小女子肆意妄为的程度,他压根就不会停下来跟她讲句话,也不会禁不住她三哄四骗去了茶楼,一杯茶下肚,一股邪火直蹿脑门,喉头一阵阵发紧,梁净的影子暧昧地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一觉醒来梁净躺在他怀中,身无片缕,跟他一样。崔恕脑中轰然炸裂,电光石火间,他从茶中窥见的一切给了这个严守男女大防,视礼义廉耻如性命的状元郎剧烈一击,他难以置信地朝她看去,梁净就在那样的目光下怡然仰首,乌发如水泻,成了此刻唯一遮蔽她躯体的东西。她说:“三日后到我家提亲。”
崔恕怒极反笑:“凭什么?”
“我会怀孕,”梁净淡定地给他陈述最可怖的结局,“我会向我父亲禀明这是你的孩子,你和你的仕途将从此一蹶不振。”
她给的威胁与奇耻大辱无异,崔恕大怒,扬手朝她挥去,最后却一拳击在桌面上,震得茶杯四下跌碎,他竭力按捺怒火:“你知不知道我早有了妻子的人选?”
“我不介意与别的女人分享你。”她面带微笑,一件件为自己披衣。怒火烧得他浑身战栗,他咬牙切齿丢下一句“荡妇”后摔门离去。
她的奴婢幽兰就等在门口,他震惊到了极点,脱口就问:“姓梁的连脸面都不要了吗?”
三日之后他果真上门提亲,梁丞相大吃一惊,崔恕未必不是女婿的最佳人选,只是他一心盼着女儿嫁入宫中,两两对比,高下立现,他委婉地拒绝,原本崔恕求婚的心也不强烈,只待他摇头说一句不行,自己掉头就走。岂料梁丞相刚把头一摇,梁净从屏风后走出,严妆高发,与当夜烟视媚行浑然两样,但一样有令人难以逼视的艳光。她朝父亲盈盈一拜,两行泪旋即沁出密如蝶翼的睫,她开始叙述自己对崔恕的相思之情,请父亲成全。崔恕心想,自己当时的表情一定像是受到了非礼。
梁丞相疼女儿,不是一般的宠,而是毫无原则地纵容。女儿心中已有他人,将她送入宫的心思也淡了,当下应允了崔恕的提亲。
洞房当夜,崔恕带着凛然怒意掀了梁净的红帕,将交杯酒泼到地上,以行动表达完所有愤怒后他转身往外走。他必须要走,因为别房还有个哭泣不止的女人亟待他抚慰。
今夜确实是他的婚礼,不过该娶的不是梁丞相的嫡女,而是他的青梅竹马温翩翩,他落魄失意时不离不弃的女子。在最潦倒时变卖身上一应首饰供他科考,甚至不惜和父母决裂随他上京,这情深义重让他感动,相应的,也让他愧疚深重。崔恕推开房门,她仍跟从前那样安静地迎他进来,神色如常,只有微红的眼圈泄露她曾痛哭的真相,崔恕揽她入怀,以吻触她发顶心:“放心,我会一心一意待你。”
梁净并没有因为他的忽视表现出任何委屈,相反,她以别人始料未及的速度投入了新婚生活中。她嫌弃自己住的屋室狭小潮湿,从府外请人重新整修,挑剔府中吃食不洁,厨子来了一批又去了一批,丞相府的生活真正教会这千金小姐何谓珍馐佳酿,她奢侈的习惯对崔府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
管家报府上开销,光是夫人这一项就占了大半,多少次崔恕忍无可忍,摔笔起身要同那女人理论,最后还是翩翩好说歹说拽住了他,姑娘嫁作新妇,难免疏于应对,劝他多多忍耐,听得崔恕恨声反问:“这些人情世故连你都懂,她一个相府出身的小姐却一窍不通。而且还……”
他双颊诡异地红了,他没有补充之后的内容。
光是奢靡也就罢了,梁净性子倔,稍有不顺就肆意打骂下人。一次崔恕在书房与同僚议事,远远从她居处传来女子的痛哭声,待他一脸尴尬送走同僚赶去事发地时,温翩翩前脚刚到,跟跪在地上嘤嘤哭泣的奴婢一同接受她的高声训斥。见这一幕崔恕气不打一处来,拉过翩翩到一边,气急败坏质问梁净翩翩到底哪点惹她不快。
“她插手我管教下人。”梁净应声抬眸,形状完美的唇带着讥讽冷笑,这个过分漂亮的女人确实有惊人的容貌,哪怕处于盛怒,怒气也只是增强了她眼中迫人的光亮。
崔恕忍了又忍:“下人所犯何事?”
“偷窃。我的玉簪在她衣物中被发现,她抵死不肯承认,我抽了她几鞭。”
翩翩怯生生欲解释,梁净直截了当打断了她:“你的翩翩菩萨心肠,劝我网开一面,被我骂了。”
她倒是直接,崔恕一时是恨一时又气,硬声质问:“下手何必这样狠?”
梁净垂眸打量受鞭刑的奴婢一番,赞同似的点头:“像是打重了。”
二、
崔恕气急攻心,拉着翩翩转身就走。出了门幽兰追他们上来,连喊了四五声姑爷才勉强将他叫住。崔恕一回头,认出她是梁净带来的丫头后脸色立刻转冷:“又怎么?”
“偷小姐玉簪的丫头跳井了。”
当他和翩翩赶回时人已捞出,众人一时不敢接近,唯有梁净蹲在旁边俯身细看,须臾抬首,环顾四周,她的目光落在崔恕身后,朝某人弯出一点冷淡笑意:“没死,只是岔了气,叫大夫过来看看。”
崔恕倒吸一口凉气,命管家去请大夫,转身之际正听到梁净疾言厉色教导下人:“想死?刀、剪子、绳子都可以,谁都不准打这口井的主意。死了你倒干净,还让不让活着的人喝水?”
崔恕一口血卡在喉咙里。
“她有病,”出来后崔恕悲愤交加,连声咒骂,朝身边人数落这个女人离经叛道的地方,他实在想不通,梁丞相看着温良恭谨,怎么养出一个女儿比土匪还要刁蛮。
“一个活生生的人可能死在她面前,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温翩翩强笑:“都说梁丞相很疼这个女儿,看来是不差的。”
崔恕只管恨恨道:“这个女人的心是石头砌成的吗?她都不怕?”
晚上入睡前,崔恕转身握住翩翩的手,轻言细语:“将来我们的女儿不要像她。”
温翩翩提了一天的心刚要放下。不过片刻他又开口,两只瞳仁困惑地看向窗外月光照进来的地方,喃喃道:“她这个女人真是胆大……连死人都不怕,她还怕什么?”
大夫被幽兰请去为她家小姐梁净诊脉,这些天她的精力空前不济,整天像是睡不够,沾着枕头就想闭眼睛。大夫的手搭上梁净的腕,须臾眼一眯,退后几步忙不迭要道喜:“夫人这是有孕了。”
梁净尚未怎样,幽兰先连念了数声“阿弥陀佛”,听得梁净扑哧一声笑:“说得好像孩子是菩萨的!”
幽兰脸色骤变,双手合十朝上念念有词:“菩萨在上,我家小姐一向口无遮拦,罚她下辈子当个哑巴,只要小少爷平安无事。”
她微笑着抚摸小腹:“怎么知道是儿子?我猜是姑娘,我们来打赌。”
“赌什么?”幽兰轻声问。
“要是女儿,你走,要是儿子,你留。”
幽兰的泪一下子涌出来。
崔恕听说这消息时温翩翩就陪在左右。要说酸楚,有,这些天崔恕几乎夜夜宿在她房中,倒叫梁净先蹦出一个肚子来。庆幸,也有,翩翩留心观察,崔恕并没有太意外,倒也不是非常开心,挥手告诉来人说了一句知道了,便继续做适才未完的事。
这本来就是个难伺候的主,有了身孕后口味更是偏僻入里,有不愤她颐指气使,或者吃过她两三回苦头的,也有在前头伺候听见一两句梁净同贴身丫鬟幽兰玩笑的句子,断章取义截了一字两句,硬生生编了珠胎暗结,生父另有他人的事,将脏水泼到了梁净的身上。
梁净哪是个能忍气吞声的姑娘,一气之下将相关的人绑了起来,管家暗自叫苦,偷偷溜去禀告崔恕,等他赶到的时候该打的已经打了,该骂的也已经骂爽了。她就坐在树影下怡然喝下人沏好的茶。
崔恕在背后凝望着她,很久回过头,也不知跟谁在讲:“千万别是个女儿啊。”
三、
翩翩从背后环住他,在云雨之后的床上,他就势牵住她的手放在唇下,浅吻,眼睛习惯性地落在窗台月光射进的地方,须臾像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异样,转身与翩翩相对,这才注意到她眼睫潮湿,于是柔声问:“怎么了?”
她垂下眼睛,低低说:“不要离开我。”
他想也没想,直接答:“我不会离开你。”她柔软地偎入他怀中,片刻,听到他喃喃的声音,像是对某处空气自言自语,“生个女儿也好。”翩翩缓慢转身,任由一滴即将滑下的泪渗入枕中纤维里。
这个孩子来得意外,去得也意外。梁净中午贪凉,多喝了碗冰镇酸梅汤,到了下午就开始腹痛。幽兰眼见她裙下一层层渗血,已知大事不妙,不巧崔恕陪翩翩去府外过寿,将府中能干事的都带走了,等幽兰大费周章从外边请来大夫已是夜半,梁净痛到极处,下唇咬得血迹斑斑,却连一声痛呼也无,连大夫都瞠目:“夫人这是何苦?”幽兰忍了许久的泪终于轰然坠下。
孩子没有保住。
第二天才回府的崔恕听到这消息后脸色骤变,当他大步赶去梁净居处时却先听到一片哀泣痛哭的求饶。他努力摈弃脑中最坏猜测,镇定片刻,推门,她由侍女搀扶靠坐床上,抬头迎视他的目光令他有如刀锋迎面的错觉,那杀气割裂他肌肤,对视碰撞激发的光焰让他眼前有一瞬空白。
很久,他看见那曾因偷窃遭罪的婢女,此刻奄奄一息俯跪地上。
最后他看清梁净,长发及地,脂粉未施,她有空前憔悴但令人屏息的美丽容颜。此情此景,她依然倔强的防卫让他忽然无力开口。
翩翩骇然低问:“怎么回事?”
她应声看去,长发垂在两边,从中扬起的头颅美丽,下颌尖尖,她出口的句子与她容颜一样有令人窒息的感觉:“她承认在我茶中下药,我割了她舌头,打断她两条腿。”
她进攻的姿态终于瓦解他心中仅存的酸楚,她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惜,哪怕这来自孩子的父亲。许久,崔恕冷静开口,命令左右:“将那贱婢拖下去,问清楚了,送去妓院。”
婢女似预见她将面对的可怖结局,哀号着朝崔恕身后的翩翩扑去,崔恕闪身一挡,抬脚踹上她的肩,将她狠狠踢开,这婢女咿唔痛号摔出几丈外。
翩翩煞白小脸藏在崔恕怀中,他抬头,与安静旁观的梁净目光陡然相撞,很久,他才意识到她看的并非自己,而是自他背后射进窗内的一束光。
当夜翩翩数次自噩梦中惊醒,每次醒来都发现崔恕尚未入睡,而是睁眼茫然地看着上方,他并无意识到她的清醒,而她听见他心底的叹息。
第二天她告诉崔恕自己怀孕的消息,如她所预料的,他在很短暂的惊讶后变得异常开心,拉她坐下,细数她生下孩子后所能得到的种种好处。翩翩强笑听他讲,敏感地注意到他话中没有一字涉及孩子的性别,这诚然是对她的爱护,可还有别的什么,她不愿深究。
她闭眼,抚摸自己尚未隆起的腹部,暗自期盼这会是个儿子。
幽兰试图向梁净严守这秘密,小产过后她身体一直未康复,或许是崔恕的有意照顾,服侍的人并未因此懈怠,相比从前更加殷勤。幽兰总试图用这些细节上的改变让她开心,比如崔恕特意遣人送来的瓜果,他向大夫询问她的身体状况,有空的时候他会到她房里坐坐,哪怕一句话都不说……幽兰不止一次感慨:“别看姑爷这人面冷,心里其实还是关心小姐的。”
梁净似笑非笑睨她一眼:“哄我呢还是骗你啊?哄我就算了,你家主子没这么可怜。”
崔恕止步于房前,抬手叫住前去叩门的下人,转身沿原路返回。此刻溟濛空气薄有潮意,化作水雾悄然潜入他心底,连带他的心都开始变得晦暗不明。
四、
翩翩来探望梁净,正巧有崔恕遣人送来消暑的瓜果,她刚要伸手去取,嬷嬷大呼小叫不准她碰,歉意地同梁净解释:“我家姑娘有了身子,这些冷的凉的少碰为好,夫人也是,小产了更得注意。”
两人一走,幽兰就对着梁净哭:“什么人啊这都,前脚说她姑娘怀孕,后脚就提我小姐的事,不是给人添堵吗?”
梁净脾气差,受不了比她脾气更差的,手一拍桌子:“得了,那是人本事,你有本事把孩子变到你肚皮里去。”
“小姐,”幽兰又好笑又好气,“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梁丞相知她小产的事,连连叹气惋惜,劝她放宽心,他自己却仍旧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梁净知道是为了苠之,从前苠之痴胖,苠王都不爱,所以拖着迟迟不肯立太子,现如今虽瘦成翩翩少年郎,却忽地迷恋上一个出身低贱的宫女,还扬言非她不娶,梁丞相同皇后劝了一轮又一轮,苠之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副“我连太子都不做看你们怎么办”的样子。梁丞相气咻咻跟梁净讲:“幸好我女儿没嫁给他。”
幸好他足够爱自己的女儿,爱到她任她胡闹也心甘情愿,梁净眼一热,眼泪差点滚下来。看得梁丞相笑了:“崔恕这人真不错,模样学识都上佳,给太子当太傅也是尽心尽力,就是心思太重,弄不明白他整天想些什么。”
梁净沉默片刻,方才抬首看定父亲的眼,迟疑地问:“如果他想的,跟爹想的不一样呢?”
梁丞相虎眼一瞪:“他要是敢,爹帮你休了他。”
自她房中回来的翩翩持续腹痛,下体见血,有当初梁净小产时的症状,崔恕及时从宫中请来御医才堪堪将孩子保住。前头已有梁净一例,崔恕因此大怒,一一逼问翩翩身边服侍的人,最后是嬷嬷透露温翩翩白天去梁净屋中小坐,吃了些点心。
迎接梁净回府的是满室通明灯火,还有一脸怒容的崔恕。梁净一看翩翩不在顿时了然,这原本就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女孩,焉能不懂其中龌龊离奇,也不等他质问便直接开口承认:“是我做的。”
背后幽兰心惊胆战。
崔恕咬牙:“你做了什么?”
她微笑:“你所想到的,都是我做的。”
白瓷杯应声碎于他五指间,他拍案而起,扬袖怒指她:“你当真以为我不敢休你?”
“你最好休了我,否则我保不准弄出一点意外让孩子流掉……”
他瞳孔急速收缩:“你敢?”她粲然一笑,媚人的眼线随之上扬,她不经意展现的美艳有进攻的味道:“你大可试试。”
他怒极,扬起的手大力落下,清脆的高音匿去庭中一切声响,周遭一时如死般寂静。被掌掴的梁净以手捂面,低头,借垂下的发丝掩住她受辱那瞬的表情,轻声冷笑:“除非你有能力将你的翩翩护得周全,要不然你看我敢不敢。”
崔恕震惊地后退数步,垂手负于身后,借由晚风吹去心底和掌心热度,茫然问:“你怎么是这个样子……”
她再不看他,转身回房,幽兰泪流满面在背后追得跌跌撞撞,到僻静处她才终于止步,回头,原本阴冷表情瞬间换成另一副狡黠笑意。幽兰的泪要坠不坠愣在那里,半晌才含着哭腔叫她:“小姐!”
“我是故意的,”她压低声音,同她分享秘密,“我故意激怒崔恕,崔恕就不敢把她放在府里,温翩翩一旦被送走,将来再出什么事,可不准赖我头上。”
幽兰的泪刹那凝结:“小姐,你可是相府的千金,是梁丞相的掌上明珠……为什么就不能跟姑爷好好解释……”
梁净下颌微扬,廊下烛火的光映入她眸心,她整个人都因此熠熠生辉:“我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凭什么要跟他解释,我的父亲是当朝宰相,我凭什么不让自己快活开心,我凭什么要低声下气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五、
翩翩果真被崔恕送去别院,但之后他也并没有再细究。翩翩哭得我见犹怜,崔恕反复保证会经常去看她方才作罢,她抬起迷蒙泪眼:“她还会害我吗?”
崔恕一怔,摇头:“没有人害过你。”
翩翩心下恻然:“你还是信她。”
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抬头,见适才还灿烂的晴空已被阴云笼罩,枝丫低垂,渐成躲避遮掩的颓势,秋还未至,而天与地,他的家和国都已开始呈现风雨欲来的姿势。他心中一凛,眼中被一道突如其来的光线入侵,是梁净。她并没有注意这边二人动静,快步穿过庭院,边走边厉声问身后跟来的小厮:“病了这样久,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
“老爷怕您担心。”
“对,怕我担心,”她切齿,嘴上说着相反的话,通红的眼却出卖了她的心,“我嫁出去就不是他女儿,他死了我是最不会伤心的。”
崔恕命人先送翩翩走,交代完后快步去追梁净,他甚至无暇回头看一眼背后女子含泪的眼睛。
“怎么回事?”
梁家的马车就停在崔府门外,梁净心如汤煮,直接回他,“我爹病了。”
“怎么病的?”
“气病的,”她掀帘坐定,催促马车快行,时间紧迫他二话不说跟着进去,梁净顾不上跟来的男子昨夜还扬言要休了自己,简单交代事情始末,“太子苠之要娶一个宫女为妃,我父亲劝他许久,你猜那只猪怎么说?”
她从不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所以她固执地保留了称呼太子苠之为猪的习惯。她咬牙切齿模仿苠之的表情让人又爱又恨:“‘孤是太子,你们逼我娶别的女子,孤要是不做太子,孤是否就可以娶孤爱的女子。放他的狗屁,他做不做太子岂是他一人的事。”
盛怒中的梁净双眼异常明亮,双颊艳若红霞,看得崔恕怔了一下。
回了相府,梁丞相又入宫去见皇后,她苦等至入夜也不见父亲回来,就在梁府住下。如何安置崔恕成了难题,梁净担心府中上下瞧出端倪,直接领他去了自己未出嫁前的闺房。
房间干净整洁,崔恕扫了一圈,见梁净动身往外走,奇道:“你去哪儿?”
“书房。”
“我们是夫妻。”他忍无可忍,冷声提醒。
梁净扑哧一声笑了,越笑越停不下来,最后扶着桌子才勉强站住:“你该让你的翩翩来看看你说这句话的表情,我们要是夫妻,她跟你算什么?”
崔恕默然。梁净转身折回他面前,望着他的眼,第一次用这样心平气和的目光:“这样不就挺好,你我是名义上的夫妻,但我不会干涉你跟温翩翩的感情,你放心,我们只到这里。”
“只到这里”四个字落进崔恕耳里,让他觉得荒谬无比,牵起嘴角想与她一起笑,却无力笑。她是相府的千金,她凭什么不让自己快活开心,她甚至连对他的感情都可以控制。
崔恕视线飘落她放于桌面的无茧手指,肤色莹润如白玉,柔长纤细没有一点瑕疵。很久以前她就是用这只手拨开他们相遇那天遮挡彼此的窗帘,她那样突兀而决绝地进驻他的生活,她的坏脾气、奢靡、任性,她没有一样值得人怜爱的特质,却仍旧有扰乱他波澜不惊的人生的能力,可现在她又通知自己,一切只到这里。
长久的静默后,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为什么是我?”
“因为我是相府千金,”她慢慢站起来,费了一点力气说下去,“我刁蛮,我胡闹,我做事不经过大脑……”
“因为太子?”他看着她的眼睛。
六、
梁丞相从宫中回来后,天开始变了。
苠王处死了太子苠之深爱的女子。苠王驾崩后他仍是苠国的王,却是个伤了心的昏君,他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举国怨声载道,早有异心的诸位公子趁势而动,包括公子苠人。
翩翩生产当夜,崔恕陪着她住在城外。苠国发生兵变,梁丞相最担心的一幕发生于冬日将开始的萧索秋夜,苠人自城外率兵逼宫,苠之自焚于当年他所居住的太子宫。相府首当其冲,成为新君将要血洗以震苠国的第一步,当夜,梁丞相被擒,投入秋冬将要行刑的牢狱中。
梁净闻讯直奔梁府,早有兵士把守,她要强入,被看守的一把掀翻在地。她气急攻心,激烈地连声质问:“我爹犯了什么罪,要苠王这样心虚把他关起来?”
幽兰胆战心惊,劝她住嘴。她冷冷拂开侍女的手,直视从府中出来的一道颀长身影,如今苠国新晋的王,苠之的弟弟苠人:“我爹触犯苠国哪条法例,能大过谋朝篡位弑兄辱父的罪名?”
苠人眼中厉色一聚,强自按捺,简单吩咐左右:“送崔夫人。”四面围上人来,梁净高声斥对方放手,动用全力仍旧不能改变她被兵士拖远的命运。苠人冷冷提醒她:“崔恕屡次托我,我才不同你一介妇人计较,不要不知好歹。”
她被兵士拖开丢在远处。幽兰跑来相扶,已被吓得唇无血色:“姑爷不是太子太傅吗?怎么成了他的人?”
梁净咬唇,忽然问:“温翩翩生了吗?”
他早已听闻京中兵变,待翩翩生完孩子便连夜赶回府中,虽数次求苠人对她网开一面,苠人也一力应承,但见眼下情势他仍旧无法放心。他快马加鞭赶回,一推门他就看见梁净等在厅前。
他从未想过她第一次深夜相候,是为了请他休了自己。
自负如他或许想过,他所设想的种种原因都不是事实,他不敢深想的动机才是真相,她的任性娇纵,她的离经叛道只是因为她深情,深情所以孤意——对他孤意。
崔恕几乎想要放声大笑,从头至尾他算个什么东西,她横冲直撞进入他的生命,可她那样固执坚决地保护好自己的心。
“温翩翩生了孩子,她不可能不明不白跟着你,而我要我爹平安无事,哪怕只是一介庶民,我要他活着。”
“我们做个交易。”她说。
那一刻,他浑身力气流失殆尽,他感觉他的灵魂四溢弃肉体而去,他感觉他的躯体因此无力放声哭泣,因为他听到她说,她竟然说,她竟然在说:“你休了我,我把崔夫人的位子让给翩翩。”
他怀疑连自己的耳朵都在欺骗自己。
“你走,回你的房间。”
“你不答应我就不走。”她倔强迎视他的眼睛。
“回去,别逼我,”他静静道,“我可能会在休你之前先杀了你。”
吓坏了的幽兰硬生生将梁净拉走。那一夜想要安然入睡已是惘然,他索性抱一坛酒独坐廊下,夜半听到身后传来的细碎而迟疑的脚步,他不用回头就知是谁:“她睡了?”
幽兰在他身后几步远处跪下,含泪哀求:“姑爷,你不要休了小姐,她为救相爷心切才胡说八道的。”
崔恕不答,幽兰只当他介怀过去的事,不住叩首:“小姐不是姑爷看到那样的,她人很好,别人待她好的,她嘴上不说,可都记在心上。小姐这一生,待她真正好的就只有相爷和姑爷您了……”
崔恕一愣,半晌回头:“你觉得我对她好……”
她含泪不住点头:“姑爷的好小姐都记着,是绝对不会去害温小姐的,姑爷要是不信,姑爷要是不信……”她并没有切实有效的途径让他相信,话至这里语调转至凄凉,“小姐这一生过得太苦。我看在眼里,我看不下去。”
她俯身又一跪,起身,撞向距离自己最近的红漆木柱,用最简单的方式佐证她的证词。
七、
苠人继位,崔恕居功至伟,颁赐群臣时他却拒绝一切赏赐,只要梁丞相的安全,言辞恳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苠人终于应允。
梁丞相以平民之身放归老家,一生不准入京。
梁净用她一生幸福来赌的一步棋,换回了政变之后父亲的全身而退。崔恕感慨她的良苦用心,他恨她的无情。
梁净送走父亲的那天傍晚,崔恕将翩翩母子从城外接回,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梁净安静地旁观,带着恬淡安然的笑意,苠国天空阴云彻底散去,积郁她心头数年的阴霾也将迎来晴天。
就算她不再是相府千金,她凭什么不让自己快活开心。所以她离开,她将这决定告之崔恕,他早已预见别离,而当她亲口告诉自己时,他仍觉得茫然凄清,他清楚,那不可摆脱的深重孤独再不可能放过自己。
但最后他只是笑:“不能不走?”
梁净开口,那样清又静,仿佛只是记忆深处荡出来的回音:“崔恕,我是愧疚的,对你还有翩翩,我歉意深重,我破坏了一切,理当由我终结。”
“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为什么是我?”这一生他都无法释怀的问题。
“第一次见面我揶揄太子是猪,忠心的臣子不可能有讥讽的眼神,他会愤怒。所以我猜你有二心。”
仅此而已?只是这样?他在心里急切地追问,却并未发出声音,他清楚再问不过自取其辱罢了。最后他只是笑,连珍重也无:“好,你走。”
待梁净策马离开他的视线后他拐去翩翩的房间,她抱着孩子神情温婉,如果没有梁净,这将是他一生圆满的终点,但现在缺了一块。他静静地问:“当年偷梁净玉簪的人,是你安排的吗?”
翩翩身体一震,没有回答,轻拍襁褓中的孩子继续哄他入睡。
万籁俱静中他开口,料想这姗姗来迟的道歉她也不会稀罕,只是他想说,他要说,他必须说。他的心有一块被涨满,他得让它流出来:“梁净知道是你安排的,所以她割了那人的舌头,你害了她的孩子,她仍想要保护你……这是为什么,翩翩,这是为什么?”
翩翩的双肩抽动,有压抑的啜泣,伴随孩子不安定的啼哭,她歇斯底里地爆发:“这是她欠我的,她欠我的……”
崔恕眼中的平静有粉碎的趋势,半晌他摇头,双眼猩红,但慢慢笑开:“不,不对,她不欠我,更不会欠你……她所做每一桩每一件,对不起的人只有她自己……和我们的孩子……”
她永远不可能知道他爱上了她,在她离开后。
他同样不会知道她早已死去,苠人派去的暗卫埋伏在城外,将她伏毙。
可幸好两人都被蒙在鼓里,一切照旧,除了梁净走后,他再也听不得别人叫他崔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