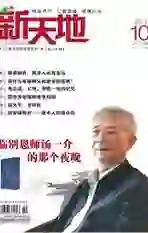父母,伴我一生的记忆
2014-10-10毛志成
像参天大树,为我遮风挡雨——这就是父亲,这就是母亲,这就是家。
不幸的人,父母已远走,满怀的爱无处投递;幸运的人,父母健在,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在 “情感”版组推出“我的父亲母亲”名人专栏,邀请各领域名家、名人,以他们饱蘸激情的笔触,书写感人至深的父母情。
如果你也有与父亲母亲难以忘怀的情感故事,欢迎来信来电,与大家分享至爱天伦。
(来信来电信息见本刊目录页。)
作者简介
毛志成,男,生于1940年,汉族,北京人。北京作家协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教师写作中心理事长,全国中小学教育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小学素质学会名誉会长。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我与小城告别》《琼楼隐事》《大地的脉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乌纱巷春秋》《前夫》等五部,杂文随笔集《毛志成杂文精品选》《毛志成短文自选集》等八部,学术专著《文学智能品质论》等三部。《“饱食者文学”的困惑》获全国报纸副刊奖,《别处死那匹马》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
父亲的学识——
“不喜文墨,是俗气!”
一个人从记事起,直到年老,能够成为永久回忆的人只有父母。
我已年逾七旬,大约因为年老,对近事往往多忘,而对越是久远的事越回忆得清晰,恍如昨日。
我对父亲的原始记忆,即我对父亲产生了第一印象,是我两三岁的时候。记得父亲那时还是个年轻人,不足30岁。他每天早晨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牵着我的手,到他的祖母(我的曾祖母)的房中,把她搀扶起来。继之端上一盆洗脸水,随后送上一碗白开水,并说上几句问候之语。
这件事办完了,便来到他母亲(我祖母)的房中,像对待我曾祖母一样对待我祖母。我祖母起身之后,也要去问候一下她的婆婆(即我父亲的祖母)。我母亲做这样的事必须在我父亲做此事之后的一段时间(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父亲对我说:“孝顺父母,孝顺长辈,男人率先!”
这可能是我自懂事起对父亲记下的第一句话。我父亲读过书,所以才懂得“率先”这个词。
我父亲因为读过古书,故而有一定的书法功力。因此每到年节,为大半条村的人写春联的事便落到父亲头上。裁纸、研墨、措词等等事加在一起,很累很累,但父亲从不拒绝。
我在私塾读书时,写毛笔字是基本功之一。我的那一点书法基本功,既得力于父亲,也得力于先生。当我五六岁时,为村民写春联的事我父亲就不去做了,由我接班。每户的春联各种条幅很多,包括贴在房门、梯子、灶台、猪圈、马棚、篱巴上的,而且春联的内容都要有针对性。我写多了,很累也很烦,因而有了怨言。父亲打了我一巴掌,喝令我说:“写!一定要认真写!而且写的字一次要比一次好!若是胡乱凑合,马马虎虎,既是对人家的不恭,也有违书生之道!更何况不喜文墨,是俗气!”
若干年后回想起来,我感谢父亲。
我几岁时最有深刻印象的事之一,是听父亲和他友人的闲谈。在父亲结识的友人当中,一种是读过书的人,一种是信佛的人。
我父亲虽然主业是务农,但却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人,大大有别于一般的农民。他和这些友人聚谈时,无论是谈书中的道理,还是谈佛教的佛理,我都愿意在一边旁听。这对我很有益,至少可以使我懂得不能去做十足的愚人。而且,也大大强化了我的记忆能力和思考能力。
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父亲对读书的极为看重。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逼我认了大量的“字号”。“字号”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写出一字,要我去认去读那些字。当“字号”积了一大堆的时候,父亲便随意抽出一个要我去认,如果错了便要挨打。
我4周岁时,由于我村尚无正式的小学校只有一个私塾,我便被父亲送到了那个私塾,先生姓李,他要我读的当然是古书。由于我有认“字号”的基础,读起书来并未感到很难,甚而很有兴趣。
父亲的智慧——
“话是最贵也最贱的东西!”
我的父亲有时是超沉默的人,能够终日无语,很少和人开玩笑。但在需要开口说话或必须讲玩笑之语的时候却异常健谈,而且十分诙谐。他曾对我说:“话是最贵也最贱的东西。人有时离不开说废话,只是为了凑趣。但话之所贵,首先在于有用。”
此外我还见到了他做的有智之事。某次我陪他到集市上卖一车粮,事成之后便到饭馆吃饭。刚要坐下来便看到几个土匪也进了饭馆,由于这伙土匪在一方很有名,我父亲便抢先与之打招呼,所说的话既有假意的亲切感又夹杂着故意式的玩笑,随后又争着付款。接着便对那伙土匪笑着说:“这个饭馆的菜我吃不惯,我要换个饭馆。”我们离开后,父亲对我说:“土匪多疑,对他冷落了他会跟你结仇,你不付钱他更会恨你。可是你跟他坐在一起吃饭,若是警察来了,会认为你是同伙,一起抓起来,这就倒了霉。”
父有智,也是子女之幸。
母亲的善良——
“饿死不丢人,干缺德事才丢人!”
我对母亲的最初记忆,像世上的大多数母亲一样,首先记下的是母亲那温馨的脊背。我伏在母亲的脊背上,母亲在村中走来走去,一边哄着我一边和别人说话。母亲虽然没读过书,但是健谈、直爽,因此人际关系极好。我从记事起记下她的“民间格言”也不少,如“紧走一步赶上穷,慢走一步穷赶上”,“小时越懒,大时越累”,“好心越多,好事越多”,“一心只想算计人,终归定被人算计”等等。我偎在母亲温暖的脊背上时,感到幸福极了。因此我也最怕母亲会死,于是我在母亲的脊背上突然鸣咽起来,喊了一声:“妈,你千万别死!”母亲坦荡地说:“只要孩子活得好好的,大人死了怕什么!孩子是父母之宝,父母老了也不能成为孩子的累赘!”那时母亲才30岁,她居然想到老了之后不要成为儿女的累赘,可敬。
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已经像魔鬼一样把人吓怕了,饿死人的事时而有之。这时,村中大队里仅有的那一点花生种子便异常宝贵。放到谁家最放心呢?这是对一户人家的道德判定。最后,那一堆花生种子便放到我家的一间小房中。虽然上了锁,但房门已经十分残破,而且房门的上半部是用窗纸糊上的,伸手就可以摸到那堆花生种子。抓几把放到锅里煮一煮或炒一炒,不仅可以解饿,而且很香。我回农村老家时,连饥饿过甚的我都想偷吃几粒,但是已经饿得近于卧床的父母宁可吃糠,也未动过抓几把花生的念头。这就使我联想到我几岁时父亲从古书的语句中讲给我的话:“取人不义之物,匪盗也。”
母亲说:“饿死不丢人,饿得去干缺德事才丢人。”
改革开放之后,我陆续出了名,先后当了作家、教授。七十多岁的母亲从老家来到我处小住,见到每日都有人(包括我的读者、学生)来看望我。在母亲面前,我往往要表现出自己的不凡。向在场者滔滔不绝地“讲经论道”,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式。别人走后,母亲不快地说:“你的话太多了,应当多听听别人的话!话太多不叫本事,俗话说喜欢叫的鸟是没肉的!”这不仅是善意的规劝,也是有益的批评。
母亲健康地活到86岁,无疾善终。她的去世,我于悲痛之余也有欣慰处。因为她从患病到去世只有9天,没有忍受太久的痛苦,而且这9天我始终守在她的身边。
她喜欢生活在农村,由我弟弟照看,由我来提供给她高于农村的物质生活所需。她的去世,本村人和外村人参加她葬礼的人太多了,原因中就包括她具有行善济人的天性。
年老父母去世前说过的话,凡是我能记起的,都很像遗嘱或遗训。记得父亲说过:人生应多悔,首在悔己之过。母亲说过:不做亏心事,躺在火葬场里也睡得香。
世上的一切父母,离世之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会将另一种遗产或遗债留给子女。我的父母生前既没欠过别人的债,也没欠过子女的债,这是真正的安息。
(责编:辛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