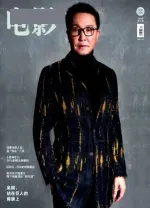两部与大提琴有关的电影
2014-09-27李金秋
因为喜欢电影,我半途从中文系跑到了艺术系。因为喜欢校园,毕业后我又从电视台跑到传媒类大学当老师。我觉得只有这种生活能很好地满足我对未来的设想——生活在大学校园,一直看电影。做老师已经做了几年,这几年看的电影也不少,有两部电影让我一直念念不忘,一部是《马友友在檀格坞》,一部是日本电影《入殓师》。
《马友友在檀格坞》更多的时候是被当做一部音乐教学片,尽管它其实获得过电影节的纪录片大奖。第一次接触这部影片,是因为参与电视台的纪录片创作,那时候一个年近五旬但仍旧十分愤青的少数民族导演,要求编导们跟着他一起“拉片”。他觉得当时跟着他做纪录片的人思路都有问题:“你们的脑子都在大学里被教坏了”他说。
我很奇怪他会跟编导们分析这么一部影片。那天,他从《马友友在檀格坞》的第一个镜头开始讲起,用他那急速而带着口音的普通话,不断地告诉编导们如何纠正他们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好的影片应该关注人,关注人的生活,从真正的生活细节入手。
我被他的讲解思路所打动,因为在大学,我们通常不这样上影视欣赏课。我们的看片课,大部分在分析人物、故事、结构、社会、文化……即使从专业的角度分析镜头画面和声音,也较少去关注导演制作影片所使用的思维方式。
从电视台回家,我再次打开这部影片。试着从导演的思维方式出发,去“研究”这部音乐教学记录片。但看到最后,我却被音乐打动,根本忘记了“研究”任务。原来大提琴竟有这样触动人心的力量,原来在乐队中只是配乐的大提琴,有那么多我没注意到的优美音色。我彻底被这部影片征服了,之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我都会拿出这部影片,一遍一遍地看。

《入殓师》剧照
从这里,我真正了解了大提琴,真正认识了马友友,也慢慢理解了前辈导演说的“导演的思维”,“生活里的文化”。我的世界被这部影片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发现了之前从没见过的风景,很美,很美。
如果说,这部影片出乎意料的给非音乐专业的我带来了非比寻常的音乐的享受,让我体会到一部教学影片也可以拍得这么有魅力的话,那么,另一部和大提琴有关的电影则给了我更多关于生命的感悟,让我对大提琴,对艺术境界的理解,又深了一层。这部和大提琴有关的电影就是第81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入殓师》,一个大提琴手做入殓师的故事。
很奇怪故事会用大提琴和入殓师做叙事组合,因为它们毕竟一个是音乐艺术,一个是让人忌讳的丧葬仪式。但这部电影就是将两者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并将后者作为了前者境界提升的基础。它用一种温情的叙事,讲述了一个失业的大提琴手小林大悟不得已从事入殓师工作,最终得到心灵提升的故事。
“死亡可能是一道门,逝去并不是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程。”日本人对待死亡,从来都是独具民族特色的。他们看待死亡如同看待樱花的飘落,认为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而入殓师,就是赋予这场旅程以永恒美丽的艺术家。入殓师装扮亡者的过程,就像大提琴家认真演奏的乐曲,是艺术的演绎,灵魂的修行。
小林大悟在跟着前辈一家一家为死者入殓的时候,慢慢地走出了内心的纠结。当他能够严谨细致地为死者做好最后的装扮时,他在大提琴上的造诣,也到达了更广阔的境界。当他拿起小时候那把普通的大提琴在地垄上自由的演奏时,他的音乐和马友友的演绎一样,也开始触动我的心灵。
《马友友在檀格坞》和《入殓师》,两部跟大提琴有关的电影,一部讲述马友友和他的大提琴,一部讲述日本入殓文化,内容迥异,但带给我的触动却那么一致,它们都让我在影片中感受到了来自灵魂深入的力量。最重要的,除了这些触动,我还开始换个角度思考“导演的思维”。
看了多年电影,写了很多影评,也经常给学生讲解影视术语。但每当我给学生放映或者自己回看这两部电影时,都还会有新的收获。每当谈起大提琴,谈起影视制作,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影片里一场场的小故事,一个个的小细节。也许,这就是我到今天还会对他们念念不忘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