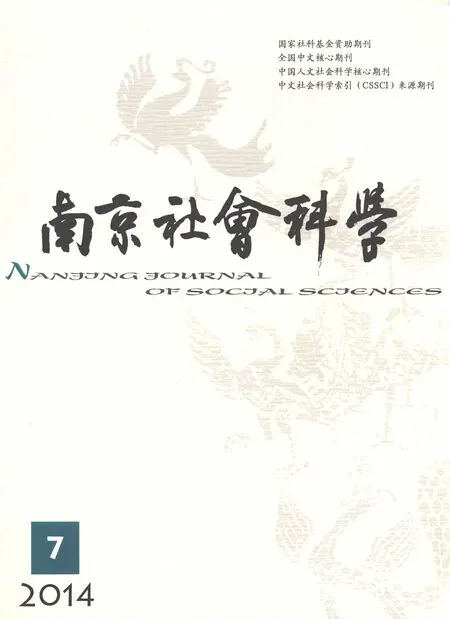宽大抑或宽纵: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处置论析*
2014-09-18严海建
严海建
宽大抑或宽纵: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处置论析*
严海建
战后国民政府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日本战犯采取宽大政策。这一政策取向既反映了国民政府试图实现战后中日两国和解的良好意愿,又是战后若干内外现实因素影响的结果。国民政府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一方面借重投降的日军配合其接收沦陷区,另一方面为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而追随其对日政策,这两方面因素都直接导致其对日处置的宽大取向。在对日本战犯审判过程中,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证据的调查尚不全面,从而造成引渡战犯的困难,使得中国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存在一定的缺失。从整体来看,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在政策层面表现为宽大,而在实践层面不免失之宽纵。
日本战犯;国民政府;宽大政策;日本战争罪责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深刻影响了战后中日关系的走向。对此,学界已有一些研究。①然而,既有研究多偏重于对国民政府战犯处理过程的叙述和整体评价,而对其确定惩处日本战犯政策的初衷及其实施过程中主客观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将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惩处置于战后盟国对日本战犯处置的整体框架中进行比较分析,并从这一角度考察其处置的宽严程度。同时,探究国民政府对处置日本战犯的实际认知,分析影响其决策和实施的各个层面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客观分析国民政府惩处日本战犯的历史意义。
一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出于对日关系的长远考虑,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采取宽大政策。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指出:“战后对日政策,本‘仁爱宽大’、‘以德报怨’之精神,建立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故处理日本战犯,亦当秉承昭示,且联合国对纽伦堡主要战犯之处置,采取教育及示范性之惩戒政策,与麦克阿瑟将军对日管制之重视收揽人心,恰同我国宽大精神相符合……故现今决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宜循主席意旨,详加研讨,厘定方针,务期宽而不纵,使正义公理与民族情谊,兼筹并顾”。②
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主要表现在严格限制对日本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力度。据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所言,“在渝参加中枢对重要战犯审查会议时,主管机关各提名单百余,而奉主席批准核列者仅三十余名,其处理之宽大审慎可知”。③另据冈村宁次回忆称,1946年2月17日,国民政府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芃生私下对其透露,“根据蒋介石主席方针,确定战犯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④
由于立场和身份的不同,日本战犯与国民政府对战犯处置宽严度的认知大相径庭。国民政府自认为对日本战犯的处置是极为宽大的,而日本战犯及其家属则认为处置过于严苛。实际上,对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政策的评价不能局限于审判中原被告双方的单一视角,而应该将之置于战后盟国审判日本战犯的整体框架下进行分析比较。
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外,同盟国分别在中国、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地设立了51个法庭,审判日本乙丙级战犯。据战后日本法务部的统计,乙丙级战犯的审判情况如下表所示。

战后盟国对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情况统计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其设立的法庭占盟国审判日本乙丙级战犯法庭数的近20%,受理案件数占盟国审判案件总数的27%,但实际判刑者(含死刑)仅占11%。国民政府审判的战犯嫌疑人仅占总数的15%,在7个国家中,只比法国和菲律宾多,比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都少。国民政府无罪释放的战犯嫌疑人数为350人,占到总数的近40%,占整个盟国法庭无罪释放人数的34%。单从上述粗略的数据对比,即可见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处理的宽大程度。
从具体要案的处理亦可见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惩处的宽大程度。以南京大屠杀案为例,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立案时,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提出的战犯名单有83人,确定被告姓名、官阶、隶属单位的战犯有59名,仅师团长以上的战犯就有12名,⑤但是在审理和结案时,所列12名重要战犯只有原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人受审,这样的结果与南京大屠杀暴行罪责的重大程度是不相符的。
战后国民政府实际判刑的日本战犯人数不过500多人,这与长期侵略中国并犯下累累罪行的日军数量相比,实在太不相称。除了处罚面有限,被判刑的日本战犯的量刑也偏轻,师团长及以上的战犯嫌疑人多未追究或做了轻判。作为对照,因南洋作战而被盟国设立于东南亚各国的法庭处决的日本战犯几乎包含了所有战时中高层将领。如在菲律宾马尼拉判决的山下奉文大将、本间雅晴中将、田岛彦太郎中将、河野毅中将、藤重正从少将;在新加坡樟宜判决的福荣真平中将、佐藤为德少将、斋俊男少将、原鼎三中将、大塚燥少将、日高己雄少将、原田熊吉中将、河村参郎中将。
曾亲历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的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参与占领日本的同盟国军中,只有中国对日本处理特别宽大,它虽然对各国的观点有所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⑥从中可见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处理的宽大程度及其与其他盟国之间的差异。
国民政府对判处有期徒刑的战犯,其执行力度亦较为宽松,且将此类战犯全部移交日本服刑,其余未经审判的战犯嫌疑人则全部释放。对此,今井武夫也认为,“这些战犯在国内服刑和获释,刺激了其他各国,使之逐渐仿效。但全部释放的壮举是其他各国长期以来难以做到的。”⑦
然而,这批战犯嫌疑人返回日本后,又受到美军的重新审查。据今井武夫回忆,在他们返回日本后,仍被关押了一段时间,“最后,美军将校从东京来了,我们在楼下列队点名,再次检举战犯嫌疑者,从而带走了以宪兵为主的一百五十人。”⑧根据驻日盟军总部的规定,“主要战犯如各盟国发现新证据与各该盟国单独有关者,若本审判结束后仍可由各盟国政府向盟总交涉要求引渡,依新证据另行起诉。”⑨美军即依据此项规定,对中国释放的战犯嫌疑人重新审查。反观国民政府,并未对被他国逮捕并涉嫌在中国犯罪的战犯嫌疑人提出重新审查的要求。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是非常宽大的。
二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并亲自在重庆中央广播局宣读,向全世界播发。蒋介石根据基督教义,主张要“待人如己”、“要爱故人”,并从中国传统思想出发,主张“不念旧恶”、“与人为善”,对国民强调中华民族具备的传统美德。蒋介石虽然强调必须确认日本是否忠实地履行“投降条件”,但又劝告国民,“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⑩该讲话表明了国民政府对中日战争的基本认识及战后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
国民政府战后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其试图实现战后中日两国和解的良好意愿。蒋介石在其讲话中指出:“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11)可见其宽大政策是从实现中日民族和解,以维护东亚持久和平的长远考虑出发的。正如1945年10月22日《中央日报》社论所指出的,“日本的处置,既有关于远东整个大局的安定,远东的安定,更有关于世界整个大局的安全。”(12)
从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来看,国民政府之所以对日本“宽大为怀”,主要是考虑到战后中日在东亚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反共和制衡苏联的问题上,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战后对日本不仅未采取报复政策,而且试图协助日本复兴。在国民政府对战后国际格局的设想中,日本是亚洲最应信赖的盟国。(13)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在送别今井武夫时,赠送其手杖一根,并谈及“两国在这次大战中,由于列强的参战终于决定了胜负,现在两国国力都很疲乏,今后的复兴也是不容易的。”“让我们用这根手杖,分别肩负起勿使本国颠覆的重任,为求国运的昌盛而共同努力吧!”(14)秦德纯的这番话表明,中日两国关系已从战时的敌对关系逐步向互助合作关系转变。
除了上述考虑之外,蒋介石在战后初期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日军的受降问题。在蒋看来,这是涉及到国共两党势力消长的重大问题,其顺利与否有赖于日军的配合。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多集中在后方,相较之下,中共军队在沦陷区的力量不容小觑。为了确保日军只向国民党军缴械投降,防止中共军队抢在国民党军之前接受日军投降,国民政府利用日军代为维持防区秩序,以遏制中共军队发展。因此,国民政府对日军采取较为宽大的政策,以获取日军的全力配合。1946年10月,在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的政策会议上,对战犯处理的决议称:“对于此次受降,日军负责执行命令之尽职人员而有战罪之处理,俟东京战犯审判告一段落后,再行决定。”(15)实际上,国民政府的这一决议是对配合接收的日军网开一面。
战后,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者,出于延续和巩固战时与美国盟友关系的考虑,国民政府在对日政策上一味追随美国。在审判日本战犯后期,美国的对日政策逐渐从遏制转为扶助,国民政府亦追随美国,进一步放宽了对日本战犯的处置。1947年9月4日,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谈话会上,曾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的张道藩提出,“日本何者应宽,何者应严,固应先加决定,但先决问题在于经我决定之后能否办到,不致遭遇他国之反对,如美国主张对日从宽,我主张从严,是否可以办到。”(16)外交部长王世杰认为,中国在许多问题上拥有否决权,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在现实中国民政府因顾及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往往不坚持自己的主张。
三
在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上,国民政府在政策层面较为宽大,从实现中日民族和解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国民政府在实际操作层面则难免存在宽纵之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既有国民政府对战犯处置重视不够的因素,亦有其无法克服的现实困境。
国民政府在战时即开始着手进行日本侵华罪行的调查统计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获得了部分证据,但这些成果和证据在战犯审判的过程中并未能发挥应有的效力。据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查团首席顾问的倪征回忆,当时国民政府“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而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料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17)战犯土肥原贤二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时,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称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台。(18)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也曾提及此事,称:“梅法官(汝璈)、向检察官(哲浚)回来的时候,我们曾讨论土肥原问题,远东法庭要他的罪证,我们拿不出来。土肥原和张宗昌、孙传芳说了些甚么话,写了些甚么信,我们全不知道。秦次长(德纯)虽然说过三岁的小孩都知道他有罪,却算不得罪证。好像某人本卖军火,但我们若没有拿到证据,还是不能说他有罪。”(19)可见,战犯之罪证不足及相关资料的缺失,使国民政府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中一度陷于被动。
以往国内学界对盟军总部大批释放战犯嫌疑人,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袒护日本战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忽视了战犯嫌疑人的起诉是以相应的战争罪行证据为基础的。由于国民政府对侵华日军罪行的证据调查存在不足,造成乙丙级战犯引渡困难,并使中国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完整性和彻底性受到很大限制。据负责引渡战犯的中国驻日代表团工作报告,截止1947年9月,各国已引渡之战罪嫌疑犯之人数为,英国290人、法国120人、荷兰64人、澳大利亚19人,而中国只有9人。(20)另据1948年1月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处理战犯业务报告记载:“经本部(国防部)申请业已引渡来华之日战犯计十三名,经本部申请尚未引渡来华者计四名,拟申请引渡者计七一名,非经本部申请引渡者计八名,国防部径自向盟军引渡来华者计六四名”。(21)从上列数据中可见,国民政府实际引渡至中国审判的战犯人数相对较少,与盟国其他法庭相比,差距较大,与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极不相称。
虽然根据盟国间互相引渡战犯之国际公约,被请求国不得藉口政治罪行而拒绝引渡,但请求引渡战犯的国家,必须提出相关战犯的罪证。据时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成员的廖季威回忆:“当初我们中国能提出确切的战犯及具体犯罪事实的人不多。因为有许多虽有具体事实而提不出其具体人名,这样不知放过了多少战犯。”(22)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对盟军总部大批释放战犯嫌疑人作出解释称:“盟总释放战犯是因为监狱里人满了,而我国又因难找确实罪证很久没有要求引渡的原故。盟总迭次催询,我国主管机关久无回答,所以只好暂予释放,但关的是嫌疑犯,并不是已经判罪的战犯,即是等于普通的拘留,虽经释放,将来我[找]到罪证,仍可随时要求逮捕并加引渡。”(23)
国民政府对侵华日军罪行的调查效果不彰,确实存在诸多客观因素,与盟国在其他各地所设法庭有很大差异。之所以对侵华日军罪行的调查效果不彰,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所致。
首先,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战盟国所遭受日军暴行的不同,中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遭受日本侵略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之久,许多受害者或死亡或迁移,大部分人证物证已很难寻觅,使得战后日本战犯罪行的调查取证工作难以顺利进行。此外,由于战后审判距暴行发生当时已过了数年或十数年,一些战犯嫌疑人在战前即已亡故,且大多数都已退役,在华投降的现役官兵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相关罪行责任人的搜捕存在现实困难,
国民政府行政院1946年1月的工作报告对战罪调查工作的成效有限及面临的困难有如下分析:
关于敌人在华罪行之调查,本院于三十三年即设立委员会,专司其事,……惟因司法机关人少事繁,且多事隔数年,调查难周,而罪行人姓名职位,被害者多不详悉,须向主管军事机关行查,公文往返费时甚多,计该部自接办至今,经审查认为罪行成立者计二千八百七十九案,日籍被告四百五十名(因实施犯罪之敌人难以查明,每由其长官负责,故被告人数不多),被害民众可考者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24)
其次,战后,美国在东亚占主导地位,盟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的法庭,大多由美、英主导。因此,由美、英主导的法庭在引渡战犯时自然较为便利,而中国这样完全由受害国自主设立的法庭实属少数,在战犯的逮捕、拘押、引渡等问题上受制于盟军总部。虽然国民政府一直在积极要求引渡相关战犯,但实际引渡来华的战犯只是很少一部分。
据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回忆,在国民政府向盟军总部要求引渡日本战犯谷寿夫时,当时的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就提出疑问:“中国法庭能否给谷寿夫一个公平审判,至少做出一个公平审判的样子。”(25)有学者指出,“东京审判对太平洋战争十分重视而对中日战争不够重视”。(26)美国主导的审判对侵华日军战争责任的忽视,必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
再次,战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动也影响到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在华罪行的调查。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随之爆发,政局动荡使国民政府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国共内战上,加上财政拮据,经费不足,使相关调查不能持久深入,同时,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以虎头蛇尾告终。
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战罪证据标准,日本战犯证据的搜集应包括:“子、物证——应予搜集:1.计划准备发动罪行之计划书命令或其他公文;2.足以证明罪行之日记函件及其他私人文书;3.足以证明罪犯思想主张或行为记录之著作;4.足以证明罪行之画报及照片;5.敌人使用酷刑所用之刑具;6.被害人之遗骸集体坟冢或受伤者之伤痕照片;7.医师或有关方面之调查书报告书或证明书;8.战俘或战犯之口供书自首书或报告书;9.非人道武器之破片或战利品;10.见证人之见证书或陈述书。丑、证人——应予登记:1.被害人;2.被害人之亲属;3.罪行目击者;4.参加罪行者或参加罪行计划者。寅、凡属有证据价值者皆应搜集之。”(27)实际上国民政府对侵华日军罪行证据的搜集偏重证人,而物证相对缺乏。
由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罪行调查工作存在不足,战犯嫌疑人的确定基本是依靠检举。检举主要来自中国受害民众,此外,也有部分来自侵华日军内部为推卸责任而发生的检举行为。冈村宁次回忆称,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虽拟将战犯范围尽量缩小,但又不能不考虑和其他同盟国处理战犯情况保持平衡,加以经过八年战乱,日军所蹂躏过的地方百姓,对日军官兵的横行霸道,纷纷检举,被拘留的人也将与日俱增。”(28)由于战时各地民众受害主要来自维持治安的日本宪兵队,所以战后民众检举的战犯嫌疑人大多是日本宪兵。据今井武夫回忆:“中国政府在七月初(中国派遣军的最后遣返日期)曾以尚未查明战犯嫌疑为理由,在上海留下了冈部直三郎大将以下将官为主的高级将领和宪兵等一千一百十七人,在汉口、广州、河南等地留下了宪兵一千人,不准乘船。”(29)可见日本宪兵作为战争期间违反国际法实施犯罪的重要主体,也是战后国民政府追究的重点。从另一角度来看,单纯追究日本宪兵的战争犯罪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日军作战部队官兵在华暴行的追究。
在中国法庭实际审理的案件中,最后被无罪释放的战犯嫌疑人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与日本战争罪行的调查不够充分有着密切的关系。1946年10月,行政院战犯处理委员会政策会议提出,“我国对战犯处理历时一年,对战犯之罪证及一切资料之收集多不齐全,倘勉强牵连处罚,似为有悖处罚战犯之本意。”并决定除对“与南京及其他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之首要战犯,应从严处理”外,对日本普通战犯的处理,“应以宽大迅速为主”,要求对已拘押的战犯,在1946年底前审理完毕,“若无重大之罪证者,予以不起诉处分,释放遣送返日。”“战罪嫌疑犯中无罪证者,应尽速遣送回国。”(30)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是战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其难免受到内外因素制约。然而,后人对其评价多脱离其所处历史场景,且未考虑主导战犯处置的国民政府本身的利益。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的原则着眼于中日两国和解和东亚的持久和平,而不是以“战胜者”自居,对于日本进行“复仇”式的惩处和民族情感的宣泄。显然,国民政府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建立在理性的人道的基础上。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处置采取宽大政策的同时,在执行层面存在一定的宽纵之失。没有正义公平就不可能奠定持久和平的基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及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对国际正义的彰显。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失于宽纵,一定程度上造成日后日本一些人对战争责任的模糊认识,甚至美化战争的错误认识。这一结果既不利于中日两国共同努力,维护东亚的持久和平,也与国民政府战后“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对日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
注:
①代表性的成果有宋志勇:《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李东朗:《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百年潮》2005年第6期;左双文:《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6期;刘统:《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概述(1945—1949)》,《民国档案》2014年第1期。
②③《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记录》(1946年10月2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编印,第420、421页。
④【日】稻叶正夫整理,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页。
⑤《司法行政部关于南京大屠杀案战犯名单》,胡菊蓉编:《南京审判》,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7页。
⑥⑦⑧(14)(29)【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该书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版,第 296、297、296、289—290、294页。
⑨《中国驻日代表团关于东京处理日本战犯概况报告》(1947年9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⑩(11)蒋介石:《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1945年8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124、124 页。
(12)《处置日本与安定远东》,《中央日报》1945年10月22日,第二版。
(13)关于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的战略思考,具体论述参见【日】家近亮子《蒋介石外交战略中的对日政策——作为其归结点的“以德报怨”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5)《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记录》(1946年10月2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编印,第424页。
(16)(19)(23)《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会谈话会记录》(1947年9月4—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 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版,第367、386、379 页。
(17)(18)倪征:《淡泊从容莅海牙》,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6页。
(20)《中国驻日代表团关于东京处理日本战犯概况报告》(1947年9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21)《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处理战犯业务报告》(1948年1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编印,第457—458页。
(22)廖季威:《参加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代表团见闻》,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卷(中)血肉长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91页。
(24)《行政院工作报告》(1945年5月—1946年1月),《国民政府公报》,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公报室1946年9月7日印行,第4页。
(25)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26)程兆奇:《东京审判研究手册》(序),程兆奇、龚志伟、赵玉蕙编:《东京审判研究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3页。
(27)《日本战犯罪证调查小组搜集战罪证据标准》,郭必强、姜良芹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上)》,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9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5页。
(28)【日】稻叶正夫整理,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6页。
(30)《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记录》(1946年10月2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编印,第424—425页。
〔1〕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
〔2〕林博史:《BC级战犯裁判》,岩波书店2005年版。
〔3〕茶园义男:《BC级战犯关系资料集》,不二出版1992年版。
〔4〕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7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版。
〔责任编辑:潇 湘〕
Leniency or Indulgence:Discussion 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n the Disposal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Yan Haijia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ok policy of leniency to Japanese war criminal with“return kindness for evil”treatment guidelines towards Japan from Chiang Kaishek after Word WarⅡ.This policy not only reflected the good willing attempt by national government to creat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fter world warⅡ,but also the result influenced by som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listic factors.Based on consideration of its own strategic interests,on the one h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nted to retake enemy-occupied area with the help of surrender Japanese army,on the other h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ollowed the policy toward Japan of American allia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alliances,there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 of their aspirations.During the practice of the trials to Japanese war criminals,due to limitations of some objective factors,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idn’t investigate crime evidences of Japanese atrocities sufficiently,and led to difficulties of extradition criminals,this made the court have some deficiencies on trials of several major cases.On the whole the performances of national government about disposal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re leniency from policy level and indulgence from practice level.
Japanese war criminals;The National Government;leniency policy;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K265
A
1001-8263(2014)07-0142-05
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南京210097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研究”(11YHC77007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