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他者之书
2014-09-10思郁
思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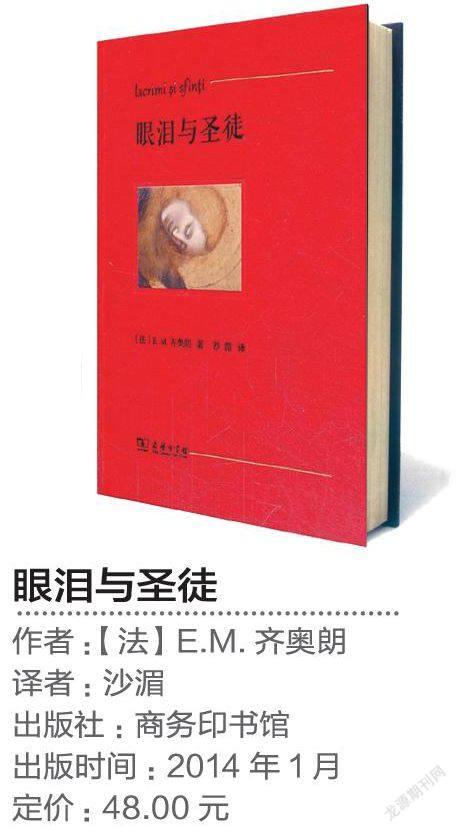
齐奥朗在《眼泪与圣徒》写到:“人们常说,只要有苦难就会有上帝。但是好像还没有人发现,苦难也可以否定上帝,而且一旦被过多的苦难罢黜,世上没有什么能够恢复他的权力。以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漠不关心的名誉去否定上帝,远不及在痛苦的狂乱中抵制上帝。”
这位1911年生于罗马尼亚的哲人和作家,虽然生活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但是并没有成为一种信徒,反而这种信仰最终导致他走向了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齐奥朗早在1934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但是这部用小语种书就的作品注定要湮没在大语种的文学风暴中。1937年离开罗马尼亚时,他的《眼泪与圣徒》即将出版,而后他就移居法国,再也没有回去。他开始尝试用法语写作,并于194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法语作品《解体概要》。迄今为止,这是中国大陆唯一能看到的他的两部作品。
齐奥朗的写作风格在他早年《眼泪与圣徒》中早已成型:一种反体系和反智性的哲学随笔,一种源于极度个人化和情绪化的沉思碎片,一种继承自尼采和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对整体和系统哲学的反叛。齐奥朗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对生命哲学的摒弃,但这种摒弃不是彻底放弃对哲学的反思,而是采用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把生命中的一切都推向我们难以理解的极致。桑塔格评价他的写作时说,齐奥朗的写作特色是,他用于开头的正是别人用于结尾的,“由结论开始,他就是从这里开始写”。所谓从结论开始,即是说把我们理解的能力拓展到我们无法理解的地方,比如说从死亡和自杀开始,从绝望和虚无开始,从腐烂的生命开始,从哲学与妓女的关系开始,从疯子的胡言乱语开始……
《眼泪与圣徒》是这样一本书,无关乎上帝与信仰,无关圣徒与宗教,它只是齐奥朗表达出一种对生命之底、存在之惑的质疑和追问。与那些圣徒的热忱相比,我们看不到一个虔诚的信者对上帝的顺从;相反,他从开始就在不停地追问,追问死亡、孤独、恐惧。他诅咒上帝,因为“诅咒比神学和哲学沉思更接近上帝”;他恐惧上帝的存在,“我们皈依宗教是出于恐惧,唯恐在这个世界的狭窄局限里窒息死亡”;他会憎恨上帝,“人类发明出上帝来平息自己对于爱、特别是对于恨的饥渴,就连上帝不存在的确凿证据也无法压下他的怒火”;他又怜悯上帝,因为“对这样一位孤独、悲伤、居丧中的上帝,一个人会很愿意表示同情。对上帝的怜悯是人类最后的幽独”。上帝只是一个普通的他者,而 “他者不存在,”这是齐奥朗的结论,只有孤独,及其孤独是唯一要紧的事情,“宇宙是一个独居的空间,全部圣灵所做的一切只是加深它的孤独”。
阅读《眼泪与圣徒》与《解体概要》的印象并不尽相同。在远去法国之后,齐奥朗沉寂了十年之久,基本没有写任何东西。他无法做到舍弃母语,用法语写作。用这种语言写作,让他感到了巨大的困难。在他看来,法文完全是某种硬化了的语言,而罗马尼亚语是一种斯拉夫语和拉丁语相混合的语言,是极富弹性的,尚未结晶的语言:“在罗马尼亚语里,没有这种对清澈、对明晰的苛求,我理解了用法文就必须明晰。”他用法语写了第一本书《解体概要》,重写了四遍,才达到一种喷涌而出的“法语的真实”。但是这种真实也意味着舍弃了原本母语写作的某种优势。在《眼泪与圣徒》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彻底的虚无,彻底的背叛,对他者的彻底追问,从圣徒到上帝,都一一成为了否决的对象。他弃绝了上帝,也弃绝了自己。写作似乎是他唯一的凭借,能够达到某种救赎的可能,但是他连写作都弃绝了。
他在《眼泪与圣徒》中写到:“在图书馆里读着精妙而无用的哲学辩论,一股不可抵挡的渴望有时会攫住我,让我想要投身于沙漠的荒芜。于是我看到万物颠倒离乱,在逻辑问题的荒谬中狂欢。就好像石头纷纷滚落,在大规模的精神滑坡中撼动了观念的秩序。”齐奥朗的写作归根结底是一种极端个人化的、抒情性的、自传式的、反体系化的哲学书写。从他的写作中,我们能感觉到哲学从一种闲暇的职业成为一种痛苦的思考,思考吞噬着自身,思想在抽象中战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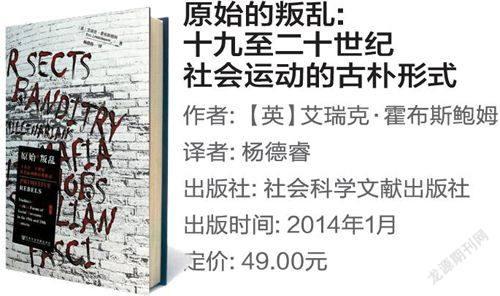
作为一部研究现代社会运动“原始”形式的专著,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重点考察了五种前现代社会运动形式:绿林好汉(盗匪)、黑手党、千禧年运动、都市暴民以及劳工教派。我们由此可理解到:现在的中东地区首都的“暴民”是如何发展成现代政治运动的;原始的卫理公会派和宗教仪式在我们现代的劳工运动中如何起到了奠基作用。一贯的霍氏风格,视野深闳,格局庞大,不仅展现出历史的本相,更成功投射出历史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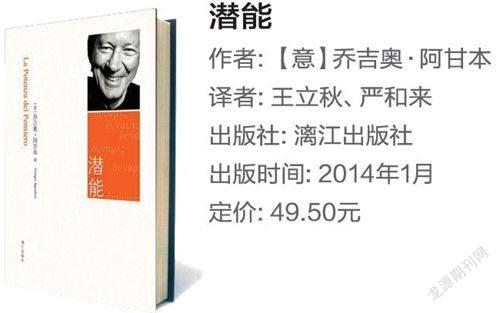
《潜能》收录了哲学家阿甘本三十年来的重要论文共22篇,涵括了阿甘本最关键也是最著名的思想成果,例如他对亚里士多德“潜能”概念的当代诠释。这些论文涉及哲学、语言学、古典学、文学、宗教、艺术史及历史等多个领域,虽各自独立,相互间又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阿甘本是那种有本事将思想化为激情,或者说将激情化为思想的学者,所以完全不必在意是否果真读懂阿甘本说了什么,而是更该关注阿甘本就这些前人论及的话题又将怎么说。

意大利边城那不勒斯的穷学者维柯、革命之都巴黎正密谋颠覆拿破仑皇朝的革命家巴贝夫、伦敦革命传单陪伴着的马克思、圣彼得堡红旗狂潮中的列宁与托洛茨基……跨越两百年的时空场景,《到芬兰车站》巨细靡遗地书写这些狂飙人物的所思所为。而更关键的是,本书清晰地展现出观念究竟是怎样生成为行动的。埃德蒙的笔触极为生动,叙及历史细节极为周至,而文笔气息绵长,足可感人,当得起梁任公所谓“笔锋常带情感”,是一部充满历史体温的杰作。

科恩兄弟的新片《醉乡民谣》,讲述的是“卢瑟”民谣音乐人戴维·范·洛克的遭遇,影片最后定格在一个看上去酷似鲍勃·迪伦的家伙在歌唱。而今天被国内熟知的鲍勃·迪伦,他所自称的“我的精神导师”,正是这本自传的主人伍迪·格斯里。作为影响几代人的美国民谣教父伍迪·格斯里,在自传中通过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琐事的描写,既展现了一个非凡艺术家的癫狂人生,也将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关于反抗与对峙的精神力量传达了出来。

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一生传奇,年轻时辞去可以带来富足生活的职位,仅仅为了到处去旅行,此后创作出来的作品屡获读者和奖项的认可。这部《我在这里做什么》是布鲁斯·查特文一生将尽之时的离别之作,包括游记、传略、故事和随笔等诸多文体,在这里除了可以读到一个传奇作家的丰满文字意外,还能看到一位作家在生命尽头要对自己一生叙述的迫切感,以及这种时候所特有的一种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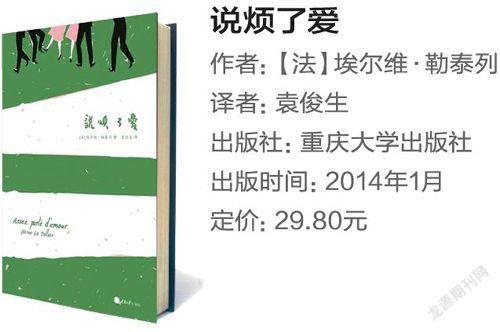
关于爱情,有相爱,自然也有出轨;有相聚,也有离别;在爱情中有甜美,也一定有煎熬。《说烦了爱》是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圈子发生的法式琐碎爱情故事,当家庭被一个个关于爱的网编织起来时,其中的背叛和分手就更具杀伤力。而法国作家埃尔维·勒泰列具有轻松讲故事且又不乏诗意的本事,一群中年男女的爱恨情仇,在他笔下就犹如单位里的八卦女王在给你讲领导家的往事旧账那般清楚迷人……而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窥视者的角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