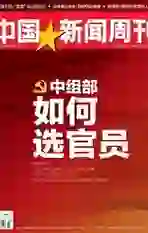翻译家孙仲旭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
2014-09-06
发了个短信,但是没有得到回复。
8月28日下午,新经典文化公司的编辑黄宁群准备给译者孙仲旭寄样书,是奈保尔的《看,这个世界》。她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其实,就在她发短信时,孙仲旭已自己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8月29日晚,孙仲旭的好友雷剑峤在微博上发布,“本人受家属之托,向诸位友朋沉痛通告: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先生于2014年8月28日在广州辞世,享年41岁。”
这条消息迅速在出版界和读者中炸开。翻译家余中先,作家张悦然、阿乙等在微博上表示哀悼。
孙仲旭8月4日在豆瓣网上的最后的留言,也引起了近百条的网友回复。
他在豆瓣上发表了和儿子的对话:
“别放弃我。”他对儿子说。
“我不会,就像你没有抛弃过我一样。”儿子Mickey回。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李玉瑶哽咽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编辑和好友,她还在自责,“如果我早一点劝他就医,或许会好很多。”
“稿费和样书先别寄,等我回来再寄吧。”一段时间之前,孙仲旭也嘱咐了上海雅众文化公司的编辑陈希颖。3月至7月,作为广州一家远洋运输公司职员的孙仲旭到喀麦隆出差。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由孙仲旭翻译,几个月前出版了,陈希颖正准备寄样书,但看到雷剑桥发布的消息,她一夜没睡觉,“第一反应也是不相信。”
新世纪以来,孙仲旭就像一个矫健的泳者,奋力徜徉在文学的翻译之海。据他自己去年统计,其译作已有400万字,从《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经典名著到《小人物日记》《恋爱中的骗子》《有人喜欢冷冰冰》等均有涉猎。
而读者提起更多的是,他重译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翻译之路的开端

“他的愤怒就是我的愤怒,他的迷惘正是我的迷惘,他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大学二年级时,孙仲旭从图书馆读到原版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说书中主人公赫尔顿跟自己有“息息相通之感”。
1999年元旦,刚毕业几年的孙仲旭,将广为流传的施咸荣译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装进书包,当作去郊区爬山时的读物,“然而一读之下,觉得不是很满意,于是萌发了自己重译一遍的念头”。
这一年,他首次发表的译作《爵士乐简史》在音乐杂志《我爱摇滚乐》上连载。一边在海运公司上着班,一边还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大概在次年完成。
“当时他自己还没有什么翻译作品发表,我是从一堆自由来稿中发现了他的译作。”译林出版社的老编辑施梓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看到他的简介,单位是航运公司,好像是业余译者。”而通常出版社的译者都是由专业译者或高校、研究院的老师担任,正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半个世纪来权威译本是施咸荣那版,他曾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
孙仲旭将自己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用16开纸打印,“并且装订得非常好,我至今都还保留着,有时候看到那个书稿,我还想起当初的事。”施梓云回忆,在文稿中还附了一封孙仲旭的信,大致说,他特别喜欢这个小说,翻译此书纯属个人爱好,并列出了老版本语言风格比较老了等重译的理由。
“没想到不久就接到了译林出版社施梓云老师的信,提到目前不可能出我的译本,但是多少肯定了我的译本,又对我推荐的新书《塞林格传》表示有兴趣。”孙仲旭也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日后每出一本新译作,他都会给施梓云捎去一本。
2001年9月,孙仲旭在译林出版了《塞林格传》。不过后来他在豆瓣说,“我出的第一本译作,现在很不满意,建议不要读。”上海雅众的陈希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这个人非常严谨,会去思索以前所翻译的东西,会修订,也经常跟我们讨论翻译上的问题。”
多次修改后,译林最终权衡,决定让市面上同时出现同一家出版社同一本书的两个版本。2007年初,孙仲旭译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他自己写道,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这也是他翻译的第一本书,“让我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但按照出版时间这是他的第十本译作。孙译本《麦田》,至今累计销量已10万册。
此后,他还在译林重译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巴黎伦敦落魄记》等。近年来,他还和上海译文、人民文学、新经典、楚尘文化、上海雅众等出版社或机构合作,成为炙手可热的年轻翻译家。
“他是我们社里很多编辑的朋友,关系都很好,这个事情对大家的打击很大。”施梓云说,“我们以前也经常见面。”他讲起有一次译林的书展到郑州,孙仲旭专门从广州赶来,“他是河南人嘛,他觉得自己是东道主,应该来跟大家见一见。”
“世界上的事情
没有什么是值得悲观的”
“我感觉他是交流欲不很强烈的人,我打电话时的感觉也是这样,但他在网上很活跃。”陈希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施梓云也说,“他的性格很温厚,做事情很实在,不是太善于言谈,但是对人很诚挚,比较重感情。”
7月19日,在杜阿拉的港口,孙仲旭用手机发了条微博,是尼采的话:“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孙仲旭在豆瓣上的网名叫Luke,在他的自我介绍中都会简短地写道,“1973年生,毕业于郑州大学外文系,现供职于广州某航运公司,业余从事文学翻译。”他有自己的微博、豆瓣小组和小站,也有自己在网易上的博客并会经常更新;每个月有读书和看电影的清单。
但从非洲回国后,尤其是8月份时,在网络上的更新已经不多。此时,他已经因抑郁症住进了医院。
施梓云在电视上看到讲抑郁症患者的,说是对这种病人讲安慰的话没用,关键是劝其就医。当时,他给孙仲旭打了电话,“你有病就要治疗,听医嘱。”也不忘安慰的话,“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值得悲观的。”孙仲旭当时表示了赞同,甚至状态还很好。
8月4日这一天,他最后一次在网络上更新了微博。这一天,他还跟新经典之前联系他的编辑黄灿灿打过电话,说样书和稿费寄到哪儿。“我跟他说,孙老师,我已经离开新经典了,我会交给同事黄宁群去落实。”黄灿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以为他还会稍微多问两句,比如你为什么不在新经典干下去了。”
但是孙仲旭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寒暄几句题外话。“我只是想他是比较简单的人,就事论事吧。”黄灿灿当时完全没有感觉到孙仲旭有患病。“给我的感觉,他是比较直率的人。我们之前出《百年孤独》时,说要给他寄一本,他说几个版本他都有买了。”
“外国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翻译不是一个职业,很多都是业余时间做,即便是大学里的老师也是有自己的主业的。大家既不是为了树碑立传,也不是为了经济收入。”黄灿灿说。
也就是说,孙仲旭近年来几百万字的翻译,均是在本职工作之外完成。陈希颖说,孙仲旭翻译《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就是去年在非洲完成的。
作为航运公司的职员,孙仲旭会经常出海,或者待在港口。“今年在非洲,他都待在港口。”编辑李玉瑶和孙仲旭每周都会通电话。
“这才是最适合我的生活”
“美景当前,凭栏良久,感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出海时,孙仲旭在博客上写道。这篇博客他用手机拍了傍晚的江口、天上的白云、路边的杂草、黑夜里的新月。
“除了工作,就是看书、学习、翻译,感觉这才是最适合我的生活。”孙仲旭在喀麦隆的杜阿拉港口,住在船上,甚至打趣道,“这几个月里,我可能是这个繁忙的港口唯一的‘常住居民。”
他喜欢拍照,专门有标签为“I Shoot”的多篇博客,尤其喜欢拍天空与海洋,特别是夕阳时的海景。
在广州时,他也喜欢街拍,记录下喝咖啡或者吃饭的地方,其中有:体育东路财富广场的猫屎咖啡,东川路的仁信牛奶老铺,大沙头的天成川菜馆,员村的陕西面馆,东圃的关中手撕面。
甚至在几年前,他还在赤道几内亚的巴塔港口出差时,“把自己拍进了局子”。当时该国在举行一次宪法修正案的公民公决。他在傍晚时决定去海边看看日落,就出门了,看到一个废弃的房屋,“很感兴趣地挑好角度照了一张照片”,然后就被警察叫住并带去警察局问话。
而最近孙仲旭被读者提及最多的还是那篇《我和Mickey》的万字博文,在去年年底由微博整理而成,里面记录了他和如今在读中学的儿子之间的各种趣事。
“我怀疑你上微博的时间比你翻译的时间都多。”Mickey说。
“没有!”孙仲旭嘴硬。
“每次我进来,你都在上微博,难道是我的运气比较差?”Mikckey反问。
孙仲旭说,Mickey英语一般,后者把部分原因归咎于“家教”,甚至说,“你那么抓我的英语,是不是想让我子承父业?”孙仲旭博客上说,“天地良心,文学翻译这么苦逼的事,我指望他也来做,我有病不成?”
就在今年出海时,孙仲旭也在电话里跟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李玉瑶讲起自己内心会因为生活上的各种琐事而焦虑不安,还有失眠。
“我也给他疏导。”李玉瑶回忆说。“他也一直说我是他的Doctor,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是这样重度的抑郁症。”
8月初回国后,孙仲旭住进了医院。就在出事前一个星期,好友雷剑桥还去医院看了一次,“就跟平时差不多的聊天。”8月19日,译林出版社的编辑张远帆在广州出差,也去医院探望过孙仲旭,“看起来恢复得不错。”
几天后,医生说,可以回家治疗了。而8月28日那天,他又选择了一个人回到医院,并自我了断。
光是今年,孙仲旭的出版译作或者再版就有十来本。上海译文的陈玉瑶和译林的张远帆都提起,孙仲旭这两年对自己的翻译也产生过怀疑,最后也表示过怕自己的身体状况会耽搁进度。
7月19日,在杜阿拉的港口,孙仲旭用手机发了条微博,是尼采的话:“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而他今年出版的译作《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原作者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也是因重度抑郁症而自杀,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