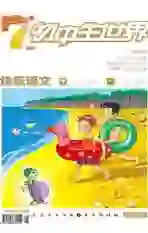假如李白遇见苏轼
2014-09-05孙伊凡
孙伊凡
假如时光能调皮一点,或许李白和苏轼便能相遇。我曾无数次地遐想,他们会是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隔着月光会心一笑,还是会在大好河山下相望无言?也许这只是我的假想。
李白遇见苏轼的那一天,会恰好带上珍藏的那壶烈酒吧。空气里酒香氤氲,宛若他们快要满溢而出的才华。苏轼大概会握着一杆毛笔,残留的墨香与浓郁的酒香融合在一起,把一切衬托得理所当然。也许,他们的相遇也似这味道,仿佛理所当然。
李白遇见苏轼的那一天,也许就是他吟出“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日子。狂妄而自由的声音一定能惊落那位独坐窗边的男子手中的那杆笔。他们毕竟是同样不羁、不拘小节的人。窗外必会有江,江水滔滔,就像感叹他们相见恨晚。太白的视线也必会落在墨迹纵横恣肆的素纸上,上面的一阕,不知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许窗外的江水也未如过去那般湍急,只是凝固在了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
李白遇见苏轼的那一刻,应该是长安桃花盛开的时刻。他们会结拜兄弟,会挥毫写下对方的诗词,会谈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会因为共同的见解而兴奋地扬起俊朗的眉毛。也许太白豪迈飘逸的仙骨会让东坡“明月几时有”的感叹变得薄一些。东坡会就着太白刚磨成的墨,重新书写一遍《赤壁怀古》,太白会发自内心地感叹气势磅礴,执笔却不再写什么,他只能脱口而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都是他们见第一面便必然要吟诵的句子,都生动准确地勾勒出了对方的形象。
我的想象始于此,也终于此。历史终是历史,不可由我恣意的想象而改变。
我明知如此,却不止一次地梦见他们相遇时的模样。
只记得那儿有明明灭灭的光,还有淳淳的酒香浸润在时间的轨迹里。李白的身后是怒放的桃花,是阳春三月繁闹的长安,他月白色的长衫与身后的繁华格格不入。他眼角含笑,缓缓对着眼前的男子开口:
“吾姓李,名太白,敢问兄台大名?”
光都快融化在那样的长安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