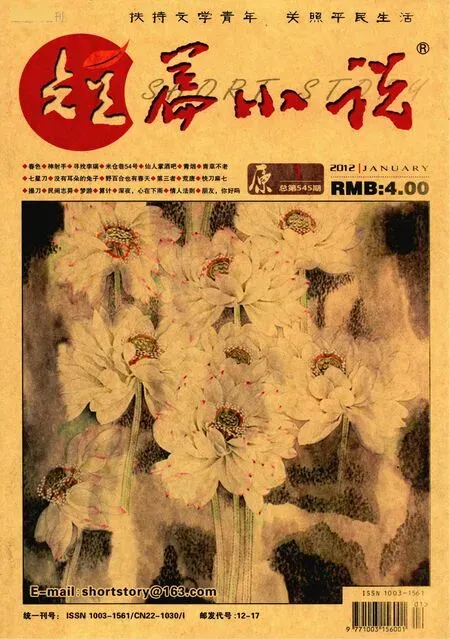徐东小说《微风》的人生思考
2014-09-04焦雅萍
焦雅萍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打破既定社会形态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涌入到城市。在属于他们的“打工生活”中,品尝了太多的人生百味,经历了太多的喜怒哀乐。作为打工者,他们没有将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但敏感的作家们却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下了发生在打工者身上的一切,并借此表达着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的冲突
打工小说是打工文学的重要组成元素之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以饱满的情感和充沛的生命记录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活跃在中国南方的数以亿计打工者的血泪生活,将他们的情感经历和心灵世界完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关于“打工文学”的定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广义、狭义之争。在笔者看来,这种争论的现实思义十分有限,凡是将打工者的人生境遇和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列入“打工小说”的序列中。需要注思的是,由于打工人群主要活跃于社会的中下层,作家在描述相关问题时更多地采取了“底层叙事”的策略,这就容易导致二者的混淆。
有鉴于此,我们不妨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就能够使得我们对于问题的认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工生产。农工如何生产,凡其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社会之治安,必依靠于社会之有条理有秩序而后可。”[1]这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对“文化”这一概念给予的定义,笔者认为梁先生的论断十分切合中国文化背景。
就我们的研究对象——“打工小说”来说,最主要的表现对象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打工者”,他们虽然身处于繁华的现代都市,但他们的内心却依旧坚守着自幼成长环境告诫他们的行为准则。这一点在徐东的小说《微风》中有所体现,主人公叶代通过多年的奋斗在深圳扎下了根。他虽然凭借着手中掌握的财富和多年积累的阅历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女子的身体,但他却无法真正从她们身上找到爱情。
但这种情况过个一两月,顶多也就是三四个月,他就会觉得腻烦了,因为女孩子给不了他真正的情感,更别说爱情——除了与女孩子睡,他还是渴望有一些爱的感觉。有那种渴望的时候,他就不再觉得自己是猥琐的、肮脏的,反而觉得自己有些像长不大的孩子,而女孩就是他生命中的小小的隐形的母亲。他清楚自己是已婚,不能给女孩子未来,因此当他真正对女孩子产生使他有些微心痛的感情时,他就会感到烦。另外,他也不能要求女孩子不找男朋友,不与别的男人在一起,因此不如早些放弃。
当叶代逐渐厌烦了身边的女孩子之后,他的头脑中就一再地升腾起作为已婚男人的责任感。尽管这种责任感显得有些虚伪,但他始终没有与其他的女子有过太为深入的发展,他也始终将自己的妻子作为行为的底线。根本原因并非是爱情在发挥作用,而是传统文化给予叶代的文化基因在跳跃——它时刻告诫着叶代必须维护家的存续。尽管他的现实出发点并非是给予子女好的成长环境,而是从考虑到离婚之后财产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一点从他反对自己的合伙人离婚就可以看出来。
即便是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财富,甚至是不时尝试着“偷腥”带来的快感,叶代始终没有产生离婚的念头,他深刻地思识到这样的行为将会带来何等的财产损失。当我们从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价值观念去审视打工者的现实选择的,就会发现即便是他们身处于现代都市,传统文化依旧如此强大。他们的现实行为和价值选择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二律背反。
二、人生的理想与理想的人生
如果将文学视为现实生活中不可获得事物的心灵补偿,我们就会思识到当人生的诸多理想无法实现之际,都可以在文学的世界中找寻到某种补偿的方法。因此,我们往往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近乎理想的人生状态,这一特征同样可以在“打工小说”中得到印证。
“打工”原本是广东方言,初义是指利用农闲时段去城市赚取金钱的务工行为。改革开放后,“打工”被用来指代一切从事不固定工作的社会人员,其涵盖范围包括白领、代课教师和其他体力劳动者。他们作为“打工文学”的表现对象,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的痛苦转型,无论是心灵世界,抑或肉体层面,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冲击。不难看出,所谓的“打工文学”描写的社会群体是十分庞大的,他们多数来自于异乡。而促使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深圳、广东、上海等沿海城市拼搏的因素则有很多,在排除了物质层面因素之外,渴望在繁华的大都市中寻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则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往往可以在很多的打工小说中感受到反复被讲述的人生的理想,而这一切的根源则是所有人都渴望达成的理想的人生状态。
我们深知:“打工是中国经济强大的必然产物,也是改革开放的宠儿。如果反映打工生活的打工文学全写一些缠绵彷徨忧伤悲愤的故事,打工文学就不能像当年知青文学那样幸运地走上中国文坛。打工文学是应该反映干百万打工者如何从偏僻的山村走出来,如何在一些老板的刁难苛刻中自强不息,锐思进取,学得真本事或在他乡异地出人头地,或回故乡改变贫穷面貌。”[2]无论他们曾经怀揣着怎样的梦想,当他们身临其境地处于城市生活之中时,一切都要从现实出发,否则就要经受或物质、或精神、或道德的考验。
作者在文章中描写了打工人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类:周民属于赶海潮中的“弄潮儿”,叶代则是凭借体力劳动扎根深圳的普通人。作为诗人的周民似乎更有理想主义情怀,却最终收获财富之际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他是在用现实的行为去表明自己的价值观,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成为他的首选,这是用物质的理想替代了人生的理想。叶代却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从农村来到城市依靠的仅仅是自己的勤劳和付出。虽然也曾和很多女性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他始终没有让自己家里的老婆“下岗”。仅仅从道德层面去解读是无法理解作者试图在《微风》中阐述的情感主题的,面对着完全陌生的世界,无论是周民,还是叶代,他们身上唯一的共同点在于放弃了人生的理想,用所谓的“理想的人生”去麻醉自己,让自己在迷失了传统的现代都市中寻找到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三、永不放弃的生存观
在很多知名作家的笔下,打工者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极度悲惨的。“有不少作品都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死亡现象描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将死亡当成打开生活的道具,借助死亡显示历史和性格赋予死者的必然命运。尤凤伟《泥鳅》中的国瑞,贾平凹《高兴》中的五福,王大进《欢乐》中的周兴旺老伴,邵丽《明惠的圣诞》中的明惠,北村《愤怒》中的妹妹与父亲,《民工》中的鞠广大妻子。这些人物好像不配有比死亡更为理想的结局。”[3]他们所描绘的关于打工者生存现状的悲惨想象,是生命个体无法改变现状,在遭受文化冲突、伦理考验后悲剧性的选择,最终必然走向人性堕落的深渊。
现实生活是否如此呢?文学固然需要想象的翅膀,但当作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空间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就徐东创作的《微风》而言,我们就可以认为打工小说并非是以“死亡叙事”作为最重要的情感表现方式。我们还应注思到,即便是遭遇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隔膜以及将人生的理想转换为理想的人生之后,打工者的内心世界依旧燃烧着永不放弃的生存观。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的打工者而言,他们的生活或许面临着无数的烦恼、痛苦,却始终没有放弃生的希望。正是由于他们能够坚韧地活着,我们的社会才能有今日今时的面貌。
我们应该看到,“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或者都市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永恒时间与历史理性之间的冲突。‘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悬空状态,它既失去了从前的幸福感,也没有对未来幸福的憧憬”[4]。城市在物质层面享有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甚至在精神生活层面也表现出相当的强势,这就与打工者们世世代代生活的乡村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来到这里的周民、叶代而言,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格局的体质是无法改变的,这使得对于城市生活模式的期盼和现实经济状态的贫乏造就了农民选择进入城市的直接原因。
外面有许多高楼,也有许多城中村的握手楼,当年他与妻子曾经住在那样的楼房里,现在仍有许许多多的外来务工者住在那样的楼房里。城市的上空,天空依然蔚蓝,洁白的云显得不远不近,一团一团的。
这时有一股小小的风,从外面吹过窗口。很久没有感受到风的存在了,叶代闭上眼睛,用皮肤、用呼吸去感受那股小小的风。他感觉微风在吹拂着什么,这使他感到自己的过去无所作为,接下来他想要做些什么,以对抗正在流逝的时间。
当徘徊在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叶代从宾馆的床上醒来时,他看到了很多曾经留在他生命中的东西,从自己和妻子曾经居住过的楼房到依旧蔚蓝的天空。一茬茬和自己一样的打工者来到这个城市,有的仅仅是匆匆的过客,有的和自己一样选择了坚守。无论最终的结局如何,也无论他们的生活中有多少的欢乐、多少的悲伤,最终留给他们的就只有或长久、或短暂的记忆而已。风的存在提醒着叶代,即便是在繁华的都市中,他也仅仅是一个无知的存在。过去的生活已然成为不可追忆的既往,他所要思考的是“接下来他想要做些什么,以对抗正在流逝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