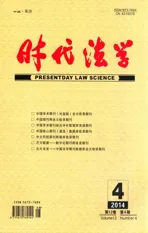论输血及血液制品感染的侵权责任
——基于日本法上的经验*
2014-08-08李雯静
李雯静
(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北海道,札幌060-0809)
论输血及血液制品感染的侵权责任
——基于日本法上的经验*
李雯静
(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北海道,札幌060-0809)
在医学界,血液被称为“生命的源泉”。然而,近年来,随着临床用血和血液制品使用的大量增加,患者感染梅毒、肝炎、甚至艾滋病的案例已屡见不鲜。而上世纪末,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曾遭遇过同样的“血液之殇”,日本司法实践在处理诸如“东大梅毒事件”、“药害肝炎事件”、“药害艾滋事件”上的成功经验会带给我国怎样的启示,以下将对日本法上血液的法律属性、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因果关系的证明以及医药产品责任主体的责任分配等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针对我国司法现状,探讨日本法对我国在法律解释适用方面的借鉴意义。
输血;血液制品;过失;因果关系;事实推定
一 、输血用血液的法律属性之争:是否属于产品
在我国,由于血液和血液制品在法律属性和伦理构成上存在一定区别,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对两者进行区分。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我国司法实践当中,由于普遍存在血液并不属于产品的认识,对因输血感染疾病的情况,一般是追究医疗机关或者血站的过错责任。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血液制品属于产品并无异议,因此血液制品导致的疾病感染,一般追究制药公司的无过错责任,或者医疗机关的过错责任*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第102条的规定,血液制品属于药品。。
与我国不同,日本法并未对血液与血液制品在名称上进行严格区分,而是统称为“血液制剂”。根据《安全血液制剂安定供给确保法》(「安全な血液製剤の安定供給の確保等に関する法律」)第2条第1款的规定,血液制剂是指人血浆及其他以人体血液作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医药品。
具体而言,日本法上的血液制剂可分为“全血制剂”、“血液成分制剂”、“血浆分化制剂”三类*中井一士「血液事業の現状と展望――血液製剤の自給をめざして」社会保険旬報1738号(1991年)15頁。。其中,全血制剂与血液成分制剂被称为“输血用血液制剂”,可对应我国法上的“血液(包括全血与成分血)”;血浆分化制剂是指,用化学或物理方法对血液中的血浆部分进行分化后提取的血浆蛋白制品,例如,用于血友病治疗的血液凝固因子,或者用于治疗感染症的免疫球蛋白*手嶋豊「血液製剤(製造物責任法の論点)」金融·商事判例増刊960号(1995年)19頁。。血浆分化制剂可对应我国法上的“血液制品”。
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对于“血浆分化制剂”属于产品这一点上并无争议。而对于“输血用血液制剂”是否属于产品,早在1994年《制造物责任法》,即产品责任法的立法审理过程中,实务界就对此展开过激烈争论*松本恒雄「製造物責任法における血液製剤の扱い」金融·商事判例948号(1994年)2頁。。
1994年6月11日,日本输血学会发表了“输血学会对将输血用血液纳入产品责任法对象的意见”声明,主张“输血用血液”不宜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规制对象,其理由如下:(1)输血用血液,包括全血血液与成分血液都只经过基本加工而未经过高度化加工;(2)血液来源均取自献血血液,且采血的日本红十字会属于非盈利性组织;(3)如果追求完全的血液安全,避免窗口期感染,必须在采血时对献血者的私生活进行详细询问,这样不仅容易侵犯献血者的隐私权,而且会使得输血用血液的制造陷入一时的中止状态*「輸血用血液を製造物責任(PL)法の対象と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の日本輸血学会の考え」NBL548号(1994年)66頁。。
与此相对,当时的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发表了反驳意见,其主张如下:(1)输血用血液在被添加了保存液和被包装后,对社会进行大量供应,应当属于产品;(2)输血学会的主张正是导致患者输血后丙肝感染率高发的重要原因,对由于血液检测技术受限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疾病感染,不应由被害人个人来承担,而应由血液的利用相关者全体来分担;(3)再者,把输血用血液纳入产品责任法规制对象的EU(欧盟)各国并没有因把血液视为产品而给血液的安全、安定供给带来任何障碍或不利影响*「(輸血用血液製剤に関する)日弁連会長談話」NBL548号(1994年)67頁。。
针对输血用血液的法律属性之争,作为产品责任法的立法提案者,日本政府对此进行了明确说明,“输血用血液(包括全血血液与成分血液)被添加了保存液与抗凝固剂,被进行了处理,这些行为应当被看作加工行为,因此,输血用血液应当被解释为产品。”*衆議院商工委員会議事録平成6年6月3日12頁参照。由此可见,政府为血液的产品论与非产品论之争画上了句号。政府支持了血液的产品论主张,1995年7月1日日本的产品责任法实施以后,因输血用血液导致疾病感染的情况,由日本红十字会作为输血用血液的产品提供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药害艾滋事件*药害艾滋事件是指,日本的医药公司经政府批准进口和销售针对血友病治疗所用的非加热型浓缩血液制品,导致共计1434名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的严重社会事件。厚生省药物局生物制剂课长也因该事件被判犯有“业务上过失致死罪”。1996年3月29日,原被告在大阪及东京地区裁判所达成合意,由被告(政府和制药公司)向受害者公开道歉并承担连带责任,向每位受害者赔偿4500万日元(约45万美元),其中政府承担40%,制药公司承担60%。塩野隆史「薬害HIV訴訟と薬害HCV訴訟について」古村節男=野田寛編集『医事法の方法と課題――植木哲先生還暦記念』(信山社、2004年)364頁。该事件中所涉及的浓缩血液制品是由美国血液贩卖所收集的血液为原料而制成,该血液贩卖所里集中的多数卖血者为吸毒人员和同性恋,他们的血液被收集在同一容器内加工成血液制品并贩卖到他国。卖血者中只要有一人是艾滋病感染者,该容器内所有血液均会被感染,由此所制成的血液制品被输入血友病患者体内,使得大量患者感染艾滋病。淡路剛久「HIV訴訟と和解」ジュリスト1093号(1996年)53頁参照。「薬害エイズ(特集)」外国の立法34巻5=6合併号(1996年)1頁。和药害肝炎事件*药害肝炎事件是指,1994年之前,用于大量出血时止血的血液制剂里混入了丙肝病毒,导致很多患者(如分娩或手术时大出血患者)感染丙肝的严重事件。受害者以制药企业和国家为被告,在大阪、福冈、东京、名古屋、仙台五个城市的裁判所提起诉讼。之后,在二审阶段,原被告达成和解,2008年,日本制定《特定丙肝肝炎病毒感染者特别救济法》(「特定C型肝炎ウイルス感染者救済特別措置法」),由政府和制药企业为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薬害肝炎全国弁護団編『薬害肝炎裁判史』(日本評論社、2012年)119-150頁参照。中所涉及的血液制剂由于生产日期均在产品责任法颁布之前,因此并不能适用产品责任法,而只能追究制药公司的过错责任。
二、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医生的注意义务为中心
在患者因输血感染疾病的案件中,判断医生是否具有过失是以医生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作为前提的。观察我国与医疗输血纠纷相关的裁判例,不难看出,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一般根据“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来确定医生注意义务的内容,尤其强调医生在实施具体诊疗行为时是否遵守了医疗惯例和相关行为规范,而鲜有基于“当时的医疗水准”对医生苛以“高度注意义务”的判决。以下将考察日本法上的经验,从对医疗惯例的定位、医生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以及输血·血液制品使用必要性上的争议这三方面对医生过失的判断标准进行阐述。
(一)医疗惯例的定位问题——过失判断是法律判断还是医学判断
在东大梅毒事件(输血感染梅毒事件)*简言之,该案是卖血者持有血清反应阴性证明的检查结果书和血液斡旋所的会员证,医生也按照医疗惯例对其进行了询问,但由于此人的血液中含有尚处在“窗口期”而未能被检测出来的梅毒病毒,最终导致受血者感染梅毒的事件。中,对医生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是应根据其是否遵循了医疗惯例,还是应根据对医生注意义务的法律评价来判断这一问题上,原被告间存在争议。对此,日本最高裁的意见是,“医生是否尽到注意义务,不在于其是否遵循了医疗惯例,而是取决于独立于此(医疗惯例)的法律判断。”*最判昭和36年(1961年)2月16日民集15巻2号244頁。换言之,医生是否遵循了医疗惯例并不是决定医生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唯一要件,而只是作为判断医疗过失轻重及其程度的一个因素而已。即,对医疗过失的判断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必须与医学上所谓的“医疗过失(违反医疗惯例)”在概念上进行区分。医生遵循了医疗惯例也并不必然得出医生已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判断结论。
此外,星野英一教授也对此案中医疗惯例的定位问题进行了如下阐述。即,“医生的注意义务应该基于超越双方当事人的、更为广泛的社会观念或常识来进行判断。某一组织或行业的惯例即使能够作为判断的酌情要素而存在,也不能成为解决争议的基准。”*唄孝一=星野英一「輸血による梅毒感染についての医師の過失責任――職業的給血者に対する医師の問診義務の有無程度」法学協会雑誌81巻5号(1965年)568頁(星野英一執筆部分)。即,判断医疗过失时,不应仅局限于医生的诊疗常识、医疗规范、惯例、或者医学文献记载来进行判断,而应扩展到一般的社会公平正义观念,考虑国民的全般感受。
(二)医生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围绕着医生注意义务的判断问题,在东大梅毒事件的判例当中,最高裁认为,由于被侵害的法律权益是生命和身体这样最为重大的法益,对医生应苛以高度注意义务,即“最善的注意义务”。该判决认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进行管理的医疗行业从业者而言,根据其义务性质,为防止危险而被要求具有‘最善的注意义务’,这点不得不说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该判决也是日本最高裁首次明确提出对医生抽象注意义务的判断基准,在此后的医疗过失判决中该基准被经常引用*奥田昌道「輸血梅毒事件」『医療判例百選(別冊ジュリスト50号)』(有斐閣、1976年)25頁。。
与此同时,在具体医疗过失个案的处理当中,日本司法界在确立医生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时适用的是“医疗水准论”,即以“诊疗当时临床医学实践上的医疗水准”作为基准,确定医生应履行的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和程度*“医疗水准伦”源自与“早产儿网膜症”(「未熟児網膜症」)相关的最高裁判例“日赤高山病院事件”。在该判决中,最高裁明确指出,“一般而言,医师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应当是诊疗当时基于临床医学实践所确定的医疗水准”。 由于日本最高裁判例对下级裁判所具有约束和指导作用,在往后的医疗纠纷案件中,该判例所确定的“医疗水准论”被固定下来,并被下级裁判所沿用。最判昭和57年3月30日判タ468頁。。日本最高裁还认为,“临床医学实践上的医疗水准不应该是全国统一的,而是要考虑诊疗时医生的专业领域、所属诊疗机关的性质、所在地区的医疗环境等诸多因素来进行判断”,即,承认了医疗水准的相对性*未熟児網膜症姫路日赤病院事件(最判平成7年6月9日民集49巻6号1499頁)。腰椎麻酔ショック事件(最判平成8年1月23日民集50巻1号1頁)。。
综上所述,在日本法上,医生是否尽到了作为专家所应尽到的“高度注意义务”是判断医生是否存在医疗过失的前提。裁判所在判断医生是否尽到了诊疗上“最善的注意义务”时,由于这一概念相对抽象,因此,在确定其具体内容时,需要结合“医疗水准论”,观察医生是否达到了诊疗当时临床医学实践上的医疗水准,而且还要考虑当时的整体医疗环境。简言之,“最善的注意义务”是以当时的医疗水准作为基准来确立的,且医疗水准是相对的。
(三)关于围绕输血、血液制品使用必要性的争议
一般而言,加大输血、血液制品的使用频率会导致细菌感染(如:HBV、HCV、HIV)危险性的增加。因此,对输血及血液制品的使用应控制在真正必要的场合。输血感染丙肝的个案中,在认定医生过失时,判断是否存在输血的必要性往往成为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飯塚和之「輸血による血清肝炎罹患事件」『医療過誤判例百選(第2版)(別冊ジュリスト140号)』(有斐閣、1996年)105頁。。然而,裁判所多认为对包括判断输血是否具有必要性在内,医生采取怎样的治疗手段均属于医生的自由裁量权,倘若医生能够证明为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在当时的医疗水准下已尽到“最善的努力”,那么一般不予追究医生的责任*植木哲「輸血による血清肝炎罹患事件」『医療過誤判例百選(別冊ジュリスト102号)』(有斐閣、1989年)167頁。。
例如,在多起输血感染丙肝的裁判例中,裁判所认为,在当时(1980年代)的医疗条件下,尚未存在检测血液丙肝病毒的方法,亦不存在预防输血后肝炎感染的治疗方法,因此,医生在客观上对患者输血后感染丙肝病毒并不具有预见可能性,更不存在基于预见可能性而产生的结果回避可能性,由此否定了医生违反关于损害结果回避的注意义务,判定医生不存在医疗过失*京都地判昭和62年2月20日判時1248号97頁。大阪地判昭和58年2月25日判タ502号170頁。東京地判平成3年11月25日判時1417号83頁。。至于“最善的努力”的具体内容、以何为基准来确立“当时的医疗水准”,还需要结合具体个案进行判断,并无整齐划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三、医疗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证明与认定
在因输血或血液制品感染疾病的案例中,我国法院常常以“输血或血液制品的使用与被告感染之间不存在直接或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并不能证明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是导致病毒感染(HBV、HCV、HIV)的唯一原因”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下从日本法的理论和实践出发,探讨日本医疗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以及在重复感染的情况下如何对因果关系进行认定。
(一)因果关系证明原理的不同
与我国不同,日本司法实务界在判断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事实因果关系时,采用的是最高裁在“ルンバール事件”中所确立的判例理论,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简言之,最高裁认为,“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并非是不允许有任何疑义的自然科学式的证明,而是依照经验法则,综合全部证据,特定事实很可能招来特定结果发生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最判昭和50年10月24日民集29巻9号1417頁。。
药害丙肝事件中,东京地裁也引用了以上最高裁的判例法理,认为,“因果关系的证明是基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对它的判定要达到普通人不存疑的真实程度,但同时表明只要达到了这种程度就足够了”*新美育文「薬害C型肝炎訴訟東京地裁判決の意義と残された課題」判例時報1975号(2007年)48頁。。
(二)重复感染的因果关系认定及事实上的推定
1.日本药害丙肝诉讼中大阪地裁认为,即使存在输血和血液制品以外的原因造成原告重复感染丙肝病毒的可能性,但只要原告能证明血液制品的使用与乙肝病毒感染之间存在“高度的盖然性”,就应当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并且,即使在原告重复感染HCV的情况下,被告只是抽象地指出原告存在多种原因的感染可能性,而未能提供原告由于其他途径而感染丙肝的具体证明,那么,可以认为被告的主张只停留在对抽象可能性的概括指出之上,而不能认定被告的反证成立*手嶋豊「製薬会社の責任(平成18.6.21大阪地判)(特集C型肝炎関西訴訟第1陣第1審判決――C型肝炎訴訟大阪地裁判決をめぐって)」判例時報1942号(2006年)8頁。また、渡邊知行「因果関係論·損害論(平成18.6.21大阪地判)(特集C型肝炎関西訴訟第1陣第1審判決――C型肝炎訴訟大阪地裁判決をめぐって)」判例時報1942号(2006年)16頁参照。。换言之,被告在主张原告(非因输血或血液制品而是)由于其他途径而感染丙肝病毒时,不能仅提出一种抽象可能性,而是需要提出具体事实证据来证明其主张,否则裁判所不能否认原告使用血液制品与丙肝病毒感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总而言之,无论是血液制品导致的肝炎感染,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重复感染,由于这两种因果关系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不论是否存在重复感染的情况,只要能认定血液制品与肝炎感染之间的高度盖然性,就不能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手嶋豊「製薬会社の責任(平成18.6.21大阪地判)(特集C型肝炎関西訴訟第1陣第1審判決――C型肝炎訴訟大阪地裁判決をめぐって)」判例時報1942号(2006年)12頁。。
2.药害丙肝诉讼的东京地裁也同样认为,在存在重复感染原因的案例中,“如果原告能够证明使用了血液制品,其后感染了丙肝,那么可以推定血液制品与肝炎感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一种对因果关系事实上的推定*在日本民事诉讼法理论中,对推定的规定(包括对过失的推定和对因果关系的推定)可分为法律上的推定与事实上的推定两种。法律上的推定是指在原告证明一定的事实后,裁判官根据法律规定而实施的推定,而事实上的推定是指在原告举证一定间接事实存在的基础之上,法官根据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对主要事实进行的推定。参见,平井宜雄=新堂幸司=金子宏編『法律学小辞典(第四版補訂版)』(有斐閣、2008年)499页、1139页。。由此可见,裁判所根据经验法则,通过对因果关系的推定来达到减轻原告方因果关系证明度的效果*潮見佳男「C型肝炎訴訟東京地裁判決をめぐって因果関係と損害賠償」判例時報1975号(2007年)39頁。。如果要推翻这种因果关系的推定,被告“单单证明可能抽象存在其他原因导致的感染是不够的”,而必须证明“从感染时期来看,原告使用血液制剂与HCV感染之间存在不自然”这样的“特别事由”。换言之,在因果关系被推定的场合,加害方在不能证明“存在排除适用经验法则的特别事由”的情况下,裁判所认定了因果关系的存在*潮見佳男『不法行為法Ⅰ(第二版)』(信山社、2011年)375頁。。
3.疫苗接种乙肝集团感染诉讼中,最高裁认为,“本案中被告不能证明原告由于预防接种之外的原因而导致乙肝感染的具体事实,且,其他原因导致感染的可能性只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存在,而预防接种注射器的重复使用和原告乙肝病毒感染之间存在‘高度的盖然性’,根据经验法则,应当认定预防接种和原告感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判平成18年6月16日判時1941号28頁。由此可见,最高裁认为,在被告方仅抽象指出存在其他感染原因而不能具体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应当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四、血液制品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分配问题
日本法上,血液制品(“血浆分化制剂”)属于医药制品的一种,与血液制品相关的医疗事故,主要是医疗机关、制药公司与国家三者之间的责任追究问题。对此,浦川道太郎教授对医药制品(包括血液制品)的有效性与副作用进行了比较考察,并对责任主体的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参见图1)*浦川道太郎「医薬品·注射と医師の注意義務〈報告〉(シンポジウム2医療上の注意義務のあり方――判例の変遷を踏まえて)」年報医事法学16(2001年)110頁。。他首先将医药制品的副作用分为如下两类,①即使医药品的使用方法正确,也无法避免的副作用,②如果医药品的使用方法正确,则可能回避的副作用。然后,根据医药品的有效性与副作用的关系,区分责任主体的不同。其理论构造,具体如下:
1.在即使医药品的使用方法正确,副作用也无法得到避免的场合,(1)当该医药品的有效性超过副作用(即,存在“可以容忍的副作用”)时,该医药品不属于缺陷产品,因此,不能要求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即,原则上,由该副作用引起的健康损害,不应由民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来解决,而应通过1980年确定的医药品副作用被害行政救济制度*1979年,日本制定《医药品副作用被害救济基金法》,对正常使用医药品引发的副作用健康被害提供救济。内田貴『民法Ⅱ債権各論(第三版)』(東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22-523頁参照。2004年,日本成立医药品医疗机器综合机构,专门负责医药品副作用被害的行政救济业务。来解决。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存在医生对医药品副作用说明不充分的情况,那么由该医药品引发的健康损害问题,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患者可以医方“违反说明义务”为由,要求医方承担过失损害赔偿责任。(2)当医药品副作用的危险大于有效性(即,存在“无法容忍的副作用”)时,该医药品应当被认定为缺陷产品,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应当追究生产者的产品责任,即无过错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法上的产品责任只针对产品生产者而言,而不包括产品的销售者。即,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责任主体是生产者,而非销售者。销售者只基于买卖合同承担契约责任,而不承担产品侵权责任。。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对该缺陷医药产品的许可生产以及未对该缺陷产品进行及时回收也可能引发国家赔偿责任的问题。当然,对存在缺陷的医药产品如果医生在使用上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也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2.如果适当使用医药品本应可以避免副作用的产生,但由于医生的不注意,未能对该医药品进行正确使用从而导致副作用产生的情况下,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追究医生的过失责任。对此,医生是否遵守了医药品说明书上的规定,是否对避免副作用被害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都应该被考虑在内。

图1 医药品副作用事故的责任主体与责任分配
事实上,如果对日本因输血或血液制品导致的感染事故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可以分为如下两种情况*手嶋豊「血液製剤(製造物責任法の論点)」金融·商事判例増刊960号(1995年)24頁。。一类是由于血液制剂本身的副作用(我国法上所称的“医药品不良反应”)所导致的疾病感染,例如,输血后紫斑症、输血后单球增加症、甚至还包括心脏手术后由于大量输血而引发的(发生频率虽低而致死率却极高的)移植物抗宿主症(GVHD)等*与GVHD相关的裁判例,请参见横浜地判平成12年11月17日判時1749号70頁。在该案中,患者因输血后GVHD导致死亡,患者遗属要求提供血液的日本红十字会承担产品责任,同时要求医疗机关承担过错责任。最终,裁判所未判定日本红十字会承担责任,而是判定医疗机关因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而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一类是由于血液中存在致病菌,例如,基于漏检或者尚处在窗口期而未被检测出来的HBV、HCV、HIV等病毒,而使得患者感染梅毒、肝炎甚至艾滋病的情况。
对于第一类情况,如果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或未尽到应有的说明告知义务,则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反言之,如果医生已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和说明义务,则应当由患者自身承担责任。倘若血液提供者或血液制品的生产者未尽到对产品的警示说明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类情况的处理与第一类情况存在类似之处,如果血液或血液制品的提供者由于过失存在漏检而导致患者感染,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而如果是由于病毒本身处于窗口期而导致的感染,倘若医疗机关已经尽到“输血可能感染疾病的危险告知”这一说明义务,则应当由患者自身承担输血感染的风险。并且,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免责条款,血液制品的生产者存在“开发风险的抗辩”也不需要对此承担责任*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生产者不承担赔偿责任。。
五、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启示——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
(一)输血用血液的法律性质
日本早在1994年《制造物责任法》制定之时,政府方面就已经对输血用血液是否属于产品做出了肯定解释。而我国在2010年《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司法实践当中仍然采取的是“输血用血液不属于产品”*张国香. 输血感染案件的法律适用——民法学家梁慧星答记者问[N].人民法院报. 1998-9-29(3)。另见,张国香. 为什么说血液不是“产品”——民法学家梁慧星再答记者问[N].人民法院报. 2000-3-23日(3)。这一主流观点的意见。《侵权责任法》公布之后,理论上对输血用血液属于产品应当不存在争议,然而仍然有学者认为血液不属于产品,血液提供者不应承担产品责任(即无过错责任),而应承担过错责任*例如,梁慧星. 论《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 法商研究[J]. 2010, (6): 39. 另外,对于医疗机关是否应当被视作医药品(包括血液制品)的销售者而承担产品责任这一点上,学界仍存在很大争议。反对医疗机关承担产品责任的意见,例如,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改革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成功与不足[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 (4): 13-14. 廖焕国. 医疗机构连带承担药品缺陷责任之质疑[J]. 法学评论, 2011, (4): 55-60. 支持医疗机关承担产品责任的意见,例如,奚晓明.《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414.。
从《侵权责任法》第59条*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明确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的条文可以看出,立法者将“不合格血液”与“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相列举,而“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均属于医药产品的范畴,由此不难推测出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应当是将“不合格血液”比照“缺陷医药产品”来进行处理。退一步而言,即使“血液”在性质上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医疗产品”仍有争议,法官也应当根据第59条的文义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将血液“视为”医药产品,参照适用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
(二)过失的内容和认定以及对过失在事实上的推定
中国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所谓过失,是指行为人因违反行为义务所表现出的、具有可非难性的主观心理状态*关于我国对过失的学说整理,参见高圣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争点、立法例及经典案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3-87.。与此相对,根据日本民法学界对过失的一般定义,“过失”是一个客观的概念,即,“对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却未采取防止结果发生的必要措施(结果回避义务违反)”。*潮見佳男『基本講義·債権各論Ⅱ不法行為法(第二版)』(新世社、2013年)27頁参照。可见,中日两国在过失概念的着眼点上存在差异,我国侧重于强调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日本已将过失概念客观化,着重强调行为人在客观上的“行为义务违反”。
日本涉及医疗过失的许多裁判例都强调医生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且医生的医疗行为即使符合医疗惯例也并不必然得出医生不存在过失这一结论。例如,在东大梅毒事件中,最高裁对医生苛以了“最善的注意义务”。同样,日本在产品责任法颁布之前所发生的药害和食品公害案件中,裁判所通过对生产者苛以高度的注意义务,通过对其过失进行事实上的推定来达到救济被害者的目的。
我国2002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但是,医疗机构未违反法律、法规或医疗惯例,并不能必然得出医疗机构不存在过失的法律结论。归根结底,法官对医生是否具有过失所作出的判断是一种综合性的法律判断,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认为医生的行为只要符合医疗惯例就不存在过失的医疗判断。换言之,医疗过失的内容并不能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所完全涵盖。
因此,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7条*第57条的规定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出台了关于医生“医疗水准”的规定。这条规定更具有原则性,是一条较为柔软的规定,法官可以发挥自由裁量权确定诊疗“当时的医疗水平”,判断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失。“医疗水准论”源于日本的司法最高裁判例,是以“诊疗当时临床医学实践上的医疗水准”为基准来确定医生注意义务的内容。“医疗水准论”的法理基础在于医务人员作为拥有高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理应负有高于常人的“高度注意义务”(有时甚至是“最善的注意义务”),若违反该义务则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8条*第58条明确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是典型的对医疗过失在法律上进行的推定(“过失的法律推定”),即,由法律直接规定存在哪种间接事实时能推定被告具有过失。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对过失在事实上进行推定。一般而言,对过失进行事实上的推定是指,即使不存在能够证明加害者过失具体内容的直接证据,倘若能够确认与加害行为相关的间接事实的存在,裁判官也可以通过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来推定加害者的过失*中野貞一郎=松浦馨=鈴木正裕『民事訴訟法講義:基本的理論と判決手続(第三版)』(有斐閣、1995年)333頁。。例如,日本在スモン事件中,当某种程度的事实状况得到证明之后,裁判所会对缺陷医药品的生产者进行过失推定,制药公司在没有反证来推翻这一过失推定的情况下,需要承担赔偿责任*スモン事件の福岡地判昭和53年11月14日判時910号33頁。同样的思维方式还体现在カネミ油症事件的判決当中,参见福岡地判昭和52年10月5日判時866号21頁。。
根据我国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3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该项前半段是对“法律推定”的规定,后半段则是对“事实推定”的规定。这项规定很容易被忽视,也不如同规定第4条“举证责任倒置”条款那般有名,但实际上它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规定,也是法官能够发挥自由裁量权,或者“能动司法”的依据。
众所周知,“推定”因其性质和依据的不同可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两种。而同样,在侵权法理论上,过错推定也可分为“过错的法律推定”与“过错的事实推定”两种。法官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8条对医疗过错进行法律上的推定,也可以发挥自由裁量权根据经验法则对过错进行事实上的推定。当然,无论是过错的“法律推定”还是“事实推定”,由于都是“推定”过失而非“拟制”过失,因此都应当允许被告提供反证,如果被告提出的反证足以推翻这种“推定”,那么可以免除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在中国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在认定医疗过失时,可以采取日本法上的经验,对医生设定高度且客观的注意义务,结合“医疗水准论”,通过严格解释来提高医生注意义务的标准。此外,除了对医疗过失进行法律上的推定之外,法官还可以通过适用经验法则,对医生过失进行事实上的推定来达到保护被害者、实现司法公平与正义的目的。
(三)因果关系——特别是证明责任的减轻和证明度的问题
在日本,为缓解医疗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减轻患者的证明责任,裁判所对原告方因果关系证明采取“高度的盖然性”这一证明度标准,并且围绕间接事实适用经验法则,对因果关系进行着事实上的推定。值得关注的是,近年以来,日本裁判官通过对经验法则积极而具有弹性的多样化运用,为原告的举证困难提供救济*吉田邦彦『不法行為等講義録』(信山社、2008年)43頁。。具体而言,基于一般人的经验法则所做出的合理判断,或者基于日常生活中事物间联系所做出的合理判断都是认定事实因果关系存在的主要手法。
与此相对,我国医疗过失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为解决医疗过失诉讼中患者“举证难”的问题,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中第4条第8项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这一规定出台之后,由于各地医院采取“防御医疗”、“过度检查”等手段来规避风险,近年来学术界对该条规定提出了不少质疑和尖锐批评*例如,胡学军. 解读无人领会的语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评析[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1, (3): 100.。
同时,《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当中也未对举证责任倒置有任何规定。可见,今后医疗过失诉讼举证责任的发展方向是缓和或减轻而非免除患者的证明责任。即,患者应当承担医疗行为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但是这种证明责任并不是要患者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直接且必然的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说”源自旧苏联,随着我国侵权行为法研究的深入,这种学说已逐渐被“相当因果关系说”所取代,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而只要证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的盖然性”即可。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日本最高裁在判例中对因果关系证明度的说明,即,“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并非是不允许有任何疑义的自然科学式的证明,而是依照经验法则,综合全部证据,特定事实很可能招来特定结果发生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
换言之,即使患者不能证明医疗行为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只要能够证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的盖然性”联系,即存在客观而合理的关联性,就应当视为患者方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裁判官基于间接事实,根据经验法则应当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被告倘若要推翻这种已被推定的事实因果关系,应当提出存在足以能够排除经验法则适用的特殊情况或特殊事由(日本法上所说的“特段の事情”)来进行反证,否则不能被免除赔偿责任。由于医疗诉讼这类现代型诉讼在构造上存在医方更容易掌握证据的特点,为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法官灵活运用经验法则对因果关系在事实上进行推定也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
此外,进一步观察因输血及血液制品感染艾滋或肝炎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法院常常以输血或血液制品并不是导致原告病毒感染的唯一原因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然而对因果关系进行学理分析,无论是由输血或血液制品引起的感染,还是在此之后又由于其他原因而导致的重复感染,这两种情况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原告只要能证明输血或血液制品的使用与自身感染之间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我国语境下的“相当程度的因果关系”),不论是否存在重复感染的情况,法院都不能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若要推翻这种因果关系,被告需要提出反证来证明其主张,若其主张原告是由于其他途径而导致的艾滋或肝炎感染,被告不能仅仅提出一种抽象的重复感染可能性,而需要提出更为具体的事实证据来证明其主张,否则法院应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四)各责任主体的责任分配问题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明确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该条款被视为是对医疗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从该条文的内容也不难看出立法者的意图是为了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防止产品生产者和医疗机构互相推诿责任。同时,若将该条文与同法第43条相比较,不难发现,对第59条最忠于立法者原意的解释应当是将医疗机构视作医药产品的销售者,与产品生产者或血液提供机构一起承担产品责任。
近年来,我国实施医疗体制改革,国务院在2009年颁布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法案(2009—2011年)》,提出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并对“医药分家”作出了些原则性规定,包括“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物加成,不得接受药物折扣”、“积极探索医药分开的多种有效途径”等等。这些规定的出台旨在逐步取缔存在已久的“以药养医”这一特殊现象,最终实现“医药分业管理”。
按照这一趋势,医疗机构并不必然等同于医药品的销售者,因此,在认定医院是否为缺陷医药产品(包括血液制品)的销售者时,法官还需要结合具体个案,根据事实情况(如:医院是否对医药产品进行加成销售以及加成程度)进行分析。医院倘若被认定为销售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3条的法解释论*由于《侵权责任法》第7章“医疗损害责任”并未对医药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责任承担方式进行具体规定,法官可参照该法第43条的规定,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判定缺陷医药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对患者负有不真正连带债务,应承担无过错连带责任(对外责任),而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销售者则是承担过错责任(对内责任)。,则需要和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包括血液提供机构)一起对患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即“纵无过失仍要担责”);倘若医疗机构不能被认定为销售者,则不需要承担产品责任(无过错责任),而只需要承担一般的过错责任(即“若无过失则不担责”)。在后者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根据自身过错承担责任,这种过错不仅包括对医药品的不当使用或强制使用,还包括违反说明义务,未就风险对患者进行合理说明。在现阶段,由于“医药分业”尚未被彻底实施,出于政策性考虑,倘若医药机构确实存在加成销售的情况,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9条,笔者更倾向于将医疗机构视为缺陷医药产品的销售者,与制药公司一起对患者承担产品责任。缺陷医药产品给患者造成人身伤害的,患者有权向医疗机构或者制药公司请求损害赔偿。医疗机构在对患者进行赔偿之后,倘若其并无过错,医药品对患者造成的伤害也确由产品缺陷所致,其有权向制药公司行使求偿权。当然,倘若医疗机构由于自身过错造成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或者不能指明产品的生产者或供货者的情况下,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2条,只能自己单独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非缺陷医药产品”由于自身性质给患者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严重伤害的,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医药品副作用被害行政救济”体系,只能依靠患者自身通过保险制度来分散这种风险,或者由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判令制药公司、医药产品销售机构或者医院共同给予患者一定程度的“补偿”(区别于“赔偿”)。
最后,关于国家责任及对被害者进行行政救济的问题,由于日本存在医药品副作用被害行政救济制度,基于医药品性质,即使正确使用也会产生副作用的医药品给患者带来重大健康损害时,国家对受害者进行行政救济和补偿。作为司法救济手段的损害赔偿制度与作为行政救济手段的补偿制度相得益彰,为医药品致害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此外,无论是药害肝炎事件,还是药害艾滋事件,国家都承担了一定程度的赔偿责任,甚至为彻底解决血液制品致害的问题还出台了特别法律(如,《特定丙肝肝炎病毒感染者特别救济法》),这对我国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Tortious Liability Regarding Infectious Disease Due to Transfusion of Blood and Blood Product—Focusing on Japanese Cases
LI Wen-jing
(SchoolofLaw,HokkaidoUniversity,Sapporo, 060-0809,Japan)
In medical community, the blood is called “the source of lif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ransfusion of blood and blood product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atients who have been infected by virus such as HBV, HCV or HIV. Japan also had the same problem like us but succeeded in dealing with it.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roduce and analyze the Japanese court’s relevant judgments in recent years, sort out the main issues of this legal theory from discussing the feature of the blood, medical negligence, causation, assignment of responsibility while attempt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offer legal remedies to the victims.
blood; blood product; negligence; causation; presumption of fact
2014-05-19
本文系作者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公派留学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一。
李雯静,女,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民法学博士研究生(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主要研究方向:医事法学。
DF522
:A
:1672-769X(2014)04-009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