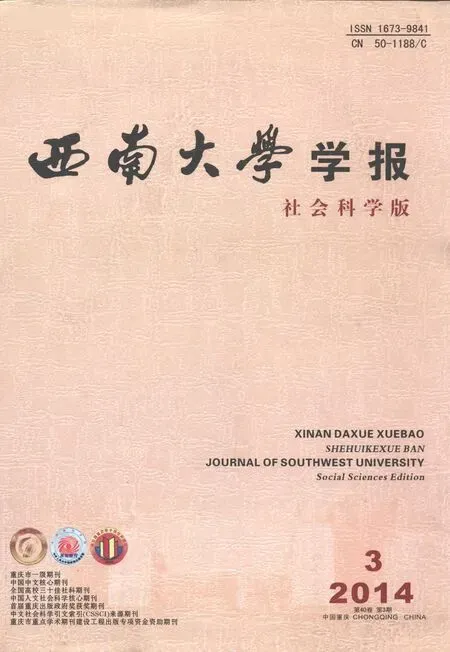中国自然法基准下的“现代目的价值等级体系”
——用符号学重释《老子》第38章
2014-07-18费小兵,陈进
费 小 兵,陈 进
(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法学院,上海市 201620;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2.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国自然法基准下的“现代目的价值等级体系”
——用符号学重释《老子》第38章
费 小 兵1,陈 进2
(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法学院,上海市 201620;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2.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老子》第38章中的“道、德、仁、义、礼”可演绎为法的“目的价值等级”,与之相对应的“意素核”也可作同样的等级排序。排除不同意素,相对应的现代的目的价值的“意素核”也可形成现代法之“目的价值等级”:自然法←自由←博爱←正义←功利(自由特指老子式的自由)。在无根的现代性中,此现代的“目的价值等级”可作为法治的整体目的,为现实中无法解决的法律价值冲突提供参考。
自然法;目的价值等级;符号学;意素;现代法;功利;正义;自由
如果我们要走向“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走向“主体性中国”,而不以“西方范式”作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及其法律文化[1],其结论必然是:中国需要人文复兴,从自我的传统中寻找“中国法观念的基准”。而在《老子》中能够“发现”此基准,而此古代“价值等级体系”的每一个价值的“意素核”也可作同样的等级排序。那么,与这些“意素核”相对应的现代词汇亦可开启出现代法的“目的价值等级”吗?本文将围绕此问题展开探索。
在正式论证前,笔者不得不坦承探索此问题的动因:现代学者惯常认为,近现代西方语境的自然法是良法的“标准”和法治之根!但笔者认为,只有走出二元分裂导致的现代性危机,让“终极至善”成为可能,价值判断才有基准,人才不会迷失在现代性之中!因此,“逻辑”理性思辨之后还应有“直观”方法(反思理性“设计”),才可发现真正的自然法![2]下面将以此缘起而转入正题。
一、以符号学为方法:古今“价值”的“意素”对比
(一)以古代法“目的价值等级”为等级模型
“指引”意味着行走有路径和目的,这就必然形成目的的高低,因此,就必然存在“目的价值等级”。[3]《老子》第38章(“上德不德”章)主要是针对这几句似乎有叛教意味之语:“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4]150-152这可推衍出如下的古代法“目的价值等级”:
道(上德)←德←仁←义←礼(下德)←⊥……………………(各种法)
作这样的“目的价值等级”有何意义?除了为现实中的法律价值冲突提供参考外,还有一个缘由是反思牟宗三先生的判断。他认为“无限智心”(未被人格化)和“智的直觉”是儒、释、道三家皆有的观念,只是三家路径不同而已。[5]在这一认识上,笔者深表钦赞。但是,他认为“仁是宇宙的本体”,佛、老是“纵贯横讲之非创生系统”,笔者却不敢苟同。笔者作此“目的价值等级”,亦是要证明,“仁”之上有“德”,“德”之上有“道”,“道”才是本体,“仁”仅仅是“道”这本体的“大用”、“正用”、“常用”,但却不是“道”本身;就算在牟宗三本人的语词系统中,其“无限智心”也不等同于“仁”,“无限智心”的用是“仁”,两者谁是本体?
本文将证明,“目的价值等级”中的每一目的价值都是整体目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道家(限于篇幅,对佛家另文详述)不是“非创生系统”,而是当创生系统出问题时,能够“超越创生系统”,回归自然、根本、本性。笔者回顾牟宗三,是为了防止现实(法律实践)中出现价值混乱时,能够参考古人足够的智慧,发现法治的整体目的,去辨析这些价值。
故理解老子的关键是:“上德不德”并不是说老子反对德,而是要回归“无为”之德、“整体”之德,而非表象、片面、虚伪之德。这就是建立“法的目的价值等级”的意义:即目的与手段冲突时,取目的而舍手段,即择道之本真,弃道之表象。
那么,如此古老的《老子》推演出的古代的法的“目的价值等级”怎样才能被发掘出对现代法的参考、借鉴和启迪意义呢?
(二)古今相近词汇的“意素”对比
本文以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符号学作为古今语言转换的基础方法,即:意义效果(Sm)=意素核(Ns)+语境意素(Cs)。[6]从《老子》第38章的“基本精神”(意素核)出发,然后从《老子》语境意素与现代语境意素的比较中区分出异同,抽取出与现代语境“相同的意素核”(以下简称为意素),从而得出五个价值(意素核)的现代阐释(意义效果)。
因此,第一步,就应对《老子》第38章中的“目的价值”关键词(道、德、仁、义、礼)与现代对应词汇的异、同“意素”进行分析比较(由于中国的现代语境深受西方影响,所以本文描述现代语境词汇的意素时多参照西方理论而阐发,其中的难点是“德”与“自由”):
1.“礼”与“功利”
《老子》第38章中批判:“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4]151这个“礼”本身仅注重礼法(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习惯的“外在形式或表象”——它含有重视“结果”和“为了社会的正常交往秩序而存在”的“功利”意素。
而现代的“功利”派学者也主张外在“他律”的现代伦理和法律是“为了社会的正常交往秩序而存在的社会规范”,其内含一种“为了社会的正常交往而存在”的“功利”目的。功利的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果有助于增进幸福,则是正确的;如果导致与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7];要重视行为的结果——一个行为本身并没有内在的善或正当[8]151。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存在的纽带,其最低的道德要求和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正常交往秩序而存在”的“功利”价值。
而“礼”作为传统伦理规范,有与“宗法等级”相关的意素,其与“功利主义”中的“现代民主、权利基础”的意素不同。但是,“礼”与现代“功利”却有此共同意素核——即“以追求某种结果为目的”及其是“为了社会的正常交往秩序而存在的手段”。
2.“义”与“正义”
传统文化(包括《老子》)中的“义”,有合宜、公平、正直、应当之意,有明确的是非判断,这是非判断亦不“因功利需要而改变”。且《老子》曰“失义而后礼”,其“义”也比“礼”的价值地位高。
而现代的正义价值,亦有一种内在的价值即尊严,它不会由于害怕惩罚而产生“市场”或“功利”的思维——尊严反对“价格”的计算和技术性的思维,而要求渊源于义务论的绝对义务。[8]151这种内在价值“不因外在的功利需要而改变”,例如康德的实践理性理论中对理性存在者的道德“绝对命令”。”[8]147
虽然现代的“正义”与老子的“义”比较起来,言说路径不同,且多了个“一旦违背就有对等惩罚”的意素,但在高于“为了社会的正常交往而存在的手段”即“不因功利需要而改变”和“有明确、恰当的是非判断”的意素核上,现代“正义”价值与《老子》中的“义”有共同性。
3.“仁”与“博爱”
老子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4]151,“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174,又曰:“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4]271,其“生”,其“仁”,其“慈”,追求对“每个人的平等的仁慈之爱”。
与之相区别却又相关联的是现代的博爱价值。与博爱价值关联最紧密的是现代的“人权”:“人享有的人身自由和各种民主权利。”[9]1208现代人权以每个人平等“享有的尊严、自由和各种权利”为价值追求,建立在人人皆是主体、尤其是立法的主体这一民主前提上,也追求“对每个人的人权的平等关爱”,但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比,自有不同的语境。
二者的区别是:“民主”立法中的人权体现了人人对“自我”的关爱,“圣人”立法中的人权体现了圣人对“他者”的关爱。“民本”思想虽以民为本,但人民不是立法的主体。这体现在老子的思想中,似乎依然追求“圣人”立法和“天道契约”(与道立约),圣人才是立法者,其对民众的“仁慈”依然倾向于“民本”思想,只不过,圣人无为、无私、“外其身”、“容乃公”,尊重民众的自主、自然生活,与“民主”基础上的现代人权思想不抵触,在“关爱人权”这一点上有共同的意素核。并且,在老子看来,每个生命都是“道生万物”之一分子,是道的体现,故是崇高的,则从中抽取出与现代民主也一致的“每个人都是平等崇高的”意素核。这构成现代“博爱”价值和老子的“仁慈”共同的意素核。由于“仁慈”是“正义”的目的价值和上位价值,那么“博爱”也是正义的目的价值和上位价值。
4.“德”与“自由”
中国古代的“自由”一词,由来已久,并与“德”紧密相关。如《三国志·吴·朱桓传》:“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其“自由”的含义是:“不受拘束,不受限制”[9]1937。但“自由”更原初的含义还得从“自”、“由”两字的原始符号开始探索。

更进一层,如果说“本”、“末”这两字是从草木中抽象出来的,则这个“由”字也是从草木中抽象出来的,联系起来顺通如下:“叶”(末)从“根”(本)中“自由”生长出来;这样的生长是“自然”的,是顺随、听任生命逻辑的,而非勉强的;“根”(本)是“叶”(末)生长出来的生命逻辑之原因:“根”决定着(末)“叶”的“本性”,末叶的自由生长展现着“根”本来的“本性”。此“自由”是生命逻辑运行的实然、必然(展现),也是应然(本性),是应然与实然的统一、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这里需注意《尔雅·释诂》“由,自也”,与《玉篇》“自,由也”,竟然是互为解释的字!“自由”这个词应与这互为解释的初义有关,都源于这“‘叶’(末)从‘根’(本)中‘自由’、‘自然’生长出来”和“鼻子本来的呼吸是自动、自然、自由、无勉强的”本义。
所以,“自由”一词在古代中国的本义是:“任其自然、由其根本”——而《老子》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也”[4]10-11,恰表达此“无为”而“任其自由生长”的智慧。可见,《老子》恰继承了远古这真正的“自由”的本义。因而“自由”一词曾代表中国远古的观念之一,亦是《老子》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另一方面,世间有些“放任”的“妄为”却非“由其根本”。例如:任性地将花儿的根掐掉放在花瓶中,或强求未开之花开花,就是让花儿失去其“根本”、“自由”、“自然”;又如让小孩过早地负担繁重学习功课或劳作,是不遵循小孩成长的规律,“拔苗助长”,让小孩失去“任其生命逻辑自然成长”的“自由”。故“自由”的“不受拘束,不受限制”义,仅仅是“任其自然、由其根本”义的引申义,必须以后者为前提。在此意义上,“自由”的“不受拘束,不受限制”也是有限制的,这限制就是不能违背自然法则——这就是“自由”本来的德性(但这限制其实很容易做到,只要不妄为即可)。反之,道的本用是德,德的本性是自由。故老子曰:“上德不德”。
而回顾西方现代的“自由”价值,其肇始于近代的洛克等西方启蒙时期的古典自然法学家,然后被康德等哲理法学家进行逻辑有力的论证,并被现代西方哲人发扬和捍卫。洛克主张,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拥有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尤其是财产权)。[12]但康德论证,人的自由不是任意的自由,而是理性“自律”下的自由意志,自由是以“道德命令”为基础的。[13]不言而喻,康德的论证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所以,以内在“自律”为基础的自由是非常有尊严的自由。[14]而西方另一脉络的自由源于休谟的情感论,其继承者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自由”强调激情和欲望至上于理性,要解放欲望。[15]
国内现代的“自由”含义是:“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9]1937
通过此“自由”之含义,笔者发现其源头——东西方“自由”的不同意素和词源,蕴含着各自不同的“德性”:中国远古的自由(即《老子》的自由)既非康德式的“自律”自由,也非休谟、哈耶克式的“放任”自由,而是“任其自然、由其根本”。
《老子》之“上德”重在“任其自然”,是顺应自然法则,故绝对是“无限制”的限制,“不勉强”的限制,而康德式的“自律”可能是“有限制”、“有勉强”的限制。而“自律”可能会因不合自然而成为强忍的自律;老子“回归自然”的“自由”却是回到其“根本”和“本性”,而非忍受、勉强。可见,中国原初的“自由”含义与康德式的自律的“自由”存在微妙的区别。
因此,“上德不德”,老子的“自由”与注重外在“礼”(伦理)束缚的儒家,或西方“他律”的神权教条,或康德式的“自律”自由比较,毋宁更注重“不勉强求道德”的“上德”境界即实质的道德。[16]老子的“自由”是老子的“上德”。
但老子的自由,绝不仅是“感性”的自由,而是源于“直观”对感性(如休谟式的主情论下的自由)和逻辑理性(康德式的主知论下的自由)的整全把握。这里,法自然就有个层次问题了:在最底层次,圣人只需“无为而治”、“治大国若亨小鲜”[4]244,不去扰民,雷同守夜人即可,这与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学者倒也有相应点,顺应人的自然欲求即可。但《老子》却有更高的精神方向,即虽平常时是守夜人,“我无为,人自化”[4]232,但当人们“化而欲作”时,即欲望大发作、智慧用过度、远离自然法时,就必须要“返”——“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4]147,用“朴”(自然法)矫正异化的欲望,从“下德”返回“上德”——这绝不仅是休谟、哈耶克式的放任激情和欲望的自生自发秩序,而是含有内在“道德”的自由。但这“返朴”之“为”不是“妄为”、“过度为”、“强为”,而是“辅自然为”,否则将会形成人的后天意识对真理的主观偏执使用。而假如人的“放任自由”不“返朴”(返回正常的自然之道),非正常秩序就会自己崩溃,逼使人“返回自然法则”。故老子的“自由”是直观发现的“自然的自由”,而非“理性自律”、“建构”、“设计”、“主观正用”的自由,亦非“放任的自由”。
不过,“自律理性的自由”只受自己的束缚,不受外在“他律”的束缚,哈耶克的“放任自由”,亦“不受外在他律的束缚”。老子的“自由”亦引申有“不受外在他律束缚”的意素。总之,综合东西方“自由”的意素核,现代自由的意素核是:“不受外在他律的束缚”。
5.“道”与“自然法”
法治的最高精神追求,在国际上一般言之为“自然法”,在中国可勉强名之为“中国自然法”乎?
近代在翻译英文“Natural Law”时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字组成的新词“性法”、“形气自然之法”、“自然法”等词,但这些词都不能完全表达西方的“Natural Law”。当然,在“最崇高的超越性法则”上,“Natural Law”与中国哲学的“道”是有同一“意素核”的。不过,为了与西方“Natural Law”的某些不同意素相区别,笔者曾考虑将“道”一词在法理学意义上冠之以“中国的自然法”的代名词。于是“中国自然法”作为“道”的替代词时,它们之间是可以互换的。
由于我在另文详述了“道”[2],这里从简,但一定要再次说明:宇宙真理只有一个!“中国自然法”作为人类的“自然法”的表达方式,不过是后者的代名词之一而已!强作“中国的自然法”和“西方的自然法”的区别仅是为了凸显中国人在追求真理时与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已。这仅是暂时的方便,当“普世共识”达成时,最后应消除“中国自然法”前的定语“中国”才对。
综上,在进行古今词汇的比较并将不同意素区分后,《老子》第38章中的五个“目的价值”(道、德、仁、义、礼)在现代法的目的价值中能够找到对应的“意素核”。
二、《老子》的启发:现代法“目的价值等级”之呈现
为了用老子的原理理解、观察现代,第二步就是把前述从《老子》中推衍出的古代法的“目的价值等级”的“等级模型”保留下来,通过意素核的中转,推演出现代法的目的价值等级,以之为现代价值追求的方向和解决价值冲突提供参考和启发。
(一)“自然法”是最高的目的价值
当我们探讨现代法的价值时,其实已经暗含一种西方的价值与中国的原有价值的融合。并且随着中国政府当局不断签署相关国际人权条约,这一事实已经证明“普世共识”不仅在意见中达成,并且在实践中被逐步推广。因此,行文至此,应该消除“自然法”前的“中国的”的定语才对,直接以“自然法”表达法律的最高目的价值和精神追求(只是,为了凸显中国古典哲学的独特方法,笔者不得不将其表述为“中国自然法”)。那么,从老子视域看来,“道”即“自然法”是“本”,是最高的目的,不以“自然法”为目的的“德”是“伪德”。
(二)“自然法”是“自由”的目的价值
承前所述,“直观的自由”是老子之“德”的核心要义。在“不受外在他律束缚”这一意素上,老子的“上德”与现代西方的“自由”有共同性,但老子言:“常无,以观其妙;常有,以观其徼。”[4]6老子不仅不放弃“无欲”之观,并且也不放弃“有欲”之观,这与后现代哲学那种放弃逻辑精神的方法,以及近现代西欧以逻辑精神为主要方法的区别在于,这是一种完全的“综合的直接之观”(简称直观)。[2]故“直观的自由”可能有“自律”,也可能超越“自律”——是由其自然、任其根本的自由,则“直观的自由”比“自律的自由”更自由。因为在老子看来,经过人的“直观”发现的“本性”本身不是逻辑、理性设计的,而是自然的。由于这“直观”是来自于“本性”的直接观察,能够辩证地发现“外在他律的束缚”的合理与否,故不易受逻辑论证过程中各种表象知识的束缚,是更大的自由,是更合于自然的、无为的、返本的自由。并由于其来自于道,是“合道的自由”——是以“自然法”为目的的“自由”。故本文追求的“自由价值”应是以此“合道的自由”为内涵的。
(三)“自由”是“博爱”的目的价值
老子的“自由”是顺应自我本性发展的自由。众所周知,没有自由的人是一个“异化”的人,失去自我本质的人,从而便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如果这个世界是由没有“真正的自我”的人类构成,那不过是一群被“豢养”舒适的奴隶或牲畜,绝对无法凸显现代的“民主”价值和人格尊严。因此,自由是人之为人的规定性,是人权中最高的权利,换句话说,没有自由的“博爱”不过是虚伪的“博爱”,是虚伪的人权。因此,“自由价值”高于“博爱价值”。在老子看来,有“道德”的“自由”是“博爱”的目的,反之,“博爱”是“自由”的手段。由此,本文采纳的“自由”价值必须以老子继承的中国远古观念中的“合道的自由”为核心要义,才能让“自由”价值高于“博爱”价值。否则,如果采纳康德式的“自由”,其核心意素却是“自律”的绝对命令即“正义”价值,低于“博爱”价值了。
(四)“博爱”是“正义”的目的价值
承前,“博爱价值”与“仁”的价值存在共同的意素。因为道生万物而有好生之德,道就自含某种仁,没有仁的义是机械呆板甚至冷酷的义,不合道的本质,结果是“政复为奇,善复为妖”[4]236,即正义变成了不正义,甚至是更具隐蔽性的不正义,其危害可能胜于一般的不正义,更是逆道的假象。而“博爱”因“爱罪人”而消减了“正义”的机械呆板,对悔改保留宽恕的权利,故可补救“正义”的机械呆板导致的恶果。并且,“博爱”并不等于功利,即便没有功利价值也要维护,它涵盖了功利与正义,又高于二者。因此,站在老子视域看,“博爱”是“正义”的目的。
(五)“正义”是“功利”的目的价值
《老子》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4]152-153承前所述,“礼”与现代“功利”有一个共同意素,即“以追求某种结果为目的”及其“规范是为了社会的正常交往秩序而存在的”。假如以此为最高价值,法律仅为了“功利的结果”,就可以不顾行为内在的善或正当。即是说,如果不以正义为前提,得来的可能是暂时的利益、权衡下的退让和内心的不服与困惑,所以功利观下达成的“对价”及其“良序”可能是暂时的假象。因此必须以“正义价值”为更高价值,才能是非清晰,让人心服口服。并且,这才能体现“为自己负责任”的人之为人的尊严。[13]如果人类以功利为最高目的,就可能让钱、权以暂时的“对价”给予一定资源给弱者,但最终却可能促进弱肉强食、豪强霸占的风气占上风,任由私欲导致的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甚或核战争危机、恐怖主义四处泛滥,以“对价的功利”蒙蔽人们的眼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最终把人类带入毁灭之境。
故只有无功利的正义才会产生最大的功利——那就是人类不会因自相残害、掩耳盗铃而自相毁灭,而是保证人类心灵和智慧的整体方向,以及人类因互助互爱而产生更大幸福。因此,在老子视域看来,“正义价值”是“功利价值”的目的,反之,“功利价值”是“正义价值”的手段。
三、结论:现代法的“目的价值等级”是法治的整体目的
回首现代法治精神的关键:人定法有自然法的批判与指引,在此前提下形成的世俗法律才有标准,才能确称为良法。而“道”是这种“自然法”的一种表达方式。悬置具体内容的区别,在内容可通分的符号学意义上,老子之“道治”与现代“法治”的共同特点是:以“自然法”作为现实法律的批判和指引。这为“道”的现代启发提供了可能。
本文推演出的现代法的“目的价值等级”的价值都是正面的价值,是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其全部价值内容,而仅是与“目的”有关的几个价值,并且是与《老子》第38章推演出的古典法的“目的价值等级”中的价值的意素核相对应的那几个现代价值而已。
从而,将现代法的“目的价值等级”置于老子的视域中发现,这个“目的价值等级”是不能分割的,即下位价值失去上位价值就没有了目的和方向,分割上位价值和下位价值就不能从整体上体现现代法治的精神追求。换言之,现代法治的精神就包括自然法、自由价值、博爱价值、正义价值、功利价值,它们共同构成不能分割的现代法治的目的(以及宪政的追求)。可见,现代法治精神有不可分割的整体目的。人们可以分割分析它们,但却必须混合起来直观、整体理解现代法治精神。
如果各家各派各以其目的价值作为唯一目的(例如牟宗三仅将“仁”作为本体和唯一目的价值),就可能失去法治的整体目的,诸神之争将无法止息,法治也将受此瓶颈制约。当然,在现实中,各家各派、各种价值皆有其意义。笔者只是提醒人们,当价值冲突无法解决时,不妨回到古代哲人(例如老子)那里,寻找解决的智慧。
另一方面,现代的民主、程序等价值作为现代人认可的自相保护的最佳方法、手段、工具,可以抵御专制对法治的腐蚀和阻碍,保障前述法治的基本的“目的价值”。
在此意义上,民主和程序等价值无论如何崇高,却仅是现代性社会不可抛弃的手段价值。而“自然法”却是前述手段的最高目的,也是中国人的法治精神之最高追求。但自然法不可见,自然法体现在自由、博爱、正义、功利这些可见的目的价值中,而自由是可见的目的价值中最珍贵的价值。
总之,通过《老子》推演、启迪出这样的现代法的“目的价值等级”,其目的就是为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决断的价值冲突提供参考,在无根的现代性中寻找并坚守法治的根本。
[1]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
[2] 费小兵.法之“道”与法之“理”的由来[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95-101.
[3] 卓泽渊.法的价值[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
[4]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 牟宗三.圆善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0,198.
[6]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7:299-305.
[7]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8] 韦恩·莫里森.法理学[M].李桂林,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9]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古今汉语词典[R].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0] 汉典网:http://www.zdic.net.
[11] (东汉)许慎原著,吴苏仪编著.图解《说文解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03.
[12]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两篇[M].赵伯英,译;来鲁宁,校.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13]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4] (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44.
[15]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55-78.
[16] 黄圣平.《老子》所谓“德”[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1):135-141.
责任编辑 刘荣军
2012-11-05
费小兵,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B223.1
A
1673-9841(2014)03-0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