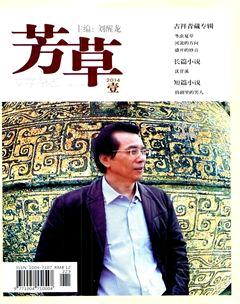心结(短篇小说)
2014-07-16班丹
班丹
伦桑和女儿扎西德吉跟其他七八户人家散居在大山里。他们是农区的牧民。而伦桑家说是牧民,其实只有七十几只绵羊和二十来只山羊,吃的酥油也是用羊奶提炼的。因为家中严重缺劳力,养不起那么多牲畜。老请别人代放,不是个长久之策,便把原有的十几头牦牛都卖掉,用卖牛的钱改造住房、添置一些家具后,把余下的钱都存入了农行乡营业所。
伦桑曾多次对山下的农民朋友说:“如果没病没灾,当个牧民,待在山里很有意思,至少比聚居在山下的农民清静许多。”直到最近这两年,伦桑父女俩都还过着安逸、宁静的日子。然而,这种日子被他的腿病彻底搅乱了。
“爸爸,妈妈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
“你今年多大了?”
“十九岁。”
“啊。她是在十九年前走的。”
这天扎西德吉休牧。
自從伦桑身患奇怪的腿病后,扎西德吉被羊群牢牢拴着,除夜间能睡上几个小时,就得不到休息,更别说到县城或拉萨逛一逛。说来够残忍的。由于家里有一大堆琐碎的事情等着她来处理,她就把羊们关进棚圈里,使它们的活动空间大大缩小。看着用哀怜的眼神望着自己的羊们,盈盈的泪花,一如美丽而凄楚的涟漪在扎西德吉的眼眶里打转。
伦桑把用好几年时间准备的细呢袍子、绸子衬衫、衣裤、松巴鞋,以及祖上留下来的用真真假假的绿松石、珊瑚和瑟瑟串成的项链、金戒指、金耳环等首饰摊在一大块帆布上,向扎西德吉投去充满爱怜的目光和微笑。他几次想问扎西德吉喜不喜欢这些嫁妆。可是话到嘴边,又跟往常一样,带着几分苦楚跟唾液一起咽了回去。
扎西德吉知道那些衣物和首饰是给自己准备的。父亲脸上那一堆难言的微笑分明在暗示自己——你该成家了。一抹羞涩的红晕疾速爬上扎西德吉的脸颊,烫烫的,感觉即刻就要燃烧起来,心口也堵得不能均匀而顺畅地呼吸。但她却极力掩饰,啦啦啦地哼哼着,把一大堆脏衣服装进编织袋里,带上一瓶买来很长时间,却一直没舍得喝的橙汁到沟里,啦啦啦地洗了起来。其实她那一声接一声的啦啦啦完全失去了以往的韵致,显得十分牵强、蹩脚,且令人心酸。
扎西德吉的啦啦啦在叽叽咕咕的流水声中渐渐停歇了。她的意志被刚刚在家里看到的衣装和首饰击垮了。她变得跟很长时间没有吃到盐巴的羊子一样焦躁、烦闷。爸爸很有可能被这古怪的腿病从我眼前掳走。他不能走,他还不到五十岁呀!
伦桑拄根木棍,拖着很难挪动的步子,双脚相互磕碰着,宛然因中风致残的人,颤颤悠悠地朝扎西德吉洗衣服的河沟方向挪步。他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多看女儿几眼。因为平时女儿放牧归来,要料理家务事,干完这个,拾掇那个,忙活到深夜,头一挨枕头就呼呼睡去。早晨不等天大亮,就得出牧,他们父女俩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太少。
伦桑好不容易把身子挪到离扎西德吉不远的一处断坎上。他出了一身汗,湿漉漉、黏糊糊的,仿若刚刚从油桶里爬了出来。他解开衣扣,让想象中的凉风透入肌肤,吹进心里。长大了,女儿长大了,也懂事了。这说不清楚的腿病,有可能把我很快拖进阎王府。我一走,她这本来就可怜的孩子就更加可怜了。到那时,我还能痛快地闭上眼睛吗?睁着眼睛上天葬台,不把秃鹫吓死才怪哪……
扎西德吉使劲搓揉起伦桑那件半年多没沾过水的外套领子和袖口。搓到手发麻,便在清澈而冰凉的水里清了清,细眼瞧瞧,衣服再脏也能洗净,而且一眼就能看清哪儿脏了。可爸爸的病就不一样,哪个大夫瞧了,都瞧不准。要是人的病痛也跟衣服上的污渍一样,一搓一揉一清就能祛除掉该有多好啊!
她把那件外套的水拧干,抖一抖,挂在树枝上,歪着脖子盯一会儿,取下,贴到胸口,闭上眼睛,喃喃祈祷,蹲下身子,把衣服轻轻放进水里,任由它慢慢漂向下游。
衣服顺流而下,漂过十几米,便被横在水里的树枝卡住了。她哼的一声走过去,把衣服拿起来,像甩抛石绳那样甩几下,往水流集中的地方一掼,返回到原处,接着洗其它衣物。可当那件衣服从眼前漂走后,她心里一沉,觉得爸爸的腿病跟这件衣服实在是挂不上钩,扔掉它太可笑。于是她就顺着曲里拐弯的沟河跑去,把衣服捡回来,重新挂在树上,拣起一条洗得发白的裤子,啐几口,把它扔进水里,愿你把我爸爸的病气全带走,让他跟过去一样能够正常行走。
伦桑看得呆头呆脑的。这孩子要干什么?他揣摩起女儿的心思,愕然觉得女儿今天的行为非常诡异。他凝神注视女儿的一举一动,怀疑她有什么心事瞒着自己。她是不是又被哪个臭小子调戏了?不会是我在无意中惹恼她了吧?他险些朝女儿喊,问她在干什么。可转念一想,女儿不会有事的。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令我伤脑筋的事儿。再说,她去洗衣服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地哼哼着,一脸高兴的样子,如一朵盛开的杜鹃花。不过他这心里还是结了个难解的疙瘩。
扎西德吉洗完衣服,垂头丧气地朝回家的方向走去,眼里蓄满了茫然、无奈、忧悒的液体,一闪一闪的,透着几许悲凉。半道上她遇见伦桑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将木棒戳在地上,凝视着远方一座座傲视大地的雪峰。男人应该是不倒的大山。我可不能在女儿面前流露出对病魔的恐惧和对她的怜悯。
爸爸,您跑到这儿来做什么。
哦,随便走走。
天擦黑,扎西德吉就张罗起晚饭。她的脸上满布愁云,阴阴的,犹如雨天山头的云雾。她把带骨头的羊肉块放进锅里,倒上适量的水,把锅坐在炉子上,拿起铜盆,取来面粉,没好气地和了起来。她连看都没看一眼在她看来没啥意思的嫁妆,赌气似的揉捏盆里的面。不一会儿,她就把面团成一坨,拿起来,狠劲儿砸在盆子里,用拳头挤压,捶打,摊开,团起来,狠劲儿砸下去,翻个个儿,拿起来,团一团,在两手掌之间倒来倒去,好像那不是一团可以吃进腹中的面,而是折磨她父亲的病魔。
而伦桑却独自欣赏起女儿的衣装首饰。他不时看看跟手里的面过不去的扎西德吉,心忖,看样子我这病没治了。哪天我突然不行了,孩子的婚事可就没人张罗。我一定要在自己断气之前,风风光光地把闺女的喜事办了。他不怕女儿嫁不出去,也不怕找不着上门女婿。她虽然算不得美若鲜花,但也出落得有模有样。皮肤白净,不像个山里娃。身板结实得像只秋天的獐子,走起路来很有劲儿。而且老实、本分、能干,又懂礼数。自打她长到十六岁起登门提亲的人就没断过。怕就怕她摊上个倒霉的婚事或者白白地让人糟蹋了。他唏嘘着,心想,这两年上山砍柴的、采石的、折腾工程的老是骚扰她,我总是放心不下呀。
就在一年前,修建水电站的一队人马开进伦桑家附近的沟里。这对常年居住在山坳里的牧民来讲,肯定是件大好事。不过自打他们到山里晃悠以来,山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多少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还危及到牧民们保持了千百年的生活秩序。具体来说,电站还没修到一半,不少女孩子的肚子被一些外地民工弄大了,还传出话来,说是那些个种山羊似的民工会为她们和她们肚子里的生命负责,让她们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舒心日子。这使得那些女孩及她们的父母心花怒放,仿佛到了极乐天界一般飘飘然,一时间乐得把手头很多事情都撂到一边,整天价谈论起他们不曾享受的另一种幸福生活。
一想到这事,伦桑就变得惶恐不安,心口堵得快要爆裂。扎西德吉毕竟是个女孩子,天生就是个吃亏的命啊。我这倒霉的腿病拖累得她……唉。
扎西德吉一聲不吭地收拾盆里的面。看她那爬满一脸的阴霾,像是无缘无故地被人揍了一顿。
沉闷的气息随着面疙瘩四处飘散的香气散去了。
爸爸,我明天也不去放牧。
嗯。那你……哦,羊怎么办?
再关它们一天。
扎西德吉准备搀扶父亲到寺庙转经礼佛,以求伦桑的腿病痊愈或者有所缓解。她相信三宝会佑护父亲,使他摆脱病痛的煎熬。
又一个远离云雾的早晨。
扎西德吉聆听着轻风喷射的音乐,跟那群羊子爬向青油油的山头。路在山间穿行,弯弯曲曲、起起伏伏。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都好几天了,那只领头的公羊变得和伦桑的腿病一样怪异,硬是不听使唤。不是跑得太快,跑到离羊群老远的地方,就是把头伸进乱石缝里,撅屁股、摇尾巴地磨蹭着,挺像一头意外发现萝卜坑的毛驴。扎西德吉用抛石绳抽它的后肢,用手拍它的脊背,用膝盖顶它屁股都不顶用,就只好丢下它跑到前面,拦住其余的羊等它。
咩——咩——
咩啥咩,它不走我有什么办法。
伦桑那随着一瘸一拐的脚步扭动的身子,又一次把扎西德吉的脑子填得满满当当。纷乱的心事如同黑云压进她的内心,使她眼前一黑,仿佛世间所有光亮顿然消隐。
爸爸能吃能喝又能说的,一点也不像个身患重病的人。可他那双腿怎么就迈不开步子了呢?是不是真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年轻时杀害太多的狼啊豹子呀獐子啦狐狸啥的野兽,还把血淋淋的野兽皮晒在山神寄身的磐石上落下的病?
一个念头像流星般嗖地从扎西德吉脑子里闪过。她蹦了蹦,为自己作出的决定暗自欢喜。
此时,伦桑的目光直愣愣地扑向一纸脏兮兮的存折。当眼睛移向“余额”一栏时,他的嘴角堆出漂亮而惬意的笑颜。一万九千元。给女儿办事顶多花掉六千元,还剩个一万三千元。这点积蓄是用牦牛换来的,我不能把它随便糟蹋掉,得留给女儿。
他把存折照原样夹进长条经卷里,用夹经板把经卷夹好,绑牢,放回佛龛边,吃力地走出房门,到路口等女儿回家。
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扎西德吉用细长、尖厉的声音喊了几声。所有散乱的羊子立马鱼贯而出,蹦跳着循声朝岩崖下面的扎西德吉聚拢。羊们上当了。它们的主人为招它们提前回家,用一小把盐把它们收拢起来了。
她用力抡了抡抛石绳的尾梢,像个男孩咯嘿嘿地大喊几声,踩着羊们细碎的脚印,啦啦啦地跟快乐的羊群快速往山下走。
一路上,她琢磨起要对父亲说的一件事儿——爸爸,您非要给我找个男人,也行。但必须得是倒插门的女婿。
看着药盒子堆成一座小山,而伦桑的病情每况愈下,第二天,扎西德吉从山下的寺庙请来三位僧人做法事,并按佛教仪轨,把那只不听使唤的领头公羊放生了。
过了三十多天,伦桑的腿病还是不见好。扎西德吉又把一只山羊放生了。她听一位到家里做法事的僧人说,放生一只山羊,等于放生十三只绵羊。考虑到放生山羊的功德远远超过放生绵羊,她就决定不停地放生山羊,就算把家里的山羊全都放生完了,也要用绵羊换,或者买来放生,直到父亲完全康复。
当放生第五只山羊达时,父亲的病似乎有所好转。她喜出望外,以为发生了奇迹,并确信父亲得的这身怪异的腿病就是经占卜证实的毒龙病(妖龙造作的病害)。于是,她让父亲每天喝念了经咒的水,用这种水擦洗腿脚的同时,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法事,放生一只山羊。
那天是藏历七月十七日。对于伦桑来说,是个吉日良辰。这天,晨风要把他送到山下的村庄给女儿提亲。
下了一整夜的大雨把从山头七拐八弯地延展至山脚下的道路冲得俨然老人脸上的皱纹。伦桑一步一瘸、连走带滑地朝下山的路走去。他才走到离家三百米左右的地方,就已经摔倒了十余次。当他摔到第十九次时,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笑了笑,依我的年龄,还不到走不动路的地步,怎么一摔就爬不起来了呢?想当年……哧哧哧……
伦桑起不来了。他可是真的起不来了。他又笑了笑,起不来就起不来吧,人总要走到起不来的那一天。
起不来的伦桑干脆把身子拖到一块磨盘样的石头上,伸开双腿,端端正正地坐着,琢磨起在他看来比他的腿病重要几千倍、几万倍的事情。想到奇怪的腿病,女儿的未来和未来女儿的生活,令伦桑心里着了火似的焦急。女儿跟我生活了整整十九年。这是多好的缘分呀。可现在……
今天我的右眼皮跳个不停,这绝对是个不好兆头。要不是怕你们吃不饱,我早早赶你们回家了。扎西德吉一路疯赶羊群下山,推推搡搡地把羊们关进羊圈,三两下锁上圈门。羊们想不通,这女羊倌今天是怎么了?对我们凶巴巴的,往日的温和劲是被山风刮跑了呢,还是跟清茶一道喝进肚子里啦?
扎西德吉疾步冲向家,爸爸,爸爸……她撞进房门,扯开嗓子屋里屋外地大声喊叫。平时不管多晚,也不管天气多坏,总能看见父亲坐在门槛上,或者到路口等她回家。可是,可是这次连他的影子都找不见。莫非……
扎西德吉哇地嚎起来,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她冲出房门,如一股旋风绕房子跑一圈,深一脚、浅一脚地射向通往山下村庄的凹凹凸凸的山路。
她的脑子乱成脚下满布石头的山路一般。爸爸,我打小就没了妈妈,连她长得什么样我都想象不出来。我长这么大,完全是您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的。直到今天,我们父女俩开开心心地过着叫人羡慕的日子。可现在……爸爸,您可不能出事呀!
跑了半截路,却不见父亲的影子,连一声咳嗽声也听不到。惊惧使她两耳嗡嗡作响,小腿肚触电似的颤抖,心脏突突突地蹦到嗓子眼儿,脑子一片空白,俨若空荡荡的沟壑。她的脚板滑过一面面陡坡,像一只强悍的鹰隼疾速向下俯冲。
父亲背着一大捆柴火,小跑着从山顶下来,朝山坡阳面的家走去。扎西德吉赶着快乐的羊群,快乐地跟在父亲身后。啦啦啦的哼哼声清风般飘向远方……
那一场场断断续续的梦影断断续续地在她脑子里闪现。
呸呸呸!她相信梦是反的,料定父亲出事了。
她隐约看见一个人影在灰蒙蒙的夜幕下轻轻晃动。爸爸,您怎么在这儿?她一下子扑倒在伦桑怀里,哭嚎声震荡着群山。
伦桑像曾经被自己打伤的猎物,蜷缩在路边的泥坑里,喘着粗气。
一滴滴泪水从扎西德吉的眼里噗噜噜地溢出。她背起父亲,一步一颠地朝回家的山坡爬去。汗水浸透了她的全身,仿佛淋了一场瓢泼大雨。
这一夜在扎西德吉悲悲切切的抽泣声中一点一点地消遁了。
新一天的曙光把扎西德吉早早地从被窝里拽了出来。
她强行背起父亲朝山下走。
歇一歇,爸爸有话跟你说。
扎西德吉不搭理。她的心与漫山遍野的石头一道哭泣。沉闷的哭声打动了山头的花草,它们一棵棵埋下了头。
伦桑像个孩子,在扎西德吉的背上摇晃、摆动。他用力捶她,拧她,甚而揪住她的头发,如同勒马一般往后拽,要她把自己放下来。这让本来就看不见路面、身体失去平衡的扎西德吉,几次踩空摔倒,腿脚多处擦伤了。
扎西德吉把伦桑背下山,雇一辆手扶拖拉机,上拉萨大医院给他瞧病。
做完所有项目的检查,医生悄悄告诉扎西德吉,伦桑的腿没治了。与其把钱扔进医院,还不如把他带回家,他想吃啥喝啥,就让他享用好了。
扎西德吉听明白了,医生这话分明在告诉自己父亲活不了多久,让他在自个家里慢慢地平静地断气。但她对医治父亲的腿病仍寄予一线希望。她双膝跪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恳求医生收下病人。然而,医生遗憾而又痛心地摇摇头,补充了一句,别让病人知道病情。
别让病人知道病情,这句话像一把尖利的刀子,深深扎进扎西德吉还没有多大承受能力的心,刺痛她的神经,使她颓然坠入了绝望的湖底。
她哽咽着离开了医生办公室。
走出门诊大楼,她揩干眼泪,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带父亲回家。可她的心从离开医院起一直没有停止过哭泣。
伦桑为医生拒绝收治自己既感到难过,又感到庆幸。难过的是意识到自己即将要离开女儿,走向生命的尽头;庆幸的是不住医院,可以减轻女儿的很多负担。
扎西德吉强忍着泪水,把头紧贴在父亲干瘪的胸前,伴着手扶拖拉机烦人的轰鸣声,暗自呜呜呜地哼起了哀婉的心曲。伦桑不时看看自己已无动弹之力的腿,苦笑一下,陪我走了近半辈子的一双腿如今竟然成了摆设,除了说明它还在自己的身上,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从此,伦桑的腿在梦中与扎西德吉一道穿行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而扎西德吉的腿却行走在自己与父亲的心灵之乡。
伦桑的微笑依旧灿烂如高原的阳光。可扎西德吉的啦啦啦却在灿烂的阳光下远离了父亲的微笑。
为了使父亲减轻病痛、驱逐寂寞、打发难熬的时间,有一天扎西德吉把托人从城里买来的一本《米拉日巴传及道歌》捧到伦桑手上。伦桑高兴得鼻头都堆出了笑褶,他恨不能从床上跳下来,几步跑到扎西德吉放羊的山头大声朗读。从那天起,只念过初中的他整天费劲地啃起那本传记,陶醉于书中娓娓道来的故事,被米拉日巴悲悲凄凄的身世以及苦修成道的经历感染得像个女人似的潸然泪下。
他一遍又一遍地捧读米拉日巴,命令自己一定要坚强地走过余下的日子,绝不能让女儿为自己落泪。
那天,心爱的羊们徜徉在绿草如茵的草甸间。有一阵没一阵的清风拂过绿草、野花、灌木,把山雀的啁啾声和旱獭的哔哔声断断续续地灌进扎西德吉的耳中,使她感觉到这寂寥的山坳愈发显得寂寥,回家见父亲的心情变得更加迫切。
扎西德吉强迫自己调整低落的情绪,像往常一样,头枕着羊毛兜袋,仰躺着凝望天空。天蓝透了。蓝透了的天让她的思绪一如骏马纵情驰骋。她头一回发现太阳和月亮同时挂在高远的天际。太阳在东,月亮在西。一丝莫名的意绪袭上她的心头。那轮月亮是脸上写满笑意的妈妈,那轮太阳是面容黝黑发亮的爸爸。那么我是什么呢?应该是快乐的星星吧。
她坐起身,望着碧空下的群山,暗自描绘起从未见过,也不可能见到的母亲的音容笑貌。打小向往着的有爸爸、有妈妈陪伴的生活,似一只小兔子在她的脑子里窜来窜去,让她一会儿喜上眉梢,一会儿又嘤嘤啜泣。
坐在三石灶上的烧茶壶里沸沸扬扬地潽出细碎的泡沫。浓浓的茶香随着她的呼吸沁入鼻腔。爸爸特别喜欢喝山上的茶,可惜他上不了山。也许他这辈子再也闻不到山上的茶香了。
扎西德吉和她的羊群身披一袭融融的夕阳回到家里时,暮色中的父亲躺在门口的地板上,脸上挂满了孩童般的笑意。
扎西德吉把他扶到床垫上,问他怎么躺在地下。他乐呵呵地说,这双没良心的腿……唉……
爸爸,我们再到拉萨看看病好吗?
不是到所有医院都看过了嘛。不要再浪費钱啦。
说来也是的。仅这两年的工夫,扎西德吉陪父亲到处求医问药,看了西医看藏医,看了藏医看中医,看了中医看江湖郎中。可这腿病就是不见好,给他们父女俩添了桩比身体的疾病更叫人难受的心病。
要不到堆龙。听说有一个阿姨什么病都能瞧好,可神了。
你说的是传说中的那个女神医?
空行母。
哈哈哈,凡间哪有什么空行母?能见到空行母的不是神,就是鬼。
人家农民说她是空行母嘛。
啊——哦。
说好了啊,我们明天就去堆龙。
我不去。
那我就从悬崖上跳下去。
我也跟你一块跳。
爸,我可不是吓唬您哟。
行,可这是最后一次上医院哦。
呵呵呵……
爽爽的笑声,朗朗地飞出了黑乎乎的屋子,飘向苍凉的夜空。
季节促使大地更换金黄色衣裳那会儿,扎西德吉为伦桑那双细瘦如柴的病腿放生了第九只山羊。被放生的山羊们为不知如何向扎西德吉表达感激之情愁眉锁眼。而忘情地沉醉于米拉日巴故事的伦桑终于离开米拉日巴,回到活生生的现实中来。然而,他正被死神一步一步地拖向生命的最后尽头。
伦桑吃力地抬抬手,招呼扎西德吉靠近自己坐下,孩子,爸爸快不行了。他茫然地看着女儿,米拉日巴帮我消除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只是怎么也割舍下你,我的宝贝女儿。
扎西德吉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爸爸,您不会有事的。
伦桑鼓起勇气,横下心来,一字一顿地把隐藏了十九个年头的扎西德吉的身世弹出了舌尖。
扎西德吉紧紧抱住伦桑,泪如泉涌,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爸爸。
其实她早就从别人嘴里听说过有关自己身世的只言片语。可她以为别人是在逗弄自己,回人家一句,你才是弃婴,压根就没当回事,也就没有进一步向伦桑问个究竟。但这话从伦桑嘴里说出来,可信度就大不一样。
好女儿,不要哭,爸爸想看到的是你快快乐乐的样子,而不是……话哽在喉头,说不下去了。
十一二歲就没了爹娘的伦桑非常后悔从城里拣来被人遗弃的这个女孩。当初我要是狠点心,不去管她,她总会被哪位好心人抱走,兴许她不会像现在这样受罪。天底下恐怕没有比我更傻的人。
一天收牧的时候,扎西德吉十分郑重地向羊们宣布:
哪天我爸爸没了,我就把你们全送给孤儿院。已经放生的羊们,请你们放心,孤儿院不会宰杀你们。其余的听着,如果你们有幸被放生了,那是你们前世的造化。还有一句话,我不能不给你们讲,为了我,爸爸这辈子连女人的手也没有碰过一下呀!
(责任编辑:王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