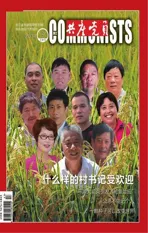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2014-07-10
文/本刊记者王一伊
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文/本刊记者王一伊

水稻抽穗时,细心做杂交工作。/田建明摄
两只小狗、两间温室、一间10余平方米的工作室,这就是“江南水稻育种大王”、曾任嘉兴市农科院院长姚海根在海南陵水育种基地的工作环境。
这位头发斑白,皮肤黝黑,身穿灰色衬衣,迷彩裤,凉鞋,裤腿上沾着泥巴的“老汉子”现是嘉兴市农科院名誉院长、研究员,71岁的他现仍奋战在工作一线,他是第一代“南繁”成员的领军人物。
所谓南繁,就是冬季利用海南独特温暖的气候条件加种一季作物,一年内南方、北方交替种植。一般选育一个水稻新品种最少需要7~8年时间,有了南繁北育,就可以缩短近一半的时间。
嘉兴农科院南繁基地。院子里一片忙碌,在椰树、芒果树的遮蔽下,到处堆着刚收获来的水稻种子。光膀的,穿短袖的,赤脚的,忙碌着的汉子们皮肤一式发散着“农民色”。他们正在给稻种脱粒、装袋、贴标签。“农民色”掩盖不了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都是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或中高级职称的嘉兴农科院农业科技专家。
水稻新品种选育过程异常艰辛。播种、杂交、观察记载、选种、核产等育种过程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要蹲在田间地头。下田,双脚泡在水里,这时蚂蟥、蚊虫就会趁机侵袭。水稻抽穗时间很短,但这是配组杂交、孕育新品种的关键时期,而选配杂交组合成功的概率只有数千分之一,必须大量配制组合提高选育成效。水稻新品种选育过程异常艰辛。几天之内要完成上千个杂交配组,所有育种人一早下田,顶着高温烈日的烘烤,一刻不歇地拼命抢时间,饿着肚子干到下午授粉结束是家常便饭。

姚海根在基地将稻种人工脱粒分装。/田建明摄
到了晚上,孤灯一盏,抓紧整理分析白天观察纪录,拟定明天的杂交组合,直至凌晨。
从1965年起,每年的11月中下旬,来自嘉兴农业科学院的育种人与家人作别,像候鸟一样追赶春天的脚步,奔赴海南培育水稻良种,次年4月才回来,年复一年。南来北返之间,相继育成水稻良种140多个,累计播种面积6亿亩,增产90多亿公斤,籼稻两次突破了长江流域纪录,并使嘉兴2009年以来全市晚稻平均单产连续3年突破550公斤,位列全省第一。
“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交通非常落后,从嘉兴出发到海南陵水的基地,少则七八天,多则十一二天。物资非常匮乏,我们做饭就像《三国演义》里行军打仗一样,在沙土上挖个坑,捡一点柴禾生火,埋锅造饭。不过,只要育种需要,天涯海角都要去。”面对艰辛,姚海根说得那么轻描淡写,而眼神中却又透露出无比坚定的信念。
辛劳过后的丰硕成果,姚海根被称为水稻育种界的一个传奇,已培育86个水稻新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2.9亿多亩。育成品种之多、覆盖率之高、应用时间之长、应用成效之大,全国罕见,农田面积不到全省14%的嘉兴,粮食产量能够占全省48%,他功不可没。
目前,嘉兴农科院6个水稻育种课题组共30人,年纪最大的70岁,最小的28岁,一批新生力量正在崛起:31岁的西北农大硕士高荣村、33岁的华南农大硕士蔡金洋、34岁的蔡之军和李友发……虽然目前还置身在公众视野之外,但他们依然选择与泥土做伴,与种子痴情相守。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就是这样的力量,南繁基地也贴着一条姚海根写的标语:“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为了这粒种子,他们离别家人,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蚊虫叮、蚂蟥咬,却比常人更坚定,更踏实!

嘉兴南繁育种基地试验田,70岁的杨尧城顶着烈日在丰收的稻田选种。/田建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