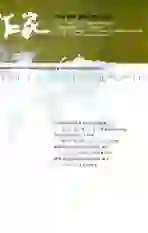一位沙漠之子的生态旅程
2014-06-30单畅
摘要 爱德华·艾比是一位常年居住在美国西南部沙漠的生态作家和环保先锋,他把自己称为一株独居在沙漠中的仙人掌,后世评论家因此把他称作“沙漠之子”。《孤独的沙漠》是爱德华·艾比的一部生态散文著作,文笔流畅优美,充满了智慧的闪光和思想的反叛精神,是美国生态文学史中可以与《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孤独的沙漠》 唯发展主义批判 民族挽歌
20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坛涌现出一批致力于书写自然,反思当下环境恶化现状,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流派——美国生态文学。这些洋溢着浓厚的自然主义情怀的艺术文本,虽然展现的自然景观和风貌迥然不同,但大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内涵:“非人类环境不是仅仅作为背景框架来展现,而是表现为人类历史是暗合在自然史之中的;人类利益不被当做唯一合法的利益;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的一部分。”在这三个层次上理解,爱德华·艾比的生态散文《孤独的沙漠》以作家与沙漠这一自然空间的朝夕相处为叙事线索,通过展现美国拱石国家纪念公园的岩石、树木、牛蛇、荒野的自然存在来表达人类的历史只是自然历史发展序列中较为微小的一环;通过对过度开发国家公园旅游业谋取经济效益的现实批判,来阐释人类唯发展主义的思维导向是生态危机恶化的深层原因。作家平实、朴素、简洁的叙事语言,自然、真切、虔诚的对沙漠、溪流、荒野的原始热爱,赋予了这部生态散文丰润的艺术审美境界。
一 融入沙漠荒野的生态理念
在生态文学发展的艺术历史中,生态散文的写作是极为重要的一隅,主要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植根于走向自然、融于自然的文学传统,因此,在《孤独的沙漠》中,我们可以找寻到梭罗《瓦尔登湖》的身影,可以倾听到约翰·巴勒斯《醒来的森林》中婉转的鸟鸣,可以领略到约翰·缪尔《夏日走过山间》中群山的风姿……这些生态文学的经典之作完全跳出了以人为主要叙写中心和对象的思想藩篱,挖掘出已被人类深深遗忘的自然界万物的审美价值,旨在引起一场关注生态环境、修缮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暴动,正如作者所说:“我想创造这样一个文字的世界,其中的沙漠不再具体化,而只是一种媒介和形式”,《孤独的沙漠》颠覆了人类对沙漠的人类中心主义解读,重铸了沙漠的生态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是几个方面。
首先,作品以沙漠的艺术描写展示了一种生态系统的和谐之美。“所谓生态系统的美既非纯自然的美,也非人的‘移情的美和‘人化的美,而是人与自然须臾难离的生态系统与生态整体的美。”传统的散文写作虽然不乏自然世界地描写,但都是人的对象化存在,自然的审美品质常是人类感受、情感的反应物,是一种人类中心主导的审美视角。在《孤独的沙漠》中,爱德华·艾比勾勒了一幅由奇形怪状的岩石、浮云和天空组成的自然景观:“向东望去,太阳正在为最后一跃积蓄着力量,在它散发出的光芒之下,笼罩着更多的峡谷、岩滩,以及层层叠叠的红色悬崖和干燥的台地,它们穿过淡紫色的薄雾,越过雄伟的科罗拉多河谷,一直延伸到沙漠的边缘”,作家毫不掩饰面对此种非人类世界的探究野心:“我想揭开它所有的秘密,占有它的全部,并深深地拥抱它,就像一个男人渴望得到一个美人一样”。在作品中,沙漠是比高山、大海更变幻莫测的所在,它简单、朴素的外表显露出古典的气质。由此,沙漠的清晨与日落,河流与浅滩,老鼠与响尾蛇,在作品中都被作家设定为艺术表达的核心,那种充满凶险、饥渴、苍凉的沙漠经由作家之笔幻化成一种万物和谐相处,充满美感的诗意所在,它使人沉静,回归自我,开始思考。
其次,作品以对生与死的关注传递了一种遵循自然规律的情感。当代环境理论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在1915年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所谓敬畏生命绝对不仅是敬畏人的生命,而是要把植物、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一样神圣。在《孤独的沙漠》中,作家首先看到了生命存在的食物链条关系,例如,在《牛仔与印第安人》这一节中,猫头鹰与兔子的掠食与被掠食关系在作家的生命理解中已经转化为朋友的关系:“经过一生的恐惧后,这只兔子很有可能是带着一种感激之情,心甘情愿地而且是很高兴地向猫头鹰屈服,并让它吃掉。他们中一方在寻求一个结局,而另一方就是这个结局的执行者。在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操作和程序系统里,我们怎能谈及天敌呢?”在《格兰维角的死人》一节中,作者通过与约翰寻找叔叔遗体的亲身经历表达了对于人类死亡的生态性理解。作者认为在开阔地区,天空下,远离水蛭与牧师无礼的烦扰,在这永恒的空旷沙漠面前结束生命是擁有了好运气;死者的死亡并不是令人悲痛万分的事情,而是大自然生命系统一种自动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转现象。
最后,作品以动物与人的存在形式表达了一种家园意识的寻找。在工具理性主导的后工业时代,环境破坏的日益深入,在人类的贪婪、欲望得到无限放大的同时,人类也面临着精神家园的坍塌与陷落,现代社会的人成为了失却家园、无根的物质存在。《孤独的沙漠》正是秉承着寻找家园的宏伟使命,在作家的铿锵脚步声中一步步走向神秘的沙漠世界。在作品中,爱德华·艾比是一个人踏上征程的,但是,在国家公园的第一个早晨,他不觉得孤独,因为“三只大乌鸦正在平衡石附近盘旋着,叫嚷着”,与他为太阳的回归感到欣喜;在寒冷的夜晚,他也不觉得孤独,因为有对牛蛇帮助他赶走危险。在作家看来,户外生活可以使自己免受孤独和心灵禁锢之苦,而静谧的沙漠就是自己最温暖惬意的家园:“我感觉我的整个人都融化在天空之中,并逐渐消失在远方的群山之外。”此时,人类与沙漠中的更格鲁鼠、长耳大野兔、浣熊以及黑尾鹿都是独立的生物个体,但同时又是生命共同体,共存于地球家园之中。一生致力于荒野保护的爱德华·艾比在病逝后,被安葬在亚利桑那州西南部卡韦萨普里埃塔荒野,魂归大地,实现了一位沙漠之子重回家园的生命理想。
二 走出唯发展主义的思想误区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人类和地球母亲》一书中说到:“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这种人类放肆的贪欲在爱德华·艾比的思想意识里就是一种危害生态环境的唯发展主义观念,在《孤独的沙漠》中,爱德华·艾比针对旅游工业与国家公园之间的剧烈矛盾深刻批判了为满足人类娱乐、闲适生活的需要对荒野的过度开发、利用的生态破坏行径。
对唯发展主义观念的理性质疑来源于作家对荒野“可进入性”的思考:“在地球上究竟还有什么地方是人们不能通过用脚和心灵这些最简单的方式进入的吗?甚至连麦金利山、珠穆朗玛峰都已经被人类征服在脚下。”美国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在一篇名为《装了门的大山》的作品中揭露了暴发户们沿着塔基河山脊建造房屋的人类侵袭自然的行为,充满野性的自然被扼杀在“山门”的街道命名中。爱德华·艾比在国家公园的“可进入性”问题上,主要是探讨游人及他们所拥有的机器,也就是汽车、摩托艇等交通工具的涌入。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一部分人对金钱利润的追逐,他们直截了当地鼓吹将国家公园全部开放,完成人对自然的最后的征服,以迎合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在爱德华·艾比看来,“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急遽损坏,也必将消灭人类文明最后的荒野之地,在《孤独的沙漠》中作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实际效用的明智建议来倡议资源管理者、游人共同加入荒野保护的实际行动中,建议不要再让更多的汽车进入国家公园,不要在国家公园修建公路,让公园管理者负起责任,履行自己的职责。可见,爱德华·艾比不仅是一位沙漠的朝圣者,也是一位极富有行动力的生态保护者,正如他的好友杰克·莱夫勒给他的评价,终其一生、竭尽所能,以其良知和理性去阻止那不可抗拒的发展。
从爱德华·艾比对“可入性”的质疑和深入思考中,我们看不到某种狭隘的偏见,例如,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号召的完全封闭荒野之地,拒绝人类进入最后的文明领地。相反,我们能够深刻体悟爱德华·艾比希冀游人在自然地召唤下,用脚步、呼吸及心灵去亲近沙漠,在那种孤独、甜美、偏僻而又原始的世界深处安放灵魂、舒展精神。正如爱德华·艾比在作品中所说:“你在车里看不到任何东西;你得从那该死的机器中出来,用脚,最好是爬行,用手和膝盖爬过砂岩、多刺的灌木丛和仙人掌。当你的血迹留在旅途中,也许你就能看到一些东西了”。沙漠是神性而充满诱惑力的,对于人类,沙漠永远也无法穷尽,在沙尘的背后,秃鹫出没的天空下,沙漠——岩石台地、峡谷、悬崖、山峰、迷宫、沙丘和山脉,仍然等待着人类的探寻和进入。
三 唱响一个部族的生态挽歌
在《牛仔与印第安人(二)》中,爱德华·艾比写道:“牛仔和印第安人正在消失,他們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就是已经被扭曲成另外一副模样。他们身上的那种原始的东西已经泯灭或是湮没在如潮的人群之中了。传说中的敌人和他们的灵魂一起远去——最终成为了朋友——消失在西部的斜阳之中”。现今,人们只能捕捉到一些印第安人不同部族生活的痕迹:在泉水附近,在悬崖下,在适合露营的地方会发现散落在地上的数百片打火石,那是阿那萨奇族的捕猎手加工箭头所留下的;在峡谷平整的两壁,会看到岩画与象形文字,那是带有某种宗教或仪式色彩的神迹……这是一处没有边界的世界艺术殿堂,在经历了大自然无数个世纪的洗礼后向我们展示出了一种无声的世界文化语言。作品中还介绍了那瓦霍人在工业化发达的当下,因为土地贫瘠、缺乏教育、医疗等生活基本保障,正面临着巨大生存挑战的现状。虽然旅游产业能够为这个部落增加一些经济收入,但是那瓦霍人不得不付出贩卖灵魂、遗忘祖先的代价,他们必须学会机械式的微笑,学会礼貌和友好,学会适应那些衣着奇怪的陌生人进入他们的家园和土地,习惯被参观和拍照,仿佛他们不是在展示土著风俗,而是在兜售和叫卖日用品。在这个经济报酬获取的过程中,那瓦霍人必须忘却他们曾是骑手、牧羊者、羊毛编织者,或者至少要为这些过去的事情感到羞愧,才能更好地取悦游客。在爱德华·艾比现实主义的叙述笔触中,流露出作家对那个与自然朝夕共存的印第安人命运的关切,也从侧面体现出了爱德华·艾比对生态文明陨落的沉重心情,一首印第安部族的生态挽歌正从沙漠之地袅袅飘来。
参考文献:
[1] [美]惠特曼,马永波译:《典型的日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3] 王诺:《爱德华·艾比与唯发展主义批判》,《世界文学》,2006年第2期。
[4] [美]爱德华·艾比,李瑞、王彦生、任帅译:《孤独的沙漠》,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单畅,渤海大学大学外语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