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超现实主义的想法当作一个技巧
2014-06-24痖弦阿九
痖弦+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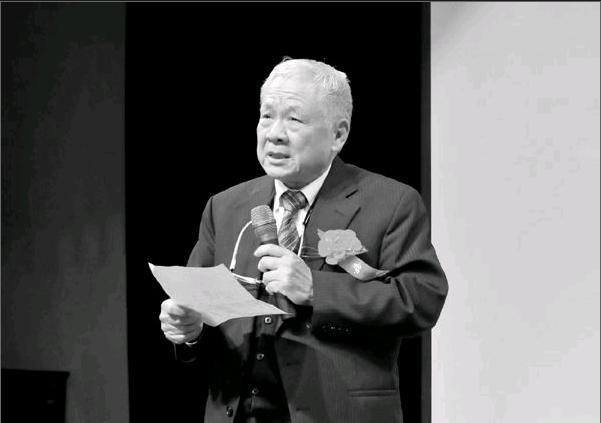
主持人语:
诗人痖弦是台湾《创世纪》诗刊的三驾马车之一。我是198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诗选》上第一次读到痖弦的《瓶》、《地层吟》、《水夫》等三首诗歌。后来,又在诗人流沙河选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上读过他的一些作品。1990年,诗人商禽给我寄来不少台湾诗人的诗集,当然也包括《痖弦诗集》。去年11月,痖弦荣获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说句实话,谢谢阿九从温哥华发这个访谈,我们也许会从这个访谈中读出作为诗人痖弦独有的诗歌精神与文化观察视角。(雨田)
时间:2009年3月16日(周六)
晚8:50 - 11:50 pm
地点:加拿大,BC省Delta,痖弦先生府上
一、漂学
阿九:您曾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脐带,任何人都有他自己的血系。我想请教痖弦先生,您的精神血系是怎样的?我很想了解您年轻时关注过的作者。他们对您曾经的影响,或许正是您后来对别人影响的渊源。
弦:以前中国人取名字都是按照家谱排辈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谱系。这就是文化,所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血缘。文学上也是如此,我年轻时自然也受过前辈作家的影响。
九:您曾经在一本书里讲到您寻找李金发的诗集《微雨》的事情。据我所知,大陆在1986年左右影印了这部诗集,我自己还买了一本。我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在想,不知您现在有没有找到这本书。
弦:已经找到了。我在做中国新诗研究的时候,就在找他的这本诗集。有些人喜欢回忆自己年轻时的辉煌,有些人则不大愿意提起。我曾为他做了一篇很长的访问记,并且相约再纽约见面,遗憾的是当我赶到时,他已经过世一个星期了。金发先生便是一个不喜谈他过去的人,很少接受访问。他在美国退休多年,一直过着非常低调的隐居生活。
九:我这里有一个名单,是从散件在您的诗集和研究您的文章里搜集起来的。汉语诗歌方面,对您早期诗歌影响很大的作者是何其芳。萧萧说您的诗跟何其芳有着某种血缘关系。
弦:是的,我年轻的时候,何其芳是我的诗歌偶像之一。我曾经形容,这个影响是我年轻诗土上的第一场春雨。
九:后来您说过,偶像的破灭是很痛苦的。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弦:那倒没有,只是他离政治太靠近了。
九:国外方面,法语诗歌您研究过波德莱尔、瓦雷里、苏佩维埃尔、还有超现实主义的艾吕雅、布勒东;英语有惠特曼、艾伦·坡、康明斯、济慈、葛里康;德语诗人有梅特林克、里尔克;西班牙语的洛尔迦,此外还有俄语的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等。
弦: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其实影响我的还不止何其芳一个人。按我们河南老家的话说,我这个叫做“漂学”,漂字读瓢(piáo),意思就是到处学一点儿,走到哪儿学到哪儿。
九:如果要用最简单的一两句话来概括,您觉得您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
弦:应该是人道主义吧。我觉得每个文人都应该是个广义的左派,不做狭义的左派。广义左派始终站在社会基层苦难大众这边,作不平之鸣。而狭义左派却往往受到党团的牵制而身不由己。咱中国字很绝妙,黨(党)字正写“尚黑”,碰到政治,人的脸就黑了,就复杂了。
九:我从您的作品和研究您的文章中了解到您的一些创作手法。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您借鉴过哪些人。
弦:我“漂学”的范围很大,举凡“波德莱尔以降”(纪弦语)的欧洲重要诗人,我都涉猎过。先是学腔调,后来是学精神。梵乐希(瓦雷里)我们也迷过一阵子,超现实主义也迷过。后来拉丁美洲的诗人在我的写作后期也有过影响。
九:中南美洲的诗歌非常精彩,比如聂鲁达、巴列霍,还有博尔赫斯。我最近正在读博尔赫斯。
弦:博尔赫斯是不是眼睛瞎了的那个?他当图书馆长,几万册书,他眼睛却看不见,你说多残忍。博氏什么文章都写,有很高的文学教养,是杰出的诗人和批评家。
九:此外,拉美还有奥克塔维奥·帕斯。
弦:帕斯很精彩,我的《深渊》就受他一点的影响。我说“一点的影响”是因为只有前面几句有点像他的调调,几句以后就是自己的创发了。重要的是,那首诗的总精神是我自己的。我们那时候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出头,抵抗大师的影响能力最弱的年龄。我不喜欢改写早年的作品,宁愿留下一些摹仿的痕迹。
二、深渊
九:我对您的《深渊》特别感兴趣。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用一篇文章去概论您的全部写作。您的写作广度和深度不是一篇文章能概括出来的,它也许是一本书或者几本书的研究对象。假如我要写一篇文章来评论您的一首诗,那应该就是《深渊》。我读过张默和无名氏的文章,以及一些网络评论。我觉得这些文章都有自己不同的侧重点。我自己希望从另一个方面来着手。首先,我觉得要对文本作足够的解析。比如,在《深渊》的第一句:“孩子们常在你的发茨间迷失。”这个“你”指代的是谁,它可能有一个文本的意思,还有一个文本背后的意思。这个“你”有可能指代不同的人。您提到过在爱荷华的时候结识的美国青年诗人高威廉(William Golightly, 1949-2007),还有您的英文版的诗集Salt。那个诗集的初稿应该是您自己译的吧,然后他来修订,是这样吗?
弦:他不懂中文,我的英文当时也有限,我们两个一起工作。他是个很好的诗人,英文极好,博览群书,思路敏感而快捷。他不懂中文。我们大概是这样工作的,先由我告诉他英文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记下来,推敲、修改,然后我再看。两个人一起整出那个翻译。他是我的同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19岁,是一个奇才。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他把我当父亲看待。可惜他已经过世了。
九:真可惜。
弦:他跟我还回到台湾住了几年。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没有饭吃,但一定要买一朵玫瑰。
九:在《深渊》的英译里,“你的发茨”被译成his hair。这是您的意思呢,还是他的意思?
弦:我跟他推敲很久,觉得这样译比较恰当。两个人中间还是有很多盲点,不容易克服。不过高威廉(我为他取得中国名字)极为聪明。我说是他译的,他说:“不是。我又不懂中文,怎么译呢?”所以后来就说我译的,不过是在他的协助下译的,这样才对。尽管态度严谨,还是有很多错误。两个人不对头的地方,我们就用林琴南(林纾)的做法。林琴南也不懂英文。有一个懂英文的人告诉他什么意思,他就用最漂亮的中文把它写出来。
九:我觉得这首诗的英译也很有特点,因为它有很多新的意思出现。
弦:论者说庞德译中国古典诗,就出了不少“美丽的错误”,完全出乎意料,弄拧了,但拧出新的美,新的趣味来,那也无妨。比如这个“你”,其实是作者的自称。我是学戏剧的;我把我自己也作为一个剧中人物来分析,同时也代表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所以说“他们”也就是说我自己。译的时候,不能照字面作生硬的传达。
九:在这首诗里面有很多人称自由转换的地方。我知道您的戏剧功底。在舞台上并不是单口的,而是不同人物(人称)之间的对话,所以它是一个多人称的narrative(叙述)。同一个故事由不同的人说出来,有时是“我”,有时就变成了“你”或“他”了。我想请教一下,《深渊》里的人称转换是您有意为之的呢,还是写出来就是那个样子?
弦:不是有意的。就是说,有时候觉得用“你”比较好,或者用“他”比较好,就是那个样子。
九: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曾经把人称转化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技巧。而我之所以有这种念头,是因为我读过很多中东古代文献,比如史诗或者创世诗。这些文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里面有大量的人称自由转换,因为这些作品都是由大量泥版或残篇拼接而成的。同一个故事,一部分是由某个行吟者用第二人称“你”来叙说,而另一部分则由另一个吟者以另一个人称来演绎。这就像舞台上多人称的叙事,人称转换就变得非常自然。
弦:有时候是直觉的,用“你”或是“他”,“你们”或是“他们”,并没有分析过,就这么用下去了。
九:在我看来,《深渊》里的“他”就是“我”,一个大我,或者说是所有的人。
弦:对,一个荒谬时代的荒谬的人。
弦:那时候台湾是政治戒严(白色恐怖)时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象征的方法,把我们自己对社会不平的呐喊,对黑暗的诅咒表达出来,而不会受到政治上的牵连。比如“向坏人致敬”,在高呼万岁的时代,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啊?“向坏人致敬”这样的诗句,你在五六十年代的大陆也不行啊,在台湾同样不行。
九:两岸的人民都曾经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这是一个悲剧。
弦:有时候我会故意地把背景放在国外。这些都是有一个同样心理背景的。
九:比如您在有一句诗里写道:“在西班牙,人们连一枚下等的婚饼也不扔给他。”这里西班牙是不是指的就是中国啊?
弦:是中国,因为西班牙当时反共的情况跟中国很相像,跟台湾当时的情况很像。两个人独裁却都是反共的,一个是佛朗哥,一个就是蒋介石。他们两个很相像,他们给人民有限的自由的程度也很相似。他们是共产党的专家,跟共产党缠斗最久。他们在世界上的形象也非常类似,所以我就用西班牙来指称当时的台北。
三、“本刊正申请登记中”
弦:很长一段时间,文艺界也有反对现代诗,反对超现实主义的人。他们说我们的诗歌是胡闹,根本没有艺术和社会价值,说我们缺乏对群体生活的关心,也没有思想深度。后来我们就去进行自我分析,我们究竟有什么。我们发现,我们是隐藏式的表达,比如我的《深渊》,洛夫写金门炮战的《石室之死亡》,商禽的《逢单日的夜歌》(也是写金门炮战前线生活的),非战甚至反战的思想很浓。
九:(点头)
弦:你知道,国民党是一个很糊涂的政党,它不像共产党有一本很清楚的帐。这方面国民党比较欠缺。它的文化审检人员有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其实我们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偷关漏税地”进行我们的超现实主义实验。国民党的文化审检人员程度很低的。他一看看不懂,就觉得没有问题。(笑)
九:那共产党就不一样了。(笑)我也讲一个故事。我当时还在大学读书,我们学校有个保卫处。他们平时是看大门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在校园四处走动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贴一首诗,只要是他们看不懂的,保卫处的人就会说它是反动的,把它撕下来。他们的理由是:我们都看不懂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弦:那俄国又不一样。据说俄国的文化审检人员可以在无标题的音乐里找出你的资产阶级意识。那就可怕了!(笑)让你无可藏匿。国民党和共产党里没有那么高段的审检人员。好像没有人分析过陈钢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究竟有没有“个人温情主义”、“小资产阶级”气氛,作曲家只要根据“政治正确”(梁山伯是无产阶级,马文才是压迫穷人的有产阶级),把本来以纯音乐的态度完成的作品放在这个民间故事上头,就可以在审查时过关了。这真是聪明的做法。
弦:所以我们《创世纪》很长一段时间永远都在版权页上写有一句话:“本刊正申请登记中。”可是一直也没有真正申请登记过;登记也无法过关,反而引起注意,还是“地下文学”安全。
九:大陆这样的刊物也很多,包括我在大陆加入的同人刊物,也一直没有正式登记,但一般是不会管的。
弦:但是两党比起来,共产党的一本账还是很清楚的,不像国民党糊里糊涂。我跟你讲糊涂到什么程度。我是1949年到台湾来的,一下船就到凤山当兵。当时军人队伍外出作兴唱军歌,我们就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唱歌,还唱了一年多共产党的歌。比如有支歌词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痖弦先生在很有节拍地唱着)那就是共产党的陆军军歌嘛,我们在台湾军队也在唱。(笑)还有《团结就是力量》,那就是共产党进北京的时候唱的歌嘛。(笑)后来才有人指出:“不行!不行!这个不能唱,这是共产党的歌嘛!”你看,这个军队让人家打到台湾来了,还在唱着敌人的歌,是不是傻里呱叽的啊?(二人大笑)后来有人就说,这一定有“匪谍”(地下党)在里面捣鬼。
弦: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原来是上海青红帮的底子。绝对的愚忠,对领袖绝对的忠诚。但是,知识水准有限,可以说无知。
九:文化上也许欠缺一点。
弦:比如说,对待台湾的知识分子,就犯了很大的错误。
九:当然,共产党也犯了不少错误。如果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好一点,就不会有文革里的种种悲剧。文革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打击非常大。
弦:我们这里也有对待日据时代的左倾知识分子的问题,比如杨逵,一些主张民族自决的人。当时的情治人员认为他思想有问题,把他下狱,其实冤枉,绝对是个错误,完全不了解日本统治区华人青年的心态。当时富有民族自觉的人,对现实有多么绝望。试想,当时日本马上就要让他皇民化,让他改名了。万古长夜没有天亮可以期待了。怎么办呢?那时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了。他很自然地就把自己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想法、救援的想法,寄托在新兴的国际主义思想上。因为祖国是无望的,祖国没有力量来救台湾啊。而当时是没有什么好抓了,就来抓国际共产主义,以此画饼充饥,当梦来做,其实那只是一种反帝国主义的自卫思想,跟共产党人八杆子打不到,跟地下党毫无关系,不能当成思想有问题给关起来,而且关那么久。特别是杨逵这些文人,他们都是很纯粹的知识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就关起来,甚至毙了,这就不了解他们。他们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把他们当成狭义的社会主义者,更不能把他们当成是地下党。其实他们距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远得很,远得很。二·二八事变跟这个误判有很大关系。
九:这也是个很大的悲剧。我在读《台湾地方史》时了解到共产党早期的民族理论,也许是从前苏联移植过去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弱小民族自决的。
弦:胡风的书里就有杨逵的《送报伕》。胡风当时编的是一本弱小民族文集书名《山灵》,就有台湾这一部分,选入了杨逵的文章。
九:弱小民族理论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民族层面的人道主义。弱小民族老是被人欺负,如果有一天它想自由或者独立,本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弦:而且它也是寄托在宏大的、讲世界主义的、各民族平等的、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联合起来的主张里。
九:这一点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也是有意义的。
四、禁书时代的盗火者
弦:我们早年是生活在一个禁书的时代。我们得到的文学资料不多,资讯很闭塞。所有在大陆出版的书,不管有没有问题,不管书的作者有没有从政,只要作者人在大陆,都是被禁的。大概只有朱自清、冰心没有禁,徐志摩没有禁,其他都是被禁的,尤其是三十年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得到一本就很小心,并且视作珍宝,然后就手抄,像中世纪的僧侣一样抄书。那时候也没有影印,我们就一直抄。
九:我特别想看您的书架,想把您抄的那些书,摆在您书架上的那些书拍下来。我觉得这肯定非常有意义。
弦:都在地下室堆着,哪天整出来给你拍照,现在不怕戴红帽子了。讲到抄书,书抄了以后,还画封面,把封面也画下来。最疯狂的就是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整个抄下来。抄一遍就一辈子不会忘;抄一遍对你的影响就非常大。
九:我记得您还抄过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另外一些苏俄作家。
弦:《普希金诗全集》我抄过,还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大部分章节,整本高尔基的《母亲》。
九:还有一个,也是革命前后的。
弦: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是快乐而自由的”都抄过。都是借好朋友的禁书,不轻易示人的“黑货”。
九:文学理论方面还手抄过谁的书?
弦:别林斯基。那样文起八代的大批评家,今世少见。
九:据杨牧先生在您的《聚繖花序》序言里说,您还手抄过卢那恰尔斯基的《艺术与批评》。
弦:是啊,抄禁书抄疯了。
弦:早年台湾的小说家是从来不读诗的。因为不读,他就不懂。后来,几个有成就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就开始读诗了。写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文字是用普通的语言,不是意象很多的那种。后来电视出现以后,小说受到冷落。小说家觉得,叙述本身的艺术还是小说形式的主要特点,比电视更要站得住。电视再怎么讲,深度不行,所以大量的小说家向诗歌学习。现在读通了,特别是散文跟诗歌,彼此的关系非常密切。过去散文就是身边琐事的散文,跟诗没有关系,写实主义小说跟诗也没有关系。而且那个时候诗人也不太看得起小说家,认为一个诗人改行写小说没有好下场。(笑)
九:加拿大也有一个说法。我曾读到一本书叫Where the Words Come from,中文可以译成《词语之所从来处》,是一本诗人访谈录。其中有一个诗人就说,加拿大很多诗人本来是写诗的,诗人“毕业了”就变成了小说家。
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些小说看上去像诗一样。小说的容量大,可能性多。
九:小说至少在表达空间上的自由大一些,而诗歌更强调的是一种张力,它需要高强度甚于它的广延度。
弦:说得好。这两方面应该是相通的,所以我告诉年轻的学生,如果你不懂诗的话,你将来连小说也看不懂。不但你小说看不懂,你到了剧场也看不懂戏剧了。
九:我有个朋友就是做实验戏剧的。她本来写诗,现在自编自导自演,写一些实验戏剧,都很诗化。所以说,至少戏剧是充分诗化了,尤其是一些独幕短剧。一些很重要的作家都在写独幕短剧,包括萨特,他有个独幕短剧叫Huis Clos,英译作No Exit,就是“没有出口”。对了,您的《深渊》里有一个片语叫“没有出口的河流”,跟萨特的这个短剧有没有关系?
弦:当时我没有看过这部作品。后来,比如我说,一个雪橇到了非洲刚果那儿停了,那其实是学海明威的。海明威不是有个小说里说一个雪豹死在雪岭上吗?不知道它为什么到那么高处去死。
九:去年夏天我回国的时候,在杭州的颜如玉书吧里看到一本《动物感恩故事》,其中第一篇就是这个故事的梗概。
弦:《战地钟声》吧,“丧钟为谁而鸣”嘛。(For Whom the Bell Tolls,出自邓恩诗句)。海涅也有一首诗,好像是说南国热带的一棵棕榈树,想到北边最冷的地方去。彼此的差异性,也很有趣。我还有一句诗,“今天的告示贴在昨天的告示上”,其实也是学海明威的。海明威说过,那些光荣啊,勇敢啊,奋进啊之类抽象的字眼,远不及枪炮火药来的实在。一个军事单位的番号,一个小兵的兵籍号码,比抽象的牺牲、勇敢还要动人。一个在墙上被炮火熏黑的告示,比你说任何光荣什么的字眼都更有力量。
九:就像一面布满弹孔的军旗一样。
九:这倒是今天的一个发现。就我所知,此前所有研究您的文章里,都没有提到过海明威。
弦:所以,年轻时候学人家的东西,慢慢地,到老了也就招出来了。(笑)
九: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您的一位翻译家朋友写的,他曾笑言,利用友情关系逼作者去交心是很不仗义的。
弦:其实我觉得还是招出来吧,招出来比较好。(笑)杭州的龙彼德先生也一定要看我的书房。他讲啊:“是不是古代的英雄都不让人家看练功房?”(笑)
九:这个比喻很恰当。
弦:我说“我倒不是。”我看书的时候拿个铅笔。看到好的东西就勾一下,然后写札记的时候就把它写下来,记下好的意念。年轻时候更注重好的句子,后来觉得句子不太重要,意念更重要。那些话我记下一个要点,或一个语字,日后重读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们说的是什么了。看完以后,如果说这本书是借的话,就用橡皮把它擦掉,免得别人知道我是从哪里看来的。所以说练功房是不让人看的。(二人大笑)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九:痖弦老师读过《圣经》吗?您的诗歌里有很多基督教话语。
弦:我读过,读得很仔细。是啊,我的很多意象是跟宗教有关系的。我那时候把它当作一个美感来看,当时还不信教,后来渐渐觉得心灵靠近了。我跟我太太谈恋爱时,她经常叫我送她到教会去。送她到了之后,我就去逛街去了。大概预估到快散会了,我就去接她。有时候时间算错了,早了,牧师还在讲道,就听一段。我太太劝我,一个人应该有信仰。我现在虽然是[基督徒],实际上我的问题也蛮多的。有人说,对神怀疑最多的,有可能是更好的基督徒。我并不逃避或隐瞒我对神的怀疑甚至愤怒。
九:我也是个基督徒。我是在1999年受洗的,但我是个有更多疑问的基督徒。
弦:这样才深刻嘛!现在好的基督教作家不多,台湾更没有。有的只是灵修的书,没有多大文学价值,只是教会一般的小册子。我期待比较深刻的宗教文学,这方面应该有很大的领域可以发展,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佛教传入后,对中国的文学影响多么大,可以说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基督教这方面就没有这样的发展。
弦:我最近喜欢看老电影。以前的默片时代有个电影叫作《风》。你不要看是默片啊,里面有很多是很好的东西。它的语言是笨拙的,但是它的形象是很丰满的。一个女孩子怕风。一开始就是风在刮。整个电影一直在刮风。到后来,她有了男友,得到了爱情,她不怕风了。那个女孩子说,我现在不怕风了,两个人就把门打开,二人迎着风吹。《铁达尼号》里,两个人不是在船首迎风而立吗?这个可圈可点的镜头其实有来历。看到这个场景时我就想,那是从《风》这部老片来的。别认为老东西没用,很多观念就这样被新的导演拿过来了。
九:这种学习是很应该的。我有个朋友叫刘翔,目前在浙江大学做副教授。他家里藏有近万部电影,至少五千个音乐CD。以前,他如果每月有一千块钱人民币的收入,他自己全部的消费大概也就一百块钱,剩下的九百块钱全部用来买书买碟。
弦:噢,那是真正的专家。我也有几百部电影,我也喜欢。我当时买的时候都是VHS大盘,现在没有办法变成DVD了。就是有DVD,我也不想去买。我还是喜欢看我的老带子,就好像看旧书一样。倒带子就像翻书页一样。
五、外省老兵
九:您平时什么时候休息?
弦:我其实生活很没有规律,很随性。有时整晚不睡觉;累了就睡,想运动就运动几天,然后又停下来。我兴趣也挺多的。我喜欢看家乡戏,所有老兵的癖性我身上都有。(笑)喜欢看家乡戏、吃家乡食物,找同乡老友谈天。这老友不一定要是文艺界的人,有些老同学老朋友“混”得不好,日子艰苦,还有在公寓大楼给人看大门的,也有在垃圾填埋场拣东西的,那没有关系,绝对影响不了我们的友谊。
九:那您肯定到Broadway上的少林面庄去过吧。
弦:对对,我去过。面庄有个同乡会。你是哪里人?
九:我母亲那边祖籍是河南光山的。
弦:你母亲说河南话吗?
九:会啊,我也会说。所以我在读您的诗的时候,凡是有河南方言色彩的,我一点没有问题。我跟河南诗人的交往也特别多。
弦:有好样儿的没有?
九:有啊,像耿占春、蓝蓝、森子都很好,他们是河南实力最强的诗人,还有一些也很不错。
弦:我找一张纸出来。我的乡情很浓,能不能请你把河南一些优秀的年轻诗人的名字写出来。
九:非常乐意。
弦:家乡对我是蛮重要的。
九:(信手写了一个河南诗人的名单)不知道有没有漏掉谁,但至少有这些人。只要找到其中几个,就能找到另外一些。
弦:很有希望啊这一批人。我只认识苏金伞、青勃等老一辈的诗人。
九:我没有见过苏老。
弦:我到郑州去过,苏老请我吃饭。他那时还是河南省作协的主席。请吃饭的时候还有几位河南作家作陪。苏老站起来致辞,说:“今天是欢迎痖弦同志回家乡。”有人在下面拉拉他的手小声提醒:“不能说‘同志啊。”他说:“咋不能说同志啊?文学的同志嘛!”引来众人大笑。苏金伞四十年代中期就成名了,代表作诗集《窗外》(巴金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我有这本在台湾的“禁书”,一直留着,秘藏了几十年,那次也特别带回郑州请他签名留念。老人家非常高兴,在书的扉页上写:“一本破诗集,谁为你保存了几十年!”《窗外》中有很多动人的诗,如《我家的头发》,我百读不厌,那是他的名作。餐会上有人开苏老的玩笑,说苏老八十几岁还写恋爱诗,诗中写跟他女朋友“走着,吻着,晚风把河里的星星吹得叮当作响。”有人就问他:“苏老啊,‘走着,吻着,吻的是谁啊?”他说:“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子!”(大笑)苏老当然也是左翼的。河南本土有很多诗人非常特别,在非常政治化的年代,还有一批诗人不管政治正确,坚持写个人主义的诗,唯美的诗。带点儿恶魔色彩的诗人于赓虞(1902-1963,著有诗集《骷髅上的蔷薇》)那样的风格在1949年后还有人在偷偷地写,逆流而上,这也难得。另外,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所引起的俗文学语言,所谓的民歌体的新诗,最左最左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诗,也有人在写,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弦:北京上海两大文学城市之外,别的省份有没有像河南这么旺盛的写诗风气?
九:也有。中国的江南省份比如四川、浙江,诗歌人口很多。
弦: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好诗人,乱糟糟的;还是乱中有序嘛。
九:乱确实乱,但也是有点序的。
弦:乱没有关系,乱中有序,就不怕乱,说不定愈乱愈旺。你想啊,任何一个繁盛时代表面上看都是 “乱”的。因为乱,所以丰富嘛。你想唐朝不乱吗?唐朝自天子以下直到庶人都写诗。那有多少人啊,多少坏诗啊,能不乱吗?天子写得一塌糊涂,周围的坏诗人一大堆,一天到晚瞎捧,只要皇帝老子高兴就好。后来慢慢的,时间老人爬梳整理,自然而然把好诗都留下来了。你说呢?唐朝也许是最乱的一个时代。
九:也是成就最高的。
弦:所以不怕乱。
六、半神半兽的先锋
九:您说过“一日诗人,一世诗人”。如果一个人不年轻了还在写诗,那么他肯定是一个真的诗人。年轻时期的诗也许注重于某个方面,但是如果他一直与诗以某种方式保持联系,那么诗歌在他身上就是——
弦:生活方式。
九:您在《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序言里引述过《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望今致奇,参古定法。您也说过“真正的传统精神就是反传统。”我很想了解一下您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我还想问一下,这篇文章是40年前写的,现在您对此问题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新的想法。
弦:没有什么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还是有同样的想法。
九:在我看来,这句话本身代表了一种先锋精神,就是先锋诗歌的精神。
弦:往往有这样的情形,“革命者”变成“被革命者”,到后来时间久了,“被革命者”又变成“革命者”,就这么一路滚上去,因为文学的钟摆是有摆荡性的。
九:正如有人说的,您写了《深渊》后,模仿的人太多了,弄得本来的作者都不知道怎么写了。
弦:我也觉得没有什么新话好说。后来我的精力和时间主要放在编辑事业上。不过,因为编辑常常要给别人写序,我的序言也花了很多功夫,常常借题发挥把我的很多想法也放在序言里。
九:您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想法非常好,也非常有趣,比如您说“所有伟大的思想都是半雄半雌的”。(大笑)
弦:是这样子。
九:实际上,这个讲法非常有道理。我上次跟您说过,我会问一些“魔性”的问题,这个就算其中之一。我想问一下,您整个的思想和诗歌是否也是半雄半雌的。
弦:或者说半神半兽的。
九:在我看来,所谓雌性的部分,就是您的人道主义,那种悲悯,它是母性的。
弦:说得好。
七、乡音
弦:我小的时候,是在社戏的戏台下长大的。对戏剧很熟悉,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看戏。
九:河南那边主要有哪些戏剧?
弦:河南是地方戏剧的故乡,剧种很多。最常看到的是豫剧,原来叫河南梆子,敲一个很响的梆子,后来成了剧名。
九:折子戏也是河南的剧种吧。
弦:折子戏也有。折子的意思就是“幕”或者“段落”。河南梆子现在叫豫剧,代表河南的主要戏剧。豫剧现在是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一剧种当然是京剧。豫剧流传最广,观众也最多,河南相邻的省份,包括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山西都看得到。河南人到了外地,人口到了一定的数目就要组织个家乡戏的剧团唱戏。梆子响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豫剧团很多地方都有,还有新疆豫剧团,内蒙、山西、青海都有豫剧团,所以它变成一个大剧种。除了河南梆子外,还有曲子。曲子最早的源流可以远溯到宋代的词,本来是很文雅的,是厅堂里的知识分子才能听到的。到了民国初年,渐渐通俗化,小调出现了,才变成一个剧种,现在叫做曲剧,至少已经有一百年了,但它的调子则更加古老。大调中有很多曲牌,如“山坡羊”、“银纽丝”、“剪剪花”、“打枣杆”,宋元就有的,现在还活在曲剧里。
九:我生在安徽广德县,那里约有一半人口是清代从河南移民过去的。
弦:所以他们也唱河南梆子?
九:他们唱花鼓戏。您知道花鼓戏的渊源是什么吗?我只知道,它的腔调就是河南的腔调。
弦:河南现在还有花鼓戏,乡下人叫“打花鼓”。但是讲到花鼓戏,在河南不具代表性。花鼓戏流传很远。湖北也有花鼓戏,有的是“地蹦子”,就是说不上台的,就是背个包袱,敲敲锣,有个四五十个人看就开演。歌调为主,戏剧性不是很强。
九:安徽那边的花鼓戏似乎是五十年代之后,在大众文艺的旗帜下发展的,并给它注入一些情节。
弦:中国人很聪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古人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那样比较完整、系统性、文法性的记谱工具,所以咱中国的东西没有留下来很多。
九:记谱也有啊。
弦:就是工尺谱嘛。那就比较简陋,基本上是口传心授,师徒制,有时绝对到“传子不传女”,因为女儿出嫁后成了外人,所以失传的情形很严重。
九:另外古代中国没有交响乐,没有和弦的概念。
弦:中国人对乐工也不太尊重。像作《二泉映月》的阿炳,就是乞丐嘛。
九:属于“三教九流”里的九流之列。
弦:在西方,巴哈(巴赫)以后的西方,他们的音乐家地位多高啊。在宫廷里,连皇帝也要准时出席,不准时的话把琴盖一盖就走了,多厉害啊!我们没有这个情况。所以现在要想找中国音乐究竟在哪里,就要找老戏,还隐藏在老戏里面,像南管啊,北管啊,崑曲,特别是河南曲剧中的大调。
弦:我的幼年是生活在韵文的世界里。韵文对我们影响很大,后来写东西的时候,音乐性自然就带一点出来了。比老祖宗还差得远呢,但也带一点出来了。
九:关于诗歌的音乐性,我正好有个问题向您请教。音乐性当然可以在句尾押显韵,比较隐含的还有中间韵和头韵。但我觉得,汉语的音乐性和西方语言的音乐性应该有所区别。汉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四声,而四声的平衡在古典诗歌里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比如平仄对仗。那么您认为现代汉语在音乐性方面是否也要从汉语本身的特性出发来阐发呢?
弦:对。离开了音乐寻找意义的时候,意义就变得好简单,但是加了音乐之后就特别有意思。其实音乐本身就是内容,你要去找它的意义就很无聊。比如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就是有味道,就是好听嘛,改一点都不行。人们已经忘掉它的意义了,只是在音乐里陶醉。你不要说翻成英文,就是翻成白话都没有意思:“摆摆手再见吧,马就开始叫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诗经今译》的书,都看不下去。
九:比如高亨先生所著的《诗经今译》,我承认我就没有读完。很多时候想自己去翻译古诗,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没有意义。
弦:过去河南有很多长工不识字,但是会编这种顺口溜,称得上是不识字的诗人。比如我小时候有个磨面的老头儿,我们叫他二伯。河南管故事叫瞎话。孩子们都喜欢找二伯讲瞎话。他说一个,我们就很喜欢。还没等两分钟又想听:“二伯您再说一个吧。”二伯说:“二伯有点累了,让二伯吸袋烟。吸袋烟,把心宽,肚里的瞎话往外钻。”有时候二伯说瞎话嗓子说干了,想喝口茶再说,就说:“吸袋烟,喝口茶,肚子里的瞎话往外爬。”你说多好玩啊。他不识字,他就会编。所以我有一首写乞丐的诗里面也有“莲花那个落,小调那个唱。”也都把它录进去了。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不也是用西班牙的民谣风来写诗吗?我也想学他的办法,把我们的民谣写进诗里。
九:这就像柴可夫斯基一样,如果你不让他用俄罗斯民歌的曲调,他可能什么也写不出来。所以说,一个民族自己的声音,包括他的语言,才是最重要的。
弦:你喜欢音乐吗?
九:懂得不多,但我喜欢巴赫。
弦:巴哈?那个一般来讲有点昏昏欲睡的,很多人受不了,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花样。但是他的大提琴确实很好的。他那个时代不作兴浪漫,是很理性的。
九:我儿子现在就在学大提琴,当时就是我推荐的。他想学的时候,我在报名之前就先让他听巴赫的大提琴组曲。他听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感动。
弦:通常都会比较喜欢小提琴,因为小提琴比较浪漫,也比较浅一点;钢琴比较纯粹,比较理性。钢琴在气质上接近中晚年的味道,季节上讲就是秋冬的样子,而小提琴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是春。
九:有时候小提琴也会有秋的音色,比如巴赫写的几个帕提塔(Partitas),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伤感。
弦:有的人喜欢李白,到了晚年就开始改喜欢杜甫了。那个时候就进入大提琴的时间感、季节感了。
九:那您更喜欢哪一种?
弦:我喜欢大提琴,慢慢地,原来觉得受不了的,后来觉得那个时期的东西还是耐人咀嚼。
八、风云际会
九:(拿出一篇打印出来的网络文章)这是一篇关于创世纪诗社的文章。我读到的其他相关资料都说,创世纪是1954年(民国43年)创立的,但这一篇则指创世纪是民国41年,也就是1952年创立的,然后在1954年9月开始筹办诗刊,1954年10月正式创刊。
弦:这是哪里的资料?
九:这篇文章来自台湾,是大学课程的讲稿。
弦:民国41年创世纪就创立了,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民国43年,我在左营认识洛夫和张默,先认识洛夫,后认识张默,时间相差一个礼拜。我认识他们两个的时候,《创世纪》第一期创刊号已经出来了,所以我是那一年加入诗社。到了第二年出第二期,我就正式参加编务工作,也开始分摊印费,记得是每期新台币两百元,差不多是当时我官拜少尉一个月的薪水。出钱、出力、出作品的“诗的长征”就这么开始了。
九:这就是说,一些文章在史实方面也许有误。
弦:创世纪并非先成立诗社,后来才创办诗刊;诗社和诗刊事实上是一回事。创世纪不像纪弦先生领导的“现代派”,有社员制。创世纪不是派,只是一个同仁刊物的同仁小集,并没有所谓的“派性”。当然,办了半个多世纪了,团体意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弦:总之,说《创世纪》1952年成立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其实应该是1954年出第一期的时候,诗社也就成立了。《创世纪》诗社也就是因为刊物的出现而存在。不会有那么久的时间来筹备嘛。
九:是啊,一个诗社不大会成立了两年还没有刊物吧。
弦:不会。本来想给你看一本新出版的书,但最近修房子,家中太乱,这书堆在什么地方找不到了,我以后再给你看。最近《创世纪》出了个大画册,近千张照片,就是《创世纪》半个多世纪以来诗人的照片,一个图册的书。洛夫跟我各写一篇序言。改天我把那个序言影印出来寄给你看。
九:多谢!
弦: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军队里面。因为是军中的人嘛,政府不让你考一般的大学,只让考理工医三种科系。人文的,文学艺术的系所不让考。说喜欢文学艺术的,可以考我们自己特别办的学校,指的就是政工干校。政工干校这个名字常常给人一个印象,以为它是政治性的学校,其实它里面音乐系、美术系、新闻系、戏剧系,都很健全。学校也有很好的师资。当时有人问蒋经国为什么取一个政工干校的名字,不大好听呢,蒋经国说,我办政工干校就是培养军中干部。我不是训练一般的大学生,我是要干部。我想他是苏联那一套,坚决不改校名。其实干校(简称)的师资很好,请的教授都是一时之选的名家。但是后来因为受到校名的影响,很多人误会以为它是情报学校,不愿意提起。
弦:其实这个学校我是很感念的,因为有很多好的老师,我的知识启蒙都是在这个学校完成。我念的是影剧系,可以说名师如云,王绍清、李曼瑰、齐如山、俞大纲、张徹、崔小萍、姚一苇,都在系里开课。那么好师资的学校,叫作政工干校实在没有气势。有人对蒋经国说,你不是有个国防医学院吗?你把干校改称国防文化学院不是也很好吗?干校也有法律系啊,你叫国防文法学院也很好啊。为什么一定坚持这个名字呢?后来这个名字跟大陆的五七干校又搅在一起,就更不行了(笑)人们还误认为跟劳改营一样呢,产生了不必要的政治联想。我在干校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可是对我的启发很大。
弦:民国43年9月我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海军。洛夫是第一期毕业的,是我的学长,我是第二期毕业的。他分到海军去,我也分到海军去。第一期同学就在海军“四海一家”大礼堂开了一个欢迎我们的茶会。余兴节目中有一个人高唱《白云故乡》,嘹亮的男高音。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就是洛夫。开完会后他来找我。他说,你是不是痖弦,我说是。他说,我在校刊上看过你的诗,我说,我在校刊上也看过你的东西。
弦:接着他说,我们现在要搞一个新刊物,叫《创世纪》,创刊号已经出来了。他在杂志上签了名字,送给我一本。他邀我入伙,说:“你一定要参加我们,大家一起干。另外一位合作伙伴是张默,他也知道你,他会来找你。”就这样,先认识洛夫。一个礼拜以后,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快的张默就来了。
九:我读张默先生的文章,能感觉到他是一位温厚长者,说话想必是很慢的吧。
弦:不,一个混身是劲,行动带风的人。他是南京人,说话很快,做事敏捷,同仁们称他“创世纪的火车头”。没有他,我们的刊物办不到今天。创世纪这三个人中间,最快衰老的就是我。其实我最年轻,洛夫比我大四岁,张默比我大两岁。办刊物,是他最先提出的,加上也是行动派的洛夫,就动起来了。创世纪这三个字就是张默想出来的。
九:你们三人的组合互补性很强。
弦:彼此年龄虽然相近,但大几岁在认识上就差得很远,大几岁感觉就大很多了。所以洛夫、张默跟我在一起,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增进。开始的时候,我不会写文章,而洛夫一开始就很会写文章。所以,我跟张默两个编《六十年代诗选》的时候,那个序言我们就是写不出来,后来还是请洛夫写好,置于卷首,这才像一本正式的书。我们三个人中,洛夫的文字组织能力特别强。
九:作为台湾诗歌的两个代表性人物,您与洛夫先生之间的共同点和相异点是什么?
弦:我们两个性格不太一样。洛夫比较刚,刚性的。当然他到晚年比较温柔,跟禅有关系。他年轻的时候很刚,很刚毅的一个人。他后来得到心灵的疏解,跟他神往禅宗有关。你看他《石室之死亡》的阶段,他是那么暴烈、紧张。
九: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习禅的?
弦:最近二十年吧。
九:你们二人的共同点呢?
弦:我们两个是同学,分发海军又在一起工作,是同事。两个人关系密切,就像高更跟梵谷(梵高)住在一个屋子里。你知道美术史上,高更跟梵谷住在同一个屋子里。他们两个人在飚画,我和洛夫两个在飚诗。他写一首,我也写一首。文人之间彼此的那种惺惺相惜,以及轻微的嫉妒的那种感觉……(说到这里我们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
弦:那种复杂的感觉啊,真是难以理清,就像高更要到海外去,而梵谷要去日光浴,要到一个把脑浆都要晒枯、都要晒沸腾的地方去。他们两个人散伙了,但我跟洛夫两个人在一起就很久,同在左营广播电台当编辑,住在一个宿舍里面,工作也在一起,彼此的影响是有的。但是因为个性的不同,所以走的是不一样的两条路。可是他成就比我大,因为他后来写了好多东西。
九:您过谦了。除了作品的数量外,我也信奉绝对海拔的概念。有一次我去雪楼,曾就台湾诗歌请教过洛夫先生,他提到过三个名字,一个是您,一个是商禽,另外一个我没听清楚。他对你们三位非常推崇。
弦:洛夫后来在炼字炼句这方面的功夫实在要得。我跟他开完笑说:“你成精了!”像他写的隐题诗,就是典范。
九:还有《漂木》。
弦:他的《漂木》当然是重量级的东西。而他独创的新诗的隐题形式,也发挥到淋漓尽致。随便的一句话,他就代入隐题诗。有时碰到一个字,根本没有诗意的字,他硬要用下来,而且用得天衣无缝。你说这个功夫有多大啊。他自己总是要搞来一句话来难自己,给自己出难题。那里面有游戏的成份,但是他把它弄得很有深度。这你不能不服气。
九:我曾请教洛夫先生,写作方面他最注重那些因素。他列举了一些,其中第一个就是意象的营造。我想您也一定同意这个说法。
弦:我们那个时代就是重意象。你知道,影响这个东西,它半知半解的时候影响最大,全知全解的时候影响很小。全知全解是学术研究,半知半解就是文学影响。重意象,几乎是我们那个时代共同的诗艺训练,其影响多半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品。其实中国古典诗人也都是经营意象的高手,不过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要向老祖宗(诗的列祖列宗)学习。这是受了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影响,一股脑儿向西走,成为那个时代的局限。
九:非常赞同。
弦: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懂什么超现实主义啊?我们不过读了几本沙特(萨特)的书,读一点加缪的小说,像《异乡人》,就燃烧起来了。典型的半知半解。我们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懂法文的。商禽靠收音机学的一点法文,还是后来的事。
九:萨特的作品您读过哪些?
弦:加上这几年的涉猎,差不多有中译本的都读过了。
九:当时已经有哪些译介过来了?我是说五六十年代。比如,《存在与虚无》有中译本吗?
弦:记得当时已经有很好的译本了。
九:您在《深渊》里引用的一句题记,是不是在《存在与虚无》里面?我曾经找过这句话,结果在大陆的三联版中译本里没有找到直接与之对应的话。
弦:当时是从我的读书札记中引出来的,忘记是谁译的。
九:跟它较接近的话也许是在该书的第一卷第二章里面。
弦:各种译法可能会有出入,不容易查考了。思想和语气是萨特的。
九:在您的诗里还有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技巧,比如当你说“床单向南”时,就我的理解,您其实是说凌乱下垂的床单。上北下南嘛。
弦:那时候正是一个求偶的年龄,青春期嘛。对于女性和性有很多的想象,很多发狂的想法。那时候我跟一个画家在一起。他是我中学的同学,一位画家,也是五月画会的中坚份子。我们两个是同学又是同乡,长期地住在一起。当时我还没有接近音乐,最早接近的是绘画。所以绘画的技法也在诗里做实验。
九:绘画的技法,您指的是?
弦:比如说现代画里面有很多技法,线条的游走跟光色的游戏,用文字来表现出来。我曾为马蒂斯写了一首长诗,尝试把绘画意象转化成文字意象,并找出两者的灰色地带,发现彼此渗透的可能。
弦:影响有时就像着了火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像我有一首诗,我认为它是失败的,是典型的“误认为”。
九:您指的是《致马蒂斯》吗?
弦:我误认为,超现实主义就是那么干的。
九:我不觉得这首诗是失败的,我觉得它其实是相当好的。
弦:哦,你喜欢它?
九:对,我挺喜欢这首诗。
弦:那一首诗是我对马蒂斯的抽象画作意象的延伸。那首诗谈的人比较少。我自己表示不满意,所以研究的人也比较少。其实那首诗是真正是中了超现实主义的邪(大笑)以后,做的实验。
九:那首诗在语言方面相当成功,所以我读了以后,一点没有觉得它像您自谦的那样“是一首失败的作品。”
弦:我们中了超现实主义的邪。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说法:洛夫的说法是他主张“中国的超现实主义”,我则说是“制约的超现实主义”。把超现实主义的想法当作一个技巧,当作技巧之一,是好的,但作为唯一技巧则是一条死路。
九、批评与影响
九:您本人对其他诗人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一些更早的诗人,国外的、身边的诗人对您也有影响。在这两个影响之间,您是怎样找到平衡的?我想,通过了解您所曾经读过的作品和理论,再结合您今天讲的这些,就可以基本上廓清您的诗歌理念。
弦:《诗人手札》是一部份,即将出版的《记哈客诗想》也是一部份,整套的、系统性的理论是没有。还有一些借题发挥的序跋《聚繖花序》(上下二册,四十万字),再就是那些未加整理的札记和手抄本了。我不是诗论家,写点诗话而已。
九:读书札记甚至手抄本也都很有价值。
弦:在我论无名氏的小说的文章里可能提到过。
弦:上次我给你的那些资料里面有没有一些影印的东西?
九:有,这些都是。我把它们都带来了。还缺几篇。
弦:啊,《诗人与语言》,现在这个不容易找到了,我再找找看。
九:这篇对研究您诗学方面的思考非常重要。
弦:不过,类似的话我在《诗人手札》里也有一点。
九:这一篇是在手札之前写的还是在它后面写的?
弦:在后面,是稍后的一个独立的一篇,但不是很长。
九:那手札应该是最早的。
弦:对对。其实我很想写一本诗话,就像《夜读杂抄》那样的,比较集中,语录式的,每句话都像一个结论那样。但我发觉很难。
九:那种形式也很好。
弦:但是很不容易写。你看戴望舒啊,弄来弄去,他在诗论方面据我所知就是一篇短文而已。你有没有找到戴望舒论诗的文章啊?他有创作,有翻译,但是论诗的文章不多。很难写,我必须说很难写。
九: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的思维很有系统性,一写出来就是一篇文章。而另外一些人很有创意,但他们的思想结构是跳跃性的。
弦:我们都没有办法整本大套地写文章,都是些诗话,吉光片羽。可是别小看吉光片羽,有时候一两句话能让学者写一篇大论文,甚至一本书。
九:我读过刘绍铭先生的《望湖书简》。他对您的诗有许多真知灼见。他提出的有些问题,我也想再请教您一遍。他曾问过,自从您写《手札》和《现代诗的省思》,到目前已有二三十年了。在这个历史跨度下,您对诗歌的基本看法有哪些延伸?有可能您现在已经不同意您30年前说的话了。
弦:没有创作实践,说不上来。因为诗不写的话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现在让我写诗的话,我也不可能根据我的理论来写。理论是自己希望变成的那个样子,能不能变成那个样子就难说了。所以,好的评论就是诗人所写的有启发性的意见,照那样写的话可能发展更大。所以诗人要谦虚地读理论,或者读评论自己的东西,这很重要。有时候其实你没有做到,但它给你引导到了。它给你说的比你原来说的更好,那就给你很大的启示。如果你那样做,会发展更大,可是统统要通过创作实践才能做得到。
九:(点头)这个看法很好。所以您说过:“诗歌评论是与创作价值等同的一种创造。”及时而中肯的创作评论对于一个人的后续写作很重要。
弦:像王尔德常常对评论家进行嘲弄。他说评论家其实就是创作失败的人,一阵阵的狗吠而已。我想,没有一个作家不受评论的影响。虽然嘴巴很硬,但偷偷地在看,悄悄地都作了修正。评论很重要。
九:我还想听听您对语言张力的理解。
弦:我的理解是,张力其实就是中国诗歌所说的诗眼。有各种小诗眼、主要的诗眼、次要的诗眼,弄到最后成了一个大诗眼的时候,高潮就出现了。诗还是要有高潮的。诗不像小说那样必须有高潮,但诗也类似高潮的设计。散文对诗还是很有用的,因为散文可以纾解诗的过分的张力,过度的紧张。散文可以让诗的紧张情绪得到调节。
九:也就是说,诗应该有张有弛。
弦:像你的诗的好处就是,你用散文语言,但有时候,比如你说祖父“用胡子在等待”。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你说“用胡子来等待”,这就不一样了。你很善用这种方法,这是很好的。
九:谢谢。
弦:所以,当用胡子来等待的时候,语言是散文,但其实已经不是散文了。因为诗眼已经出现了。有时候,你故意让有句话你好像不在留意,其实那一句话是为了高度的——
九:铺垫。
弦:铺垫,在等待另一句话的出现。如果每一句都是高潮的话,那就令人疲倦、甚至生厌了。
九:对。实际上您对张力的理解就是有铺垫的,或者说亦张亦弛的,而不是一以贯之的紧张。
弦:一贯的紧张不行。你看西方悲剧里面都会设计一些喜感的人物,来松弛观众过分紧张的情绪,使在虚实之间所有配置,在虚实、疏密、轻重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每一句都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那是错的。年轻人难免喜欢炫才,后来会觉得这个办法是不对的。你看洛夫在《石室之死亡》时期里面有密集的意象,等到他的《外外集》、《西贡诗抄》出现的时候,他就改变作风了。他就知道,原来松弛的设计也是必要的。他后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像我写的那个《一般之歌》,已经知道怎样来用松弛的办法把沉重的思想含量借助于散文表现出来,我发觉仍然用《深渊》的办法是不行的。
九:您这个观念是什么时候成型的?
弦:我大概在写《如歌的行板》、《一般之歌》、《复活节》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比如说《复活节》里,我说一个女人在街上走。好像九月以后她不太高兴的样子。她战前曾经爱过一个人,其他的我们对她都不太熟悉。而她现在正在街上走,走过一个牙膏的广告牌。然后走啊,走,然后走过去了,就算了。就写现代人那种失去面貌的感觉。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她战前爱过一个人,是因为月光的关系,还是因为什么,因为那天晚上的月亮或者琴声?不知道。后来她就是一个人。而她现在在街上走。那种快进的手法。那时候就知道,有时候用散文也可以营造一种张力,一种更大的想象的可能。
九:我有一个朋友是基督教画家,他的每一张画里面都看不清基督的面孔。
弦:噢?
九:我一直很好奇,上次见到他就追问,为什么要这样画,因为所有人的画都有一个清晰的面孔,为什么他的画里面,基督只是一些色块呢?他给我翻出来一本很旧的笔记本,指着上面剪贴的彩页说,他的灵感来自于中国古瓷,其中一些瓷器上的彩绘就是一些色块。这些色块“可以相互入侵,却没有明显的线条和轮廓”。正是这样一些相互入侵的色块给人以最大的想象。他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形象交给了看这幅画的人,让他们自己去完成,就像您诗中妇人的形象,是读者和您一起完成的。
弦:嗯,嗯嗯。
十、怀人
九:您在政工干校、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还有威斯康辛大学——
弦:后来我们都叫干校为复兴岗学院,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学院。复兴岗是干校的所在地,创办者给它取了个不好听的名字。我爱我的母校,把她的名字给改了。
九:我的问题是,在这些院校里,您学的哪些课程对您的创作和后面的诗学研究最有帮助?
弦:我想是周策纵先生为我们那一班同学开的《治学方法》。他已经过世了。他是《五四运动史》的作者。周策纵常有很特别的想法,我不理解他。他希望把现代诗定型化,鼓励大家创作“定型词”,像古人把词用曲牌定型一样。方法是分析哪几个句子是悲哀的,哪几个调子放在一起是乐观的。对于他的提倡,响应的人很少。他老先生还写了很多定型诗作为示范,在我看来是失败的。但他常常有些想法很精彩。他认为,真正伟大的东西是晦涩的。你说狮身人面兽算不算晦涩?非常晦涩,都不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因为本身就不清楚。周策纵先生的哲学体会对我有很大的启示。
九:因此对您而言,探索诗歌的晦涩领域并不是一种负担;您觉得这是必要的、应该的。
弦:对,这是应该的,因为人生本身就有很多灰色地带。你也说不清楚它,你就要去试探它。有时候很简单,虽然说简单,但简单的背后还是晦涩的。周策纵先生,以他的年龄以及他所受的训练,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九:周先生是您在复兴岗的老师吗?
弦:不,是在威斯康辛。我在复兴岗的时候,受到李曼瑰先生全套的莎士比亚的通读、赏析。我们读得很熟。她是一个历史剧编剧人、戏剧运动者、教育家,是我们的系主任。
九:应该是个女性吧。全套的莎士比亚。
弦:是位女性,一生未结婚,专心从事戏剧,把学生当儿子、女儿看。上她的课大家小心翼翼,笔记抄到手酸。她教得认真,我们听得认真,一个学年,把莎翁啃了下去。还有俞大纲先生,他教我们对传统戏曲的认识。李是西方的,俞是东方的、中国的。大纲先生是徐志摩的学生,少数到台湾的新月派的人。作品不多,述而不作,但是对年轻人的启发很大。他有一个好像马拉美的火曜日聚会那样的聚会,就在他的办公室。他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德高望重,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把他的办公室当文学讲堂了。我、林怀民、吴美云、郭小庄、楚戈等一大票文学艺术青年都到他那边去,座无虚席。他文化、文学、戏剧、人生无所不谈,天马行空。俞老也在我们学校教书,教《中国戏剧史》。他对我启发非常大。他自己也是京剧的编剧,辞章一流。写旧体诗,也写新诗。他跟周策纵先生很像,两位先生新旧都能,考据、义理、辞章,纵横古今,也写新诗。周先生是纽约白马社的社员。白马社是华人诗人在一起组成的一个诗社,胡适先生是该社的支持者,俞老则属新月社。
弦:老一辈的诗人你认识哪些?
九:我认识的老一辈诗人非常少,但认识不少中青年诗人。能认识您和洛夫老师真是一个莫大的幸运。我跟另一位前辈诗人也有交往,就是武汉大学的叶汝琏教授,法语名字叫Julien Yeh。
弦:人还在吗?
九:前年去世了。叶先生是研究法语文学的,他是中法大学毕业的。他在抗战时期就开始写诗,翻译过很多超现实主义诗歌,以及与超现实主义很接近的圣-琼·佩斯的诗歌。他译得很多也很好。我曾在网络论坛上提到过他的翻译工作,后来他的一个忘年交的小朋友胥弋看到了,就转告了他。我们就这样开始通信了,但很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弦:当时的知识分子到西方去,像梁宗岱、盛成他们,都去见当时西方的作家、学人,而不再去念学位,认为学位并不重要,问学、接近大师才重要。他们到处搜集资料进行研究、做专访、翻译、介绍,然后回国。现在这个工作做得不够积极。
九:那一批人特别刻苦。比如盛成是读桑蚕学的。他在法国呆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还用法语写了一本书《我的母亲》,瓦雷里(梵乐希)给他做的序。我读过这本书的英文版,瓦雷里在序言里还特别提到他“有足够的勇气用法文写这本书,”并且很受感动。
弦:他到台湾来了,来的时间比较早。他是我们文艺函授学院的老师,我读函校发给同学的他的讲义,但没有见过面。
九:我就是因为在您的书里面看到盛成先生的名字才说他的。我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1996年左右。他后来是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
弦:他也译了很多。他还写了一个小说叫《巴黎的回忆》。他跟人交往不多;他是一个隐士。
九:在留法的那些人中,我最喜欢戴望舒的翻译。他的散文和诗歌翻译得都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