瘐死狱中的卖国巨奸周佛海
2014-06-20孟昭庚
孟昭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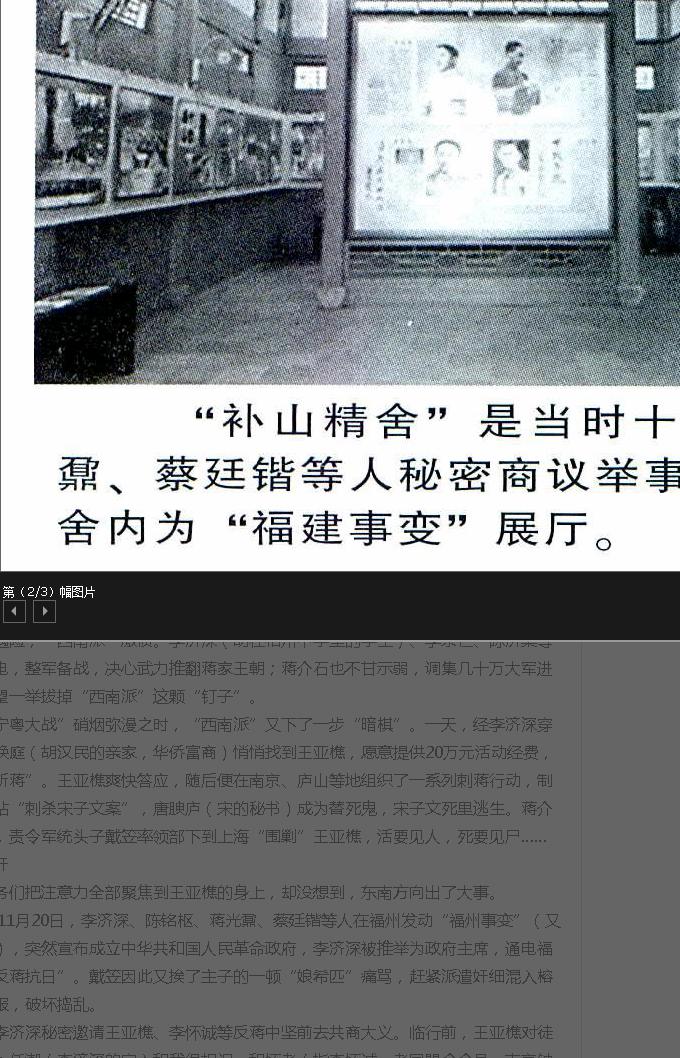
一
1897年,周佛海生于湖南沅水之侧的沅陵东乡杨树井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小名福海。父亲早亡,靠寡母含辛茹苦地将其养育成人。自小慨叹家道中落,时运不济。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不安分的青年”。
“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处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这几句诗,就是后来成为卖国巨奸周佛海当时为求日后出人头地的“抒怀言志”。在以《论抱负》为题的作文中,他写道:“若吾能当上内阁总理,也不枉度此一生而光耀祖宗矣!”后来,这个一文不名的破落户子弟在好友邬诗斋全力赞助下才得以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经过短期补习日语,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留学的待遇。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一年之后,预科毕业,被分配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继续学习。在功课之余,他专门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将其翻译的《社会主义概论》一书,寄往上海中华书店出版。他写了多篇介绍马列学说的文章,在上海张东荪主编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1920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回沅陵省母期间,在上海由神交已久的张东荪介绍结识了陈独秀,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他跟也是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留日学生施存统在日本组成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只有两名成员。
1921年7月,周佛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留学生中的代表,从日本鹿儿岛登上海轮前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跟毛泽东一道,担任大会记录。中共“一大”选举中共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他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陈独秀没有返沪之前,中央局书记一职暂由留在上海的周佛海代理。
周佛海回到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学。由于他参加了中共“一大”,被日本警方侦知而受到警方的注意,担任他导师的日籍教授便向他发出了警告,于是周佛海只得收敛言行,“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
1923年夏,周佛海从帝国大学毕业。这时,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次年4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部长的戴季陶写信给远在日本的周佛海,约他回国一起工作。正在为毕业找工作而发愁的周佛海,接到信后,大喜过望,带着妻儿,马上来到了广州。
4年前,周佛海曾读过戴季陶的几篇文章,曾写信对戴大加吹捧,内有句云:“先生的文章字字玑珠,掷地有声,名副其实传世杰作,使我油然而生景仰之情。”戴阅信后大喜,遂将其引为知己之友,二人曾一起进出渔阳里二号陈独秀住宅,高谈阔论共产主义。
戴季陶把周佛海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当秘书,主管宣传部日常工作,每月薪水为200块大洋。这么高的薪金,是周佛海没有料到的。没过多久,戴季陶又推荐周佛海当上了广东大学经济系的兼职教授,月薪240块大洋。
周佛海从一名穷学生,一下子成为国民党的官员、教授,欣喜之余,对戴季陶更加感激涕零。然而,他却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在社会上兼职的共产党员,必须要把其中一部分薪水拿来交党费,用于解决党开展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周佛海是个很小气的人,要他把已进入他口袋里的白花花的大洋拿出来交党费,他的确舍不得,便萌生了跟共产党一刀两断的念头。
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周佛海看准了国民党,以为在国民党里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周佛海开始拒绝参加党的活动,还常常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1924年9月,周佛海终于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广州区执委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曾亲自登门劝说周佛海,但周佛海却无动于衷。
中共中央知道周佛海已无可救药,便同意了周佛海离党的要求。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便很快投入到了国民党的怀抱,追随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亦步亦趋迅速转向反共。他摇动笔杆子,进行反共宣传,公开宣称:“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诚党员,挞伐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一刻也松懈不得”,发誓“与中共势不两立”。
二
1926年9月,北伐大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笔者注:前身即为黄埔军校)在武汉成立,蒋介石兼任校长,因蒋不在武汉,便由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任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佩少将军衔。从此,周佛海便开始在国民党内走红。
转眼到了1927年春。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上海街头腥风血雨,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和迫害。
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4月18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在南京另成立国民政府,同以汪精卫为首的、还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周佛海对汪精卫的“反蒋”做法表示不满,遂向中央军校提出辞呈,辞去了秘书长与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当时,武汉的革命气氛高涨,周佛海决定出逃南京,追随蒋介石而去。途中写了《逃出赤都武汉》一文,大骂共产党,并以此向蒋介石表忠心。
周佛海到了南京后,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大肆攻击武汉汪精卫政府,大骂汪精卫不是个东西。然而,就在周佛海大骂汪精卫之后没过多久,中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7月,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分共清党”,宁汉合流,汪蒋走到了一起。
1932年,蒋介石、汪精卫进行再度合作。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管军事;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务。为了进一步巴结蒋介石,周佛海赶写了《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一书,为蒋独揽党政军大权制造理论根据,蒋大为青睐,将此书定为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必读课本。投桃报李,蒋介石委任周佛海种种要职: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政训处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周佛海还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周佛海过去曾与汪精卫打过嘴巴官司,辱骂过汪精卫,现在却要在汪精卫领导下工作,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他又主动伺机接近汪精卫,处处讨好汪精卫,两人的联系也就慢慢多了起来。
三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遇刺出国治疗。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汪精卫闻讯匆匆回国。国民党中央派出周佛海到香港迎接汪精卫夫妇。
1937年1月12日上午,汪精卫乘坐“波茨坦”号邮轮抵达香港,周佛海带着一帮国民党的官员到码头迎候,气氛十分热烈。当天下午,邮轮启航前往上海。周佛海上船陪同汪精卫继续前行。以此作为契机,两人就国内的形势敞开心扉,交换看法。
此时,西安事变在共产党人的调停下已经和平解决,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终于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对周佛海说:“张学良一定是被共产党利用了。如果蒋先生答应抗日,共产党势必会乘机坐大,将来的局势将会很不好收拾啊。”
“是啊,日本人并没有吞并中国的意思,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头之患。现在,我们不去打共产党,而去惹日本人,那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周佛海恨恨地说。在反对抗日,主张“剿共”的态度上,周佛海与汪精卫臭味相投,在政治上的结合又深入了一步。
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7月7日挑起了卢沟桥事变,紧接着于8月又进攻上海。周佛海在此期间,力求避战求和,与高宗武、陶希圣一伙精心策划,并竭力鼓动汪精卫说服蒋介石停战议和,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准备外交接洽”。
不仅如此,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研究)组长的周佛海,在全国军民全面奋起抗战之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组织反对抗战团体,即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地址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公馆,其成员文武兼备,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等,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等,每天必到的则是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上述人士经常的一个话题就是,“主张在相当时期,结束中日事变”,也就是不放弃任何对日本求和的机遇。
如果说,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主人的话,那么汪精卫实质上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关于这一点,周佛海曾有所说明:因为“汪先生(汪精卫)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我们当时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后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运动。周佛海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如果不借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声望,不以汪为中心,他们将一事无成。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周佛海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在这之后,周佛海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往来于上海、香港之间,与日本人秘密接触,协商和谈条件。后来,在汪精卫的指派下,梅思平也投入到这一活动中。经过接触与谈判,梅思平与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人密签了《重光堂协议》。
紧接着,周佛海与汪精卫一起,策划了叛逃的阴谋。12月5日,周佛海按预定计划,由重庆飞往昆明打前站。在此之前,他已将妻儿安排去了香港。
1938年12月18日上午,汪精卫夫妇仓皇离开重庆,飞到昆明。周佛海登上飞机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降日。
1939年7月,重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周佛海的党籍;8月,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
四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在汪伪政权中,除汪精卫外,周佛海是最有实权的人物。周虽任行政院副院长,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职位不如陈公博,但实权却不在陈之下。他不仅身兼财政部长,掌握财政经济大权,而且还兼警政部长,直接掌握着汪伪政权的特务、警察机构。
周佛海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积极参与汪逆勾结日寇,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活动也多由他负责,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周佛海不仅深得汪精卫的信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宠信,日本天皇授予周佛海一等旭日大绶章。
周佛海手中还掌握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税警总团,多次与新四军作战,镇压当地的抗日运动。此时的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身兼数职,踌躇满志,好不得意。他在1940年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周佛海此人精于政治投机。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他已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担任要职,但他还想脚踩两条船,随时做向重庆投诚的准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接下来,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逐渐发生变化。
周佛海曾私下对人说,他有两个没有预料到:一个是万万没料到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会停止进攻;二是万万没料到日本会向英美开战。
周佛海为人奸狡滑头,最能看风使舵。眼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他决定向重庆靠拢。即使决定向重庆靠拢,他也是走一步瞧一步。
1944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周佛海便无所顾忌地暗中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病逝。汪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伪行政院院长便由周佛海接任。作为伪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周佛海先是给戴笠写信,表示要将功赎罪,为军统效力。接着又派人秘密到重庆,向蒋介石“自首”,说他当初逃离重庆时,未向蒋请示是受了汪精卫的欺骗,是对蒋的背叛,为此心中时常不安,请蒋宽大为怀,他愿粉身碎骨,报效党国,效忠蒋介石。
新四军在华东的发展壮大,正使蒋介石感到头疼,看到周佛海的自首信后,他喜上眉梢,马上打电话把戴笠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周佛海现在向我们自首,我准备接受他的自首,要他戴罪立功。我想,命令周佛海利用一切机会遏制新四军的发展,同时抢占东南沿海地区,为日军投降接收做准备。你看怎么样?”
戴笠马上回答说:“委员长英明,我立即命令上海的工作人员向周佛海交待任务。”
此后,周佛海就按照重庆方面的命令,开始大肆破坏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组织伪军,进攻我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对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在陈公博宣布南京伪国民政府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便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搭档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果然,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国民党对上海的接收。蒋还通过戴笠命令周佛海指挥上海、杭州一带的伪军“维持治安”,全力阻止新四军收复失地。
接到戴笠电令后,周佛海开始神气起来,先是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接着又以上海市行动总队的名义发布布告。周佛海还致电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中央,绝不让其落入共产党之手”。一夜之间,周佛海摇身一变,由卖国权奸变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为“保卫大上海”,为蒋介石重返江浙作出贡献。
不过,周佛海自以为得计,高兴得太早了,他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抗战胜利后,国民要求惩办汉奸的怒潮席卷全国。周佛海投敌当汉奸那是不争的事实,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包庇、重用汉奸的做法表示抗议,要求严惩大汉奸周佛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推波助澜,纷纷上书蒋介石,要求对周佛海等卖国巨奸严惩不贷。
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周佛海的处置,乃由军统局局长戴笠“邀赴重庆暂避风头”。
1945年9月30日晨,戴笠的专用飞机从上海江湾军用机场秘密起飞,机上坐着才当了40天“行动总队总队长”的周佛海,还有丁默邨、罗君强等大汉奸,戴笠随机陪同。
中午11时半左右,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随后,周佛海等人被秘密安排住进了白公馆。从此,周佛海便被软禁在白公馆,之后又被转移到当年美军顾问梅乐斯的寓所。
是时,周佛海亦曾以亲笔悔罪书托人呈送蒋介石,言道:“此次回渝,似堕落子弟回家,实无颜以见家长,辱承钧座宽大为怀,特予爱护,虽粉身碎骨,亦无以报宏恩于万一。”在悔罪书中,周并恳求,如果当局爱惜,不加诛戮,他当长期幽居深山密谷,将八年亲身经历形诸笔墨,以警戒后人。蒋介石当时虽无明确表示,但周佛海自以为有功于政府,又因为戴笠曾向自己允诺过,一定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周佛海一直把戴笠当作自己的保护人,心想只要有他在蒋面前斡旋,老蒋对自己是不会怎么样的。
哪知此后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命归黄泉,周佛海的美梦便化为泡影。
六
再说国民党的“肃奸”活动,忙碌了半年,到了第二年夏天,便鸦雀无声了,大汉奸周佛海等仍逍遥法外。其时,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各文化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姑息养奸的行为。如上海《文汇报》便曾刊登《周佛海怎么样了》的“读者投书”,指出:“试问罪大恶极如周佛海者,为什么至今没有发落?而且像他那样的人,难道真的还要调查犯罪证据?……如果周佛海不立即明正典刑,那么中国根本无汉奸,中国根本无叛逆,我们要为‘沦陷区同胞大哭。”
蒋介石虽然有意袒护周佛海,但他也知道,这种做法,理亏在己,再这样下去,无法向民众交待。慑于舆论压力,蒋介石经一番踌躇之后,终于下令军统局将周佛海等逮捕,送交南京高等法院审理。
1946年9月16日,在陈公博被枪决3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派专机将周佛海、丁默邨等人由重庆押送来南京,羁押在宁海路23号军统局看守所。
1946年9月20日开始,最高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了审讯,周佛海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
10月7日,最高法院在南京夫子庙举行“盛况空前而诡谲多变”的开庭,审理周佛海。最高法院院长金世鼎和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亲自审理周案。
周佛海请了3位在当时很有名的大律师为其辩护。法庭上,周对自己策划投敌的阴谋活动矢口否认,不认为自己在汪伪政府任职,是卖国的汉奸行为;对其在汪伪政府中的活动,也是轻描淡写,遮遮掩掩。而对自己如何找老蒋“自首”,如何效命重庆,却不厌其烦,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还拿出戴笠写给他的亲笔信为据,表明自己是为重庆做事的。
蒋介石最怕别人指责他在抗战时期与汉奸暗中往来,周的所作所为,正好犯了蒋的忌讳。
11月7日,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判决,提出抗告,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最高法院驳回抗告,核准原判。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再一次呈请高院再审,经审判长、推事商裁,又一次驳回了杨要求再审的申请。
此际,周佛海及其妻杨淑慧始发觉事态严重乃紧急采取两项措施应急:一、急请名律师戴修缵及杨嘉麟写好向最高法院申请覆判诉状,以周妻名义立即呈递,除提具周某迭向“国府”请准“自首”之证据外,并历述其秘密供应“国府”情报及协助“国军”之事实,要求覆判。二、周妻为救夫心切,病急乱投医,经人介绍,与一保密机关长官内眷见面,并送去大条黄金150条,言明钱到刑除。
不料公私双管齐下的结果依然无济于事,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于1947年1月20日宣示的判决书中,依然核准了原判的死刑。另一方面,周妻私下图以买命的1500两黄金,更是被人讹诈,毫无效用。
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已进行完毕,周佛海要想活命,只有蒋介石的“特赦令”才能救他。
这幕闹剧演至翌年2月23日,蒋介石致电司法部,命令对周佛海进行特赦改判。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1947年3月27日,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在老虎桥监狱。
周佛海死里逃生,不禁感慨万千。在狱中,他赋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
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
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
慷慨襟情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
留将负重度崎岖。
从这首诗里,我们不难看出,周虽然被改判无期徒刑,但心仍不死,希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继续为蒋介石卖命。
关于周佛海最终能获得蒋介石的“特赦令”,历来有3种说法:
一说,陈布雷是周佛海的旧友,杨淑慧找到陈布雷,请陈设法安排她径自拜谒蒋介石,哀恳蒋氏以国家元首身份使用约法(当时的“宪法”)赋予的特权,对周加以“特赦”或减刑。陈布雷一生虽行事守分守法,可是他看重旧情,对当年相交至深、朝夕相处的首席助手周佛海,无论如何不能置身事外,见死不救,乃乘蒋介石在召见他时,破例向蒋请求。而蒋念及周佛海当年扈从之勤,与战后助守京沪之功,也不能全然无动于衷。于是在陈布雷安排下,于1947年2月某日,周妻乃得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陪同,前往南京黄埔路官邸晋谒蒋介石。杨淑慧一见到蒋介石,就长跪在地,抽泣不止,一句话也不说。蒋介石皱着眉头,看着跪在地上的杨淑慧,思索良久,便以低缓的语调对杨说:“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杨得到蒋的许诺,趴在地上又磕了3个挚诚的感激的头,含着眼泪随毛人凤出了官邸。
二说,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帮的大忙。陈果夫、陈立夫与周佛海都是旧日的同事和朋友,私交笃厚。二陈找到蒋介石,以周佛海抗战胜利前后,能按政府计划暗中布置军事,使“国府”得以完璧收回上海,顺利还都,不无微功,请蒋准予减刑或缓刑,蒋被二陈说动了。
还有一种说法:周妻杨淑慧放出风声,态度强硬,称:“如老蒋出尔反尔,执意要判佛海死刑,我就叫他声名狼藉!抗战期间,委员长曾给过佛海几次手谕,我都拍成了照片,存放在香港一家外国银行保险箱内。如佛海被执行死刑,我就将它在报章上公布,让天下人看看,自诩为抗战领袖的蒋某人是如何勾结汉奸的!”
蒋闻知,为不使自己“领袖人格”受损,便下了对周死刑改判的“特赦令”。
七
周佛海得知自己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之后,才略微喘了一口气,心脏病却复发且日益严重,后来引起多种并发症。因在狱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照顾,周佛海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情绪也一天比一天坏。
杨淑慧为了让周佛海保外就医,曾请大律师章士钊给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写信,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周佛海保外就医?谢冠生看过章士钊的信,断然拒绝道:“我这个司法部长是有权批准犯人保外就医,但周佛海这个案子太特殊,我没有这个胆子。”
周佛海的病情日益严重,杨淑慧请求监狱长改善周在监狱内的生活条件。经杨淑慧再三请求,监狱长同意撤去了看守监视,由杨淑慧在外面雇请护理人员进来,进行24小时看护。
这时,周佛海已病入膏肓,全身肌肉销尽,形销骨立。
周佛海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将近一年。他在死前一两个月不能睡、不能坐,只好将被褥高高叠起,伏在上面日夜喘息、呻吟,特别是最后38天,更是不断惨呼嚎叫,痛苦万状。有人说这就是天谴,活着比绑赴法场一枪毙命还要难过痛苦。
1948年2月28日,这天是正月初五,周佛海口鼻流血不止,一阵哀嚎过后,油尽灯灭,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反复无常的罪恶一生,时年51岁。周佛海死后,他的尸体停放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杨淑慧用她珍藏了多年的一口贵重的楠木棺材为周装殓。
1948年清明节,杨淑慧带着儿子周幼海等亲属和几名周佛海过去的贴身副官,将周佛海的棺木运到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方,找到了一个穴位,将周佛海草草地埋葬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