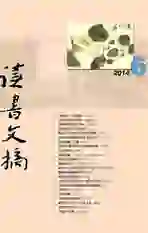我在宝古斋开展新画业务的趣闻
2014-06-10陈岩
“文化大革命”前,隶属宝古斋历代书画门市部的墨缘阁原本就经营新画业务。搞文物行业的人,历来不把新画业务当作主营,看不起搞新画业务的人,总觉得没本事的人才去干这些。从画家手里拿画,有的收购了,大部分只是替画家挂一挂,代销,卖出去了才结算画款。解放前这新画行当就不必说了,解放后,文物商店成立,也还是这么个状态,无论是多大的画家,其待遇也都是如此。
就拿傅抱石先生来讲吧,那是多大的名气呀,可是我给您说个故事,您别不信。
有一次,傅抱石先生给我们店的墨缘阁寄来一卷画。傅抱石是在我们能够收购范围内的画家,他寄画时,随画寄来一封信,大意是说:贵店如果能将这批画全部收下,就按9元一张,如果挑着要,那就12元一张。
您猜怎么着,当时主管业务的科长一看,气不打一处来,立即指示把画全部退回!不惯这毛病!这事儿可是真的,您别不信,类似的事情在我身上也发生过。
那是在1981年琉璃厂文化街重建的时候,我们店搬到了天坛公园,在天坛下面的活动房子里继续营业。有一天,我的徒弟高洪地从吴冠中先生那里拿来了几十张画,都是二尺多的斗方,收购价也就是每张三五十元。画儿很好,我一看,就问小高:“这些画儿怎么只盖了个图章没签名啊?”小高经我一问才注意到,真的没签名。存书画鉴定当中,“图章款”是有的,所谓“图章款”就是只盖图章没有签名,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不细说了。但无论从真假鉴定上,还是在价格上,有无签名,其相差都很远。图章,不是石头的就是金属的,百年、千年甚至几千年都能保存下来,人可不行。人没了,图章落到别人手里就可以随便盖,是不是这个理儿?经我给洪地这么一说,他连忙说:“那我找吴先生去,让他把名字签上。”说完就走了。
可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我问:“签好了?”洪地问答说:“没签”。“为什么?”我急着追问了一句。“他说这是他的习惯。”我一听就火了:“还有这习惯!将来谁负责他的真假,只盖了个‘荼字图章,连个名都没有,拿回去,不收!”
你看,我干的这事有多蠢,多少年后想起来都后悔,人家吴冠中先生就是不签名,后来不也是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一张的画都卖掉了吗?所以从那以后,我逐渐更深地懂得了如何尊重别人,尤其是这些艺术家,一个个脾气大得不得了。脾气,可能就是他们的个性吧!
这话儿扯远了,我就是想告诉您,新画业务在这之前,向来没值过钱,“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更别说了,画都不能画,要画就画工农兵,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反动。
以价格而论,那时的新画确实不值什么大钱,但有一点,因为我是从事文物行业的,从学徒开始就搞书画鉴定,鉴定的水平如何,咱们先放到一边,但历代书画家的画风、面貌,那是知道的,整天和这些作品打交道嘛。有了这一点,我就很清楚现在这些书画家的艺术价值在哪里,他们将有一个怎样的前程,我也心知肚明。
远的不说,近一百多年来,国画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虚谷、吴昌硕、赵之谦、任熊、任伯年,当然,不止这几位画家,他们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各有自己的风格。除任伯年画技中稍有西法外,大多数画家还是立足于本土,讲传统技法和国学功力,但任伯年将西法用于国画实则代表了一种方向。到了岭南派,这个方向就更加明确,再往后到了徐悲鸿时代,“洋为中用”的绘画技法已备受推崇。实事求是地讲,岭南派虽为中国画的发展开了先河,但从他们的作品看,仍免不了或多或少有些“东洋”味道。而徐悲鸿虽运用了西法,但仍然表现出中国画的宏大气象,很少“洋味”,用水用墨更加大胆、大块,但完全合乎素描关系,用线更加刚劲、准确而不失形体关系,此外,对宣纸、毛笔、水墨的运用都达到全新的高度和境界。那么,到了李可染、吴作人、黄胄、刘继卣、程十发等大师的时代,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后这一时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洗礼后,艺术家们大都还处在创作的顶峰时期,无论是画风还是技法,都自成一体,各有千秋。
我原先一直看黄胄先生画的驴很可爱,在单位、家里,也就学着画,但怎么也画不成、画不像。后来黄胄先生住院了,在友谊医院。我们那时还在天坛上班,友谊医院和天坛公园离得很近,我就几乎天天去医院陪他,这才发现,黄胄画驴,是利用生宣纸的特有效果——水痕来画结构的。这生宣纸,尤其是特净皮很奇怪,您前一笔的墨落在纸上以后,这块墨的四周就会出现一圈洇出来的水痕。好的生宣纸,讲究水跑墨不跑,洇出来的水痕干干净净,这样,您在画第二笔时,即便和前一笔的墨块重叠也不怕,第一笔留下的水痕就清清楚楚地留在了第一笔与第二笔中间。这样,一笔笔地画下去,画的结构前后非常清楚,只有下笔、用墨达到稳、准、狠,画出来的画才会非常干净利落、生动准确。
刚开始看黄胄画驴、画鸟、画鸡,我都看傻了。一笔下去驴的后胯出来了,再一笔下去,腿出来了,就像安装了一部机器那样准确,毫不迟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要比写字难多了,因为稍一迟疑,宣纸上就会出现一个再也抹不掉的水痕,也就是说,不该有的结构有了,不该断的结构断了。所以,在欣赏大写意的作品时,总能看到艺术家能用三笔的不画四笔,能用五笔的不画六笔,越简洁,越大气。俗语讲“大块文章”,国画讲“大块墨块”,这“大块墨块”只不过是非常难用罢了,没有深厚的功力,绝难做到。
当时这些最著名的一群艺术家、国画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处境不要说尊严,就连做人最起码的人格都得不到保证。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以及刚结束的那一时期,和这些艺术家相处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完全处于“人格恢复期”。有事实为证。那时候只要他认得你,只要你开口要画,他都会痛痛快快给你画,送不送礼物没关系,别提钱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瞧得起他,敢和他接触、交往。那时候我们店有一位同志向吴作人求了张画,先生竟用信封给他寄来。
再说稿酬,听了您会笑掉大牙,打死也不相信,那我也得告诉您:最高级别,每平方尺15元,以此类推,10元、7元、5元、3元不等。像李可染先生这样的大家每平方尺15元,黄胄先生7元。您若不信,我这儿还保留了当时的一份统计表,是1978年3月至10月份征集名画家作品的统计表,这统计表里共有当时的一流至三流画家63人,其中一流画家23人,在1978年半年之中收购、征集了473件,稿费共计19141元。不难看出,平均每件40元左右,具体的再给举个例——endprint
启 功 四十一件,叁佰贰拾捌元;
李可染 三件,陆佰伍拾元;
黄永玉 四件,玖佰元;
黄 胄 八十二件,叁仟捌佰玖拾元;
程十发 十八件,壹仟零捌拾元;
吴作人 七件,肆佰柒拾伍元;
李苦禅 五十件,壹仟柒佰元;
董寿平 四十五件,玖佰壹拾贰元;
白雪石 十六件,叁佰肆拾伍元;
亚 明 十一件,陆佰叁拾元;
范 曾 四十四件人物、鸡等,壹仟贰佰柒拾伍元;
范 曾 四十六件字条,贰佰陆拾元;
刘炳森 一百七十四件,伍佰贰拾元。
仅举以上例子,就能清楚当时的情况了。这可不是想揭谁的老底,这个标准还是比照国家出版物的稿酬标准定的,这也是画家们艰苦历程中的一段经历。回顾一下也好,要是比起来,总比一张画换一刀纸、半刀纸好多了,您说是不是?
文物商店名曰商店,其实在1978年北京市成立文物局以后,明确规定文物商店的性质是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因此,在做征集新画业务时,我们不管销售得多少、好坏,只要求认定画家本人,尤其是对著名老画家,他们的作品我们一律都当作半文物对待。
店里领导看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也就放手支持我们去开展业务,我这“画奴”也就好当了。为了搞好和画家的关系,除了征画以外,我们就尽量为画家家里多做些必要的工作。白天夜里、上班下班,能用上的时间都用上了,画家们不论是哪方面有了困难,我们都想尽办法帮他们解决。关良是上海的画家,一到冬天家里很冷,想生个煤炉,但是有炉子没烟筒,上海买不到,我们就专程从北京给他送过去。
有一点我常和朋友们说,在我和这些老画家们业务交往的过程中,二十多年,从画家家里拿走画儿,无论多少张,从没写过收条,画家们也从不让我写。当然,这不合乎手续,尤其在今天根本不可能,但当时,可是工作的一种境界,我常常引以为豪。
正当我和洪地师徒两人兴高采烈地工作着,突然有一天,文物局的文物处处长找上门来,他姓尤,小个子,长得好像很精明。
到了我办公室以后,他开门见山地就问:“听说你收了李可染一张画?”
我说:“对呀!”
“你付给他多少钱?”
“600元,怎么啦?”
“拿出来我看看,怎么付了这么多钱?”
我一听就明白了,有人到局里告我们状了,这是来调查的。我马上到存货柜子里把李可染的画拿了出来。
这张画有二十多平方尺,画的是着色的漓江山水。像这样的画,李老很少拿出来卖,通常拿出来的大多是些小幅的,其中又以柳牛居多。
这位处长看了看画以后倒也说:“够大的,但钱是不是太多了?”他的口气比来的时候有所缓和,但还是强调钱给得太多了。
我向他解释:“稿酬这些日子有所提高,从十五六元提到二十多元,大画不容易画,尤其是李可染,很少卖画,更不用提这么大的画了。您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工作才拿到这张画啊!”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位处长紧接着又问了我一句:“你和李可染是什么关系?”
这下把我气坏了,他竟然会这么问!“业务关系,怎么啦?”这么辛辛苦苦地干,竟遭到这样的猜疑,我当然不干。后来,由于处长看过此画的大小后,有所了解,也就不了了之。
(选自《往事丹青》/陈岩 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10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