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士心态与西晋咏物赋创作
2014-06-02沈扬
沈 扬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从今人角度来看,西晋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家在当时没有一位是可以被尊为一等高门的文人,钟嵘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在西晋政治格局中,无疑属于弱势群体。平凡的出身和惨毒的遭遇酝酿了他们独特的内心世界。勃兰兑斯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所以,文学风格的差别归根结底还是创作主体及其心态类型的差别。宁宗一认为:“作家之间最深层、最重要的差别是心灵和心态,而其他一切差别,都是更表层的。”(《关注古代作家的心态研究》),可见重视文人心态研究,尝试解读文人的思想意识和内心世界,对于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本文尝试从西晋寒素士人心态去考察西晋咏物赋的创作风尚,庶几可以照见西晋咏物赋更深层次的价值。
一、寒士心态与西晋咏物赋风之转变
刘勰概述西晋文坛作家队伍曰:“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其所提到的文人中,尽管年辈不同且生活轨迹各异,但在当时的门阀秩序中,这些士人皆不能与琅琊王氏、颍川荀氏这样的一等高门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可以被视作寒素文人。所谓“寒素”在当时盖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次”(《晋书·李重传》),其中少年孤贫如张华、傅玄、成公绥、皇甫谧;或以亡国旧臣之姿而被中土著姓藐视如北上的江南才俊;或因父祖官职不显如挚虞、潘岳、左思;或仕途不济、累年不调如夏侯湛,这些寒士当中,诚有如张华、傅咸等致身通显者,但正如赵翼所言:“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廿二史札记》卷八)他们多带有政治依附者的性质,这与西晋特殊的政治形态有关。陈寅恪先生概括西晋的政治特色为“唯才是举的时代过去了”和“崇尚节俭的时代也过去了”,要之,西晋以门阀政治取代曹魏尚通兑、贱名节的风尚,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文人对于国家政权的依附性加强,其心态亦随之而发生变化。汉代赋家宏阔古今、总览万物的雄奇之心在建安时代便开始瓦解,西晋寒素文人更难以沉溺在帝国想象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京都大赋创作至魏晋而衰亡,《三都赋》之所以洛阳纸贵,正在于巨丽之作的缺席。西晋赋学的开展以帝国心态的瓦解为前提,由于当时的一等高门耽于清谈,鲜有擅长诗赋创作者,故西晋文学实际“所反映的是寒素族的生命价值观和情调。”(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
咏物赋至西晋才真正实现了将物理、情境、心性三者合而为一,寒士心态类型为这一创作格局奠定了基调。诸如对于远祸全身的理性思考,抗时矫节、不阿附朋党的志趣抒发以及处幽弥显、克绍家声之情感取向的表达等,循此,便形成了后文所述的三种品格。这些都是寒士心态影响下西晋咏物赋较诸两汉建安发生的转变。言浅托深、类微喻大成为西晋咏物赋表现手法的重要开拓,同题共赋而各自申述对于具体问题的看法则又体现西晋赋家对辞赋文体功能思考的拓深。此外,在传统的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模式中,亦可以察知西晋寒士对于生命遭遇的态度。这一切都建立在寒士心态的基础上,而考察他们心态的形成则又不得不从当时的政治生态出发。
二、寒素士人心态之建构
文人心态并不同于文人思想抑或人格类型,前者具有微妙性、流动性的特点,后者则相对稳定。影响文人心态的因素很多,学术风气、政治环境、地域因素、文化背景、个人运命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参与其中的文人心态。具体到西晋寒素文人而言,政治环境的恶化是影响他们内心世界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有如下两点:
其一,党祸与文人的心态选择。西晋五十二年间的历史中自始至终贯穿的便是杀戮与党争。从剪除曹爽势力集团、诛杀高贵乡公以及残害名士嵇康等杀戮行为,到立朝之后的内廷权力之争,后者构成了寒素士人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党争政治的残酷性也正在于它先是裹挟了寒素文人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最终又将其抛弃。今仅据唐房玄龄主修《晋书》统计,“夷三族”的出现频率便达到了18次之多,其中十之八九出自西晋,此外被无辜杀害的文士如陆机兄弟又远远大于上述数字。在如此血腥恐怖的政治局势中,寒素士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1)退避隐忍以远祸全身。这种心态尤其表现在那些入世颇深的寒士人群中,傅玄《镜铭》:“惧则安,敬则正”,《席右铭》:“居其安,无忘其危”,又“感生于邪色,祸成于多言”张华通过“鹪鹩”以阐述有用以致祸、无用而全身的处世态度,傅咸借“仪凤”来揭橥效德尽智以保身的生存哲学,所主虽殊,于苟全性命之意却同一声气。(2)秉忠履道、结心绝党。夏侯湛借浮萍以自喻其宁漂泊无依也不结党营私之志,其余如傅咸《鸣蜩赋》、成公绥《木兰赋》,亦以借物申说不苟全阿附之决心态度。为论述方便,姑且将寒素文人的这类心态命名为党争心态,此种心态流露于咏物赋中,便产生了以《鹪鹩赋》为代表、宣扬退避隐忍、谦卑自牧的创作主题,和以傅玄为代表、主张尽忠竭力以趋利避害的辞赋主旨,以及以夏侯湛为代表的履道为公、拒绝结党的现实选择。
其二,门第秩序激荡出的士族情结。门阀士族阶级的形成依政事、文化、军功之不同分为武装贵族和文化世族两个大类,通常早期世家大族以政治事功和家族学术致身通显的情况较多,至西晋时期上述三类世家大族已趋于融合,武人起家的世族也渐偏重于子孙的教育以及家族文化的延续,逐渐摆脱尚武的一面转而攻文,这便是余英时先生所谓的“士族化”。如此形成的门第秩序的实质是著姓与王权在权力纷争中建立起来的利益屏障,这一屏障客观上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1)阻止寒素士人进入权力中枢。《晋书》中时常有官员举寒素而被高门士族武断不许的例子,夏侯湛曾因累年不调而著《榷论》自广,李重、阎纉曾为改革铨选制度而据理力争,都说明了当时的门第秩序的森严;(2)即便寒素士人进入了权力阵营,却往往遭到来自著姓的奚落鄙弃甚至打压排抑,故陆机北上而见遭王济、卢志的讥刺,张华官拜司空却受到荀祖的嫉恨,傅咸虽典掌天下选举却仍发无奈之叹。这里需要指出,“寒素”概念本有相对性和流动性,地方士族在其郡望虽颇享盛名,不少亦是诗礼簪缨之族,所以他们遭受来自高等士族的排挤之后托物遣怀或借物抒情,更应理解为潜意识中的士族情结被激荡之后的表现。此当以潘岳《河阳庭前安石榴赋》和陆机《羽扇赋》为代表,后者的创作是士族文学成熟的标志。
三、寒士心态与西晋咏物赋的三种品格
1.借物以申全身免祸之理
上文已指出,党争伴随着杀戮催生了文人思想中自我保全意识,体现于辞赋创作,便是通过辩证鹪鹩、叩头虫、蜘蛛、螳螂、款冬花、萤火虫等寻常物理来表达如何全身免祸的处世之道。这类创作的共同特点是,所写之物皆出身寒微、其貌不扬、弱小无依却能自全于世,映射出西晋玄学对于“自然”“任性”等命题的哲学思考。
(1)无用而存的辩证体悟
西晋初期的党争在以贾充为代表的开国功臣与以张华为代表的名士集团之间展开。张华出身少孤贫,“儒雅有筹略”,因为博学强识而又喜延誉,在士林中颇有威望。无奈却卷入了内廷权力之争,先出外镇,后因不依附赵王伦而夷削三族,《鹪鹩赋》正是张华入仕之后有感于惨毒的政治境遇而作,《鹪鹩赋序》认为“鹪鹩”:
鹪鹩,小鸟也,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得。
在赋中,张华承庄子“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的话头,以“无用之用”来审读鹪鹩之智,概其有三:一,色浅形陋,不为人用;二、形微处卑,物莫之害;三、委命任运,适性自然。以之为参照,人生也正复如此。出身仄陋诚然是寒素文人跻身庙堂的劣势,然远离政治也意味着退出了权力博弈的斗争,故能以浅薄之躯而得以自全善终。张华借赞咏鹪鹩之志以阐发物因用而致祸,以无用而得全的处世哲理。但现实中张华却未能践行这种谦卑自牧的观念,王鸣盛评《鹪鹩赋》曰:“绎其词,有知足知止之义,乃周旋邪枉之朝,委身危疑之地,以杀其身,可谓能言不能行矣。”这样看来,《鹪鹩赋》并非为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作,张华只是借此将内心的忧惧传达出来,只是这种情感与哲理思考交织贯通,非了解张华平生事迹不能透过现象而见照本质。
与《鹪鹩赋》同样声气的还有潘岳《萤火赋》“无干欲于万物,岂顾恤于网罗?”、傅咸《款冬花赋》“恶朱紫之相夺,患居众之易倾。在万物之并作,故蹈华而弗逞。待皆死以枯槁,独保质以全形”、傅咸《叩头虫赋》“人以其叩头,伤之不祥,故莫之害”,后来贾彪《大鹏赋》欲反张华之意,然远害莫侵的宗旨却又如出一辙。这类思想的远源是庄子的“无为”观念,与庄子不同的是,西晋人的“无为”并非与世俗绝对地对立,而是调和了自然名教的矛盾,故此刻的“无为”更兼有了形而上的“养生”意味,至于究竟能否将无为落实下来,则又视现实环境而定。
(2)效智立德与居安思危的个人选择
针对《鹪鹩赋》而继作的有傅咸《仪凤赋》和贾彪《大鹏赋》,二者皆不以张华无用而免害的处世态度为然,傅咸《仪凤赋》认为:“物生而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贵乎才智也。夫鹪鹩,既无智可贵,亦祸害未免,免乎祸害者,其唯仪凤乎?”在避祸免害的心态上张华与傅咸持统一立场,然其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如何避免祸害的发生。对此,傅咸持输才尽智以求免祸的观点。这或许与傅氏的性情气质有关,《晋书·傅咸传》谓:“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嫉恶如仇,推贤乐善”,考其生平,也多能尽节事主,秉持乃父风神,所以处理问题的方法角度上有别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张华。他在《鹦鹉赋》中也力主唯有尽己之智慧,方可取爱扬名于时主,从而得到人君的庇护。但这种庇护显然是以“入笼”,也即是牺牲个人自由独立人格为代价的。因此,傅咸更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如《黏蝉赋序》:
樱桃其为树则多荫,其为果则先熟,故种之于厅室之前。时以盛暑,逍遥其下,有蝉鸣焉。仰而见之,聊命黏取,以弄小儿。退惟当蝉之得意于斯树,不知黏之将至,亦犹人之得意于富贵,而不虞祸之将来也。
作者巧妙地在传统咏蝉赋基础上加了一个“黏”字,便跳出该类题材的窠臼,借黏蝉之事而联想孟子居安思危的圣训,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成公绥《螳螂赋》与傅咸同一格调,赋先叙螳螂情状,可谓惟妙惟肖,后突然笔锋一转,黄雀的出现无疑与螳螂的存在构成了一组张力的画面,可惜的是赋文不全,但从黄雀“疗饥”的目的来看,似乎螳螂难免成为黄雀的盘中美食,由此进而可以推测出成公绥之立意乃在戒骄横以自保,与居安思危的规劝不失为一体之二面。
2.托物以表介立绝党之心
西晋党祸一方面让寒士对庄子无用之用的哲学观念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另一方面则激荡出了以夏侯湛为代表的一类不愿曲阿朋党、惟正直是与的人格类型。他们的创作为西晋辞赋的柔靡风格注入了阳刚的气骨。《晋书·夏侯湛传》:“拜中郎,累年不调,乃作《诋疑》以自广。”夏侯湛时与潘岳齐呼“双璧”,却沉沦下僚,其《观飞鸟赋》以飞鸟的翩翩自得之姿入笔,欣羡其自得乐群之情状,“何斯游之自得,谅逸豫之可希。苟临川而羡鱼,亦欢翔而乐飞”,君子乐群有志于道,小人乐群有志于利,在夏侯湛看来,若因利乘便以结党营私,宁愿如“浮萍”一般漂泊伶仃,《浮萍赋》可以看作是一个久居不调的寒士抗时矫节的心声:
既淡澹以顺流兮,又雍容以随风。有缠薄於崖侧兮,或廻滞乎湍中。纷上下其靡常兮,漂往来其无穷。仰熙阳曜,俯冯绿水,停不安处,行无定轨。流息则宁,涛扰则动,浮轻善移,势危易荡。似孤臣之介立,随排挤之所往。内一志以奉朝兮,外结心以绝党。萍出水而立枯兮,士失据而身枉。睹斯草而慷慨兮,固知直道之难爽。
赋着眼于“浮萍”漂泊无依的生存状态,正可比夏侯湛本人在朝中的处境。他自谓“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凤栖五期,龙蟠六年,英耀秃落,羽仪摧残”(《抵疑》),尽管“停不安处,行无定轨”,夏侯湛却依然坦露了自己“内一志以奉朝兮,外结心以绝党”的决心。再如他赞扬荠草“钻重冰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荠赋》),亦着眼寻常细物中特立独行的一面,与其个人品格正相仿佛。夏侯湛与潘岳交好,但从二者辞赋风格来看却未受到其影响,潘以繁缛的渲染手法见长,而夏侯氏则以写意白描擅场,他青睐张衡的辞赋特色,以其为“有味”,可见,夏侯氏更加注重言外之意和意外之味,体现出其时“言象义之辨”对于文学欣赏趣味的渗透。
同夏侯湛相侔,傅咸亦以“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谠之是与。佚履道之坦坦,登髙衢以自棲”为旨归,颇有乃父家风。至成公绥的《木兰赋》在形象地展现寒士生存的环境的惨淡之外,兼抒发了作家如经冬之木兰那样的生命活力:“至于玄冥授节,猛寒严烈。峩峩坚冰,霏霏白雪。木应霜而枯零,草随风而摧折。顾青翠之茂葉,繁旖旎之弱条。谅抗节而矫时,独滋茂而不雕。”篇制虽短小,却满含激情,颇见贤人失志而不堕青云之志的风神。
3.体物以喻德才兼备之质
在士族化过程中,发迹或享誉较早的如前文所举之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荀氏等中土著姓,其地位升降并不明显,这也就决定了在权力链条中,这些高门望族始终占有着绝对优势。寒素文人固然可以凭借才华升入庙堂,但依然是在上述士族集团所建立的门阀制度下供职任事,故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贬谪、久滞、遭辱是寒素文人在门阀秩序下每每遭遇的,潘岳曾回顾自己仕宦以来的历程:“阅自弱冠涉乎之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足见一个小吏的艰辛仕途,其《河阳庭前安石榴赋》正是因才遭嫉,被贬出守河阳,于寓所郁郁寡欢、睹物兴情之作:
曾华慧以先越,含荣其方敷。丹晖缀于朱房,缃的点乎红鬚。煌煌炜炜,熠爚委累。似长离之栖邓林,若珊瑚之映绿水。光明燐烂,含丹耀紫,味滋芳神,色丽琼蕊。遥而望之,焕若随珠耀重渊;详而察之,灼若列宿出云间。千房同模,十子如一,御饥疗渴,解酲止醉。既乃攒乎狭庭,载阨载褊。土阶无等,肩墙惟浅,壁衣苍苔,瓦被驳藓,处悴而荣,在幽弥显。
赋以安石榴作为“嘉树”和“名果”两方面属性造端,工笔勾勒了安石榴的卓态殊姿,词彩浏亮,富于表现性。大抵安石榴以颖异之姿却处身陋馆,与潘岳此时的处境相吻合,故能引起作者移情联想。石榴光鲜的外表和价值功用与河阳陋馆的苔藓斑驳和室陋境狭形成对比,意谓此不堪之境不独未影响安石榴的内修外美,反而更能衬托“其华可玩,其实可珍”的弥足宝贵,末以“果犹如此,而况于人”卒篇,有顾影自怜之况味在其中。此赋浓墨重彩,与潘岳“繁缛”的文风相吻合,以此赋亦可稍窥其江海之才。
与潘岳的情况不同,陆机本自江东首望,却以亡国贱虏的身份北附洛阳的司马政权。但其内心的士族意识却从未衰减,反而在中原著姓的排挤鄙弃当中逐步被激荡出来。《晋书·陆机传》记载了如下两例陆机北上之后的遭际:
“诣侍中王济,济指羊酪谓机曰“卿吴中何以敌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盐豉。”时人称为名对。张华荐之诸公。……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志默然。既起,云谓机曰:“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祖父名播四海,宁不知邪?”
这两则材料都来自《世说新语》,只是个别字句稍有异词。从中看出,陆机入洛,遭到了来自王氏、卢氏这些中原著姓的鄙弃,他们无视江南文化,更小觑陆机父祖两代人的勋荣。可见,中原士族并不把吴中著姓放在眼中。这也就酝酿了陆机北上后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想建功立业,以绍复家声,故先后依附贾谧、赵王伦、成都王颖等势力集团;另一方面,陆氏兄弟始终未能释然自己的江东首望身份,内心的士族情结反倒在中土著姓的猜忌、嫉恨、陷害过程中被激荡日新。除了克绍家风、重敦祖业的想法外,他的露才中土而不顾恤的行为背后,当有为江东文化正名立节的思想动力。讨论《羽扇赋》的内涵亦不能撇开陆机北上后的遭遇及其心态。这篇赋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其艺术水准都远超同时期众作,充分反映陆机本人的才情藻思。以下从意象和结构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1)章华台的政治隐喻
赋中的章华台是颇有隐喻性的一个意象。首先,从赋内容看,楚襄王、宋玉和羽扇显然与山西河右大夫、五明山、周武王构成了对比,那么,为什么陆机用楚王来与后者相对照呢?这涉及到古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观念:三楚。据《史记·货殖列传》:“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三楚”的概念至魏晋而存,阮籍《咏怀》(十一):“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李善注引孟康《汉书注》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其说法与司马迁大体吻合。这样就不难理解陆机为何托楚国形象以表彰羽扇之美的原因了。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楚文化实则成为了泛南方文化的象征,故陆机此处并非信口开河;其次,《史记·楚世家第十》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於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又《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昭公)八年,楚灵王就章华台,召昭公。昭公往贺。”从两条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章华台对于楚国实有特殊的政治内涵。时东周王权式微,晋楚形成南北割据之势,章华台正修建于晋楚平分秋色之际,此时楚王有觊觎社稷之心;鲁昭公八年楚灵王在章华台上大宴诸侯。鲁昭公亦赴会,鲁人深以为耻。所以,章华台之会成为了南方势力扩张、北方势力紧缩的一个政治隐喻,在此处兼具了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内涵。它象征着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欲与中原文明相抗衡的趋势。尽管后来楚国覆灭,但在此前的割据纷争中,楚文化确实显现出与宗周文化迥异的姿态。基于“三楚”的地域文化观念,陆机此赋以章华台之会作为对问发生的场景,表面看仅仅是为“羽扇”正名,实则有为族群文化张本的深衷。至于为什么历史中的楚灵王被置换成了楚襄王,似不得而知,但从对问体赋的发展源流来看,鸠合场景,措置人物,本是赋家矜才使学的体现,从宋玉《对楚王问》《风赋》到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二都》、张衡《二京》,或虚构人物以相问难,或直据历史人物而虚拟场景,赋家本崇尚铺排夸肆之言,其宏阔宇宙、牢笼万物之心亦可以于此观之,却不必深究。
(2)对问体的结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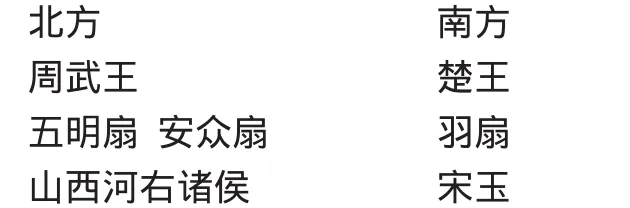
可见,赋文不仅在内容上别附深衷,艺术形式上也体现着陆机的匠心。《羽扇赋》已经不单单彰显陆机的文学天才,而是为江东士族群体、南方文化立言表德。西晋灭吴,羽扇亦流入中原,但南北隔阂却并未因陆机兄弟的北上而消失。陆机也因过分高调而罹难。初张华许之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到后来晓以厉害,“子之才患太多”,一个“患”字无疑透露出张华对陆机这位天才的担忧。华亭鹤唳、可复得闻是以牺牲两位旷世英才为代价而得到的,终成为了千古文人的悲慨。
结 语
西晋辞赋创作数量空前,体裁多样,风格多元,内涵上的精细化,形式上的小品化,情感寄托上的文人化,辞藻声韵上的唯美化,最是其特色。然何以寒素文人欲凭借体物笔法而言内心隐情?首先,赋兼才学,博学多闻、儒玄兼综是寒素文人进入仕途的重要资质,如果说吟咏题材的扩展正是他们博学的象征,那么以儒为主、兼理玄风的知识背景使得他们能够将辨物理与通人情合二为一,透过现象层照见物态背后的物理,并将其与生命体验相结合,这本身是学养功力的体现;其次,魏晋玄学对自然本体的重视开启了文人以审美眼光观照自然的先篇。汉代咏物赋作总体不离于儒家政教观念,观物表德是其主流模式,这既抹杀了物性本身之美,复难以呈露作家个人的情感意态。这种情况至魏晋而有所转机。玄学重本体探究的理性思维引发文人对于物理的探究,这就为物与道之间,心与物之间架构了桥梁,二者从对立走向了融合。文人观物不再为了表物之德,而在凸显物态之美和物性之理,晋人十分重视作品能否称物,陆机《文赋》:“每自属文,犹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陆机所追求的是“挫万物于笔端”的牢笼万态之境界,陆云则“乐思万物,观异知同”,他们不再以儒家政教眼光去审视外物,而是借体物以穷究物理,探寻自然本体的审美意义,同时,“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重视个体情怀的感发,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使得咏物赋融贯自然物理和作家情性于一炉。由此可见,魏晋咏物赋创作规模的空前繁荣并非仅仅是文学内部的自律,尚有赖于时代思潮对文人物我观念的影响。
〔注释〕
①据孙明君先生统计如下:张华、左思、潘岳、夏侯湛、陆机、陆云、应贞、傅玄、张载、张亢、挚虞、成公绥、孙楚、张协、潘尼、石崇、牵秀、杜育、刘琨、欧阳建、傅咸。这些人在当时不能与王济、荀祖这样发迹较早的中土著姓同日而语。这里必须指出,寒素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的含义本是多歧的,日本学者宫奇市定、中国学者毛汉光、苏绍林等人都曾作过探讨,见仁见智,聚讼纷纷。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寒素”作为一种身份是在他者视域中建构的,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钱志熙教授认为,寒素文人与中原著姓的一大区别就是能文博学,从这个意义来说,则西晋文学所反映的恰恰就是寒素文人的思想世界,本文沿袭了钱先生的说法。见孙明君《两晋士族文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6页。
②今据《先秦汉魏两晋南北朝诗》统计,《全晋诗》西晋部分今存作家60人,其中在当时以一等高门目之的只有司马懿、荀勖、王济、司马彪四人,其余皆属地方士族或武装豪族。高门士族不好文学在当时是普遍现象,《晋书·王衍传》:“(王衍)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王衍在当时有“一世龙门”的美誉,趋附者甚众,他对于谈玄崇虚之风尚的推广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寒素文人不同,高门士族勿须凭借才学进入权力场,门第出身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优势,所以文学才华的锻炼并不在他们先天的考虑之中。
③傅咸《赠郭泰机诗》序谓: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不知余无能为益,以诗见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沦不能自拔于世。余唯心知之而未如之何。可见,傅咸在森严的门阀秩序面前也束手无策,欲提携后进而不能。见《先秦汉魏两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9页。
〔1〕(法)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宁宗一.关注古代作家的心态研究〔J〕.文学遗产,1997(5).
〔3〕(南朝梁)刘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6〕钱志熙.唐前生命观与文学生命主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7〕(清)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8.
〔9〕(南朝梁)萧统编.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0〕(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2005.
〔1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2〕(西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西晋)陆云.陆士龙文集卷二〔M〕.四部丛刊本初编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