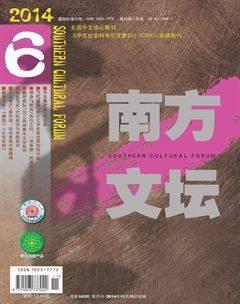在叙述与语言的利刃上舞蹈
2014-05-30陈剑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界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就是“新散文”思潮的兴起及如火如荼的发展。对这股“新散文”思潮,我曾在《文艺争鸣》杂志和《羊城晚报》发表了《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新散文往哪里革命?》两文加以评析,当然也有较为尖锐的批评。而格致作为“新散文”思潮的代表作家,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此后,我一直跟踪格致的散文创作,并在一些文章中论述了格致的散文。
迄今为止,格致已出版了《转身》《从容起舞》《替身》《婚姻流水》《风花雪月》等五本散文集。作品不算多,却有别人无法替代的鲜明而独特的创作个性,这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格致是一个具有独特的散文观念与不合常规思维的作家。她的散文,大多从个人感受和经验出发,力图通过挖掘个人经验探索人类公共经验,追究真正迫切的心灵和思想疑难。同时,她通过“记忆”的通道,展示了女性成长过程中的“恐惧”与“痛感”,其间有对女性生存境遇和存在本质的独特理解。可以说,格致的创作,主要是一种自然生命的赤诚呈现,也是对女性心灵秘史的揭示。作为极富潜质和创造力的优秀女散文家,格致的写作,不仅已达到相当的思想艺术高度,而且为当代散文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另类的标本。
一、散文叙述的革命
格致的散文创作,不仅极度地敏感,体现出一种因“恐惧”“痛感”而产生的美学特征。在艺术上,她的散文也极具先锋性和前卫性。她无视传统散文的写作法则,打破各种清规戒律,在散文创作中大胆探索实验,努力尝试散文写作的多种可能性。特别在散文叙述方面,她的散文创作具有不容忽视的革命性。
我们知道,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小说是最受关注、影响最大的文体。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小说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特別是叙述方面的革命。而散文这里,长期以来却是封闭自足,波澜不惊,停滞不前,既缺少论争,没有思潮流派的竞争激荡,又拒绝西方的理论和表现手法。在传统散文中,为了突出真实性,不管是记叙性散文、抒情性散文还是议论性散文,都十分强调主体性叙事。即作者在叙述中占有绝对的权威,是不容颠覆不可动摇的。于是我们读到的散文,几乎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点;而且散文的作者和叙事者一般都是重叠的,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性的变化。事实上,正是这种过于机械僵化、浅表单一的散文叙述,极大地阻碍了散文的发展,使得散文的影响力远不及小说和诗歌。而理论研究上对散文叙述的忽视和认识上的模糊,在客观上也削弱散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的竞争力。
从现代叙事学的意义上说,散文的叙述要有革命性的突破,首先必须摆脱古文传统和现代文学的羁绊,将研究的中心从以往对修辞、描写、意境和篇章结构的注重转向叙述,并且理直气壮地确定叙述在散文中的中心地位,以此提升散文与小说的竞争能力。其次,在确定叙述在散文中的核心地位后,不能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层面来理解叙述。或者说,不能仅仅满足于将叙述看作述说人物经历和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应借鉴现代叙事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从叙事的不同角度和层次来观察分析叙事活动。当然,散文叙述的革命,最根本的还是要落实到创作上,即通过创作实践来实现。而格致的散文创作,正是在叙述上给我们以极大的惊喜。
格致散文的最大价值或者说对当代散文创作的最大贡献,我认为是对传统散文叙述的背叛。她的背叛,主要体现在如下诸方面:
(一)呈现型叙述 了解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散文主导叙述方式主要是概括型叙述。这种叙述方式一般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新闻报道型叙述。这主要是指从30年代末期到五六十年代这段时间的一种散文叙述方式。由于这一阶段的散文以叙述性散文为主流,同时将散文视为“轻骑兵”,要求散文及时地对现实生活进行“朴素”而“逼真”的再现。如此一来,这一时期的散文基本上是以单一的事件和人物为叙议的对象,叙述的方式也高度地一致,即首先推出人与事或景物,然后介绍背景,讲述人物事迹,总之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其次是追忆式叙述。这一叙述方式集中体现于“四人帮”打倒后到80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中。这一阶段,不论是歌颂、缅怀老一辈革命家丰功伟绩的散文,如何为的《临江楼记》,毛岸青、邵华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还是控诉“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颂扬知识分子抗争精神的作品,如丁宁的《幽燕诗魂》、黄宗江的《海默难默》、黄秋耘的《往事与哀思》等散文,均采用了“追忆式”的叙述方式。这些散文在叙述视角上与以前的传统散文并无二致:一般都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在叙述时间上则是按照作者与叙述对象认识的先后;或是遵循所追忆“往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叙述。不过,与十七年间那种纯客观报道式、创作主体被完全“虚化”的“外向型”叙述方式相比,“追忆式”叙述应该说多少渗透进了一些作家的主体意识,不仅有“内向型”的心理体验和生命灌注,也更注重细节的筛选与提炼。因此与十七年的叙述方式相较而言,“追忆式”叙述在中国现代散文的文体演变中仍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散文界出现了一系列革命。这种革命包括对散文写真实的质疑,在题材上求野求杂,主张披头散发的散文,等等。而在散文叙述上,则是由呈现型叙述代替传统的概括型叙述。所谓呈现型叙述,主要是借助想象与联想,通过对现实场景、生活细节和事件的精确细致的描绘,将叙述者的主观意识、心理状态形象地呈现出来,并由此把读者带入到某个特定的情景中。这种富于革命性的散文叙述,在“新散文”“在场主义散文”时可见到,而在格致的散文中,则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在《转身》这篇散文中,格致讲述了一个强奸未遂的故事。作品分三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是我与企图强奸者在楼梯转弯处的相逢、对峙到最后说服作案者放弃犯罪的过程;二是20世纪40年代中叶“我”母亲在乡村路上遇到一名苏联红军,当这位红军战士对母亲发生兴趣并将母亲外衣撕开时,因战马看到母亲身上的红色内衣,受惊飞奔起来将手上缠着缰绳的红军战士拖走,母亲因此得以虎口逃生化险为夷;三是因陌生男子拥抱而联想到若干年前在松花江边男友拥抱她时的感觉。尽管作品采用了“内文本”与“外文本”交替叠加的叙述手法,在现在与过去、真实与虚构间恣意穿梭,同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叙述视角的转换,展现了散文叙述观点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但作品更为吸引读者,更为成功的地方,却是那些呈现式的叙述。举例说,当那个陌生男子在楼梯转弯处从背后将“我”抱住时,作品将叙述的笔墨定格于“我”手中抱着的一包衣服上。先是写衣服“砰的一声落到了地上,溅起的灰尘像水波一样荡开又如花朵一样开放”。接下来描写声音:“这是一声闷响,地面给予包裹的反弹力如一片细嫩的禾苗被重重压在一块石头下面,发不出一丝声音。”再接下来写味道:“它们被洗了又洗,纵横的纤维里充满了洗涤剂的香味。它们是不能接近灰尘和泥土的。灰尘是它们的敌人。”最后再写“我”的感觉:“此刻,它掉到了地上,在它们湿漉漉的时候,掉到了可怕的尘土里。我觉得是自己砰的一声滚了下去,顷刻被尘土包裹。”在《转身》中,像这样呈现型的叙述可说是随处可见。作品以楼梯为场景,以“转身”为化解矛盾的聚焦点,以客观真实性和“我”的感受为前提,敏锐地捕捉住了生活的细节和人物的表情、动作及心理活动,并加以精细确切的描写。其间有说明,有叙述,有联想,有议论,有评价,有比喻和反讽,但这一切都服从于呈现或展示。这可以说是格致在散文叙述上的创新,也是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有志于散文革命的年轻散文家的一种艺术选择和创作倾向。
(二)隐喻式性的多元叙述视角 这种叙述方式在小说创作中较常见,但在散文创作中采用此叙述手法的还不多。祝勇、张锐锋等新散文主将曾在此作过尝试,而在格致的散文中,这是一种常规的叙述手段。例如《硝烟》有三个叙述视角:一个是男司机,一个是倾听者,另一个是桌子。男司机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他对他身边的一位同事李援朝身份的疑惑;而“我”(同样是第一人称)和桌子则是倾听者。所不同的是桌子又承担着解疑者的角色。作品的叙述以对话形式展开,男人是疑问的提出者,桌子则是答疑者,但桌子和男人互相听不到对方的话语,只是一个劲地自顾自说,而作为倾听者“我”能同时听到他们双方,以旁观者的身份倾听着他们对李援朝的看法。男人和桌子的叙说交叉出现,一个是以被叙述人李援朝目前的同事的身份,一个是以知晓李援朝过去的“老友”的身份,二者共同完成对李援朝这一人物的建构。《站立》中则同时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作为叙述人的“我”;另一个病人,即作为叙述对象的“我”,而这个“我”有时又变为第三人称“他”。《站立》正是以“站立”为叙述中心,让“我”与“我”与“他”的视角不断变换,交替出现。而这种跳跃断裂式或意识流式,打乱叙述的时间,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糅合在一起进行大跨度叙事,而且无视思维逻辑,在真实与虚构、寓言与纪实间任意穿梭,常常有意偏离故事,带有隐喻性的叙述,还出现在《替身》《庭院》《花朵的布局》等作品中,通常讲述的是一些日常生活、生老病死的老套故事,但由于它们有着独特叙述魅力,同时格致有一种本领:她善于将隐含在故事之中的深层话语准确无误地提取出来。这样,格致的叙述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封闭的叙述方式,呈现出丰富性和多元性的叙述特征,而且她的叙述渗透进了情感因素和心智因素,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意味和发现话语的乐趣。
(三)自然形态与断章碎片的组合 格致对传统的散文结构并不尊重。她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编排,以各种各样的自然形态呈现散文的内容。《听懂的时候》一文就由《笑脸》《芥川龙之介》《游戏》三篇看似不相干的片段组成,而且片段中还有片段,《芥川龙之介》《游戏》内部还分别有两节不同的文字,两段文字之间直接以序号表明,连过渡语都被省略掉,完全不顾传统写法里对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追寻。这样断章残片式的组合,使文本呈现出开放、自由的状态,造成一定的反差意味,留给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告诉》则是她将自己作绿化科公务员时的工作记录稍加改造而成。工作记录表上有如下栏目:上访时间、上访方式、上访人、接待人、上访内容、处理结果,“这个记录本我填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应该增加一个栏目,也就是‘辩护内容,于是我着手制作了另一个记录本,这个记录本就是我的散文《告诉》”。“辩护内容”很奇特,包括“我”让沉默的大多数树木说话,让已被砍倒的大树说出源于“我”的猜测的真相……从工作上的公文提炼出散文的形式,似是顺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在《告诉》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对于树的指控,而事实上,树既与疾病、失眠、恐惧没有什么联系,也与失窃没有什么瓜葛,然而树却成了人类生存困境的替代品和符号。格致在叙述上的独特处在于,她用轻松幽默,甚至带点反讽意味的笔调,通过生活自然形态的实录与散落各处的断章碎片的随意组接,将蕴藏于生活深处的各种语言、符号、表征凝聚起来。于是,格致的叙述便具有深刻其内,自由其外,以俏皮随意的讲述开掘沉重的主题,用生动丰满的细节折射出敏感紧张的心理状态的特点。
从引小说、诗歌文体入散文,到呈现型和多元视角的叙述,再到创造性地组合断章残片成文,格致的散文抛开了传统散文文体上的束缚,打通了文体间的界限,文本呈现出开放、多样的状态,在体式上展现了崭新的面貌。若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各种文类之间形式上的杂糅,深谙技巧的格致当然不会仅满足于此,她在许多篇目里还更深入地化用其他文体因素,如灵活运用小说技巧来写散文。比如《婚姻流水》,你很难说它是散文还是小说。可以说,格致的“跨文体”写作,以及她在叙述方面所做的实验,在推动当代散文艺术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也许,这些探索还不是十分成熟,甚至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读者因长期形成的审美惯性,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这样的散文。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越轨”的探索对于过于成熟、过于老成持重的中国散文是大有益处的。起码,它拓展了散文的叙述空间,给了我们某种艺术革命的新启示。
二、创造散文语言的新秩序
诗歌有“诗到语言为止”的说法,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由于散文不像小说那样可以靠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和多层次的生活场面的描述来吸引读者,又不似诗歌那样以精致的意象组合和瑰美的想象力给读者以美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散文对语言的要求可以说超过了小说和诗歌。然而在过去,我们对散文语言的认识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我们一直认为,语言只是为了表达主题和思想而存在的工具。这其实只是从修辞的层面上来理解和运用语言。于是,在“语言是一种工具”的观念指导下,传统散文特别强调炼词、炼句和炼意,人们对散文语言的要求是精确生动和形象,而忽视语言的个性化、排斥语言的异质化,更没有意识到语言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最为基本的表现,是一种如苏珊·朗格所说的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由于传统散文的个词的旨意、词与词的配搭关系被严格固定,散文语言无法容纳进无限的能指,无法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自由的组合,如此一来,散文的语言自然也就越来越公共化和平庸化:许多散文包括一些经典散文的语言看起来简洁优美,精确形象,且十分符合语言规范,而内里却是老气横秋,迂腐雷同、毫无个性,更有的甚至是一种“木乃伊”式的語言。
格致的散文显然不满足于传统散文语言这个“常态”和“常量”对散文文体的束缚,她善于从叙事中提取“语言的毒液”,并着力于从多方面对散文文体的“变量”进行探索,而语言的革新正是她进行艺术革命的重中之重。因为她意识到散文的最终问题是语言问题。一个没有语言自觉的散文家;或者他的语言不具备创造性和纯粹性,他的一切努力都注定是徒劳。因此,她执着于寻求新的语言表达方式,试图使每一个语词,每一个句子都熠熠生辉,透出个性的力量和创造的光芒。也就是说,在格致的理念中,散文的任何词语、句子或段落都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它并不仅仅是记事与传达思想的工具,也不依赖于整体的框架而存在。这与那种炼词炼句、字斟句酌的传统散文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格致对散文语言秩序的创造,最突出且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简直就是一个语言的冒险家和魔术师。她随时随地都能通过想象与联想,让词语无限地生长扩张,并衍生出各种可能性和意义的空间。这是从《站立》中随手摘出的一段:
在困境中找到出路的弹拨神经疗法的具体步骤是这样的:先在那选定的神经穴位的表皮打一点普鲁卡因(局麻药),然后切开一个大约三厘米的口,再然后用粗壮的、比针灸针强壮百倍、千倍的止血钳子,从切开的入口插进去。娇嫩、颜色鲜艳的肌肉丛,直抵深处的骨骼,最后它猛地合拢,紧紧咬住这束惊慌失措的肌肉。那藏匿在肌肉里的神经也就跑不掉啦。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要不停摇动、弹拨那节露在皮肉外面的钳子。
神经都是些胆小而敏感的孩子。它们被圈在一个狭小的圈里。门被死死地插上了,而驱赶的鞭子在不停地抽打着它们。它们在圈里疯狂地转圈,疼痛得大叫。它们都疼得疯了。我至今无法描述那种疼痛,只有体验才知道。
这样的手术我做了十五次,每次间隔半个月,每次至少四个穴位。我的肉体每次至少插进四把止血钳子,它们还被不停地摇动。弹拨结束,那条被抓捕被折磨得发疯的肌肉还得被一条羊肠线捆绑,不让疼痛的翅膀收拢、降落。疼痛被拽成了绵长的丝线,以供我在间隔的十五天里细嚼慢咽。
在《站立》这篇作品中,像这样无限扩张,在物与词中产生“变量”的语言比比皆是。这是什么样的语言状态?在我看来,这是进入某种特定的氛围环境,抵达某种形式之后,从事物本身,从具体的细节,从生命意识深处,从女性的“恐惧”与“痛感”中自行涌现出来的语言。这种语言其实是对语言活力的发现和恢复。而发现和恢复散文语言的活力,则意味着必须对人们熟视无睹的语言进行伤害和治疗。这正如于坚所说:写作就是对词的伤害与治疗。你不可能消灭一个词,但你可能治疗它,伤害它,伤害读者对它的知道。于坚在这里所强调的“伤害”与“治疗”,其实就是语言的“陌生化”。即排除固定的、程式化的语言秩序,到公共词汇的人迹罕见处去寻找散文语言的个性,而从充满歧义的地方感受到散文语言的诗意。这是一种极具文学张力的语言组合。这种语言有无限的扩张性,可以变幻出各种花样,甚至能装进无限的内容。这种语言,显然是对以往的散文标准语言的偏移、扭曲和变形。所以,从根本上说,格致的语言实验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以往的散文话语,应予充分肯定。
这是一种如耿占春先生所说的“物的语言分析”。所谓“物的语言分析”,即物不仅是客体,而且是主体。物既具有一般文学中拟人化手法的表征,更是一个个的语言符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格致的散文中,她通过对物的独特想象与联想,使语言延展到创作主体的不同层次——从认知、情感、心理到生理;同时,这种语言还有效穿透了日常生活、感性经验与思辨界限。因此,物的语言分析是一种全新的、独特的、有力量的语言。它一方面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一方面又具有精神分析学属性与符号学特性。比如《站立》中对“止血钳子”“肌肉”“神经”等物的语言分析就是如此。而在格致的成名作《转身》中,她对“楼梯”所进行的物的语言分析更为精彩:
恐惧是从楼梯的积尘中衍生出的怪物。它从灰尘与阴暗潮湿中获得了生命后就迅速长大,然后从楼梯上一阶一阶地慢慢爬上来。从楼梯上爬上的恐惧是一个高大的黑影,它立在我的面前,张开手臂拦住了我的去路。
在这里,格致显然运用了拟人化的表现手法,于是我们看到,“楼梯”是一个“从积尘中衍生出的怪物,”它不仅获得生命后能迅速长大,而且“从楼梯上一阶一阶地慢慢爬上来,”并“立在我的面前,张开手臂拦住了我的去路。”但迷恋物的语言分析的格致并不止于此。实际上,“楼梯”在这里被安排了一个重要角色,承载了一个恐怖故事。“楼梯”既与“黑影”“黑色”“恐怖”等可怕词语纠结在一起,“楼梯”也生长出希望与激情,还延展出许多童年的记忆。格致就像一个熟练的烹调师,她将各种词语投进冒着气泡的锅里,然后在锅里加进一些语言的毒液和精神分析的元素,再利用想象的风力使语言燃烧起来;或者将锅里的语言煮成浓稠的恐怖的汤汁——这就是格致物的语言分析的本质。
格致在进行“物的语言分析”时,特别喜欢通过肢体语言传递出与众不同的微妙感觉经验。比如:
当那些对付我尖叫的士兵如潮水一样退却后,手掌与我的嘴唇之间出现了一丝空隙,我的声音得以从这空隙爬过。如一颗种子的幼芽蜿蜒地爬过压在它头顶的石头,从一侧将头探了出来。我的声音从他细窄的指缝中滑出,如饴糖一样扯成粗细不匀的条状。
他的手被我紧紧地抱住了。他略挣扎了两下就不动了。它们如两只小绒毛动物,在我手掌的温暖怀抱里很快蜷缩成一团,又闭上了眼睛,准备睡上一大觉。它们似乎为寻找这个小巢跑了很多岔道。我的热量不断地从双手的气孔里喷射出来。潮湿温暖的气流包裹了他的手,使他一直不安地处于被催眠状态。
对“手”“手掌”“嘴唇”“指缝”等肢体语言的描写相当准确细致,这样的肢体语言,再配以“我的声音得以从这空隙爬过”,“我的声音从他细窄的指缝中滑出,如饴糖一样扯成粗细不匀的条状”,以及“它们如两只小绒毛动物,在我手掌的温暖怀抱里很快蜷缩成一团”等等的关于声音和手的想象,的确读之有一种别样的感觉,一种独特的气味与声音,一丝奇异的、令人战栗的艺术美感。
而在《利刃的語言》中,格致更是将这种在场的肢体语言状态发挥到了极致:
残留的西瓜汁液,正从刀尖一滴一滴缓慢地滴到地上。它们是淡红色的,跟人体的血液极其相似。刀是月牙形的,刃口比刀背长出约一倍,在强光下反射出刺目的光。它距我只有二十厘米,只要二分之一秒,刀就能将这段距离变成零甚至负数。·……
刀是嗜血的,它永远乐于在柔软的不堪一击的肉体上证明自己是一把锋利的刀。刀面对石头的时候是会低头并且绕行的。但我不是石头,恰好是一堆柔软的肉。刀已看见了我,并且露出了笑容,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向我移动。它可能是厌烦了那堆西瓜、厌烦了西瓜发出的嘎嘎嘎嘎清脆的哭叫声。它想换一个略有些弹性的东西。
将“利刃的语言”描状得如此惟妙惟肖,且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我想唯有像格致这一路信奉“每个词都呈现意义”的新散文作家才能做到。如果对“利刃的语言”稍加分析,我们还发现这些细节或物的背后都散发出一种不安的气味,折射出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这正如南帆所说:“格致叙述的世界隐藏了许多莫名的敌意。危险潜伏在所有的角落,随时可能一跃而出,攫住柔弱的猎物。格致始终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个警觉的距离,惊悸与不安闪动不已。”(1)不仅如此,在作者笔下,利刃和卖瓜人、卖瓜人的手还结成了可怕的同盟:
握刀的手是黑色的,上边的血管如老树的裸根盘错着。他的手臂像是刀黑色而有力的柄,刀和他的手是一体,他是一个身上能长出刀的人。刀从他手臂的顶端长出来,并且在他的血液的浇灌下越发的锋利。
手臂和刀是一体,人身上竟然能长出刀,有着极度恐惧心理的“我”居然有这般奇异的联想。出于对刀的恐惧,只好服输,接过已经熟透的西瓜,不敢跟卖瓜人理论。这一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买瓜经验,让对生命的脆弱有着敏锐感受的作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女性这一瞬间隐秘的心理被作者很好地抓住,并被准确表现出来了。需要指出的是,在格致的《转身》《利刃的语言》以及别的作品中,类似这样通过肢体语言与精致的比喻和拟人化的修辞手法,以此来营构一种在场语言状态的例子,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这些肢体语言与精致的比喻,不但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可感,而且当它与个人的经验,与在场的状态、起伏不定的心理流动,以及一大堆说不清道不明的记忆、感觉、推理、议论纠结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一种不同于传统散文语言的个人语言方式。
在格致的散文中,我们见惯的一些词语常常被重新拆装组合,形成有别于正常秩序的语言错位,由此构成了全新的语言秩序。比如,“走街串巷的小贩,从不羞于自己发出的市井之声,他们担子里担的是瓜果、菜、豆腐脑。这些物质的商品,需要语言的有力辅助,而算命先生贩卖的是语言本身。他们将那些待售的语句整齐地码放好了,每句话都标明了价码,然后用一块干净的湿毛巾严严地盖上了。在买主拿出钱币之前,他不能翻动这些语句,要是风吹进来,词语就会风干,甚至会不翼而飞。在困境面前,算命的找到了辅助之物——两块物质的木板。木板能够发出响亮的声音,这神奇的声音不是语言本身,却有着毫不逊色的号召的力量。”这些描述足以显示格致散文话语所具有的独特感悟力和创造力。再如:“我发现,一些并不见得就重要的只言片语意外地停泊在了我的记忆之河的岸边,而那些大块的故事则如刮掉了几个鳞片的大鱼,顺着水流漂走了。现在,那些鳞片,那些片言只语,也已被时光晒干,抽缩成了一个又一个孤立的词语。”“燕子从形到神都是一把锋利的刀。她一刀插入人类的精神深处,游刃有余地在人的精神脉络中出神入化地游动,既不伤人类,也没有让人类坚硬的骨骼碰伤自己,在不知疼痛的情况下,人类已被小小的燕子大卸了八块。”这些来自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感受世界的方式,借助比喻联想,并经由自由重组、错位搭配的词语,可以说每个词、每个物都有其独特的意义,都自由而舒展地向着各个角度敞开。它一方面表现了艺术思维的可感性和具象性,同时又具有一般比喻所不具备的叙事功能和艺术质感。正因此,它们所描述的那些日常生活情境以及情景所隐含着的那些丛生的意义才这样令人惊讶,令人过目不忘。
三、文体探索与思想深度的融合
作为“新散文”运动最具代表性的散文家,格致在散文创作尤其是文体上所取得的成绩,应该说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的,但她的散文创作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她的反对传统姿态,由于她的创作偏重于个人经验的传达,更由于她喜欢在叙述和语言的利刃上的舞蹈,这样格致就难免剑走偏锋——沉迷于文体的探索而忽视了散文內蕴的丰实。她的一些作品过分纠缠于生活的细节,从而流于琐碎繁杂。比如《庭院》近二万字,主要叙写“我”从怀孕、生育到催奶的过程,以及“我”如何保护大红公鸡最后这只鸡还是被母亲杀掉了,太琐碎,也太喋喋不休了。尤其是作品笫五部分,格致用二千多字的篇幅,不仅详细写了三种不同的小鸡,还不厌其烦写弟弟如何不爱吃鸡冠和猪拱嘴。读這样的散文,读者的确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耐心。还有近期出版的《婚姻流水》,作品主要记录自己十三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取材多是个人日常生活的琐碎事件,如与丈夫在婚姻这座城堡里的相处、冲突,生养孩子的经历以及喂养宠物等等,所涉及的无非就是“我”与丈夫以及“我”与宠物“虞美人”之间,或曰我们三者之间发生的事件,题材面的确流于狭窄,内蕴也不够深厚。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在《婚姻流水》中,格致竟用了近六十页的篇幅,详细叙述收留、喂养小狗“虞美人”,以及为“虞美人”过生日,为“虞美人”寻找配偶,还有描写“虞美人”生产的过程,等等。应该承认,这些描述都很精致细腻,且透出人与动物的亲情。不过在笔者看来,格致关于“虞美人”的描述虽然精彩且富于才气,却难掩一股“小女人散文”的味道,因而其思想价值不及她早期的创作,也不及早期的散文那般自由放松。看来,在散文的“小”与“大”,“浅”与“深”,“情”与“理”诸方面的处理上,格致的散文还有待提高。
此外,格致有一些散文,明显太注重技巧,甚至有玩弄技巧之嫌。比如上面提到的《庭院》文章线索大致可归为两条:一条是“我”作为产妇在医院待产、生产及催奶的经过;一条是“我”小时候在自家庭院替母亲工作及在学校为老师工作的童年回忆,尤其是看护小鸡、照顾弟弟的工作。但文中的叙述跳跃过大,且时有中断,前几段还在写“我”在医院待产的经历,后一段突然就转向“我”在小时候看小鸡孵化破壳而出那一瞬;刚刚还在大谈“我”在庭院替母亲看护小鸡,接下来又转向年幼的弟弟和“我”一起躺在床上发高烧。此外,除了两条主线索叙述的事件以外,作者还插叙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如“我”家院子的布局和构造、母亲重男轻女的思想以及“我”的名字前后几十年的历史。《站立》的叙述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这篇作品的语言富于创造性,生命体验也十分细腻独特。但它的叙述却过于繁重,初读让人摸不着头脑,几番阅读之后才能摸清线索,因为作者设置的阅读障碍太多了。类似的还有《替身》。应该说这篇作品很精彩,但同时它又太艰深晦涩了。因此,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对其作精细分析,一般读者都会被拒之作品门外。像这样故意增设阅读障碍,以智力的优越和故弄玄虚挑战读者阅读耐心的叙述,就多少有点技巧表演性质,在叙述上用力太过了。
由此可见,文体探索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带来散文的革命,也有可能给散文造成伤害。所以,散文如果仅仅停留在文体的探索,仅仅具有一种先锋姿态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这种“文体革命”还带着游戏的态度的成分,就更不可取,更谈不上具备真实和真诚的诗性品格。在这方面,曾经十分迷恋文体探索的博尔赫斯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他认为文体不是作品表层的寄生物,不是仅仅起到装饰的效果,也不是对现有秩序的反抗。文体应是从作家的心灵、气质中派生出来,而且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作为一个真正的文体探索家,博尔赫斯的经验之谈对格致的写作是个很好的提醒。因为从格致的一些散文中,我们看到她的文体探索只是停留于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是明显受到时尚裹挟的对于传统散文艺术的恣意解构。因此,笔者认为,格致若想在散文领域有新的开拓,不能仅仅迷恋于文体层面的实验,而要将文体的探索和追求作品的深度模式联系起来。因文体探索不应是个人或小圈子的孤芳自赏,更不是逃离现实生活的借口。文体探索的目的,是将个性和自我的内心宫殿打开,让社会的氛围、时代的精神、大众的生存和情感,人类的命运融进其间。当然,文体的探索也不是非要打倒传统。其实文体探索也可以与传统共存,可以从传统中吸取有用的思想和艺术资源。总之,在文体探索和思想深度的融合方面,我们认为格致还可做得更多,做得更好。这于我们是期望,而对于格致,则可能是苛求了。
【注释】
(1)南帆:《7个人的背叛·代序》,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陈剑晖,华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