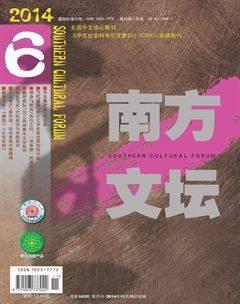自由落体:论林白小说的文学场域
2014-05-30肖晶
文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势必与“性别”有着天然的关联。因为文学的创作者和接受者皆是人,其在社会实践中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体验无疑会打上性别的烙印。这种烙印会以各种方式不同地渗入创作中,对文学文本的内在面貌以及受众产生影响。林白作为广西籍的女性作家,她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带着边缘女性与自然的生命心音,给文坛带来的不仅是审美的冲击力,更是在深层意义上对男女性别二元对立传统思维模式的挑战,开启着从某个特定角度续写人类文学史的新的可能。
一、文学的价值与镜像的隐喻
一个作家不会仅仅因为她的写作本身获得意义,一个人的写作也不可能天然地完全孤立地获得意义。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一书中,张洁从心灵深处发出这样的呐喊:“如果一曲排箫,总在月黑风高的午夜低回,而它低回的音质又如残破的风,随着午夜的蓝雾无孔不入,同时也就无可阻拦地揳进不论‘谁的空间。那个不论‘谁,难免不会陡生愁绪,沉下去,沉下去……哪怕那一天阳光明媚,万事顺遂,不愁衣食,不愁住行,可突然间,就有一种大撒手的沉落,当然,也可以把这叫做无缘无由的自由落体。”(1)如果说张洁的文学书写传达出作家对传统史观的质疑探究和不同人生态度的理解和包容,带给人们对生活,对生命,乃至对人类文明的新的思考视角,其间牵涉到五百年前陌生的异域文化,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况味,那么,林白则以“回忆”的方式叙述,巧于捕捉女性内心的情愫。林白的写作,是内敛的,封闭的,自我指涉的。同时,林白又以细腻、富于感染力和形象感的语言展示了其对中国女性生活和女性情感的独特观察、体验和想象,让人过目难忘。
20世纪90年代,林白正是以《一个人的战争》小说文本被视为个人化写作的代表。林白在题记中写道:“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一个女人自己嫁自己。”(2)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内心往往是脆弱的,战胜一个人的内心就等于战胜了自己。孔子说:“无欲则刚。”作为一个现代的人又怎能做到没有欲望呢?《一个人的战争》很多是涉及肉欲的描写,正因如此,林白的小说反映出了一个人欲望的一面。即使我们的先圣也不例外。古语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人的战争》描写出主人公多米同性恋的倾向,这一定程度上是隐喻着现代人各种各样的欲望,有了欲望就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烦恼。
“我意识不到皮肤的饥饿感,只要多年以后,当我怀抱自己的婴儿,抚摩她的脸和身体,才意识到,活着的孩子是多么需要亲人的爱抚,如果没有必然活着而受到饥饿的孩子,是否有受虐的倾向?”“想象与真实,就像镜子里的多米,她站在中间,看到两个自己。真实的自己,镜子的自己。”这种平实的语言,仿佛将现代的物欲横流社会中的人真面目原本地描寫出来。我们的内心是有许多不可告人的渴望,但能告诉的只能是自己。真实的自己已经变得不真实了,但不真实的自己正是真实的自己。
此后她又以《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致一九七五》《枕黄记》回应了文学价值。她以一种内视和自省的方式拒绝社会、关注自己的内心。这种内视和自省是林白的写作姿态,是女性文化扩张的表达方式(3)。
林白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4)最初在《十月》发表的时候叫《北往》。她以更宏阔的格局与更独特的视角,鲜活灵动地讲述了两代不同知识女性由南方到北京的坎坷经历与精神成长,描摹了社会变革大潮冲击下各色人等的悲欢浮沉,展示出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小说中,海红从广西到北京,银禾、雨喜从湖北到北京,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的一个角落,过着或焦虑或从容或自得的生活。林白的小说,那些隽永、明媚、甚至不乏妖娆的语词,像烟花般盛开在漆黑的夜空,化作点点繁星,照亮了阅读者的眼睛。
无法不爱海红,对着她,我们仿佛揽镜自照,清晰地看见了自己,那个一直处于漫长的青春期因而显得“伤感、矫情、自恋与轻逸的自己”,也看清了自己的梦想与疑难,可能与局限。因此,海红当是林白创作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有了她,那个无时无刻不在骚动着寻求生活的意义的“自我”可以稍微安定一会儿,也因为有了她,个人的弹丸之地可以与广袤的社会连接起来,愈见开阔。当然,海红也处于两个世界当中,一个世界是现实的、日日与之相处的世界。在海红眼里,这世界无非是道良的两居室单元房,那莫名其妙的气味,颀长奇壮的龟背竹,显然,生存的环境是逼仄的,大的文化环境则有一股子虚浮气,人是很难在其中找到归宿的,何况,道良也并非她的良人。海红梦想的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世界怎么样,她也说不清,终其一生,她都在寻找。
海红梦想的世界也许永远不会来临,也正因为此,才深深诱惑着海红,一往无前地去寻找。林白不仅写出了海红在两个世界的徘徊,还要去探寻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那就是打开时间维度,重建一个人的过去。海红将自己所遭遇的生活种种归因于幼年时期情感的匮乏。可不是吗,但凡遇到生活的关节点,那个几乎被所有人所遗弃、在饥饿与困顿中寻找不到出路的小女孩就跳出来了,她几乎左右了海红的所有选择,包括轻率的婚姻,对情感的渴望,对家的依恋,如此种种,不可历数。
不仅在海红自身内部存在着分裂,在小说的其他人物之间,包括史道良、银禾、雨喜、春泱……几乎在每个人身上,世界与世界的区隔无处不在。较之于沉默的、多思的道良和海红,银禾和她的女儿雨喜的出现为这本书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了知识和思考的束缚,加之来自大地的生活经验,使她们成了坚定不移的行动派。银禾的魅力体现在滔滔不绝的“说”中,她把兴冲冲的喧腾的乡村生活带入了海红和道良的寂静中。因为有了银禾,我们的生活是可以五光十色遍地生花的。至于雨喜,那简直是21世纪的新新人类。她有主见,果敢,不怕犯错,甚至有意试错,她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也付出相应的代价,她还有一个虚拟的网上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她想要的那个样子。因此,无论是谁,他们的世界并无交集,尽管他们是血浓于水的亲人。这也是这部小说令人称奇的地方,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不依靠“关系”推进情节,甚至,小说的主要人物之间也并无牵连,就像银禾永远不会知道雨喜经历了哪些,就像海红和银禾之间仅止于诉说与倾听而已。可以说,在这部小说里,林白洞悉了某种真相:世界和世界隔着深渊。这就像海红的父亲柳青林所描述的“两股并行的时间流”:一股必定要走向时间的尽头,另一股是自由时间流,可以逆流而上到达过去也可以快速到达未来。这近似于科幻小说的表述精准地描绘了我们的现在。
世界和世界隔着深渊,却不意味着放弃沟通的努力。我以为,林白的文字恰如一座桥,她引导我们走出封闭的自我的世界,去观照他人的世界;她也提醒我们,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的世界就不重要,因此,反身而诚永远是可能且必需的。
林白的写作,从一面镜子出发,从南往北,从边缘到中心,从蛮荒到繁华,从孤独到激情,出走,回归,碎片,漂移,凡此种种文学意象,无不决定着作家内心的探索走向,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讓作家在黑暗中反反复复地叙述,一直有光照耀,却更为接近真实。
二、寻找归宿与精神重建的幻象
喜欢林白的小说,因为那种往内的探索。这种内省,如安妮宝贝所说,“类似于一个封闭的暗的容器,看起来寂静,却有无限繁盛起伏隐藏其中。亦不需要人人都来懂。因那原就是一种暗喻式的存在。有它自己的端然。就像一个岛屿。断绝了途径。自有天地。”(5)因此,林白的小说,无论是人物的转换,还是故事设定的疑问,那种试图解答,或者自问自答,更像一个寻找的过程,它不存在任何立场,几近一个幻象,只是在黑暗的隧道里渐行渐远,缓慢靠近某种光亮。每个人都在寻找归宿,人们寻找归宿是因为内心某种渴望和孤独使然。“背井离乡的时代,村庄破碎裂成好几瓣,人人尘埃般四散。像尘埃,越飘越远,有些人永远不再返回。”(6)林白在小说文本中更多呈现的是寻找归宿的精神世界,不同时代背景中的不同人物纷纷出场。《北去来辞》的人物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与灵魂归宿,柳海红、史道良、银禾、雨喜、春泱、陈青铜、章慕芳、柳青林、柳海豆、柳海燕……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找到灵魂的栖息之所,有的抵达、有的失落。林白真实地描述了男人和女人的精神活动和情绪心态,他们曾有过的惶惑、恐惧、焦虑,以及紧张探寻的目的和内容。这反映出作家在寻找归宿与精神重建中的自我意识和自构幻象。
林白的文学品质和文学气场,潜藏于笔下的人物中,思考着他们的思考,生活着他们的生活。柳海红、史春泱母女和史银禾、王雨喜母女,她们代表了“北漂”中两种境况:知识分子心灵的迁移和农民工由乡村到城市的漂移,由此迸溅的生活溢满了故事,于是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海红的焦虑、压抑、忧郁,都源于无法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无法找到渴望的爱情和成功事业的道路,“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挤压得海红喘不过气。而所有的兜兜转转都是为了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宿。正如海红,在梦想与现实的割裂中倾心倾力地寻找自己的痛苦过程,这可以看作有关精神处境的“寓言”:确定位置,寻找出路的精神活动。从这一角度而言,林白的写作便具有明显的精神探索、精神重建的性质。
林白对于乡村和城市的历史与现状,有着一种天然亲近和莫名的疏离,在矛盾中透视着一种从容,她文本中的男人和女人,是有温度的,有质感的,是具体的,充满感性活力的。这种“记忆式”的挖掘,在林白的小说文本中,又集中地表现为对童年和家乡的兴趣和向往。童年,是个人的童稚时期的一段生活,也是一个民族甚至人类的童年的、原初阶段的状态。在林白看来,人类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失落了某种东西,造成了各种因素,如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本质与表象、经验与超验之间的普遍分裂。这种追本溯源的努力,带有深刻的悲剧性质,是摆脱精神矛盾的重要途径。
《北去来辞》从“一个人的战争”中走了出来,走进生活,然后寻找归宿。故事的最后,林白带领着笔下众生乘上了穿越时空的回归列车。这是通过“回忆”,沉入存在于“现实”中的“历史”来自我审视,对真实的生活进行评价和描述,其结果达到了“自我”的融化与消失的境界,于是,我是她,她是海红、是银禾、是春泱、是雨喜,甚至还是章慕芳。林白的“自我”融化与消失,最后还是要脱离由精神重建所构成的宁静与稳定的境界,投入到她既爱又怕的现实的纷扰之中去。正如美国小说家汤麦斯·沃尔夫所言:“从这创痛中突然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对于已经消逝几已忘怀了的过去生活的憧憬,渴望那‘苹果树,歌唱,黄金时代的消逝了的日子。”(7)这一切,都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人在外部各种压力下所作出的精神反应。这种精神现象,更容易集中地出现在时代的转折时期,或传统社会发生“解体”和“裂变”的背景下。林白在对待城市和乡村、理性与感情的关系上,理为同情和肯定后者。她强调了乡村村民中符合自然的道德元素的人性,关切、批评“都市文明”对乡村世界的“入侵”所造成的污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算计、虚情假意。
洪子诚提出,“从人类普遍性的心理状态说,支持、肯定变革与担忧传统的东西的消亡给精神带来的损害,这两者似乎是一组难以两全的矛盾。进化与稳定,变革与保护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永恒性的冲突。人活着,也表达着自己的生命,作为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又具有某种不朽性。”因此,林白的写作也存在两极性:在坚守传统、要求继承与打破这种稳定格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8),在力图保存旧形式与渴望创造新形式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矛盾,林白也不由自主地在这种矛盾中烦恼、焦躁,并进行顾此失彼的选择。于是,寻找归宿,成了一种生命的固执,它让林白对停滞的现实和传统的习俗始终保持一种严格审视的态度,作家的审美倾向,与传统的生活气息便有了更多的关联。对林白而言,寻找心灵家园以及对回望的依恋,使她的“为生命写作”的热情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这种审美理想,推动着作家的感情倾向传统的人情、风俗、土地和自然。因而,怀旧、回归作为一种意态,在中国文学中有长久的生命力,成为重要的主题。《北去来辞》文本呈现出“回归”的主题模式,在现实与理想、理性与感情、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与由此产生的“文化后果”的忧虑,以及物质和精神进程不和谐性等等矛盾所织成的“网”中,同样折射出作家的惶惑心态。精神重建,在作家的叙述中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对带有原始特征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同情和肯定,这几乎是林白的情绪、道德向往的象征。
三、孤独者的自由落体与原乡意象
1994年,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发表后,引起中国文坛关注。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小说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之一。林白与陈染等一批青年女作家立起女性主义文学旗帜,成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旗手。此后,林白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仍然关注当代底层和乡村生活,尤其是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在一种更具有本土意味的性别经验中见证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和《青苔》等小说则“构成了文学桂军冲击全国文坛的第一排冲击波和最初的成果”(9)。《一个人的战争》通过多米的成长故事记录了一个女性成长的寓言,这是女性的成长史,欲望,坠落,升腾,凡此种种女性隐秘的人生体验,渐渐勾勒了“你是谁?”“你往何处去?”的哲学命题。小说文本通过寻找归宿,寻找原乡的文学意象,让女性找到了一种存在的方式。
长期以来,妇女在历史和文化中都处于边缘状态。从社会性的角度看,女性在历史中长期处于缺席状态,或边缘化,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场景中很难找得到女性的身影。除了生活形态和方式有差异外,各少数民族妇女和汉族一样,从生物性的角度早已经被命运规定好既定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她们的生活天地狭小,被规定好的角色意识所约束,甚至主动向文化为自己规定的角色靠拢,以求获得男性社会的认同,乃至获得女性自身的认同。这是一个让人无言的悖论。
林白的《致命的飞翔》和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再次出现了女性以血还血的复仇事件,深入剖析了女性生命中的种种局限,呈现出对立的两极互换、互逆的过程。实际上,恰恰是这样的持守弥合着人生的创痛,成就着历史的绵延。在《致命的飞翔》中,林白对自我灵魂的无情撕裂,对苦难记忆的深情回眸,對历史命运的独特反思,对生存意义的无限追问,构成了林白写作的潜在动机。
林白始终将写作当作“宿命”,她的写作,渐渐告别了往日沉湎于语言中的自我,也告别了往日的生活姿态,进入了一种无缘无由的自由落体的境界。“把自己写飞,这是我最后的理想,在通往狂欢的道路上,我这就放弃文学的野心,放弃任何执着。我相信,内心的故乡将在写作中出现。”(10)林白始终把自己放在写作中,并不断以求新求异回归“内心的故乡”,因此,她的小说创作既有延续又有变化,而这种不断在创作路上超越自我的实践,正是她能持续带给我们阅读惊喜的可能。
林白的写作试图找到“历史的逆行”,她的《北去来辞》,无疑是关注当下的,作家的心灵也是敞开的,而我们的审美是否也需要回溯?自由落体式的表达,使林白文字里的意象跨度极大,冲击力也极大。她讲述事情的方式不是按部就班的,锐利直接,甚至出格得让人惊讶。她把普通人羞于用文学表达出来的一切,用自己的真诚变成充满感染力的艺术的语言。她似乎总是在压抑当中看到光明,她把近乎无味的生活场景放入富有诗歌氛围的表述里。从文学创作中林白得到精神上的依托,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一个被文学收留的孩子。她说,在文学中,她无根的病态和焦虑,以及与人隔绝的空虚感,都得到了安放。这就是为什么林白的小说中总会弥漫着一种现代知识女性特有的对人文关怀的缘故。因此,林白的小说穿越了时代和文化的边界,以自己独特的生活资源,揭开了乡村和城市的文明面纱,后面隐藏着奇异神秘的家族历史、故事,尤其是鲜活的女性生命。她的每一次出发,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
【注释】
(1)张洁:《灵魂是用来流浪的》,3页,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
(2)林白:《林白作品自选集》,30页,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3)肖晶、邱有源:《边缘的崛起——论文学桂军的女性书写与文化内涵》,载《学术论坛》2009年第8期。
(4)林白:《北去来辞》,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
(5)安妮宝贝:《二三事》,4页,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
(6)林白:《北去来辞》,335页,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
(7)[美]威廉·范·俄康纳:《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275页,张爱玲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8)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李建平、黄伟林:《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林白:《内心的故乡》,见《秘密之花》,86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肖晶,贺州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