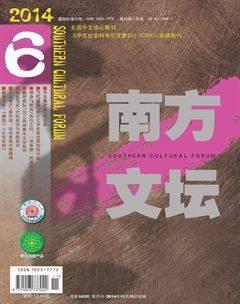贬斥“俊杰”与呼唤“圣贤”
2014-05-30刘川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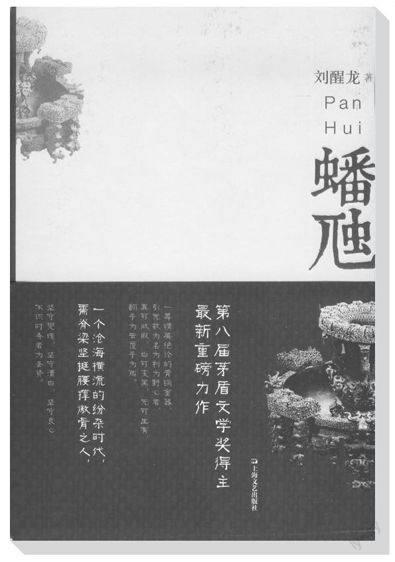
以一群文物考古学家为主人公的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似不多见。以写乡村政治见长的著名作家刘醒龙,最新推出以楚文物曾侯乙尊盘为核心故事的长篇小说《蟠虺》,题材新颖、尖端,令人惊奇、惊喜。老实说,自以为对其人其文够熟悉的了,但第一次打开这本书时,内心里很有一阵震撼,对作者更有一番感服。刘醒龙勤奋聪慧,早被文坛公认。但他以近花甲之年,驾驭如此高难度题材,一个几乎未被当代作家涉猎过的题材,文路之宽,超出了我的预期。勇气可嘉、才华可敬。
这部小说之于刘醒龙是一个勇敢的尝试,成功的探索。他过往的那些充满了时政锋芒、历史反思、体制批判、人性深掘的小说,因带有对时代、政治、革命、乡镇等宏大叙事的紧迫的峻急的表达冲动,因而免不了外露的匆忙的痕迹。《蟠虺》仍保持着刘醒龙对体制和人性关系的双向互动式拷问,却是他最有书卷气、最富文化含量的作品。书名古色古香,题材乃文物界这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落,相关人物对话文气儒雅,叙述语言老辣朴拙,故事结构从容自然、收放自如,情节发展有绵里藏针的机锋,有侦探悬疑小说的神秘,还不时掺杂着浪漫的抒情的细节,是一部好读、耐讀的长篇力作。
春秋楚国的青铜文化相当发达。楚铜器以其富丽繁缛、曲中有直的造型使其在青铜器历史上独树一帜。曾侯乙尊盘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蟠虺》以楚文物奇珍异宝曾侯乙尊盘的扑朔迷离的真伪之辨及争斗故事为主线,描绘了一系列相关人物形象。老一辈知识精英曾本之、马跃之、郝嘉,青年才俊、楚学界后起之秀郝文章、万乙,民间的文物奇才老三口、华姐,文物爱好者沙海、沙璐,以宝物捞政治资本或有政治企图的政界人物如老省长、郑雄,为发文物财而不择手段的商人熊达世及神秘的云南人。作品围绕着曾侯乙尊盘的守护与争夺,展开了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世道人心的刻画,鲜活塑造了“圣贤”与“俊杰”两组人物形象,贬斥了当下盛行的功利主义人生观,赞扬了有气节有浪漫人文情怀的“圣贤”人格、“楚狂式”人格。
圣贤形象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部长篇开头的这两句题词,乃主人公曾本之七十大寿时拼尽全身气力题写,亦是他的人生格言,生命认知的精华浓缩。实际上也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
专业文物研究机构楚学院的院长曾本之,是青铜器专家、楚学界泰斗。他早年得出的曾侯乙尊盘乃“失蜡法”铸造且不可复制的结论,写进了青铜史,并奠定了他在青铜界研究领域一言九鼎的权威地位。然而,年过七旬的他,突然接到一封用甲骨文写的只有“拯之承启”四个字的神秘来信。同事郝嘉二十多年前跳楼自杀、弟子郝文章被捕入狱等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引起他的反思,使他开始自我否定,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失蜡法的主张极有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自己出面否定失蜡法,毫无疑问会引起楚学界的大地震。在经过了痛苦的自我搏斗之后,曾本之毅然选择了对于真理的认同,承认曾侯乙尊盘铸造的年代,中国还没有“失蜡法”工艺。接着,他又撕毁了曾经有所动心的院士头衔登记表,拒绝通过走后门去换取这一曾经梦寐以求的荣誉。
曾本之还惊讶地发现,年年由他检查鉴定的曾侯乙尊盘已经被人调包。围绕着曾侯乙尊盘的真伪问题,他勇于与抢夺尊盘的各方势力斗争,沉着应对,深藏不露。最终以自己的智慧,并凝聚众人之力,揭开了尊盘的真伪秘密,并成功地取回了被盗的真品,放置回了博物馆,为这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博弈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相属”,曾本之是作者倾力打造的“不识时务”的“圣贤”形象。他不识以金钱和利益为处事原则的“时务”,爱名誉更爱真理,敢于否定奠定了自己一生学术声望的成见,放弃院士这个在当今知识界最耀眼的学术头衔,显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和良知,代表了正直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
跟一般小说家塑造一个同行冤家、对头的惯常写法不同,丝绸专家马跃之,热情乐观、聪颖智慧、潇洒大气,是一个与曾本之相映成趣的风流名士。郝嘉郝文章父子,献身钟爱的文物事业,浪漫热情,勇于牺牲,或跳楼自杀以维护清誉,或甘受牢狱之灾而无怨无悔。在他们身上,洋溢着楚文化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光芒。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将圣和贤看作是人生最高的目标,圣贤风骨更被看作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所谓“内圣外王”,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皆是这种圣贤品格的具体体现。圣贤者修心,存思至诚、少私寡欲。修行,弃恶扬善、中道而行,舍己利人、普济众生。与“圣”紧密相连的是“贤”。太史公将“贤圣”与“智者”、“调侃非常之人”视为同义语,贤者是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尊重有道德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使杰出的人各就其位,“尊贤育才,以彭有德”,“天下之士皆悦”(《孟子·告子下》)。通过“贤”而达“圣”,推“圣贤”而广之,从而实现人人“圣贤”,既是一种道德理想,更是儒家推崇的一种社会风尚。
做圣贤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有情结,代圣人立言,做谦谦君子、贤达之士,是其人格理想。现代知识分子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分工,对体制的依附性大为减少。但传统的“圣贤”情结仍为很多文化人的心结,《蟠虺》中的曾本之、马跃之、郝嘉,本以研究传统文化为业,事业志业合而为一,耳濡目染,浸润更深。
中国灿烂的古文化源远流长,从其构成看,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文化严谨朴实、注重实际,南方文化活泼思辨、务求浪漫,已在先秦就形成了特色。在南方文化中,以楚文化最为突出。《蟠虺》通过曾本之、马跃之的形象多方展现了楚文化超越现实、追求玄思、人格独立和自由精神。郝嘉慷慨赴死的壮举乃属楚人轻君重国式传统的现代版,郝文章曾小安的采蜂车之恋、老三口华姐的生死不渝之恋更显现了楚人崇尚快乐、尊重个体、追求爱情的浪漫情怀。
在这个功利主义、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文物界“圣贤”太少,“识时务的”逐利之徒太多,刘醒龙张扬“圣贤”式人物,是心中块垒的曲折迸发。“刘醒龙在把曾侯乙尊盘当成古代留给今人的青铜重器来写时,还发现了另一件古代的重器留存到了今天,这就是文人的理想操守。”(1)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赞美了一种“理想人格”,即能表现文化精华的一种人格。这种人格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更有楚文化的区域特点,是刘醒龙对当代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画廊的丰富和贡献。
所谓“俊杰”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注重个体道德的崇高性、严肃性,突出道德人格的自觉、自成与自爱,因此,特别强调“君子与小人”的严格界限。如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里仁》)。
道德靠自律,种种非道德的行为是因为现实功利的驱动而使某些人道德失据。因此古代泛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圣贤君子自有圣贤君子的操行,而势利小人自有冠冕堂皇的“识时务”的理由,那就是实用理性支配下的处事态度。
李泽厚曾经指出:“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它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在先秦儒、道、法、墨诸主要学派中。”(2)从世界观的层面看,实用理性与纯粹理性判然有别。纯粹理性关注诸如世界的本质、运动的规律、思维的形式等形上的或抽象的问题,而不考虑实际的功利的效果。实用理性则与之相反,只关心实际的利害、现世的功利。我国古代缺少发达的本体论、形上学,宗教的影响也不够大,可以说与之有关。
实用理性轻遐思玄想,不寻求超越此岸世界和世俗人生的终极意义,只执着于当前世俗的实然状态和自发倾向,只注意日常生活和普通行为的利益原则,急功近利,讲究实用。生存本身就是最高的原则,任何其他的原则一旦与这个最高的原则发生冲突,就面临被弃置的命运,人文精神严重萎缩。这种实用操作型的“中国式智慧”,养成了为私欲私利而无特操、善变通的“俊杰”人格。晏子云:“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晏子春秋·霸业因时而生》),意思是能认清时代潮流的,聪明能干的人,方可为英雄豪杰。认清时代潮流形势,才能成为出色的人物。“儒生俗士,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卧龙、凤雏。”(《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晋·习凿齿《襄阳记》)指看清时局的明达善对之士。而在日常政务军事商业活动乃至民间纠纷争斗中,“识时务者为俊杰”则是当事人的抉择哲学或旁观者规劝看不清时局情势、执迷不悟者的习用语,表明它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过分的实用主义必然导致功利主义,而事事从功利出发,产生了大量“识时务”的“英雄”。在《蟠虺》中,郑雄、老省长、熊达世等皆是这样意义上的“俊杰”,他们代表了与圣贤人格相对立的世俗功利人格。老省长靠清算盘查楚学院学潮风波起家,他的发迹史肮脏丑陋,但却平步青云、步步高升。退出权力一线了,还在借文物兴风作浪。熊达世本是一商界混混,装腔作势、颐指气使,手段恶劣,本事通天。
此类人物中作者用力最多的是郑雄。郑雄本为一介书生,却以知识捞取政治资本,以楚学院而水果湖而中南海,是他的人生设计。学问之于他,不是求知的趣味、不是真理的探寻、不是纯粹的事业、不是才华的证明,而是走向仕途的敲门砖。为达目的,他八面玲珑、巧言令色、不择手段。他讨好楚学权威曾本之,陷害比自己更有才华的郝文章,甘戴八年绿帽子,谄媚老省长。他人格极度扭曲,成为“伪娘”式人物。“伪娘”一词乃郑雄名义上的妻子曾小安发明,可谓一针见血。为了充分利用曾本之朝上爬,郑雄不惜与曾小安做了八年连岳父母都看不出多少破绽的假夫妻,伪装的功夫真真一流。在新省长见面会上,恭维省长是21世纪的楚庄王,一副令人作呕的奴婢口吻。马跃之入木三分地讽刺他:“只不过这种伪娘,三分之一是潘金莲,三分之一是王熙凤,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盘丝洞的蜘蛛精。”所幸他良心未泯,终在曾侯乙尊盘之真品失手的关键时刻倒向了正义一方。
郑雄长于钻营、精于算计、善于投机、处处利己,显然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郑雄、老省长、熊达世之流,虽出身不同、性格有异,但都是这个时代的顺应者、弄潮儿,或为升官、或要发财,没有理想、不顾尊严、不讲人格,只求实利,他们是贪欲时代的典型代表。当下所谓“时代英雄”,所谓“成功人士”,所谓“弄潮儿”,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识时务者”。他们收获了名利,却扭曲了人性,失去了人文情怀。这一类人物,是中国传统中的反道德的实用理性处世哲学在物欲膨胀的当下的反映。在作者笔下,所谓“俊杰”,实乃巧取豪夺之士,所谓“人精”,实乃人渣。
青铜重器的寓意
在这个价值多元、价值混乱的时代,作家何为?刘醒龙不仅有质疑、反思和批判,更有追寻和建构。在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潮中,近些年的长篇小说较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可资进行现代性转换的积极资源。《蟠虺》把目光转向辽远、神秘的楚文化,但不是一味顶礼膜拜、一味唱赞歌,而是崇仰中有甄别、有审视,它再现并弘扬了楚文化的精魂,又通过乱象丛生的文物界这个切口展现并剔除文化垃圾。
《蟠虺》的写作周期不到两年,但在刘醒龙心里却酝酿了整整十年。2003年夏天,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他头一次注意到了精巧绝伦的曾侯乙尊盘。朋友告诉他,曾侯乙尊盘的最神秘之处在于当代还没有人能破解它的制作工艺。从那以后,他每隔一阵总会去曾侯乙尊盘面前怀想一番。在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他购买了上百本青铜方面的书籍,一个以青铜器为核心的故事逐渐成型。“楚国用青铜铸造战争机器,随国用青铜铸造国之重器。千年之后,我们所看中的偏偏是后者。希望我与我的同时代人能够一起明白,何为国宝何为重器。”(3)
青銅重器之于刘醒龙、之于《蟠虺》,是一个情结、一个隐喻。在春秋时代青铜器是国家的象征,在《蟠虺》中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器物,而有着深刻的寓意。尤其是无价之宝曾侯乙尊盘,蟠虺纹饰令人叹为观止、内部构造至今无法复制,工艺精美复杂,气质华丽高贵。“最终促成《蟠虺》的,是近几年伪文化的盛行而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虺五百年为蛟,蛟千年为龙。当今时代,势利者与有势力者同流合污,以文化的名义集合到一起,不是要为蛟或者为龙,其蛇蝎之心唯有将个人私利最大化,而在文化安全的背后,还隐藏着国家安全的极大问题。”(4)小说以关于曾侯乙尊盘制作法的学术论争为切入点,批判的锋芒直指当下知识分子,既包括文化缺失、唯利是图的收藏界,更放大到不端和腐败行为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学术界,这些贪婪之徒不仅有“惯于歪门邪道、偷天换日的贪贼”,也有“强权在握的明火执仗者”,大胆揭露了学术腐败的社会问题和贪欲横流的社会问题。“一件在地底下埋了千年的珍贵文物,在刘醒龙的手上成为一面照妖镜,照出了现实生活中那些冠冕堂皇的强权者的真实面目,他们的贪婪欲望可以将一切都吞噬进肚子里。天真的学者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他们的生命。”(5)
对青铜重器的辨伪,是人心邪恶之辨,政商奸侫之辨。“国宝重器被赋予了远远超过它历史文化价值的象征意义,而寻找它所经历的种种扑朔迷离的过程,也就成为一部思想文化和学者人格的长篇寓言。如果说此前作家这样的敏感,或许会被认为是一种空穴来风的想象力过剩的话,那么在今天,随着某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重大贪腐案件细节的纷纷披露,作者所传达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学术界的乱象与黑暗,就是在直面当下现实问题,有着居安思危的深重忧患。”(6)所谓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并非只指一件文物的真伪与得失,而是从文物界学术界商界政界那些蜂拥而至、挖空心思借国宝而追名逐利之乱象中,显现了令人担忧值得警醒的文化溃败之势。
“《蟠虺》的价值含量是丰富的,作品呼唤的是对真的坚守,是对良心的忠诚,是对欲望、利益的抵抗,是人对自身的超越。这样的价值理念是需要与其对立的力量去压迫、毁坏、催逼和诱惑的,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其坚韧、纯洁与稀缺。”(7)
这些看法颇为精到,抓住了作品思想内涵的精髓。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小说积极而深刻的意蕴是通过对一系列人物的细致描绘和情感褒贬来体现的。小说中人物马跃之所谓“与青铜重器打交道的人,心里一定要留下足够的地方,安排良知”,青铜器仿制天才老三口在狱中彻悟之后所说的“非大德之人,非天助之力,不可为之”等话语,都是对青铜重器品质的理解。青铜器乃国之重器,具有厚重的文化含量,国之重器与人之圣雄,互为辉映。曾侯乙尊盘这样的国宝重器在小说中更是一种功业与德行的象征,天造地设,唯有德者配之。《蟠虺》以鼻屎般的卑劣人格作对照,有对贪欲时代所谓成功人士即“俊杰”的人性拷问和批判,更有对“圣贤”人格的赞颂与呼唤。它激发我们思考:在一个旧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和计划体制分崩离析、一个新的市场体制和文化多元时期,当旧的社会理想已经失去了感召力而新的理想尚未出现之际,“圣贤”会应运而生吗?作为新的理想人格的引领者、精神领袖或思想“圣贤”,曾本之们这类“蟠虺”式的精英人物,以“蟠虺”传楚文化的香火,为诡奇瑰丽的楚文化招魂,以青铜炼人、造魂,彰显楚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当代价值,具有何种承传的可能性。
当代有很多优秀小说家,但一写到当下,则往往笔力不支,价值游离混乱、笔法匆忙杂乱,刘醒龙对当下作了较为扎实深切的回应。《蟠虺》是一部凝重、大气之作,是一部批判性超越之作,标明了刘醒龙艺术功力的厚实和创作境界的再一度升华。这部小说是当代文学和荆楚文化史上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创造,也是2014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注释】
(1)(5)贺绍俊:《青铜重器的分量》,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
(2)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见《说西体中用》(李泽厚旧说四种),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3)歐阳春艳:《刘醒龙推出新书〈蟠虺〉:颠覆主流考古观点》,载《长江日报》2014年6月11日。
(4)刘醒龙:《写作者必须有强大“防火墙”才会有独立自由》,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5日。
(6)李星:《一部关于德行的寓言小说——刘醒龙〈蟠虺〉的一种解读》,载《光明日报》2014年7月7日。
(7)汪政:《刘醒龙长篇小说〈蟠虺〉:价值、知识与话语》,载《文艺报》2014年6月9日。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当代湖北文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