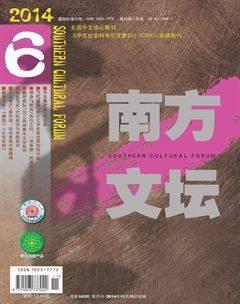徐则臣京漂小说的人文精神与身份意识
2014-05-30徐秀慧
我对大陆当代小说的阅读仅止于先锋、新写实之前,对于90年代后逐渐崭露头角的70后作家知之甚少。这也相对说明当代作家笼罩在新时期文学的光环底下,70后作家出道之艰难。这次受中国作协的邀稿,随机地选了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花了两天,一口气读完,说明他的小说可读性很高,我猜在大陆应该也有很多读者。
《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篇小说集里漂浪的小人物,颇符合我对北京街头小人物的印象,无论是情节发展、人物对话、性格与命运,都以非常直白的口语化风格,描写从土崩瓦解的农村、小城镇来到北京,连暂住证都没有的黑户,即所谓的“京漂”。就这个题材而言,我认为这是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非常务实的选择,在大陆评论界也颇受好评。在这篇小文里,我想谈谈徐则臣“京漂”系列小说中对人文精神的一点坚持;以及作为一个对于城乡发展相当敏感的作家,他自认为是这些“京漂”的一分子,写“京漂”就像是在写自己一样,这样的身份意识蕴含了令人玩味的一种务实的处世哲学。
仔细阅读收录在《跑步穿过中关村》三篇小说中的“京漂”,并不仅仅是写从城镇来到北京碰机遇的、一般世俗化的服务员或出租车师傅。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是中等教育的有文化的“京漂”。他们在北京谋生的方式也得凭借着一点现代知识或文化素养,如《西夏》中开书店的王一丁,《啊,北京》中还在苦熬等待出头的小说家“我”、攻读法律博士的孟一明,《跑步穿过中关村》中也有一些考研、攻读博士学位的配角。除此之外,小说中借以表现“京漂”的象征人物,主要是那些为了留在北京,不得不铤而走险地卖盗版光碟者,如夏小蓉,或是兜售造假证件的流动人口,如边红旗、敦煌等。其中又以最常被提到《啊,北京》中的边红旗最具代表性,可以涵盖徐则臣这一系列北京小说的社会意义。
人长得帅气的边红旗,原本在苏北小镇算是块招牌,是个颇具口碑的杰出中学教师。他有个贤惠的妻子在小学教美术,生活本来可以恬静美好地过下去。直到地方财政拮据,拿学校教师开刀,每月工资减半,边红旗在小镇上仅有一点的成就感被取消了,偶尔诗兴大发写写诗的乐趣也消逝得无影无踪。小镇上脑筋活络点的年轻人都到外面的大好世界去闯荡了,继续留在镇上是毫无出路的。边红旗也在2001年带着一本诗集和老婆坚持让带的一套中学语文课本进了北京城。边红旗一到北京就爱上了北京,觉得自己站在北京的天桥上就像站在世界的屋脊。但是他想找工作糊口,却因为没有暂住证屡屡碰壁,不得已只好放下身段,与投靠的亲戚一起蹬三轮车,但是亲戚却受不了这样出卖劳力的低贱生活,返乡了。边红旗对此却丝毫不以为意。有一次,因大意闯了红灯,没有牌照的三轮车也被警察没收了。熟悉现代文学的读者,大概都会联想到老舍的《骆驼祥子》。但是接受过现代文化知识洗礼的边红旗比骆驼祥子更幸运的是,他生活在北京成为大国崛起的中国首都,他也比祥子更机灵、更懂得人情世道。只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也只好下海兜售造假证件的非法生涯。蹬三轮车出卖劳力,得要克服贬低自己的心理障碍,边红旗当时为能够自食其力地留在北京感到惬意,三不五时还跑去北大听听久闻其名的学术大师的讲座。但是,兜售假证的非法暴利,则必须突破道德防线,边红旗原本还矜持着“犯法的事,我不会”,在小唐一句“吹牛又不犯罪”的怂恿下,好像感觉不到在犯法地上了小唐的贼船了。
在徐则臣的笔下,显然无意苛责这些“非法的”城市边缘者的道德感低下,甚至还赋予他们在人格上的胜出,他们关于这世界的公平正义自有一套准则,对于人情道义有时还挺坚持。叙述者“我”,为了节省房租,让边红旗搬进小楼时,也认同边红旗在诗人朗诵大会义正词严地朗诵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反战诗,“人的确不错,没事还写诗”,并藉此说服了在攻读法律博士的室友孟一明、沙袖小两口接纳了边红旗。边红旗只要大发利市,就会请室友们吃吃水煮鱼、打打牙祭,因为他的钱来得容易。在这种情义相挺的互惠原则下,这些小知识分子连带地也很快地接受了边红旗婚外恋的对象沈丹。在大国崛起的北京城,人情道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的封建道德,而是一套与时俱进的、非常务实、精打细算的人情道义。
小说的情节也非常简单,围绕着交代边红旗怎么与原来房东的女儿沈丹发生恋情,以及沈丹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逼着边红旗离婚而进行的。边红旗找不到理由与贤淑得没话说的边嫂离婚,采取拖延战术。在北京SARS疫情蔓延的期间,迫于沈丹的施压,边红旗由小唐陪着,两人骑着单车横过千里就为了返乡离婚。但一见贤淑的边嫂,边红旗始终开不了口。但是边红旗却目睹小唐与边嫂亲热而爆发冲突,砍断了小唐的两根指头。小唐的理由是因为边嫂打听沈丹的事情,为了安慰边嫂而情不自禁,并希望藉此能帮边红旗达成离婚的目的。我在看这一段情节的时候,总觉得像是闹剧。并且纳闷着徐则臣在处理边红旗的情爱纠葛时,完全缺乏人物内心意识的描写,而纯粹以事件或是与叙述者“我”的对话,来交代他的心理发展。这自然是因为小说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有限叙事观点,由旁观的叙述者“我”根据事后的发展来叙述这整件事的。
但是刻意不寫人物内心世界的分析,几乎是徐则臣北京系列小说共通的特点。譬如《西夏》中叙事观点采取的是主人公王一丁的第一人称叙事,他在面对自己与哑巴西夏日久生情,却又对来路不明的西夏感到恐惧时,徐则臣也很少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处理情感的纠葛。有一次两人出游时,王一丁临时起意将西夏留在开往南京的列车上,在火车开动前跳下车,此一情节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显然,这是作者绕开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盛行的意识叙述,刻意采取的一种叙述策略。但这对于很习惯在小说中清晰明朗的接受作者交代人物内心意识的读者来说,这自然也包括我,总是有点不太习惯。于是我花很长的时间去思考徐则臣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叙事策略。我刻意到网上去看他的乡土小说《花街》,发现徐则臣描写乡土风俗时,一样是个说故事的能手,但同样刻意以事件和对话来呈现人物内心的冲突。后来我终于想通,这样的叙事策略显然与作者的世界观是相应的。
我在看完这一系列的北京故事时,总觉得很疑惑,徐则臣并没有很明确地交代这些“京漂”离乡背井,冒着被捕被拷打被罚款,完全丧失做人的尊严,仍执拗留在北京的理由。我想如果仅仅是为了逮到一个机会就可以在北京发达似乎不能说明这种执念。小说中当然也不乏受不了这种煎熬,想要归返温暖家乡怀抱的小人物,例如边红旗的老乡,或是《跑步穿过中关村》中自认为存够了老本的夏小容,想要与恋人矿山一起返乡结婚生子,矿山却还想再大捞一票而无法如愿。这些明知犯法的“京漂”在小说中,最终当然都没有好下场。边红旗爱的是边嫂,与沈丹的爱恋,纯粹为了慰藉在北京的寂寞生活,同时如果和沈丹结婚落户,还可以成全他的北京梦。边红旗出事被捕后,沈丹与他建立在性基础上的爱情也走到了终点,最终还是得靠边嫂连夜从乡下进城来保他,他终究无法在北京继续漂浪下去。边嫂的夫妻伦常情义终结了他的北京梦。徐则臣借此暗示着,北京梦的诱惑,就像露水姻缘一样,一旦梦醒,春梦了无痕。因此徐则臣的“京漂”小说背后联系的还是他颇具理想性的中国乡土意识。
徐则臣曾经说过:好小说是“形式上回归古典,意蕴上趋于现代”。所以他在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这些现代性社会发展下,从城镇小知识分子沦落到城市底层的小人物时,或是另一系列描写乡镇的风俗故事时,总是刻意跳过新时期面向西方、面向世界的艺术手法,而回归到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的路数。换言之,我认为作者说故事的艺术形式,颇有意识地企图想要描绘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小人物众生相。只是当作者发现封建道德意识早已不是束缚众生存在的尺规时,当个人意识抬头,家庭伦常也无法羁绊现代人的情欲自由时,现代性的身体诱惑与物质欲望却如猛兽一般吞噬人的灵魂。徐则臣让他笔下的小人物,沉沦在肉欲与金钱的茫茫大海中,借此批判靠法律维持的现代社会体制的国家机器的冷漠以及执法人员的贪赃枉法。与徐则臣的“京漂”小说相对的,还是那个情义兼具的乡土社会。
说到这里,沈从文城、乡对立的小说世界观悠然浮现,徐则臣当然也知道沈从文寄托的那个情义乡土乌托邦,在发展主义挂帅的现代消费社会已经回不去了。所以他并没有像沈从文那样刻意去美化乡土乌托邦的情义世界。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是,当一群小知识分子说不出北京到底哪里好時,边嫂第一次到北京探亲,边红旗带她到西单逛街,她完全没兴趣,她最想看的就是幼儿园开始被教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所以她想要看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天安门!当见到天安门没有她想象中的高大雄伟时,“她哭得很认真,很伤心!她画了这么多年的天安门,原来是这样的。”边嫂在边红旗宿舍撞见沈丹,对着沈丹宣示完她原配的主权之后,毅然地回到苏北乡下继续当她的小学美术老师。从来不认为北京有什么好的边嫂其实才是牵系着《啊,北京》这篇小说的灵魂人物。徐则臣在这里透露了他的身份意识,他认同的还是那个务实的安于城镇的理想生活,如果城镇不是那么没有出路、令人绝望的话。
小说令我感到最有趣的是,边红旗的北京梦除了无法抵挡性爱与金钱的诱惑外,其实也寄托了徐则臣的人文关怀在其中。小说开场边红旗的反战诗,与小说结尾边红旗内疚于砍了小唐的两根断指,一肩扛起卖假证的罪责。相对于依赖徒有其表的律法制度维持的体制,边红旗具有反对美帝、维护世界正义的人文理想,对于堕入与北京城里贪赃枉法的执法人员相对立的黑道兄弟也更有情有义。也是在这种对比之下,徐则臣在边红旗身上寄托了那么点人文精神,并且在诗人朗诵会上大大讽刺了那些言不及义、念着让人听不懂内容的诗人,也大大调侃了那些勇于自我表现、就自以为是诗人的群众。只是在金钱万能的城市法则底下,无论是边红旗,或者是想要写出非消费市场取向的小说的叙述者“我”,他们的人文精神或是对情义的坚持,都显得有些囊中羞涩,显得有些痴人说梦,徐则臣在描绘他们的形象时都不及边嫂形象显得自信而安稳。
我想回过头谈谈我的北京经验。作为一个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戒严体制教育底下成长起来的世代,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是1998年初冬跟随吕正惠老师参加了作协举办的黄春明研讨会,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台湾乡土文学的经典作家黄春明。印象中,那是个到处都是工地的北京,除了开会,我让吕老师领着到西单的图书大厦逛了一圈之外,哪里也没去,但是八层楼的图书大厦,每一楼到处都挤满了买书、看书的人。我想有着能把八层楼的图书大厦挤满了看书的人的北京读书市场,要实现能够抵抗消费社会的人文精神,应该是有希望的吧?!我总认为人口过度集中却不适合人居的大都会,应该是历史的过渡。希望把边红旗领回乡的边嫂理想中的城镇生活,不会是另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徐秀慧,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