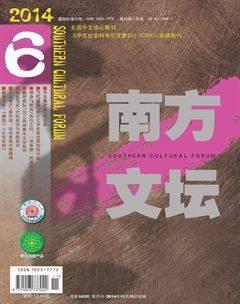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
2014-05-30吴赟
白睿文(Michael Berry),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教授、东亚中心主任,美国当今活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文学及电影评论家。著作包括Speaking in Images: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光影言语》),A History of Pain: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Jia Zhangkes Hometown Trilogy(《相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与《煮海时光:侯孝贤的电影世界》。译作包括王安忆《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2007)、余华《活着》(To Live,2004)、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Nanjing 1937:A Love Story,2003)、张大春《我妹妹》与《野孩子》(Wild Kids:Two Novels About Growing Up,2000)。现正在进行舞鹤《余生》与张北海《侠隐》的英译。
吴赟:白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也是关涉到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问题。您是在这一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曾翻译了余华、叶兆言、张大春、王安忆等多位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而且译作在英语世界的反响都很不错。同时,您还担任过红楼梦文学奖的评委,台湾电影金马奖的评委,也在包括《新京报》等众多报刊发表过文章。我想听一听您对于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我想先从您作为翻译家的这一身份问起。您从1996年开始翻译余华的《活着》,之后是叶兆言、张大春、王安忆的作品,到现在正在译的舞鹤的《余生》。原作千姿百态,您是如何选定这些不同的作品,开始翻译的呢?这些翻译选择是纯粹出于个人兴趣,还是由出版公司指定推荐?
白睿文:到目前为止,我所翻译的作品,全部都是我自己挑选的。也有不少出版公司约稿,给很可观的稿费,但都没有谈成,多半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作品。我做翻译纯粹是出于爱好,一定要自己非常喜爱这部作品,才会把它介绍过来。翻译就像谈恋爱,译者一定要对作品有很强烈的感觉,真的要爱上那个作品,不然长达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翻译过程会非常痛苦。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美国市场,要考虑在美国、在英文世界里有没有读者会喜欢这本小说。如果一本小说你很喜欢,但翻译之后没有出版公司愿意出版,那也是没有用的。比如翻译《一九三七的爱情》就受到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启发。当时《南京大屠杀》刚刚出版不久,在美国引起轰动,我就想美国读者也会对《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感兴趣,愿意去阅读它。不过这是次要的原因。我在南京住过,研究过南京大屠杀,自己也特别喜欢这本小说,觉得它有点重写《围城》的味道,是一本向钱钟书先生致敬的著作。而且这本书也挑战了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应该说它是南京大屠杀的前传,书从1937年1月一直写到屠杀开始,南京城被完全毁灭,那段时间——南京在民国时期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作者还原了1937年南京的另一种面貌,这是我选择《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进行翻译的出发点。我首先是以自己的兴趣,以自己的文学观来判断,同时市场也是要考虑的。
另外,我对作品的选择没有局限,不会仅限于大的叙事小说或者当代题材之中。选择不同题材的小说是给自己的挑战和鞭策,可以让我进入不同的文学世界。不過有些题材我可能不太会去翻译,比如武侠小说,虽然我现在手上还是有一本现代武侠小说在翻译中——张北海的《侠隐》。一般的传统武侠小说篇幅相当长又有很多专用词汇很难在英语中表达,而且武侠小说在美国市场一直不太成功,十分冷门,当然武侠电影是最受欢迎的流派,那是另外一回事。
总体来说,我喜欢用开阔的心理来面对翻译。对作品的选择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作品是否写得好,自己是否喜欢。碰到好的小说,刚好自己有时间,那我就会去接,尽量去做好。
吴赟:你最初接触《活着》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之后才看到小说原著,再开始翻译。能否请您谈谈是什么触动您开始翻译《长恨歌》的呢?
白睿文:早在1999年,我就觉得应该翻译王安忆。当时她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不多,除了“三恋”系列,《小鲍庄》等早期作品,其他重要长篇都没人碰过。我当时大量阅读了她的作品,其中最喜欢的就是《长恨歌》,非常想把它翻译成英文,但同时,我也有些犹豫不决,因为这本书翻译难度很大,开篇三十多页都在描写上海的弄堂,直到四十页才开始出现人物。这样的写作方式会给外国的读者带来不小的挑战,而且叙事风格也不好译。所以当时也想去译她的另一部作品《米尼》,篇幅较短,故事性强,叙事简单。就这个问题我和王安忆商谈了半年多。但后来还是选择了迎难而上,翻译《长恨歌》。除了自己喜欢之外,还因为这本书的确是当代文学经典,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佳作。虽然挑战性更大,但是我还是愿意尝试。
吴赟:您所翻译的作品,作家写作风格都很不一样,比如张大春是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余华是写实主义,而王安忆是细致的女性叙事,作家这些差异巨大的写作风格有没有给您在翻译过程中带来困扰?您是怎么处理这种差异的呢?
白睿文:身为译者,我希望读者看不到Michael Berry的风格。我希望我扮演是一个透明人的角色。通过我,原作可以在英语环境中开口说话,来表达原作的精神世界。我的翻译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译得好。如果在译本中我带有个人的风格,那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译者。每一个作家都不一样,译者不应该让读者在译本中感觉作品有共同点,不应该让读者通过译者的文字风格把作家联想在一起。每次开始翻译一本新作品的时候,我都要努力去寻找每一本作品的声音和风格,和切入它们的视角。我会在正式翻译前做一些实验,去看看哪种时态、哪种语气、哪种词汇最符合原作精神,最能够显现原作风格。
吴赟:在翻译的过程中,您觉得什么问题是最困难的?是逻辑?时态?词汇?还是其他的文化障碍?您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白睿文:每一部作品特点不一样,对翻译的要求不一样,遇到的困难也就不一样。有的是时态,有的是历史背景,有的是人名、地名,有的是当代文化的一些典故、对政治的影射,真的每一本书的难点都不一样。这些都要在翻译中考虑。比如《长恨歌》里开头和中间大段的散文式的描写,叙事的那种语气、语调,我做了很多实验才找到让我满意的语境来表达。再比如翻译人名,在有的书里我用的是罗马拼音来译,有的书里是把意思译出来,有的书则是音译意译混在一起,每本书都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再比如王安忆的作品,从“三恋”到《长恨歌》到《米尼》到《天香》,每一本的风格都不一样,翻译的时候也就要用到不同的方法。
吴赟:中英文化确实差异巨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是忠实于原文,还是照顾英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在这两者之间,您是如何取舍的?您是否愿意为了增加在海外的销量,使得海外读者获得更好的阅读感受,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白睿文:有一些妥协我愿意去做。每一本书的情况都不一样。首要的是和原作者商谈这件事情,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不牵涉到作者,纯粹看我个人翻译的决定,那我尽量不做太大的妥协。否则我觉得就失去了原作的精神,但有时候因为两种语言差异太大,不得已会做些修改、删节,有时候这也是必要的。
吴赟:在翻译的過程,您和作家的联系多吗?译者是不是需要经常和作家交流,来解决翻译中的一些难题?
白睿文:在翻译过程中,和作家的联系一般来说不是很多。翻译是非常独立、非常孤独的工作,但是偶尔会有问题需要向作家请教。比如在翻译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时,我发现几个逻辑上的小问题。这篇小说最初是在某个文学期刊上连载,之后缀合成长篇出版,编辑在整理时可能没太注意文字的前后呼应,出现了一些逻辑上小小的不合拍。例如在小说开头说到主人公丁问渔扇了日本妓女一记耳光;但是在后半部,出现了“丁问渔这一生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女人”的文字。对于这种前后不合的情况,我也不敢直接改动,就和作家本人联系。作家一般都很慷慨,允许我做小小的改动。读者一般不会留意这样非常微小的细节,但作为译者,这些细节都在视野之中。毕竟没有比翻译更加精细的精读了。幸运的是我所合作的作家都在世,能够直接向他们请教,得到他们同意之后,我再进行修改。如果是诸如鲁迅、老舍、曹雪芹等等大师级的作家,一旦出现类似的问题,处理起来就会比较复杂。因为我觉得译者没有权利轻易去改变原作。如果真有那种情况,就需要加个注解,或者寻找其他方式去解决。
再比如张大春的作品往往把虚构和真实混淆在一起,到后来作家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编造的,哪些是确有其事,这也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小说《我妹妹》里,作家说他引用了一段圣经的话,我把《圣经》上上下下读了好几遍,都找不到这段话。我再去问大春,他说不一定是取自圣经,可能是取自Dead Sea Scrolls(《死海文书》),我又去找,还是没有找到。又问大春,他说也有可能是取自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的某本经书。当时我正在纽约读博士,为了求证这段话就到圣公会的教堂找牧师帮忙,在教堂图书馆查阅原文,这才对应得上出处。
还有一个例子,小说中提到在东南亚的一个岛上有个少数民族叫“多布人”,我查了各种字典、辞典,都找不到相关的信息。问了大春,他说不是虚构的,确实有这样一个部族。我就开始上网找资料。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远不如今天资讯发达。不过十分幸运的是仍然找到一个有关少数民族的网站,我在下面的论坛留言问有关“多布人”的信息,过了几个星期,有人回帖说确实有这么一个少数民族,而且给出了相关的英语译文。现在网络已经四通八达了,各种信息都很容易找到。但当时远远不是这样。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多这种小细节。做翻译真的很辛苦,译者就像冒险家,东跑西跑,四处寻宝,十分刺激,也十分好玩。
吴赟:在您翻译的所有作品中,您最喜欢哪一本?
白睿文:我对《野孩子》有一种独爱。刚才我说到译者就是冒险家,这种感受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最深刻。里面有很多词非常难译,为了译好一个词,常常要上网站找资料,请教台湾朋友,要琢磨很久,就像一个个小小的语言游戏。不过后来都想到一些非常美好的方法来解决,想出了很多有创意性的译法。譬如里面讲到小孩刚学会说话,发音不准,容易把“爸爸”喊成“粑粑”,原文强调小孩的发音听起来像“狗屎粑粑”,我想了很久,在英文里找到了“pop(爸爸昵称)”和“poop(拉屎)”的对应。这本书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翻译的过程中与作家的联系也是最多的。每次灵感来了,找到一些非常好的解决办法,会觉得非常美好。
吴赟:在翻译《长恨歌》的时候,您有一位合作者——陈毓贤老师(Susan Chan Egan),能否请您谈谈这一翻译合作的情况?合作翻译的产生效果是否会比独自翻译要好?
白睿文:合作翻译挺好的,不过过程比较复杂。《长恨歌》的第一和第三部分是我翻译的,第二部分是陈老师翻译的。两个人翻译风格很不一样。译完之后,两个人都对对方的译稿进行修改,之后我又花了很多时间来统稿,做了整体风格的统一。接着还请了哈佛大学的一位博士做了文字上的统一,再送到出版公司,由编辑再次统稿。翻译本身就很复杂,再加上两位译者的语言风格不一样,后面编辑任务会重一些,要经过很多层次、很复杂的修改工作,也要花费很漫长的时间。总体来说,合作翻译的译本质量比单独翻译的要好,但是付出也很大。
吴赟:出版社为了照顾到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常常要求译者对译作进行一定的删减和改动,舍弃作者某些文学特质,使作品更为美国化。《狼图腾》的翻译就是这样。作为译者,出版社是否也要求您对译作进行删减和改动,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白睿文:我主要是和大学出版公司合作,他们的好处是比较尊重译者和原作。商业出版社则比较大胆,往往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活着》的英译本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的。那时编辑寄回给我的译稿,满版都是密密麻麻的改动,我觉得他改得有点过了,离原作的意思有点远,于是我就把那些改动都还原,再寄给他;等他再寄回第二个版本,我发现他又改回了他自己喜欢的文字风格。这样来来回回,打来打去。有时我打败了,有时我打赢了。而大学出版社这种情况比较少。
吴赟:为什么大学出版社会相对尊重原作?编辑对译作的改动会比较少呢?
白睿文:对大学出版社来说,能卖出几千本就算是不错的业绩。而商业出版社即使卖出几千本,还是亏得很厉害,因为他们的投资比较高,会做大量的宣传。而且他们对出版风格都有整体要求,要求所有书都要达到一个标准。大编辑的权力很大,会去干扰书的形成,对语言做很大的改动。这里涉及不同的写作出版流程。在美国,编辑代表出版公司向名作家约稿,作家往往会一边写一边给编辑看,编辑就会给出建议,比如“结尾要不你这样写?”作家也往往会配合编辑的意见。也就是说,美国作家和编辑的合作关系往往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形成。而中国的作家因为语言不通,只能由译者代替作家和西方的出版公司做沟通。中国作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已经成熟定型,有了完整的形态,但出版公司会觉得对美国市场来说,这个作品还没有完工,因为美国读者还没有见到这个作品。他们可能会觉得某个作品很有潜力,还想对它进行发挥改造。出版公司会觉得改动原作很自然,但我个人觉得这样很别扭。像《长恨歌》这样的中国小说已经在中国出版、获奖,有了文学名声,成为文学经典,为什么美国的出版公司就要对它进行改动呢?像《百年孤独》这样的西方经典,编辑也敢做那么大的改动吗?我作为译者,我觉得我的责任不是去改变他原来的面貌,而是尽量使得它原来的面貌在英美读者面前出现。
吴赟:我看到报道,1996年您翻译完《活着》之后,联系了十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后来才等到著名的兰登书屋。到現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中美双方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您觉得在翻译作品的出版方面,之前的困境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改变呢?
白睿文:从我个人和总体趋势来看,现在的情况都比过去好。对我个人来说,出版比较容易,因为我做过一些翻译,出版公司已经有所了解,而且我本人也越来越有经验。从大的趋势来说,中国已经崛起,出版公司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
另外,目前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国内外译者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计划,尤其是对年轻译者是一个相当大的鼓励。我当初翻译余华、王安忆的时候,没有任何资金扶持。现在好时代来了。希望将来这个计划可以持续下去。现在在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英译的刊物相当地多,有《路灯》(Pathlight)、《译丛》(Renditions)、《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等等。出版中国文学的平台越来越多。同时美国一些著名的文学刊物也越来越愿意刊登中国文学作品。现在余华在《纽约时报》都开有专栏,这是十几年前想象不到的事。
但是整个出版业也正面临电子革命的挑战,电子书的崛起冲击着传统的出版行业。所以我觉得是往前走两步,再往后退两步。不过电子革命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文学。
吴赟:您的译作在英语世界《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刚出来引起一阵轰动,当时还卖出去一些欧洲的版权。《野孩子》登上了《纽约时报》和英国《经济学人》的书评版。《长恨歌》也得到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一系列主流媒体的评论和肯定。能否请您谈谈你如何看待你的译作在美国的接受情况?
白睿文:一本书出版之后,作品就不再属于你,它已经到一个大的世界去闯荡了。书出版后的几个星期内,有一些书评会先后刊登出来。之后就没有声音了。我也懒得去打听卖得怎样。就像石头扔到海里,也不知道日后会否有人重新发现,再去欣赏它。不过有时遇到读者来信说很喜欢自己的译作,也会觉得很欣慰。比如《活着》英译本在有些高中被用来做教材,这是不太常见的,是一件好事情。总体来说,这几本书在美国的反应还不错,评价还可以。
吴赟:让我们再看看您的其他身份。您还是一位电影研究专家,在电影这一媒介有着丰富的经验,比如担任电影节评委,为电影做字幕翻译,采访电影人等。另外,您也是一位文学评论家,长期为一些中文报纸撰写文章。所以我也想问问您处理这些不同媒介的经历对您的翻译的影响和作用,会不会帮您形成新的视角?
白睿文:做电影、舞台剧、话剧的字幕翻译,以及做口译都会对文学翻译带来影响。字幕翻译要求译本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妥协,屏幕空间那么小,时间那么短,要产生一个完全忠于原作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电影公司不会允许译者那么啰唆,要求译者进行缩减,在这个缩减的过程中有时就会去重新思考文学翻译的经验。另外,我觉得自我翻译的经验给我的文学翻译带来的启示更多。比如给某家报纸写了篇中文文章,日后再做一个英文版,因为中文版和英文版都是我自己的作品,我没有忠于原作的焦虑,完全可以解放自己,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篇文章虽然同一题材,一样的内容核心和论证论据,但英文稿和中文稿的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中文和英文有着完全不同的美。一篇流畅的中文文章,符合中国文字写作风格的美学,读者读得很舒服,但如果把那种美学带到英文世界,直接用字字对应的方式来呈现,最终的英文文字效果会很难看。而我通过自我翻译来对比的两篇稿子,文字离得相当远,但我觉得这样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忠于原作。这种自我翻译的体验给我的文学翻译带来一种解放,使得我的译本会稍微大胆一些,会自由一些,不会那么依赖原文的字字句句,当然我还是会忠于原作和原作者的那个世界。
吴赟: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之后,在世界的传播往往会更为直接、迅速,也更容易被大众市场接受。比如《活着》《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成功的先例。能否请你谈谈,您是如何看待电影对于文学翻译的推动作用?
白睿文: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几部中国当代小说都是先由电影打前站,票房卖得好,之后再打开了文学作品对外的窗户。现在我觉得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当然一些像《金陵十三钗》这样的电影大制作也有英译文出版。我觉得现在的当代中国文学已经走上了相对独立的一条路。最近在美国评价比较好的小说和电影毫无关系。
具体来说,80年代之前,中国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风格,这些作品在国外不太吃香,没人愿意出版。到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一些西方读者愿意阅读的新时期作品,比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在西方引起了一些反响,虽然反响不算很大。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出来之后,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反应热烈了一些,而且那些作品的写作风格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马尔克斯在西方特别受欢迎,莫言就被看成是中国的马尔克斯,他写的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之后可以说中国文学走向西方的时机成熟了,作品在国外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群。现在陈冠中的小说《盛世:中国,2013》和麦家的《解密》在美国比较畅销,和电影就毫无关系。
吴赟:之前看过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2005年在英国《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跃进》(The Great Leap Forward)的文章,回溯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历程。文章说长久以来,西方读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学就是枯燥的政治说教”,几乎所有大陆小说都被贴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中国的宣传教育资料”。您刚才讲到的80年代的情况是这样的,这里有个时间差。能不能说,长时间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看法左右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导致了对中国现代文学阅读经验的欠缺?
白睿文:在冷战时期长大的老一代可能抱有这个偏见,年轻一代没有这个包袱。问题是,现在的年轻一代还读书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电子时代的到来是同步的,虽然年轻人没有文化偏见,但是在facebook,twitter环境中长大的人不一定有心思和兴趣去阅读文学作品。所谓的文化失衡是中美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很难解决。在我的课上我曾经说过,如果到中国的校园提问海明威是谁,每一个学生都知道;但是如果到美国校园提问鲁迅是谁,没有一个学生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去改变美国的教育体系。现在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对他们的重要性,不论是经济、文化还是其他的各个方面,中国都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越来越多的美国家长让孩子到中国去留学,但是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的。
吴赟:如果把您当成一个简单的读者,一个阅读中国文学的读者。我想问的是您觉得一般的美国读者想在中国小说中看到什么?
白睿文: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私人理由来选择阅读什么样的作品。有共性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想读好的作品,好的小说。另外有一些人想要通过阅读小说来了解中国。还有一些人,像我妈妈,希望通过小说了解过去被神话的中国形象,封建朝廷的时代,女人的闺阁,传统的服饰,缠着的小脚,希望读到中国古代代表性的特色,读到中国的传统国粹。
吴赟:同时,您也是一个权威的专业读者,是红楼梦文学奖的评委。能否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文学奖项?评奖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它和官方的茅盾文学奖有什么样的区别?
白睿文:红楼梦文学奖是二年一度举办,评选华语世界最佳的长篇小说。初评时有十几个评委会从包括中国香港及台湾、东南亚在内的整个华语地区挑选六到八本小说入围。下一轮终评,评委会会提前一个半月把作品交给各位评委,之后在香港开会,评出一等奖一名,荣誉提名奖两名。这个文学奖项评判的标准就是进行文学的、纯粹的、审美的判断,评判的宗旨就是要寻找经得过时间考验的好作品,就像《红楼梦》是中国文学永久性的经典一样,寻找当代的“红楼梦”,当代华语最佳小说。茅盾文学奖的地域性很强,而红楼梦文学奖的视角比较开阔,开放一些。
吴赟:也有不少专家从中国文学的创作本身来给中国文学的世界之路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他们认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十分不力,也和自身的文学特性有关,比如书中人物太多、情节复杂、篇幅太长等等。能否请您从中国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作家怎么写,会被英语世界接受的更好呢?
白睿文:有一些汉学家比如顾彬、葛浩文,公开说过一些很尖锐的话,说中国作家应该怎么怎么写,来呼应世界文学的口味,我不敢这样讲。作为一个读者,我从中国文学作品中得到很多乐趣。我也很欣赏中国文坛很多非常杰出的作家,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不是作家,我是一个研究者,是一个译者,我非常荣幸和几个作家合作过。如果我是世界一流作家,也许我有几句话要讲,但是他们都写得比我好,我身为人在海外、中文并非母语的读者,没有资格去建议中国作家该怎么写。我觉得一个好作家不应该去附和某一个市场或者某些读者的口味去写作。好的作家就是凭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想象力、自己对文学的敏感性,去创作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作家都应该去寻找这条路。
吴赟: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放到世界文学语境中来考察,你觉得他们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白睿文:中国当代文坛非常丰富多彩,有很多经典作品,很可惜的是那么多经典没有翻译到国外,没有得到海外的认可。这不是因为作品不好,而是因为海外视角还没有关注到它,作品还没有被开发。我认为中国文坛和世界其他文坛一样活跃,一样充满活力和魅力,没有什么觉得惭愧的地方。
吴赟:如果推出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的节译本、编译本,您觉得是不是会提高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
白睿文:我个人不太赞成。我觉得这是对原作的侮辱。另外不要把海外读者当傻子。如果有好的译本,读者当然会去看。他们不是小孩子。除非是针对儿童市场。比如《红楼梦》对小孩子可以出版节译本,对成年人就不需要。如果读者有耐心去读,就不会有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淡化中国文化。
吴赟:前面您也说了现在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电子影像时代。网络、手机、影像等多媒体越来越普及,文学的读者群越来越狭窄,文学和翻译文学的处境会变得十分糟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对策吗?
白睿文:我没有什么对策。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靠某个人的力量无法解决。目前文学和翻译文学的处境还好。再过几十年就很难说了。要看现在的年轻人还会读书吗?会用什么平台来读书?一旦实体书被淘汰,电子书的时代来临,年轻人还会有耐心去读厚达几百页的托尔斯泰作品吗?我不知道。我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做文学的人不要放弃,不要妥协。在音乐上,我有一个很欣赏的爵士吉他手Pat Metheny,差不多十年前,当年轻人开始大量地下载手机铃声的时候,他认为大家喜欢手机铃声来听几十秒的歌就是速食文化的一个十分恶劣的象征,年轻听众好像已经没有耐心和没有兴趣聆听完整的音乐,于是他做了一个名叫“The Way Up”的专辑,里面只有一支曲子,长达六十八分钟。他对媒体说,全世界都在走速食文化的路,而我却逆流而上,让听众听一支长达六十八分钟的很完整很复杂很多层次的曲子,来挑战他们对音乐的偏见和想法。文学也一样。虽然大众文化向速食文化的方向走,但是我希望作家不要放下笔去写微小说,作家要保持艺术尊严,走该走的路。如果脑海中有七百页的小说,那么就要让它自然而然地呈现,给读者一个挑战。如果我们都妥协了,那最后我们都输了。一旦速食文化打赢了,文学就到了末日。但是我也相信奇迹。比如“Harry Potter”(《哈利·波特》)就是一个文学奇迹,一共七部厚厚的书,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读。我觉得这种奇迹还会再出现。在悲观中我们还要保持乐观。
吴赟:中国官方数次邀请您来中国参加有关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会议,这是中国目前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能否请您谈谈您对“走出去”这一文化政策的看法。
白睿文: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走出去”是好事。前面说到文化失衡,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够,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文化“走出去”,让读者、听众多多了解中国文化。但是怎么“走出去”呢?文化到海外产生影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很难用一些政策来制定、来改变自然的流通的现象。不过国家可以在经济等方面,向译者、向出版公司提供帮助。不过最终作品是否被当地的老百姓接受,还需要他们具备开放的心理。这一点是国策无法改变的,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需要漫长的过程。但假以时日,我相信会改变的。
吴赟:您觉得应该如何實现中美积极有效的文化交流呢?
白睿文:我认为可以从多方面切入。文学是好的渠道,电影是,其他比如京剧、话剧、舞台剧等表演艺术也是。现在是中美交流新时代的开始。举一个例子。现在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请中国明星担任重要角色。范冰冰在去年公映的《钢铁侠3》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不过在美国版里被剪掉了。在今年刚刚公映的《X战警》里范冰冰的角色就没有被剪掉。《X战警》之后,时间久了,如果她再演几部好片子,慢慢地她就会在美国有自己的品牌名声,美国观众知道了范冰冰这个演员,说不定再过几年,等范冰冰自己的中国电影在美国公映的时候,《X战警》的铁杆粉丝都会跑去看。经过这个过程,范冰冰就变成了国际明星。时间久了,中国的明星,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文化呈现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吴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本文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编号NCET-13-0904)和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研究”(13BYY04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