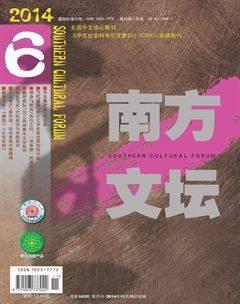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及问题
2014-05-30汤翔鹤
一、新趋向与热点聚焦
(一)关于文学史建构的探讨 文学史的合理建构及对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一直是研究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开启以来,对于文学史本身的论争就从未停息,从对尘封作家作品的发掘与重评,到对“雅”“俗”二元对立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与调整,再到对“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等文学价值标准的考量与批判,反思浪潮不断涌入文学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在不断的反思与争鸣中,文学史的起源与具体时间界定、命名、分期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价值立场、叙述方式、话语权力等成为热议的焦點话题。近年来,研究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
在现代文学史的起源与具体时间界定问题上,学界不断对以往被普遍认同的以“文学革命”为起点的“1917年”说和以五四运动为基点的“1919年”说提出修正和质疑。如学者栾梅健通过对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的语言、结构、主题意旨等的考察,认为该作具有断代价值,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标志的界尺”,其发表时间“1892”年,即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1)。严家炎先生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辟和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最初的起点,根据我们掌握的史料,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甲午的前夕。”(2)丁帆教授则主张将“1912年”作为“新文学发端的起点所在”(3)。这些观点都试图将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前挪”,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
学界对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观照主要有两个面向:其一,对既有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质疑与反思。如李永东先生撰文反思“新文学史观话语霸权地位”(4)在具体的文学史写作中的表现及其对文学发展历程的歪曲与遮蔽;贺仲明先生则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考察反思了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商业文化等权力因素对文学评价与作家作品价值定位的影响(5);而文学史书写中的古典诗词、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等的地位与入史问题更是研究者反思与讨论的焦点话题(6),如陈国恩教授就指出在海外华文文学入史问题上应当“防止学科本位主义的倾向”(7)。其二,对文学史重新建构的价值标准与书写原则等的讨论。如丁帆教授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舍不得丢弃那些坛坛罐罐,而应该有治史者的大气魄,切割掉那些不适宜入史和勉强入史的材料,抛弃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沉重包袱。”(8)主张对文学史做“减法”,对作家作品进行重新筛选与定位;王彬彬教授认为:“文学史编写的基本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叙述特定时期文学创作的面目,是尽可能深刻细致地揭示特定时期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9)因此,文学史写作要分清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并尽量避免“扯平效应”和“排异效应”;朱首献先生提出文学史书写的“个体意识”与“类意识”的概念,认为当前更应强调“文学史的个体意识”(10)。随着学界对于文学史问题讨论的深入,及诸如“现代中国文学史”(朱德发)、“汉语新文学史”(朱寿桐)、“民国文学史”等一系列新的文学史命名的出现,新一轮“重写文学史”思潮的重启,似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二)对“民国文学”的聚焦 文学史上一种新的学科命名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新的文学史观念与书写方式的转变,此前“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命名的提出无不如此。“民国文学”(11)之所以会成为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的焦点概念,其缘由大概亦在于此。随着这一概念的不断升温以及学术论坛与专栏等研究平台的形成(12),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对“民国文学”的讨论,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诸如“民国史视角”(秦弓)、“民国机制”(李怡)、“民国文学风范”(丁帆)等相关概念。
学界对“民国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对“民国文学”命名的合法性及其内涵与价值辨析。在张福贵教授看来,“民国文学”的命名采取的是“从意义的概念重新回到时间概念上来”的策略,同时也是对“现代文学”命名所暗含的“意义的单一性与判断的先验性”(13)的反拨。因此,“民国文学”不仅符合中国文学以政权更迭的朝代为名的命名方式,而且可以打通“近代”与“现代”,连接前后形成文学史叙述的连贯性。二是对“民国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视角的意义与价值的探讨。不少研究者指出,“民国文学”具有“内涵的多元性与边界的开放性”(14)特质,可以涵容在此时间段内产生的一切形态的文学样式与思潮流派,使学界可以“暂时搁置先进/落后、新/旧、现代/传统之辨,在一个更宽阔的视域内阐述文学现象,取得比‘现代文学叙述更丰富的成果”(15)。此外,它还能最大限度地还原文学产生的历史现场,让研究者重新认识文学与具体的“国家历史情态”(李怡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改变我们对这段文学史的理解与认知(16)。三是对“民国文学”概念的质疑及对其价值限度的审视。如有学者指出“民国文学”概念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是否会影响其作为纯粹的“时间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使用?能否避免外在政治因素的干扰?(17)有学者质疑“民国文学”的提出“实乃有意忽视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内部发生的根本性突变,抹杀了‘现代等因素在这一突变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18)。甚至有学者不无偏激地认为“民国文学”的提出是一种“学术炒作”,“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学术史上的反动和逆流,应该坚决予以批判。”(19)而更多的学者则从学理层面深入分析,指出了其内在的不足之处,如张桃洲先生认为:“当‘民国文学成为论者所期待的某种‘可以包罗万象的时间容器时,这个概念面临的最大难题或许恰恰是,无法确定一个像‘现代文学的‘现代那样的理论支撑点。”(20)此外,“民国文学”所指涉的对象及其时间界限等具体问题在研究者中并未形成共识(21),而对这一概念的探讨也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缺乏真正的文学史写作实践,凡此种种无疑都是这一课题研究的症结所在,当然这些还有待开拓的学术空间也正是其价值所在。
(三)“本土化”转向与传统复归 近年来,西方理论热潮逐渐“退烧”,新的理论、方法、名词满天飞的情况有所改变,以往一味学步西方的研究路径受到质疑,研究界开始检视和反思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的阐释效度,对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也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与此同时,在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都出现了转向“本土化”的呼声,要求重视“本土经验”与民族传统。在传统复归的文化语境中,“文学与传统”遂成为研究者关注与讨论的话题(22)。这当中潜含着对西方文学与文化施于中国文学持续近百年的“影响焦虑”的一种反拨与矫正,一方面试图用“本土性”来对抗与消解以西方世界为参照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创作中突出“本土经验”或“中国经验”,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并试图建构新的诗学理论与阐释体系。这些欲使中国文学及理论重新复苏并走向世界的尝试与探索都是有益和值得嘉许的,但当中传统负性面的沉渣泛起也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
当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是关注传统本身的内涵与外延,确立现代文学传统这一“新传统”的合法性,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传统的价值、意义与局限,阐明“新”与“旧”两种传统的不同指向与相互关系(23)。二是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因素与影响,尤其是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关系成为关注重点(24)。如有学者指出:“传统的小说流脉没断,它潜伏在文字中间,并没有随政治运动和政权变更而成为‘断崖。”(25)还有学者指出新诗中存在一种“反传统的新诗传统”(26),对新诗的发展与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三是探讨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对作家的文化人格、思想意识与具体创作等的影响。四是考察区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文学的“地方性”或区域特色以及区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成为关注重点(27)。此外,民间文化以及一直被忽视的书法文化、楹联传统等亦在探讨之列(28)。
(四)网络文学由边缘向中心游走 网络文学从1998年学界认定的“文学元年”发展至今,已由原来的边缘小众文学一变而为“六分天下”(29)有其一的重要文学形态。研究界对网络文学的态度也由原初“存而不论”式的漠视与基本否定转变为现在的逐步重视与有限肯定。网络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30)。近年来,网络文学研究已经从最初的对于概念内涵、特征和价值等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研究空间大幅拓展。针对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发展趋向,不少研究者对其内容与题材进行划分,分类研究其不同特征与走向;对网络文学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研究,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分析网络写手与读者的思想文化观念、审美趣味、心理动机等方面的共同特征(31);对网络文学进行溯源研究,探求其与中外文学传统的关系,考察其创作资源;传播与影响研究,分析网络文学在书写、传播、阅读方面的新变,考察其影视改编与出版的运作方式及影响。对网络文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如对其类型化严重、原创性不足、篇幅冗长、暴力色情泛滥等不良因素展开批判。此外,新媒介催生出的博客文学、手机文学等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32)。当前的网络文学研究几乎都是宏观性研究与现象分析,文本分析与个案研究极少。评价标准的缺失,网络文学批评的滞后,研究对象过于庞大且良莠不齐,研究者与网络文学的隔膜等,都是今后研究必须面对的难题。
(五)关于文学批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似乎处于一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境地,不仅作家与读者对文学批评的批评与指责不断,即便在文学批评界内部也在不停地进行着“自我批评”(33)。不少学者撰文抨击文学批评中长期存在的所谓“红包批评”“圈子批评”“广告批评”等不良风气,呼吁必须重建文学批评的文化生态,让文学批评冲出政治、经济与人情关系的重围,真正做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以期重树文学批评的公信力,护持文学批评的尊严(34)。对“学院批评”的评价与反思也成为热议的话题,肯定者认为“学院批评”以其扎实的学风与专业知识,有效消解了文学批评中的浮躁浅薄之风,给文学批评增添了学理与内涵,提升了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批评者认为学院批评由于长期受体制与学科规范等因素影响,逐渐丧失了内在活力与灵性,变成了经院式“不及物”批评和机械的文本拆解,甚至沦为了直接搬用西方理论“套”作品的“框架批评”(35)。因此,不少批评家指出文学批评应当建立在对作品认真研读的基础上,在批评实践中要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感受,要立足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写出融入个体生命经验的文学批评(36)。文学批评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如面对日益高产的中国文学,批评家时时处在疲于奔命与失语状态;作品泥沙俱下难以建立有效的批评标准;处在“自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如何应对网络文学、博客文学、80后写作等新兴文学现象等(37)。此外,对文学批评进行学理化梳理与考察以及对文学批评文体、语言等具体层面的探讨也在进行之中(38)。除了对文学批评的理论争鸣外,近年来文学批评实践也不容忽视。文学批评界对当代文学发展的介入异常活跃,这在对《蛙》《古炉》《第七天》《推拿》等作品的评论争鸣及对诸如《大秦帝国》等小说的集中批判与质疑中即可窥其一斑。
二、学术成果与重点推进
(一)文化研究 报刊研究一直是最具活力和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之一,这一方面得益于研究者的不懈开掘与一整套研究方法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界对报刊研究的重视和刊物对报刊研究的有力推动,并由此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平台。有学者认为报刊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所有研究者共同面对的作为现代文学重要载体的报刊研究,二是作为话题载体与资料库的报刊研究,三是作为獨立考察对象的报刊研究。”(39)通过考察,笔者以为近年来报刊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路径:一是研究特定时空背景下报刊的生存状况(40)。在时间维度上,研究者一般选定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革”等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时期;在空间维度上,研究者多关注如抗战时期的沦陷区、解放区等特定地域;重点考察报刊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因素、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并突显其时代共性与独特个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被学界忽视的伪满洲国时期的报刊,近年来开始成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二是研究报刊的特色栏目设置与编排(41)。报刊栏目之所以会成为关注重点,在于通过对报刊专栏、头条编排等的研究,不仅能管窥报刊的办刊特色与走向,也能寻觅出时代语境、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对报刊的规训与导向作用。如有研究者通过对“十七年”时期《人民文学》的“读者来信”和“编者的话”的研究发现“政治一方面以直接的方针政策来规训刊物的办刊方针,另一方面又假借读者公共舆论的方式来间接约束刊物”(42)。三是对报刊进行个案研究(43)。通过对具体报刊的办刊历程与特色尤其是对其创刊、停刊、改版等进行分析研究,折射出报刊发展过程中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对那些书写着特定故事却逐渐被文学史所遗忘的文学刊物的打捞,在丰富对文坛的认识、呈现一个年代文学侧影的同时,也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恢复已经被遮蔽或简化的文学史面貌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44)而以前所不被关注的诸如域外报刊、画报类刊物、市井小报刊等一些边缘报刊或民间性质的报刊逐渐成为关注对象。此外,报刊与文学运动、思潮、流派等的关系以及报刊与现代文体和作家之间的关系等仍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45)
文学制度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当前文学制度研究一般集中在对文学会议、文学机构、现代编辑制度等体制机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方面。受到新媒介与新的传播方式的影响,不少学者开始转入对文学的出版与传播研究,考察现代出版传播机制对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影响,其中对于作品出版编辑过程及主要出版机构的个案分析成为研究焦点。如有研究者指出1949年后政治意识形态通过编辑制度对文学生产形成了巨大的规约:“编辑制度的建立不但使文学编辑在出版什么人的书和出版什么书的问题上要严格履行‘守门人的职责,而且更要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实行严格的审稿制度,以确保出版物的政治正确。”(46)有学者认为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存在复杂的关系:“现代出版的特点影响和决定了现代作家的群体性特征,并对文学社团的聚散流变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作家群体或社团流派之间时常出现的文学论争,其背后往往存在出版利益之争。现代出版格局与现代文学多元化发展之间构成了一种互动和制衡的关系。”(47)
研究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新趋向,在此视域下一系列新的话题不断呈现,其中最为典型的有:现代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大学课堂教育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民国时期重点院校的学科与课程设置、现代文学作品在教学中的阐释与接受变化、院校的变迁发展史等(48)。这些研究有两种不同面向:一是回溯历史原貌,研究大学中“新旧交织的文学空间”(49)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一是分析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新文学起源于大学”,“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哺育的关系”(50)。研究文学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同时也为审视和反思现实教育问题打开了一个新视角,这当中也折射出学者深切的“人间情怀”。
(二)文献史料研究 研究界对文献史料研究日益重视,不仅召开了一系列有关文献史料的学术研讨会(51),而且不断有学者撰文呼吁和强调文献史料研究对于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如学者吴秀明提出应当重视“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学”问题,以扭转当代文学学科“轻‘史料实证而重‘理论阐释”(52)的研究取向。近年来,文献史料研究的实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家作品的辑佚与考证(53)。如对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郭沫若、刘大白、魏金枝、柳青等重要作家的佚文的发掘与考释;对主要作品与重要史实进行考证与历史还原。二是文学版本研究(54)。不仅有对作品的版本校勘,而且还通过对具体文本在创作与流传过程中的版本变迁考察,揭示出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变迁情况以及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对于文学创作的干预与影响。此外,还结合研究实际提出了诸如“汇校本”“副文本”等版本学理论命题。三是对文献史料研究的反思与方法论探讨(55)。文献史料的范围不断拓展,口述史料、书话、地方性报刊、校园刊物以及“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材料,包括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内部报告”(56)等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史料观念不断更新,史料发掘的方法、途径与史料运用中存在的问题等都成为探讨的话题。可以预见的是,文献史料研究将成为学科的一个重要学术生长点和学科分支。
(三)作家作品研究 近年来,“回到文学本身”、“回到作品本身”成为研究界日益高涨的呼声。2012年4月,学界曾召开学术会议,专门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展开讨论,与会学者认为:“作家、作品是文学史最关键的构成。没有深入研究作家、作品,就不可能对文学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在当下研究普遍地重理论、重宏观的情况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重回基点,亦即作家、作品论”(57)。由以往的理论阐释、文化视角等外部研究转入以文本细读为重心的作家、作品论的传统研究路径,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自觉。
从研究现状来看,鲁迅研究不仅仍是研究重镇而且研究的深广度几乎可以说到了“无孔不入”的境地,涵盖了从人本到文本,从文学到文化,从翻译传播到接受影响等各个层面。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鲁迅研究受日本学者影响较大,随着竹内好、伊藤虎丸、丸山昇等日本鲁迅研究者的成果被介绍到国内,使国内鲁迅研究界出现了所谓的“哈日”现象(58),并形成了对于鲁迅研究的研究(59)。随着张爱玲的佚作《小团圆》的重新挖掘出版,在读书界和研究界同时兴起了新一轮的“张爱玲熱”,《小团圆》成为新的阐释对象,而对于张爱玲的生平叙说、作品研读、文学风格与价值等仍旧方兴未艾。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界的重大事件,使得“莫言·诺贝尔奖·中国当代文学”(60)一时成为学界热议的三个关键词,莫言小说的叙事、结构、语言等也成为研究热点。此外,沈从文、周作人、萧红、赵树理等主要作家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而汪曾祺、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余华等作家也开始了经典化进程。
近年来,随着“重返八十年代”等讨论与研究的深入,“重返”已经具备了方法论意义,回归文学现场,还原具体历史语境,对作家作品进行“考古知识学”考察,成为近年来的主要研究路径。在“历史化”研究的影响下,对作品的重读、新论、“再解读”风气渐浓,掀起了新一轮作家作品再研究与文学价值重估、文学史地位重评的热潮。这股潮流无疑对当代文学中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影响最深,使之呈现出总括性的概观研究渐少,而“解剖麻雀式”的作品个案研究增多的总体趋势。对《红旗谱》《红岩》等“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的解读与评价依然是焦点话题,以往的政治历史评价模式逐渐被西方理论消解,而对作品的结构、叙事、语言等艺术形式分析逐渐引起关注(61)。对手抄本小说和“白洋淀诗派”等潜在写作的研究,一直是“文革”文学研究的重点所在,而《晚霞消失的时候》《第二次握手》《公开的情书》《波动》等也成为再解读与重评的代表性作品,此外,其时出现的诸如《一只绣花鞋》等通俗小说也受到关注。新时期文学是“重返八十年代”的源发点,其时的诸多代表性作品都成为重新解读的对象。
(四)文学思潮、流派、社团研究 近年来,文学思潮研究不断深入,尤以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最为引人关注。左翼文学思潮研究一方面集中对其发生阶段的思想资源、理论倾向、创作实践、接受与影响进行深入解析;另一方面将左翼文学思潮向后延伸,将其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文学与延安文学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三者的异同,评估其价值与意义。有学者提出“新左翼文学”“新左翼精神”等概念,并将其与新世纪兴起的“底层文学”写作相勾连,探求左翼文学思潮在当下的新变及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62)。有学者认为:“左翼作家自觉参与社会改革历史进程的昂扬姿态,左翼文学强劲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思想启蒙热情,以及它对底层社会血浓于水的深情关注,也是我们发展和繁荣文学事业的思想文化资源。”(63)既接通历史又关联当下,这也许正是左翼文学思潮长期引人关注的原因所在。此外,对女性文学、启蒙主义等现代文学思潮与新时期以来形成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知青文学”等文学思潮的研究都得到了稳步推进。
在文学流派研究中,对海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等的研究较为集中。流派研究逐渐突破复杂的历史政治与文学论争的纠葛,试图运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对流派本身的存在样态、特性及影响进行考量,以突显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以海派研究为例,不少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海派文学进行深入发掘,分析其与都市文化的内在关联,研究其出版传播途径与接受影响,在对比研究中考量其独特的叙事方式、表现手法、个性特征;从文学发展史的视角分析其与晚清市民文学及后期的都市文学的差异与联系,这种多角度的研究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流派研究的学术空间。对学衡派与战国策派等文学史上曾被压抑或批判的文学流派进行重新发掘与价值重估,也是近年来流派研究的一大亮点。此外,乡土文学研究也不断引发关注,正如研究者所言,“乡土,已经不是一种物质存在,而是被对象化的理念形态,是对抗着存在于传统或现实肌体中一切理性或非理性之病恶的理想结晶,是人类赖以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64),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文学创作与研究都将不断深入进行。与思潮和流派研究相比,文学社团研究总体趋于式微,研究主要是关注文学社团的历史考辨、创作实践、理论渊源等,文学社团的文学译介活动及其影响也成为近年来的一个新的研究趋向。
(五)文类研究 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类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板块,而在四大文类中,小说创作与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成为评判作家创作成就与水准的标尺,随着长篇小说的高产,长篇小说研究也占据主导地位,中短篇小说与微型小说研究日渐衰微。研究者多从长篇小说的文体、结构、叙事、思想倾向、美学风格等方面进行阐发,而长篇小说的语言问题日益成为关注重点,如德国学者顾彬就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对中国作家提出批评,“我们正在靠近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难题。语言不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关怀,却只是用来编造书面娱乐的工具”(65),他认为中国作家对语言的忽视是中国文学无法走向世界文学的重要原因。小说题材分类研究仍是主要路径,农村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历史题材等小说依然是研究的重点对象。小说创作与中外文学传统的关系、地域文化与小说特质、小说中的生态意识等都是研究中的焦点话题。此外,对于小说评奖、当代小说的成就与评价等问题也引发了广泛争议。有学者还指出:“现在讲文学基本就是小说,讲作家基本就是小说家。文学=小说,作家=小说家,差不多成了中国文坛不争的事实。”(66)由小说一家独大而导致的文学生态失衡问题,开始引发研究者的深层思考。
近年来,诗歌研究较为活跃(67),对于诗歌的风格、语言、形式、美学倾向、意象特征、节奏韵律等传统研究路径不断拓展。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研究,新诗与传统诗词的关系,诗歌翻译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等问题以及先锋诗歌、打工诗歌、网络诗歌等不同形态的诗歌都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新诗的评价标准、诗歌批评、诗学理论建构等仍然是有待突破的理论难题。此外,对诗歌的现状与发展走向等问题的批判性反思也在持续进行,如有的学者指出:“有些诗人或者在艺术上走纯粹的语言、技术的形式路线,大搞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实验,把诗坛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竞技实验场,使许多诗歌迷踪为一种丧失中心、不关乎生命的文本游戏与后现代拼贴,绝少和现实人生发生联系,使写作真正成了‘纸上文本。”(68)这也许道出了当代诗歌不断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戏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剧作的结构、语言、风格及戏剧的接受与影响等方面展开。抗战时期的戏剧、“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及历史题材戏剧研究较为深入。值得一提的是,高行健的戏剧创作尤其是他后期创作的“典型的现代东方式的禅境剧”(69),不断引发研究界的关注与讨论。散文研究近年来逐步走向复苏,经典作家作品分析与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女性散文等依旧是研究重点,作家人格精神与散文创作的关系,散文文体、风格及流变,散文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建构,散文史写作等引发了较多关注与讨论。(70)
三、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一)文献意识的缺失 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石与出发点,其重要性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近年来在史料的发掘与辑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史料的整理考辨与运用方面则突显出研究者文献意识的缺失。现当代文学经历了复杂的政治环境变迁,大量产生于特殊政治历史环境下的史料错伪驳杂讹误繁多,如不认真整理详加考辨,極易产生谬误。这便要求研究者在面对各种史料尤其是报刊文献、口述回忆、日记以及档案材料时,“要以知识考古学的态度,要注意梳理其流脉,发现其裂隙,还原历史语境,显出其本真面目。”(71)此外,在史料运用方面文献意识缺失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如有的研究者忽视研究文本或征引文献的版本变迁情况;有的论文史料来源单一,大量征引未经考辨的史料或二手材料进行论证。更有甚者为了便于论证,不顾及史料的完整性与具体历史语境,对史料进行断章取义式的有意裁剪与组织。因此,拓展史料来源,加强史料考辨,规范史料运用,是今后研究中一个急待加强的重要环节。
(二)文学审美价值的消解 文学的审美价值在文学研究中不断被消解与边缘化是近年来文学研究中不争的事实,文学的内部研究趋于衰微而外部研究却大行其道,文学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与专业化,研究文章也变得越来越烦琐与枯燥。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以历史考据的方式研究文学,导致对文学审美价值的悬置。用历史考据的方法研究文学是较为典型的文学研究范式,它在夯实文学研究基础,提升文学研究学术品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研究引向了歧途,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这一风气(指文学研究考据化倾向,引者注)在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研究者中造成的影响即是重考据而轻欣赏、批评,重新史料的发现而轻旧知识的理解、贯通,重作者身世、题材演变的考察而轻审美层面的体味涵泳,重外部研究而轻内部研究,使得文学研究支离破碎,难免买椟还珠之讥。”(72)而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的“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应该可以对这一倾向进行有效矫正。二是由文化研究引发的跨学科研究,导致对文学审美价值的忽视。文化研究的引入带来了文学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的高潮,它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研究空间,还原了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复杂历史形态,但它也抹杀了文学作品之间价值的高低与优劣之别。文化研究只是把文学当作出发点而不是落脚点,其指向基本上是诸如文学的编辑、出版、传播、接受等外部问题。在文化研究的视阈下文学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存在,其艺术水准与价值常被付之阙如,由此,形成了泛文化对文学审美价值的遮蔽。
(三)“理论焦虑”的流弊 近年来,虽然理论与方法的热潮有所消退,但学科研究中仍然透露出一种长期存在的“理论焦虑”,不断试图将西方新兴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学科研究中,并急切地用以对文学作品、现象、思潮等进行阐释,在看似众声喧哗的热闹后面也隐藏着各种问题。“理论焦虑”所带来的流弊主要有以下表征:一是完全忽视理论产生的具体语境与阐释对象的复杂形态,将文学当作理论与方法的试验品,将理论与对象强行扭合拼贴,进行生吞活剥或削足适履式的解读。二是过度阐释与研究空洞化日益严重。一方面是忽视理论本身的阐释效度,对理论进行随意发挥与扩容,对对象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形成过度阐释;一方面是脱离文学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不立足于文本细读与整体观照,抽象地进行理论分析与概括,使研究日益空洞化。三是过分夸大或盲目迷信理论的阐释功能,将一种理论泛化和推衍到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比如“现代性”理论引入后似乎成为文学研究中的“神器”,几乎所有的文学问题都离不开“现代性”,这反而将理论本身的阐释功能全面消解于无形。四是新理论的不断引入,不仅导致大量重复研究与跟风研究,也形成了模式化的研究套路。此外,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的频繁理论更替中,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并未得到深入研究,鲁迅先生所说的:“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73)这样的情形与近年来的理论研究状况庶几相近。
【注释】
(1)栾梅健:《1892: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论〈海上花列传〉的断代价值》,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2)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
(3)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载《江苏省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4)李永东:《反思新文学史观的话语权》,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5)贺仲明:《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构建中的外在因素影响——以丁玲等文学史评价为中心》,载《理论学刊》2013年第8期。
(6)可参看李松整理的会议综述:《武大·哈佛“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国际高端学术论坛》,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严家炎:《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长江学术》2013年第1期。
(7)陈国恩:《防止学科本位主义的倾向——关于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一点思考》,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5卷第1期,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丁帆:《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的思考》,载《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9)王彬彬:《文学史编撰的理念与方法》,载《南方文坛》2014年第2期。
(10)朱首献:《论文学史的“个体意识”与“类意识”——百年中国文学史学科发展论析》,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7卷第2期,5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对于“民国文学”的最早提出,有学者认为是陈福康教授,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张福贵教授,可参看李怡:《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载《江汉学术》2013年第2期;杨丹丹:《新世纪“民国文学”研究述评》,载《华夏文化论坛》2013年第10辑。
(12)如2011年四川、北京等高校的青年学者发起成立“西川论坛”,每年定期组织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具体内容可参看相关综述;如《文艺争鸣》杂志自2012年起开辟“民国文学史研究”专栏,刊发了多篇关于“民国文学”的讨论文章。
(13)(14)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载《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15)李怡:《“民國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载《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
(16)相关论述可参见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17)熊修雨:《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意义》,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3期。
(18)(20)张桃洲:《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角的“民国文学”》,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
(19)罗执廷:《“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的学术论衡》,载《兰州学刊》2012年第6期。
(21)在研究空间上主要涉及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时间上一般学者倾向将“民国文学”界定在1912年至1949年,但丁帆先生持不同观点,参见丁帆:《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它的几点补充意见》,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丁帆:《“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载《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22)如2009年10月24日至25日,“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曲阜举行;2010年在湖南长沙召开了“本土经验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学术研讨会;2011年10月5日,第三届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在沈阳举行,主题为“文学与传统”,并在《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2期中连续刊发了与会者的讨论文章。
(23)如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王铁仙:《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24)如贺仲明:《新时期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载《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1期;高玉:《五四新文学与古典传统及其评价》,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杨经建、吴丹:《苏童小说与晚唐诗风》,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刘惠丽:《“仁义”传统与铁凝小说》,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张清华:《“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季红真:《莫言小说与中国叙事传统》,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25)董之林:《当代小说的传统延伸》,载《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2期。
(26)骆寒超、陈玉兰:《论反传统的新诗传统》,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2卷第2期,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7)2009年11月14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学界分别于2009年、2011年、2013年召开了以“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具体内容可参看相关会议综述。
(28)李继凯:《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肖百容:《楹联传统与中国新文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29)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30)如《南方文坛》等长期关注网络文学话题并刊登有关网络文学的研究文章,引发了诸多讨论与关注;2013年7月25—26日,在西藏拉萨召开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网络与文学变局学术研讨会”,可参看相关会议综述。如马季:《网络文学边缘性主体解析》,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江腊生:《网络文学研究生态的检视与思考》,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史建国:《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
(31)黄发有:《消费寂寞——网络文学的游戏化趋向》,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32)刘海涛:《博客體小说的分析与猜想》,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33)如学界每年定期举办“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文学期刊如《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等持续开辟诸如“批评家讲坛”“文学批评论坛”“批评论坛”等专栏,专门讨论文学批评问题。
(34)黄发有:《另一种友情批评》,载《文艺争鸣》2014年第1期;高玉:《文学批评的操守与格局》,载《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
(35)王彬彬:《一个批评家应该从语言中得到快乐》,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丁帆:《有“社会良知”和深邃思想的文学批评》,载《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36)参见杨庆祥整理:《文学批评的语境与伦理——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载《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37)欧阳友权:《当传统批评家遭遇网络》,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王颖:《从主动“缺席”到被动“失语”?——传统批评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的文学》,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38)黄发有:《文学评论的文体问题》,载《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
(39)丁文:《“熟悉的陌生者”——〈东方杂志〉研究史与报刊研究的方法论思考》,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5卷第1期,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0)王冬梅:《“文革”后期文艺刊物的历史考察》,载《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李相银:《行走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上海沦陷时期的〈杂志〉研究》,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5卷第1期,1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1)陈建华:《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载《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黄发有:《文学风尚与时代文体——〈人民文学〉(1949—1966)头条的统计分析》,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高翔:《〈新青年〉“新诗歌”专辑研究》,载《求是学刊》2013年第5期。
(42)樊保玲:《“强大”的读者和“犹疑”的编者——以1949—1966〈人民文学〉“读者来信”和“编者的话”为中心》,载《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
(43)明飞龙:《当代诗歌史视野下的民间诗刊〈诗歌与人〉》,载《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5期。
(44)明飞龙:《一份杂志的命运与一个年代文学的侧影——以〈中国〉的创刊与停刊为中心》,载《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1期。
(45)张丽华:《〈时报〉与清末“评”体短篇小说》,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何宏玲:《晚清小报的新体散文——近代散文新变之探索》,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
(46)王秀涛:《当代编辑制度的建立与文学生产》,载《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6期。
(47)李春雨:《论现代出版与现代作家群体的关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6期。
(48)如陈平原先生的《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上下两部分分别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与2010年第1期;沈卫威:《“国语统一”、“文学革命”合流与中文系课程建制的确立》,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49)沈卫威:《新旧交织的文学空间——以中央大学(1928-1937)为中心实证考察》,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2卷第1期,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0)王彬彬:《中國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5卷第1期,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1)可参看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综述,文献史料问题几乎是每次年会的重点话题;再如专门召开的相关文献史料会议,如王学振:《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易晖:《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吴秀明、章涛:《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与阐释”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12期。
(52)吴秀明:《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
(53)刘家思:《新发现的几篇魏金枝作品考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9期。
(54)金宏宇、杭泰斌:《中国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55)李怡:《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张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
(56)谢泳:《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史料问题——以1951年刘盛亚〈再生记〉事件为例》,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
(57)刘恋:《作家、作品论研究对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意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的理论与方法”会议综述》,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4期。
(58)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9)关于鲁迅研究可参看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60)2013年1月5日至6日,“莫言·诺贝尔奖·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在厦门大学举行。参见洪世林:《“莫言·诺贝尔奖·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综述》,载《高校社科动态》2013年第3期。
(61)王彬彬:《〈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62)何言宏:《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载《东岳论丛》2011年第4期;张继红、郭文元:《作为“底层文学”资源的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5期;旷新年:《曹征路“底层写作”意义的再认识》,载《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
(63)程致中:《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资源性意义》,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6卷第1期,3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4)夏子:《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价值取向》,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6卷第2期,6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5)顾彬:《语言的重要性——本土语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学?》,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4卷第1期,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6)郜元宝:《“小说模样的文章”》,载《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
(67)近年来学界还举办了各种诗歌研讨会和论坛,引发了研究界的广泛争鸣与讨论;如江苏省作协连续两年举办“中国新诗论坛”,《扬子江评论》还开辟“新诗研究”专栏刊发相关文章。
(68)罗振亚:《新世纪诗歌形象的重构及其障碍》,载《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
(69)施旭升:《完全戏剧:丰富中的贫困——从高行健作品看戏剧的文学意义》,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4卷第1期,1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0)2010年《江汉论坛》设置了“散文文体研究”专栏,邀请孙绍振、范培松、陈剑晖等散文研究专家对散文文体进行探讨。
(71)张志忠:《强化史料意识穿越史料迷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几点思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72)王晴飞:《胡适与文学考据化倾向》,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73)鲁迅:《〈奔流〉编校后记》,见《鲁迅全集》(第7卷),1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汤翔鹤,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