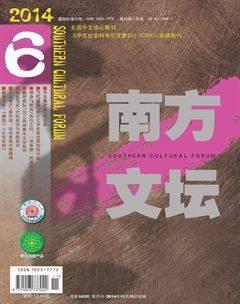新的文学史叙述原则的兴起
2014-05-30傅修海

《罪与文学》的出版和再版,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史和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情,正如鲁迅为《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时亲拟的广告词:“足以益人,足以传世。”(1)纵观新世纪以来如过江之鲫的著述,倘若要历数若干影响深远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典藏之作,则必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刘再复与林岗先生合著的《罪与文学》(2)两种。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学术语境下,面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带来的思考范式,现代中国文学史论的相关探究相当时期内陷入了“影响的焦虑”(3)。就在这左冲右突的学术史困顿期,《罪与文学》却开辟了一方新的空间,成为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4)。
《罪与文学》是一本特别的书,原因有三:一是它讨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核心概念——“罪”;二是它切入讨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维度——“忏悔意识与灵魂”;三是它衡准现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标准与旨趣——“文学与灵魂的自救”。而上述三义,在许多意义上都是令人望而却步的讨论“雷区”,或者说是“飞地”。
《罪与文学》还是一本丰富的书。全书基本上可以分为“大传统”的发论和“小道理”的纾解两部分。“大传统”从中西文化的传统差异与近现代融通为视域,阐释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忏悔意识与灵魂维度的考察”的合理性、必要性与创新性问题,最后以《红楼梦》为个案,阐述全书的关节——中国文学的“罪”的书写实践及其意义。“小道理”着墨于对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理论史的思想史辩证讨论,辅之以具体文本的审美、趣味和文本细读分析,最后以现代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的讨论为中心,回应全书的基本理念——文学与灵魂自救的关系——文学的意义。有鉴于此,作者花了整整五章的笔墨对“罪”进行相关理论上的自洽论证(第一章至第五章),有两章的篇幅对“罪”与中国传统文学世界做出追溯(第六、七章),同时还另辟两章对“罪”与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进行勾连(第八、九章)。至于第十、十一、十二章,则注重以个案(作家或文本)讨论来表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罪”的匮乏,即过于胶着于现实、俗世层面的接入,未能进入“罪”层面的超越和追问。最后一章自然归结到对有“罪”理念贯穿下的写作的探究和呼吁。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罪与文学》更是一本充满思考趣味和智慧灵光的书。读罢全书,一言以蔽之:全书理论建构和概念阐发的文字,宏阔缜密、洞幽烛微;辩难往还和文本品酌的文字,则意趣盎然、智慧闪闪。
一、罪:文学批评的新理念
《罪与文学》最大的亮点,是试图引入“罪”这个概念来讨论现代中国文学问题。为此,这本书的香港牛津大学版的副标题便是“关于文学忏悔意识与灵魂维度的考察”。不过内地出的简体版,不知为何,该副标题却被当作“多余的话”删掉了。
事实上,此“罪”并非一般法律意义上犯罪的“罪”,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作恶造孽之罪,用书中的话来说,而是指那基于“犹太—基督教教义”和“康德伦理学”而综合出来的“人类良知”(5)。因此,“罪感现象的发生,正表现了心灵对道德责任的神秘体验——良知”,“忏悔实质上是良知意义的自我审判”,其“最终结果是主体承担责任”,“使自我因承担道德责任而过着德行的生活”。“良知系统外向性的内容就是爱”,“爱如同忏悔一样,也是承担道德责任的方式”(6)。上述这些“罪”的认知,是《罪与文学》作者综括西方文化、宗教和哲学的相关思想资源,结合自己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理解和批判提出来的。要其旨,就是以“罪意识”“罪感”为关键词,生成一个“文学的超越视角”,从而为其独到的文学史、思想史言说创辟一个自洽的标准——“文学与灵魂的自救”。
在这个意义上说,被删节的副标题——“关于文学忏悔意识与灵魂维度的考察”,恰恰是《罪与文学》一书非常明确的文学史论衡的突破口。“罪”这个贯穿全书的新理念,正是两位作者精心打磨的、用以检讨现代中国文学及其批评传统的“解牛刀”。“罪”与文学的关联程度,也就是作者基于独到的文学体验和审美观察提出来的文学史书写的标准。在浩浩乎的文学史写作洪流中,这种基于文学超越视角而提出的另一种文学史写作(或者说重写),不仅标新而且立异,为现代中国的文学观察独辟蹊径,别具一格。
就此而言,在该书看来,无“罪”书写是传统中国文学和既有现代中国大部分文学的“障”,负“罪”前驱则是未来现代中国文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现代之“光”。认“罪”或负“罪”与否,恰恰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桥与墙”。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书中的这个“罪”,主要指向文学书写中作家对“良知”的追问和坚守,对人类普遍伦理责任的担当和叩问。在作者看来,这不仅是作家的应然,也是一种本然和当然。
《罪与文学》显然不是一本纯粹追求趣味性的书,也不是没有理论构建的宏图大志的书,而更是一本重在思辨与探索文学伦理问题的书。这么說并非说它没有自己的理论寄托,而是说它独特的理论探索维度和言说方式——通过检讨既有中国文学的传统,正视其自身的缺陷,进而汲引西方的文学思想资源,希望兴起一种开启未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当然,作者独特的入思也透露出了它毋庸讳言的现实依托和相关的写作语境。
写作总是有感而发,《罪与文学》也是如此。该书第三章尤其讨论了苏俄时期的文学名著,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其中有一段旁逸“秀”出的文字,令人击节:
如果一场现世的革命需要一件精神的产品来作为纪念的话,《日瓦哥医生》就是俄罗斯革命最好的纪念。因为它超越了这场革命。因为它不是以文学来大声疾呼,鼓动人们认同和参与那时尚处在尾声的革命,当然也不是单纯地谴责即将过去的革命。因为它不是以文学虚构故事的形式去描绘这场现世革命的轮廓,不是去告诉正在远离革命的后世读者这场革命的真相是什么。如果要这样做,帕斯特尔纳克懂得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将比文学远为出色,做得更好。因为它站在文学的立场质疑这场拯救现世的革命,因此它也就在精神上拯救了这场革命。所谓文学立场的质疑,不是说质疑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作为现世的拯救自然有它的理由。文学立场的质疑是关乎良知,就像所有现世拯救有它的迷失和偏差一样,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在良知的审视面前也有它的迷失和偏差。这种迷失和偏差既是革命对人的摧毁,对人心的摧毁,也是人心邪恶和无知在革命中的泛滥。帕斯特尔纳克天才地捕捉到了这一切,这种对人类事务和人心的洞察依靠的不是知识学的立场,而是艺术家的良知和心灵体验。
细细品味书中对这些经典文本的精到剖析,只要对中国现代革命和现代文学有一点点关注和感受的人,都应该能感受到两位作者“击西声东”“一隅三反”式的悲悯与叹息。的确,不都是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洗练的作家作品,不都是在红光照耀下成长的现代文学吗?可并置以观,却不免令人沉思扼腕。于是,不由得令人想起郁达夫的那句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7)同理,一个大时代里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作家没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无论是“不能”还是“不为”,都是可悲、可叹甚至可耻的事情。而现代中国文学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罪与文学》的写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不是偶然的。今日所见的文学史写作(或者说重写)的洪流大抵便是发端于彼。《罪与文学》毫无疑问也是此重写文学史大潮流中的一次思考。事实上,正如宇文所安所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几乎都是重写,只不过重写时各自所本的主义、思想不同而已(8)。不同的是,风暴一般的大陆文学史重写浪潮,更多的差异不过是作家作品的座次排序的变化,在文学史写作的理念上,多数著述并没有太多的文史观和文学识见上的差异。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在大陆现存的社会语境中,在主要落脚于文学史教材编写的驱动机制下,立足于意识形态教化和体制性市场利益分配的文学史写作,能有相对位移不一的文学史滚滚浪潮的出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数量的繁荣与质量的升降之间的关系真假姑且不论,起码不排除繁荣带来的思考向度多元和视角多维度的发生可能。时势不是也能造出英雄的吗?!
《罪与文学》不是文学史教材,也没有百舸争流般的文学史重写的利益分配焦虑,它只是旨在探索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和书写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大量的文学史写作无非都是重构文学知识的某种普遍性,那么我们不妨说,《罪与文学》也是旨在于探索另一种思考的普遍性——“罪与文学”的关系普遍性。有意思的是,这种在文学视域中的“罪”的讨论,事实上正是源于西方文学的一个伟大的传统。而置身于中国文学范畴里的讨论,众所周知,仅仅从王国维才有所发端而已。倘若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肇始,那么,《罪与文学》的思索无疑是接续了前人的思索,属于接着说的一次学术史努力。
《罪与文学》引入了“罪”来思考、书写文学的思想史与发展史,在文学史写作层面而言,固然只是一种“重写”而已,其差异仅在于标准。然而,有价值的文学史标准的确立,事实上也应该是文学批评标准的一次现代变迁,而不应该仅仅是貌异心同的、在同一批评准则下的座次轮替。那种水浒式的作家作品的位次排列变迁,实质上并没有带来文学学术思想进程的推进,充其量不过是“偶像”符号的替换而已。因此,有价值的文学史重写,绝对不仅仅是对知识普遍性构建的寻求,而应属于对思想与审美普遍性的现代探求,其本身也应该呈现出对批评思想的现代变迁的预见和多元洞察。
其实,作者早在《导言》中就说:“我们还期望写一本文学批评的书,以探索文学与灵魂的关系,即探索文学的精神内涵与灵魂深度,并且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检讨中国文学的传统,特别是现代文学的传统,尝试对中国文学作一些根本性的批评。”(9)可见,在作者的本心和初衷而言,《罪与文学》都还应该是一本“文学批评”的书,鹄的是“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检讨中国文学的传统,特别是现代文学的传统”。也就是说,这本来也是一本试图通过引入新的核心理念——“罪”——来确立其批评标准,并且以此为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的史(传统)的论衡的书。如此说来,从《传统与中国人》到《罪与文学》,不仅是作者思想旨趣的变化——从“民族的灵魂”的探索到“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的思索,也是作者悬置的文学批评理念的一次现代变迁——从文学与民族、社会、政治等的关系的群体精神反省,挪移到了对文学与个体灵魂的关系论辩。
在这个意义上说,《罪与文学》的写作既是那场文学史重写洪流的共时性的在场者,也是别一股有着更高思想追求的特异的思想潜流。其标高之处,正在于其对批评的现代变迁的独到把握与超迈流俗的追求。这和钱钟书先生的《中国固有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等著述有着类似之处,都是在朴素的讨论中引入新的理念和质素,从而看出自己眼中的文学史“风景”。这实际上也正是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说的那样:“实际上,任何文学史都不会没有自己的选择原则,都要做某种分析和评價的工作。文学史家否认批评的重要性,而他们本身却是不自觉的批评家,并且往往是引证式的批评家。”(10)
有意思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审美趣味是具有个人性的,而且也是有着地域经验的差异的。这对于属于审美的批评普遍性的构建和探求,无疑都是难以回避的现实挑战。那么,基于“犹太—基督教教义”和“康德伦理学”而综合出来的“人类良知”——“罪”的体认、担当与追问,是否能成功圆满地作为一种普遍性,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批评原则呢?按照《罪与文学》作者的设想,既然“罪”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涉及“文学与灵魂的自救”的讨论,取径于一个“文学的超越视角”,其论说前提和理论预设都已经表明其与俗世的地域性和个人俗趣无关,而只与普遍意义上的精神旨趣相连。话虽如此,但如何在无法分离文化传统的既有人类地理事实的基础上,讨论如何创辟具有超越性和普世性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精神指向和思想未来,这的确是一个需要理论自洽和现实面对的大问题。换而言之,这或许也是别一种的现代批评的诱惑。
二、忏悔意识:文学史观的新视角
《罪与文学》引入的文学观照的核心理念是“罪”,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忏悔意识”的有无作为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是自然而然的。俗话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在学术性的研究与写作中,这句话同样也有一定的适用性。每个人的立场、学识和才情不同,即便是同一则材料,其解读和适用程度也是各随其主,观点自然也各各不同。
《罪与文学》中认为:“写出灵魂对话的小说才能真正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在这些小说中忏悔意识才有真正的价值”,“忏悔意识乃是文学获得人性深度的一种精神力量。事实上,作家对现象世界的描写与揭示的深刻度,取决于他们对人的行为动机存在着紧张的心灵世界体验的深度,也就是人性的深度。”(11)独立阅读这些片言只语似有突兀,但倘若基于“罪”的确证与担当来批评文学和构建文学史,则是恰当而准确的引申。基于人类与文学在理想世界的一致性,在责任伦理的强调下,作家的写作本身就应该承载着一定的叙事伦理。为此,该书在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意识形态时,作者才会这样说:“作者要在写作中逃避责任,让叙述归结为一个具体的现世功利目标,这样做是很容易的。”(12)“以因果报应的思想模式来讲述故事实质是作者对写作责任的逃避。应当说,作者趋向于逃避责任,趋向于让故事叙述服从一个现世的功利目的,是文学史上一个明显的现象。”(13)类似论说,无疑都是在“罪”和“忏悔意识”的眼光烛照下才有的令人警醒的洞见。就此而言,人们常常说材料是被观点照亮的,信然。
可是,《罪与文学》提出“忏悔意识”来评说文学、论衡文学史的最大价值,在我看来,却并非这些璀璨夺目的观点和被重新照亮的材料本身,而是它的方法论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独特性。而说到方法,众所周知,二分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甚至是一种基本模式。逻各斯中心而形成的“逻各斯现象”,本来也是朴素的事实。但随着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省,人们纷纷对其兴师问罪,实则大可不必。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这一幕纷扰同样也共时性存在,姑且称之为文学研究二分法的焦虑。长期以来,对于文学的讨论,人们或执着于“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或斤斤于“内部与外部”的判然。归根结底,其实都是结构主义思潮下所谓“无机与有机”思维的挣扎。当然,在现代中国文学论争史上,这种激烈的二元绞缠,也许还呈现出“革命与恋爱”“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大众化”等等诸如此类的中国特色话语。
不同的文学观察与认知视角,连带生成的,就是不同的文学史书写标准。据笔者愚见和浅陋的观察,总体说来,我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标准变迁,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
1.强调文学的“内外有别”。相对于以往的文学与政治一锅端、大杂烩,相对于以政治笼罩文学的编撰模式而言,试图坚持文学的“内外有别”的文学史述显然是一次飞跃。当然,重要的并非是知道“内外有别”,而是敢于在文学史写作中坚持“诗有别裁”的“别”。这也就是所谓的不能有“出位之思”(14)。个中之“别”,也许關涉到许许多多,例如文学与政治、作者与读者、文本内外的差异与联系。就文学与政治而言,事实上,文学与政治双方无论是谁试图相互绞缠,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就文本内外而言,同样要把作者和作品有所区别。文学能否认识到这一点,对文学自身而言无疑是一种生死之别。作为艺术的文学和作为工具的文学,往往因此而阴阳两隔。正如《罪与文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从历史的实际状况观察文学,文学的确是一项可以被利用的事业。”“但是,正如文学会不断被利用一样,文学本身也应该不断反抗功利性的利用,不断地澄清和阐述文学的超越视角就是反抗的一部分。”“一句话,‘理想国是不值得追求的,于是诗就有了它的立足之地。换言之,无论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良知还是我们对自然以及人类历史的了解,都不支持一个‘理想国模式的世界。”(15)
2.凸显文学的“男女有别”。朴素地说,性别在文学史写作中从来都是有意义的。与放大性别差异的文学史价值一样,抹灭性别差异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史立场。《红楼梦》里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骨肉。何者为香何者为臭,宝玉自然有宝玉的判断标准和道理所在,但香臭相辅相成也是自然之理。以往的文学史写作采取单一的男性性别视角来观察、取径和叙述,固然是一种偏颇。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其道而行的单一女性视角的文学史观察就是全面的真理,它不过是补偏救弊的另一种观察而已。而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学史写作是双性的,也不可能有哪一种文学史观察是无性别差异的。这并非是文学史的问题,而是人类性别的客观事实。因此,立足于文学与性别关联的文学观察模式和文学史写作,其实相互之间只有“水/泥之别”,刻意放大各自的合理性的结果,只能是文学史写作上的性别撕裂,是文学史思想上“不及物”的“水土不服”。因此,除却那种以表明性别不调和的立场为目的的著述,大量以女性冠名的文学史写作和批评,其价值和局限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3.回向文学的“天差地别”。文学作为艺术之一,当然不可能是天外飞仙,它只能是人类的相关产物。从文学生产的意义上,文学发端的起点就是世俗而现实的人本身。但文学又是人类精神的结晶,尽管其神必须要赋形,作品终归要落实为语言、文字等符号,但影响到人本身的文学却又是精神的。因此,作品好坏的差别判断,最后还是要以文学是否让人完成自身超越为标准。因此,文学的观察视角不妨可以向上一层,基于文学的世俗存在样态而取其超越世俗的视角,这或许正是《罪与文学》的文学史写作的理想——探究“文学与灵魂的自救”之间的关系。这种写作与批评的路径与理想,正是作者后记中一再强调的——“通过‘忏悔意识这一个切入口,我们对文学的本性,对文学的自由与责任,对文学的世俗视角与超越视角,对中国文学的宏观长处与短处,对东、西方文学特征的基本差异,对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永恒之谜等等,都有了比以往更深也更真切的认识。”(16)的确,回到文学与人心的关系来观照文学和文学史自身,也许是一个更为超越的视角。尽管人心隔肚皮,但在关乎情感和精神的文学判断和辨别而言,侧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意义上的普遍性体验,强调人与人之间存在普遍性关联的解释,这不仅可以跨越种族、地域和文化,也让我们觉得更加朴素,也更为温暖。人天生就有灵肉的两面,“人性是一种复性。人性世界是互相冲突的双音世界。人类的灵魂天生就彼此分裂成互不相识的两半,但每一半都有充足的理由支持自己的立场,冲突的双音,每一种声音都符合充分理由律。”(17)这也正是《浮士德》里所说的:“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们心胸,一个要想和别一个分离,一个沉溺于爱欲之中,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世,别一个猛烈地要离去凡尘,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18)由此可见,《罪与文学》的文学史观,正是期待以“罪”之名,以“人类个体灵魂得救”与否来判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探索进程。在作者看来,个中差异无关乎种族、地域和性别,也不关乎政治、社会与经济。它只和作品的“灵”境界飞升与否相关。好与坏的文学存有云泥之别,好的文学,应该是让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意识到彼此休戚相关的精神省察与叩问。
由此反观既有的大量文学史著述和批评,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贴着现实和俗世的文学观察。紧跟时代潮流和俗世荣辱的记录和书写,难免会带来无法释怀的文学论断的摇摆和焦虑,其結果也不免于众说纷纭。所谓的作家排座次,所谓的文学史的“微调”,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溯源的早与晚,在部分意义上说,这些争议不妨都可以归因为“二元对立”这一共同的文学观察模式导致的结果。诚然,《罪与文学》所向往的以“忏悔意识”为猫眼的文学观察和文学史评议,当然也是一种二分法模式下的二元论说,即超越的与俗世的、有忏悔意识的与没有忏悔意识的两种。然而,相较于以往那种紧贴世俗功利逻辑的写作政治的站队,这种基于作家作品的写作伦理的文学观察,无疑是一种新的观察视角,而且是一种试图走向人类普遍经验、普遍情感和普遍伦理的文学精神的“归家”,它的理论高度和入思深度是显而易见的。
文学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19)。然无论如何,作为艺术的文学,它都应该属于精神追求,并且应该致力于更高更远的精神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与宗教应该有一定的相通,他们都是人类灵魂的栖息地和休憩所。因此,就文学观察取径的意义而言,《罪与文学》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倡导了一种回到源头的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它致力于叩问一种回到文学精神自身的写作伦理和批评伦理,它试图构建的是一种以个体灵魂清洁为审美趣味和思想原点的文学史哲学。在该书作者看来,回到个体灵魂自救的文学,才是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的“灵魂”所归。因为“人类本体性的良知所遵从的信念只有一个:人类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必须对共同的命运负责,这种信念是无所不在的、至高无上的召唤,是人类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源泉”(20)。在这个层面上,不仅文学写作如此,文学研究也不例外,个体灵魂的得救才是文学的灵性所在。
真理都是朴素的,但并非是片面的。基于个体出发和归家的文学伦理,固然是可以取径超越视角。然而人类社会生存的群体性事实和文明累积形态,却总是显示着群体性的呼声。没有广场鼎沸的呐喊及其群力之蛮,就显不出旷野荒寂的呼告及其弱德之美。在我看来,《罪与文学》从“忏悔意识”出发的现代中国文学观察,显然不是为了独树一尊而抢麦克风,而是为了在众声滔滔、泥沙俱下的同质化文学史写作中,试图发出别一种声音、增加另一个视角。这也正是我相信《罪与文学》必将会在文学史重写的滚滚红尘中有所留存,可以聊备一格,能够迎风伫立的原因。
三、文学史写作的向度
百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进程中,只要提及那些筚路蓝缕的经典著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都是难以绕过去的原点。然而,较之于冠之以“文学史”为名的著述,《罪与文学》显然是一本并不非常系统的“另类”文学史。相反,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样,《罪与文学》却是一本有着自己的文学批评标准,有着自己的文学史理念发凡的文学史,它将带给我们不少关于文学批评、文学思想史和文学史哲学方面的思考。
考索起来,文学史的写作,从发生学角度上就是现代国民意识形态教育的组成部分。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上看也是如此(21)。就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写作而言,从林传甲的为教学需要而作的文学史,到胡适的为新史观和新文学语言观而发愿写作的文学史,无一不是有着鲜明的宏大叙事或指导思想的文学史写作。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纷扰百年,尽管其间每每政权更替、话筒轮传,但在一定意义上都似乎成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更新的文学史叙述活动。如此说来,不少所谓的文学史重写——都是一种“热”的文学史写法,“解释性的写法”(22)。相对来说,围绕着一个文学史观的新理念而创辟的写作,如王国维的“悲剧”的文学史观、周作人的“抒情”的文学史观、《罪与文学》的“罪——灵魂的自救”的文学史观,凡此种种,则更像是一种“冷”的文学史写法,我姑且称之为“建构性”的写法。
静而思之,无论是意识形态的规约和教化,还是某一文学理念的史的解释和结撰,无论是“规训”还是“惩罚”,文学史的写作,本质上都是关于文学的知识化的整理,即是文学的史化过程(23)。其间或许有“史观”的洞见与盲视之别,但知识化、系统化的本质则是一致的。当然,文学本身就有知识性的一面,正如历史记录也有文学修辞的内涵。但这里还是天然地隐藏着一对矛盾,文学的艺术性、活态生机和历史的知识性、记录留存,二者本身就形成了对立面。既然如此,有了文学的史化,就必然会有文学史的文学化的反动。在文学的知识化整理之后,就必然会有对知识进行文学化还原叙述的冲动。所谓反者道之动。
冷与热的两种写法,本该是文学史写作应该有的常态,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写法。可当前的问题却是,文学史写作的“冷热不调”,“热”的过多,“冷”的太少。当然,多并非就不需要,少也未必就没价值。只不过,当“热”的文学史太多乃至过剩的时候,“冷”的文学史的写作无疑就成为难得一见的“异数”。重写文学史的潮流滔滔,“冷”的文学史写作却难得一见,《罪与文学》正是这冷不丁而来的“惊喜”。
陈伯海先生曾说:“从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来看,加强哲学思考是其内在要求。中国文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不下两千余种,论文及专题研究更多如牛毛。正因为积累了丰富经验,到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出现‘建设文学史学的呼声,要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对文学史研究本身进行一番学理性总结,其中也包括对文学史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方法论等根本性问题的理论反思。提倡哲学思考,正是为了让文学史学的建设有一个巩固的理论基础,进而推动文学史研究实践的深入发展。”(24)如果我理解得不算太离谱,所谓加强对文学史的哲学思考,理想的境界也就是“哲学的文学史”,也可以说是“思想的文学史”。文学与思想,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不存在完全没有思想内涵的文学,也不会有彻底没有泛文学意味的思想。但就文学史写作而言,既有的文学史多是侧重文学知识的文学史写作,倚重文学思想探究的文学史写作并不太多。从立足文学知识收纳,到钟情文学思想进程,这或许就是“哲学的文学史”——一种“冷”的文学史叙述原则的兴起。而彰显文学思想进程的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当然也就是一种文学思想史。从注重文学知识及其立场,到立足文学知识的叙述与修辞本身,这毫无疑问已经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一次大飞跃。但从文学知识化的“史”的反拨开始,认真细致、冷静朴素地检讨一下中国文学的传统生成与变革,进而构建一种基于对知识化的焦虑与冲动的反思的“思想的文学史”,或许将迎来现代中国文学史叙述的一次大变局。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可以乐观而大胆地预见,当文学史的撰述从“文学知识”位移至“文学思想”之时,《罪与文学》所開创的,将不仅仅是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变动,更是一次文学史观的解放,也许将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原则的兴起。
【注释】
(1)鲁迅:《〈海上述林〉上卷出版》,见《鲁迅全集》第7卷,4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初版。中信出版社2011年再版。本文引文出自香港牛津大学的初版本。
(3)[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25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4)[德]恩格斯:《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6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5)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36、40、40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50、51、51、53、54、58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郁达夫:《怀鲁迅》,见《郁达夫文集》(第4卷),162、163页,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8)[美]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见《中国学术》2001年第1辑,总第5辑,刘东主编,180-20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导言》,见《罪与文学》,1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美]勒内·韦勒克、澳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3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11)(12)(13)(16)(17)(20)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158、189、189、438、157、165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见叶圣陶编《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54、169页,开明书店1947年初版。
(15)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87、88-89、92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德]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9)钱钟书说:“兹不为文学定义者,以文学如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向来定义,既苦繁多,不必更参之己见,徒益争端。且他学定义均主内容,文学定义独言功用——外则人事,内则心事,均可着为文章,只须移情动魄——斯已歧矣!他学定义,仅树是非之分;文学定义,更严美丑之别,雅郑之殊——往往有控名责实,宜属文学之书,徒以美不掩丑,瑜不掩瑕,或则以落响凡庸,或乃以操调险激,遂皆被屏不得于斯文之列——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合而为一,歧路之中,又有歧焉!”(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见《钱钟书散文》,47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1)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2)林岗:《谈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载《光明日报》1983年9月27日。
(23)金慧敏先生甚至认为“文学没有历史,流行的各种文学史不过是用非文学的绳子将文学穿缀起来”,既有的文学史多是“科学主义对文学的‘殖民”。参见樊柯:《“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2005年第1期。
(24)陈伯海:《文学史的哲学思考》,载《文汇报》2007年12月2日。
〔傅修海,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研究”(13CZW065)、2013年河南省高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项目、河南省2013年“高层次人才国际化培养”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