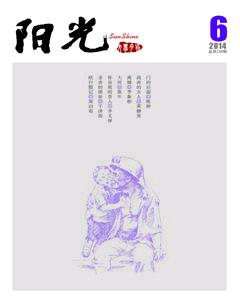从使命中绽放出宿命的花朵
2014-05-29江耶
江耶
叶臻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具体的诗人。在此前,我脑子里的诗人就像他们的诗意一样朦胧、神秘而神圣,需要我远远地进行仰视。但叶臻却非常随和,容易亲近,在某个偶然的机会突然地就亲近到了跟前。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是中年的我开始喜欢和关注文学。时间很快过去了近二十年,仿佛就是一瞬间,我已经年近半百了;长我五岁的叶臻也已经过了知天命的界线。仿佛是在配合地印证这个年龄,我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回忆,在记忆中留恋年轻时的美好时光。从不惑到知天命,应该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很多方向已经明确,悬念已经落地,对世界、对社会、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思考问题和处理事情也越来越脚踏实地,不虚无,不虚伪,世俗地活着。叶臻的人生已经从这个阶段经历过了。作为诗人的他,相信会有更加独到的体验。诗言志,诗歌也是诗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他的诗歌同样经历了这个阶段,诗风和题材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直面现实生活,沉浸于现实生活。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叫《回到生活》,我认为,文字、语言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了,已经远离了具体生活;我们写东西,就应该写生活,尽量地靠近生活,回到生活,使这些铁板一块、冷冰冰的方块字重新获得生活的温度,使我们阅读时能触摸到生活中生动的气息。
二十多年之后,整个中国的现代诗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比较注重诗意的营造,显得比较空灵。那个时候的文学地位比较高,诗人站在更高之处,居住在高高的象牙塔尖,俯视着人间的烟火,很难被这烟火熏到。叶臻在那个时代已经很有成就,成为诗歌界我们煤矿系统的代表人物,并将煤炭题材的诗歌地位大大地提升了。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物质世界也是一日千里地变化,诗歌风格和题材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叶臻的诗歌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变得更加接地气了,他的诗更多地观照人间日常,把人当作“人”放入凡间,写出的是作为凡尘中的普通的“人”的想法、做法及社会评价,向人性的根本深处回归和挖掘。
我们来看看他的这首《夫妻墓》:
在公共墓地
绝大多数墓碑上阴刻着两个人的名字
有的刷白漆,有的刷红漆
刷白漆的已经死别
刷红漆的还是生离
诗中描述的景象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风俗,我们在任何一个墓地都能看到。从这几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叶臻对日常事物中诗意的发现和提炼是很有功力的。墓地中密密麻麻的墓碑是客观的存在,一般的人来了最多看到的是人们对逝去亲人的感情寄托,诗人更进一步,把它们归纳起来,放置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放置到关系的分离情节之中,放置到感情的大起大落之中,于是这个绝大多数都熟视无睹的正常景象就有了新的意义。墓碑上的名字像一个一个破折号或者是一个通道,它们指向一段一段的历史,它们不想让人“入土为安”,它们努力地不让一层薄土将历史埋没,它们让历史在一个人、一些人的心里活着,强烈地活着,激烈地活着,让人的内心无法平静,辛酸不已。他开始讲述一个邻家故事:
隔壁的王婶,她的名字也在墓碑上刷了红漆
其实,她的名字一点儿也不红,她的丈夫
倒是和“黑”有些关系
她在一九六六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开始
守寡
头上顶了大半辈子黑纱
如今,日子安稳,儿女孝顺
儿女们把做了四十多年孤魂野鬼的丈夫迁
入公墓
在墓碑上刻丈夫的名字,也刻她的名字
两个名字住在一起,一个在阴间做梦
一个还在阳间喘气
丈夫的遗像前,她摆的祭品也很特别
一节白藕,两朵白莲,三碗白米饭
这些白东西,意在表明
时间还了丈夫的清白
前一段诗中的关于红与白的伏笔在后一段诗中得到了揭示和落实,很显然这个落实不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之中,它们在意料之外。这是诗歌的好处,它们在象征,它们在指示,它们用更恰当的方式对我们的思想进行了提示。比如这红,红在动着,不仅是身体,还是心思;比如这黑,不仅是消失了的生命,还有生命中的感情色彩;比如这白,它是白藕,是白莲,是白米饭,还是什么都没有的空白,还是干干净净的清白。三种颜色,都与生活对应着,不仅仅是一对一,是一对许多,功能非常强大。从诗歌的叙述进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无论是事件中的主人公王婶,还是作者本人,他们都看重了意象的指向意义,在指向中选择了白色,选择了它所指向的清白。至此,诗歌的目的已经清晰可见。
文以载道,诗歌要有意义。这是文化的惯性吧,鲜活的日常生活被刻意的符号提炼了。因为诗歌成型之后要摆在大众的面前,会被其中的一部分人看到、重视、回味,引起一系列的思考。所以,像所有叙述者一样,在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的时候,总是想要弄出点儿有价值的东西在里面,归整出一些可供思索或者参考的线索和线路来。诗歌处在语言艺术的顶层,它依然是语言艺术,依然要从艺术的大道中穿过,像一个人瞄准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诗歌似乎也在努力地肩负着它自己应该承担的一份使命,在这条大道上奔跑着,到达设定好的峰顶。
把意义落实到人间,使道理在普通人中执行,必须让它们蕴含的美好东西能够闪现,能够感知。这是文学、艺术的任务,它们不像规则那样对人们板着生硬的脸孔,而是用美的柔和和柔软进行打动和呼唤。什么是美,我认为,美就是愉悦,在生理上感到愉悦,在精神上感到愉悦,得到启迪,仿佛得到了享受。诗人本身要热爱美,对美有感觉,眼里要有美。这就需要他本人要热爱生活,要擅长于把生活中的愉悦发现出来,然后表达出来,再传递给大家。
怎么才能发现愉悦、发现美呢?我觉得最起码的是要真实,忠诚于生活,忠诚于生命本身。这一点叶臻做得比较好。在稍微正规一点儿的场合,他在说话前都会说,我说的是真心话,或者我真诚地说,害怕别人不相信他的真。正是因为他的真,他能脚踏实地地深入,能够矮下身子用最低角度观察事物,他看到了事物的本质,看到了事物内在的规律,看到了事物的方向:
在老诗人的墓地,我遇到了一只蚂蚁
它好像是靠释放自己体内的气味,唤来了同
类
先是几只,随后是一群,一大群
蚂蚁的小如此浩大,一条集体主义的乌黑波
浪线
扛着,不如说是载着一只死蝉的残翼
生与死的配合,如此天衣无缝
蚂蚁只想解决饥饿,死蝉用残翼
完成了再飞一次
──《残翼》
“再飞一次”是诗人从一个细小的生活细部看到的、想到的,自然界中一个极其平常的生活活动,被诗人赋予了极其美好的象征。从细微之处发现,在细微之上呈现,往往更能让人感觉其可靠,更打动人。对这样的细微之处的发现和提升,必须保持足够的兴趣和相应的能力。美国诗人、小说家卡佛说,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卡佛说的意思就应该是文学创作要向生活细微的地方挖掘,保持现场在场的感觉,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我们前面说到了美,说到诗人发现美、表达美、传递美,也就是这样一层的意思。
美呈现上来了,作为读者,就要审美。美是艺术的本质,诗歌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有手法,有布局,有谋略。作为读者,我们要把作者在诗歌里安排的任务接过来,把美重新审视一次。当然,我们各有各的认识,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审美体验,所以看到的也各有各的不同的美的发展方向。
我们再来看看叶臻另一首诗:
夜晚的晒场上铺了一层淡淡的月光
在麦草垛旁 大楞家的黑狗与二妮家的黄
狗
相互嗅着——就连在了一起
第一个往狗身上砸黑石头的
就是那个扎着小羊角辫的漂亮二妮
黑狗的两眼流血了 黄狗的两眼全瞎了
它们也没有“汪”一声 还是连在一起
大楞生气了 大楞真的生气了
他找来了一把锋利的小铁锹
朝连在一起的黑狗和黄狗狠命地扔了过去
就那么准 小铁锹扔过去
黑狗的命根子就齐刷刷地断了
黑狗“汪汪汪”地一头钻进了杂树林
黄狗“汪汪汪”地一头撞向了
乡村公路上开过来的手扶拖拉机
——它流着血的身体里还藏着黑狗的命根子
──《黄狗的身体里藏着黑狗的命根子》
美好的事物被破坏、被毁灭,就是提醒人们对一些事情的警惕,也是在表达美的珍贵和人们对美的向往、珍视。这首诗,更像一个小说,用清晰的细节展示出黄狗、黑狗在“人道”的背景下的必然悲剧命运。生命的本能,原罪中的快乐,至今仍然没有被任何一个高高在上的宗教所废弃,因为它承载着大千世界的生生不息之重任。细节就是最大的力量,最能给人以震撼。作为自然生命的人,用社会里的非自然的规则去约束、裁决,“人道”不是狗道,也违背了自然规律,在它的道路上行驶当然就扭曲生命的本性。在这里,诗歌其实已经离开了具体的生活现实,对生活现实进行了概括,在概括中进行了提升,使诗歌有了重要的力量,给读者以足够的警示。
无论是比喻还是象征,诗人能够把目光投向它们,能够在诗句里表现它们,说明了诗人自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对生活和生命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都局限在自己的生命之中,我们都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之中,我们都身陷于一个一个具体的小情境之中。小情境中有大意境,比如日月星辰在我们内心的投影,我们看到了,我们想到了,它们照亮我们,同时也被我们照亮,我们回避不了,也没有必要回避。比如在《日暮》这首小诗里,作者写道:在圆融寺外,小小的荷塘/竟然装下了落日/一池清静的河水/卸下了绚烂的落霞/风举圆荷,掸去了落日一天的尘踪/落霞有术,分身投宿于清香的莲房/淤泥里修行的老藕,一身洁白/返回斋碟,解了落日的饥渴/寺外的天灯,投影荷塘/一盏小小的禅火,顶起了随后的黑/拎水的小沙弥,被自己肥大的僧衣绊倒/青石板上,打滚的木桶/泼一地湿漉漉的落霞。非常可爱的诗,这里面充满了禅味,使我想到了那句著名的“欲辩已忘言”。禅是什么?是智慧。
智慧应该运用于生活,用来改善生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是生机勃勃的,生活是生生不息的。诗人是人,是自然生成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诗人的生命是自然界中的一个普通事物,像所有生物一样有着发生、存在和消亡的规律,他与周围甚至远方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他必须和各种关系共同生存在同一蓝天之下,共处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之上。靠近、贴近、进入过程之中,比喻和象征解决不了问题,你必须直面一切,直接与对手过招、对所有难题进行拆解。高手的方法是用艺术回旋的方式形成新的空间,把一些事情隔开,从而做到从容处置。我们能经常听到叶臻津津乐道他处理家庭关系的趣事,比如怎么跟母亲说,怎么跟妻子说,怎么跟妹妹说,怎么把众多亲戚的事情办得圆满。可以看出来,他是热爱生活的,热爱生活首先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从爱身边的朋友、同事、乡邻做起。他是宽厚的,因为宽厚所以宽容,因为宽容,在他的辛勤建设中,他的亲友和睦相处,他的世界和谐宽松,他的精力都能集中到工作中、创作上。
这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我曾经和叶臻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了四年,我知道他对工作的严谨态度,他对亲友的真诚心愿,他对学习积累的足够重视,在很多事情上他是“不宽容”的,甚至到了较真、苛责的程度。我多次听他说到他提出的工作方案得到某个领导的欣赏,他的工作建议顺畅地得到上级的采纳;在诗歌创作上,他反复说,要与诗坛进行对话,保持身在当下的敏感状态。像我一样,叶臻的父母都是农民,从农村来到这个城市,没有任何背景。我明白那些熠熠生辉的光彩背后是他辛勤的汗水,我能体味到每一个进步中的台阶上他付出的艰辛努力。诗人在生活之中。诗人尖锐地深入生活,敏锐地感知生活,深刻地思考生活。但叶臻不太尖刻,他对生活是理解的,他几乎没有抱怨。
你在跑,你从乡间的羊肠草径
跑上了通往城市的文明大道
你把自己跑得只是一个黑点了
你跑得多么的小
…… ……
你在梦里跑
刚给老家的亲人快递了一个哈欠
又向流水线上跑
你在尘世跑
你跑单帮,贩卖的是血汗
你跑龙套,却穿不上龙袍
你跑江湖,也只是个草寇
你跑码头,也只能扛草包
你这样一条草命
…… ……
你跑得看不见了
你跑得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你在跑》
诗歌跟随着诗人深陷于生活,进入了生活现场。一直不停地跑动着,是大部分农村人进城工作以后的真实写照,叶臻在这里写得可谓入木三分。可能也带上了自己的影子吧。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他的认真劲了。他通过挤高考的独木桥挤进了城市,挤进了城市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劳永逸了,他只是到达了那些出生在城市的人的起点,还够不到那些官宦子弟的出发点,他必须马不停蹄地紧赶慢跑,才能适应、维持、追赶,一点一点前进。应该说,他算是很成功的了,在工作上他获得了相应的成绩,在文学上他也是颇有成就的,但他仍然十分警省,做事仍然不敢有一丝懈怠。他说企业对他够可以的了,拿这么多的工资干这么少的工作,有时觉得有愧。他知道分寸,知道感恩,知道如何把握生活,在生活的现场中进退自如。这是诗人做人中的朴素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他创作中的映射,就是他写出了相当数量的描写底层人生存状态的诗作,他把最应该关注的生活现场呈现给了我们。我认为这是他用心回报社会的方式,他秉持着自己的观念,发出浑然却十分厚实的光芒。
五颜六色的现场不是一两个词语所能够穷尽的,也不是几句描述或者几篇文章、几首诗所能够涵盖的。但我们仍然在深入,在深入中体察、认识,看到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些花、这些叶都有独特的意义,都有自身的美妙,共同把我们经历的时空填充得丰富而多姿多彩。
诗要对这些生活进行提炼,要思考,思考人生的意义。在淮南矿区,大部分写诗的人都是看着叶臻的诗开始写诗的。我也是。相对来说,我的走近、走入还算是晚的。大约在这个世纪初吧,我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从这个时候起,我自己开始写一些诗歌作品,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诗歌是什么,诗歌与现实生活是什么关系?什么才是真正的诗歌,诗歌能做什么,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对我们的经济繁荣,对我们人生的塑造,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有时也告诫自己,不要去思考重大的、重要的事情,把每一个日子过好,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把每一首诗写好,这是我想到的诗歌意义。像生命,我不想它是不是人生,我就想这一刻,此刻此在最重要。这是我的想法。叶臻的诗歌里也有类似的表述,他在《痒》里写道:
身体里藏着痒
不经意间,它跑出来
唤一只手或别的什么
去挠
…… ……
顺便提一下挠下的皮屑
它们先于身体回归大地
结下尘缘,成为看不见的微尘
好像生命也是如此
非使命,是宿命
──《痒》
是的,生命是宿命,不是使命,或者说,使命本身就是宿命,是一个个宿命连接、堆积起来的。想到了最深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殊途同归吧,赤条条地来,也赤条条地走,不是生带来的,死也带不走。想明白了,还不如活着的时候努力活得精彩一点儿。孔子在编选《诗经》时,把从民间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风”放在了庙堂上吟诵的“雅”和“颂”前面,足见他对百姓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的看重。
高大的意义、神圣的使命已经被身在高处的人们反复、高调地颂唱。不是每一棵树都一定会成为栋梁的,成为栋梁了也不一定就能骑在一栋大厦上支撑起高大,即使真的在某个大厦中担当起重任,也不能把整个世界建设起来。我要说的是,一棵树是个体的,它有它的使命,同时也有它的宿命。使命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必要强求;但宿命是一样的,比如是树就应该长高长大,发出枝杈,开出花朵,结出果实。在树的比喻中,我们可以向栋梁的方向发展,但一年一年的轮回中,先把枝发出来,把花朵开好。这是生命的本义。这是世俗的成功和幸福。这一点,叶臻的作品、事业都已经证明他做得非常成功。在这里,我也再次祝福他,有更多的花朵绽放开来,结出更多的果实,向一棵大树的使命目标不停地靠近。
江 耶:本名蒋华刚,安徽定远人,1968年8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协理事。先后在《诗刊》《中国作家》《诗选刊》《清明》《作品》等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获安徽文学奖、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奖项,著有散文集《天在远方弯下腰来》《墙后面有人》,诗集《大地苍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