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肩起黑暗的闸门?
2014-05-12云也退
云也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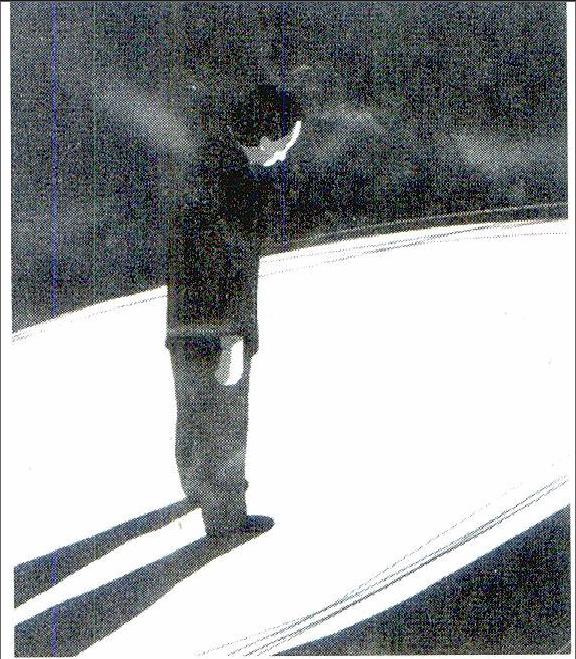
昨日恰与一位俄语教授兼俄罗斯文学专家同车,途中问起一个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像勃洛克、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在1917年后从旧阵营里脱嵌,开口讴歌布尔什维克的新时代,叶赛宁甚至咏叹十月革命的改天换日之功,他们原属的那个仍保持独立性的诗人圈,却似乎并没有群起而攻之。与之相反,尤以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诗人,仍旧保持着对前辈的敬意。是何缘故?帕斯捷尔纳克在《安全保护证》里诉诸很大的篇幅批评马雅可夫斯基的转向,细读之下,文字里浸透的却是遗憾、困惑、伤心,帕氏认为马氏的转向,导致他后来的作品鄙俗不堪,毫无美感,是他自己的损失;而对马氏的道德人品,帕斯捷尔纳克基本沉默。这又是为什么?
教授说,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俄罗斯不似中国,中国人对道德问题很是敏感,谁谁谁变节了,谁谁谁被招安了,用词都十分严重,而在俄罗斯,文人之间的信赖和依恋,如同他们与土地的依恋一样,那是紧而又紧,难舍难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崇拜,保持在诗艺的层面上,不管其人如何表现,一般都能牢固不破。
第二个原因:俄罗斯文人有妥协的习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俄罗斯文人就是一群精神十分独立,又从来不避向世俗权力妥协的人。
这旬话我听进去了。说到妥协,便想到帕斯捷尔纳克,过去读俄国人的作品和生平,得知帕斯捷尔纳克放弃了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只为不被开除苏联国籍,不被驱逐出境,那真是痛心疾首:为什么?移民难道不好吗?自由空气不是他所要的吗?多少持不同政见者一去国外,国内人再说起他们总是语带羡慕。在我看来,硬碰硬的结果固然难以预料,但作为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一点骨气还是要有的,何况,你看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帕氏可能失去的,不见得就比后二者更多吧。
但凡留下,就必然要妥协。在苏联,与在中国不同的是,“气节”之类的东西是不能与才华相提并论的,为了保住自己的才华所生长的水土,让它能有展示的机会,文人必须妥协,这并不丢人。帕斯捷尔纳克放弃诺奖,是因为不愿“断根”;而在阿赫玛托娃身上,同时期发生的妥协行为则更加耐人寻味。
十五年的禁言之后,扼住阿娃喉咙的手终于松开了一点点,根据一种道德标准审视,她付出了妥协、甚至背叛的代价。在帕斯捷尔纳克受难的时候,她竟然出了书——难道她不应该继续进行精神绝食,以声援战友吗?一个弃奖,一个破禁,而且两者之间有着因果联系,即使这两人不翻脸,旁人也该说三道四了。
说三道四的人当然不少。热血的后生觉得70岁的诗歌女神“晚节不保”,不足为奇。但这决不公平。知识分子公开表现自己在权力面前的宁折不弯,曾经会惹来流放乃至杀身之祸,但1960年前后,“解冻”的信息已在空气里浮动,倘若继续强硬地表态,一个台阶都不给,将权力逼到死胡同,是不是反而害及自己所支持的人,甚至导致时局倒退呢?
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苏联的事,如今仍然余音不绝。而在俄罗斯文人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不干涉他人的妥协选择,不要求他人去“肩起黑暗的闸门”,即使谈不上“良知”,也是个人操守的一部分。当然,阿赫玛托娃也没有做直接伤害帕斯捷尔纳克的事,她仔细考虑过自己的转圈空间有多大;她未在帕斯捷尔纳克最困难的时刻发声,但也不会像“文革”时代的那些中国人,如此积极地与过去的朋友反目。
气节良知之类,从来就不是绝对。妥协的实际效果,也是很难估计的。
独立的个体须有原则,有信念,还得有以赛亚·伯林所说的
“现实感”。个体可以掌控的只是很有限的一点东西,热血的人走向成熟,一定会对一句很俗很俗的话有所体会:岂能尽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摘自《杂文月刊》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