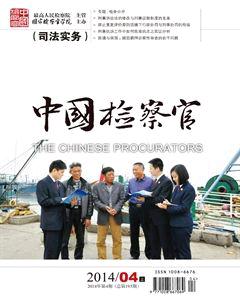程序非法的有罪供述证据之运用
2014-05-08贾潞斌牛庆辉
文◎贾潞斌 牛庆辉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046011]
程序非法的有罪供述证据之运用
文◎贾潞斌*牛庆辉*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046011]
[基本案情]2011年4月17日晨,54岁的卖淫女张某的房门已两日未开,其房东将其男友叫回后,男友从窗户上看到张躺于床上,似没有生命迹象,遂报警。警察到达现场后,发现墙上有甩溅状血迹,张某尸体上覆盖两条被子,面部覆盖毛巾,左下颌、右耳下、枕后共四处刺创,判断死于他杀。现场勘查时发现,房屋窗户完好,门锁闭锁完好;张某床头可见一黑色塑料柄单刃切刀,刀上未见血迹;被子与床褥之间可见一卷卫生纸,上面有一点状血迹。2012年3月26日,技术人员在DNA比对后发现,卫生纸上的血迹系正在劳教的杨某所留。2012年4月1日,劳教期限届满的杨某被抓获,次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临时羁押于公安机关的讯问室,当月6日凌晨4时其供述了杀害张某的经过,上午指认,并对作案过程详细讲述,下午在公安机关再次作有罪供述后,侦查人员将其送至看守所羁押。之后,杨某推翻有罪供述,辩称在公安机关受到刑讯逼供。
杨某的有罪供述证实,2010年5月,杨某在打工时认识张某,后多次在张某租住房与张进行性交易。2011年4月的一天,杨某到张某租住处,张某称其与杨某发生性关系时曾摄像,以告知杨某的妻子为由勒索现金2000元,双方发生争执,后杨某在翻找录像带时从张某枕头下发现两把刀,其持其中一把短刀威胁张某,张某持另一把较长的黑色塑料柄单刃刀与杨对峙,后杨朝张头颈部连捅数刀,杨某在作案过程中手部受伤。
一、问题的提出
综合分析本案证据,现场勘查笔录中记载的黑色塑料柄单刃切刀,侦查人员没有收集,现场墙壁上的喷溅状血迹没有提取和鉴定,杨某作案时所持刀具,没有找到。证明杨某与案发现场有关联的,一是其有罪供述,二是现场卫生纸上的血迹。而杨某的有罪供述是在公安机关履行刑事拘留手续三天后,在公安机关的审讯室内临时羁押期间获取,加之杨某关于刑讯逼供的辩解,其有罪供述可否采信,成为定案关键。在此,面临的问题是,杨某的有罪供述是否是非法言词证据,是否应当排除。
二、非法获取的有罪供述证据的采信
杨某的有罪供述共三份,第一份是凌晨在公安机关制作,第二份是指认现场时制作,第三份是指认现场后在公安机关制作。那么,侦查机关获取的有罪供述是否是非法言词证据,如果确系非法,是否一律排除,是采信证据的关键。
(一)违反程序法获取的有罪供述系非法证据
2013年1月1日施行的第二次修正后的 《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2013刑诉法”)第83条第2款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1997年1月1日施行的第一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97刑诉法”)并无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多长时间送押看守所,似乎法律出现空白,二十四小时以内未送押也似乎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根据“97刑诉法”第64条第2款规定,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应当将羁押处所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单位,所以通知前犯罪嫌疑人应被送入羁押处所,二十四小时内送入也是应有之意。只是该规定并没有和“2013刑诉法”一样加以明确表述。因此,犯罪嫌疑人送押不及时在“2013刑诉法”生效前似乎并不违法的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杨某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拒做有罪供述,侦查人员在抓获第二天办理了刑事拘留手续,但未送看守所羁押,而是在侦查机关的临时讯问室内看押,直到第四天,杨某做了有罪供述,侦查人员才送看守所羁押。从程序方面考察,侦查机关未在二十四小时内送押看守所的行为违法,杨某作有罪供述是在被刑事拘留三日后,因此,从刑事拘留满二十四小时至杨某被送押至看守所,侦查人员所获取的口供均是非法的。
(二)无法排除刑讯逼供合理怀疑的非法言词证据不应采信
根据“2013刑诉法”第54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95条的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受到非法对待的形式不同,但依据法律规定,只有在受到肉刑或变相肉刑、其他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行为后,不得不违背意愿供述的,才可界定为“刑讯逼供”。本案中,杨某到看守所后即翻供,并辩称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在被公安机关关押期间,其始终坐在讯问室的铁椅子上,吃睡等基本的饮食和休息均未能得到保障,为了获取其有罪供述,侦查人员用手铐的齿形部分夹过其手指。经向侦查人员了解,为了保证办案安全,杨在公安机关的四天内,确实始终坐在讯问专用的铁椅上,但侦查人员尽量保证了其饮食和休息。期间,杨某为了缓解精神压力,曾请求侦查人员用电棍击打他,但侦查人员没有满足其要求,也没有用手铐夹其手指。
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在被刑事拘留后近四天才被送往专门的羁押地点,这与其没有及时作出有罪供述是在因果关系的,侦查人员在该情形下留置于公安机关的行为,已属程序上的违法。在此前提下,侦查人员让犯罪嫌疑人坐在侦查机关专用的铁制讯问椅上近四天,无论侦查人员如何说明保证了犯罪嫌疑人的正常饮食和休息,也不可能使犯罪嫌疑人真正得到休息。对于正常人而言,一天中有部分时间以躺卧姿势休息是正当和正常的休息,如果让其始终坐在铁制的椅子上,显然剥夺了其正常的休息。侦查人员的这一行为是一种软暴力,是一种对被讯问人的肉体折磨,是实质上的刑讯逼供,结合杨某第一次作有罪供述的时间为凌晨,无法排除其因肉体上受到非法对待而作有罪供述的合理怀疑。为了排除合理怀疑,要求侦查机关提供杨在公安机关被临时羁押期间的视频资料,但侦查机关无法提供。因此,对于杨某所做的第一次有罪供述,无法排除是在刑讯逼供条件下获取,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
(三)排除刑讯逼供可能的非法言词证据可以采信
司法实践中,类似本案的非法取证行为可能不止一例,这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素质的高低、盲目追求口供破案等有密切关系。如果遇到类似情形一律排除,不利于打击犯罪。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才规定,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证据应当排除,而不是程序非法的言词证据一律排除。笔者认为,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合理怀疑的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能够排除刑讯逼供可能的非法言词证据可以作为证据采信。具体到本案,杨某带侦查人员到现场指认时,有录像客观记录,当其进入现场时,也有围观群众观看,排除了侦查人员在指认前和指认过程中的刑讯逼供可能,且在指认现场的过程中,杨某边回忆边对其作案经过进行了详细叙述,整个指认过程规范合法,从程序角度而言,指认的程序是合法的。因此,其指认现场的笔录、录像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三、利用侦查人员出庭完善证据体系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基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意见》第104条之规定,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才能作为定案根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依法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的证据,依照一定规则进行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综合判断,是证据审查判断活动的重要环节。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可以使证据体系得以加强,增进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
(一)侦查人员出庭有助于充实证据体系
作为公诉方而言,必须以庭审为中心,使全案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当证据体系中的某一证据受到法官置疑时,公诉方应着力于以其他方式加以充实与证明。根据“2013刑诉法”第56、57条之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的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这一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被动的证明义务。司法实践中,当被告人提出刑讯逼供的非法取证问题时,法官并非全部决定进行法庭调查,基于即使调查也无法查明等理由,法官可能不进行调查。笔者认为,当案件可能面临撤回起诉、无罪判决等风险时,检察官有义务变被动为主动,主动要求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举证,使法官排除合理怀疑,形成正确的判断与认识。
(二)杨某故意杀人案的侦查人员出庭收到良好庭审效果
杨某故意杀人一案,由于作案工具未找到,被告人在先后两次庭审中提出刑讯逼供的辩解,法官认为,依据现有证据无法得出张某系杨某杀害的唯一性结论,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面对这一早有预案的局面,检察官提请人民法院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主要说明的内容包括:案件的侦破经过、杨某在公安机关是否受到肉体上的暴力折磨。
针对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的不同职责,检察官将侦查人员出庭的先后顺序排列为看管、攻心、讯问人员,看管人员共三组六人,4月6日凌晨看管杨某的一组侦查人员被安排在第五、第六名出庭,他们证实,当日凌晨,杨某无法入睡,杨与他们闲聊的过程中,讲述了自己打工时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家庭情况等,侦查人员继续深入地触动其内心,“为何要干那样的傻事?”杨某说是一时冲动。负责看管的侦查人员一见杨的情绪有松动,立即向刑警大队长汇报,大队长随即安排攻心组成员与杨交流,当听到杨供述了作案起因和经过,且其供述与现场勘查情况相印证时,大队长即安排讯问人员正式进行讯问。第一名讯问组成员证实,杨某在公安机关期间,曾要求侦查人员用电棍击打,这一情节得到杨某的证实,其辩解,让侦查人员击打是为了留下刑讯逼供的证据,讯问人员继续证明,杨作了有罪供述后,在现场指认时边回忆作案经过边进行指认,并对其回忆和指认的情况进行详细讲述,此时,杨某的心理防线趋于崩溃,以头痛难忍为由向法官提出休庭请求。在五分钟的休庭即将结束时,杨提出延期审理申请,称其需要回去看守所理一理思路,目睹杨某激烈的情绪变化,法官和检察官并未同意,庭审照常进行。虽然杨某起初还佯装头痛,但随着庭审中其他三名侦查人员的出庭,杨逐渐也进入质证状态。当第十名侦查人员退庭后,杨提出与律师单独会谈,审判长未予准许,其又提出与律师笔谈,仍未得到允许。
侦查人员的出庭,既还原了获取被告人有罪供述的过程,也使审判人员洞悉了杨某面对侦查人员说明情况时的一系列情绪表现。笔者认为,其行为表现也是一种证明形式,与我国古代的通过“五听”断狱的制度有可比性。侦查人员退庭后,虽然杨某仍辩称其被冤枉,但在场人员已确信其犯罪事实。最终,一审法院采信了被告人的部分有罪供述,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四、小结
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较为常见,被告人提出刑讯逼供辩解的也不乏其例,最终是否认定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法律规定加以判定。笔者认为,对于非法获取的有罪供述不应一律排除,虽然违反程序法获取的有罪供述系非法证据,但应当分别对待,对于无法排除刑讯逼供合理怀疑的非法言词证据不应采信,对于排除刑讯逼供可能的非法言词证据可以采信;在应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方面,检察官在必要时要变被动为主动,要求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使法官对案件的侦破经过、证据体系等有一个更加明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