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到100岁
2014-04-29樊尚·奥利维耶/柳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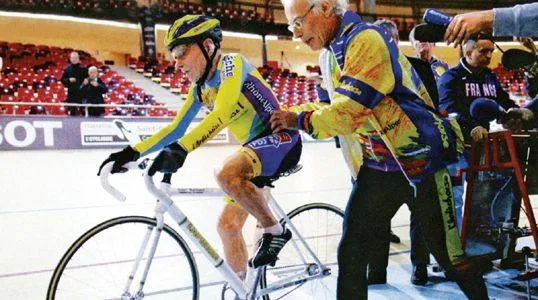

勒妮·莫里和乔治·特里舍是法国最年长的一对“新婚”夫妇,数月前,两位老人在法国尼斯登记结婚。您问他们的年龄?新郎102岁,新娘93岁。与他们相比,他们身边的伴郎和伴娘(“仅仅”只有80岁和88岁)看起来就有点孩子气了。乔治是一名退休多年的眼镜厂工人,勒妮是一位退休教师,他们俩是在一所宗教学校里认识的。当时退休的勒妮在这所学校里代课,而乔治是她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乔治在课上大胆地向老师勒妮示爱,而勒妮也欣然接受了。下课后乔治便开车带勒妮去了一家餐厅,开香槟庆祝他们即将开始的美好爱情,那天的乔治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勒妮也是一脸幸福——追求幸福的确是一件没有年龄限制的事情。
人口老龄化是许多国家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可如今“老”并不代表“弱”,老人也能活得很健康,活得很年轻。法国是欧洲百岁老人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1950年有200位百岁老人,到2010年时已经有了1.5万名百岁老人,预计到2030年时,这个数字还会翻一番。如今,法国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而人们到85岁时还能有一副健康的身体、生活完全能自理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自18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坚持“各个物种的平均寿命在它们出生前就已经由基因决定好了”这一观点。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人类的平均寿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虽然还没有从科学的角度找到其根本原因,但至少证明了平均寿命并不仅仅是由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在最近的这几个世纪里,人类根本没发生过基因突变。
“年长者”的定义
人类越活越久这一不争的事实也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带来了不少烦恼:没错,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了,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活质量也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如今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如何保证我们在变老的同时还能拥有一副健康的体魄?有一件事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当今世界对老人们并不重视。对“年长者”这个词的定义就将当今社会一种矛盾的心态反映了出来——与拥有年轻心态的年长者相比,社会更偏爱的是真正的年轻人。为什么说“年长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在不同领域,人们对“年长者”的定义都不尽相同:在体育界,23岁到39岁的人就可以被称为“年长者”;一般的工作则将45岁以后的人称为“年长者”;法国《拉鲁斯百科全书》将“年轻”与“年长”之间的界限定在了50岁;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认为员工在62岁退休之后才是“年长者”;而一些人口统计资料将年长的界限定在75岁。
“我们认为年龄问题首先是社会与文化领域的问题,其次才是科学与生物领域的问题。”巴黎高等管理学院社会学教授塞尔日·介朗强调说。很多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那些年龄特别大的老人,给这些老人贴上“丧失劳动能力”、“孤苦伶仃”等标签,甚至认为他们是社会的“拖油瓶”。2013年,法国Viavoice协会调查采访了一些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调查结果与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完全相反。8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生活得挺幸福的(其中37%的受访者甚至表示自己生活得特别幸福);62%的受访者并不在意自己变老这个事实(其中47%的受访者则完全不在意);而57%的受访者认为这个年纪正好是他们“重塑人生”的时候。至于说生理上的变化,对这些老人完全无法构成困扰,也不会影响他们前进的脚步,2/3年龄在65岁到69岁的法国人都觉得自己在这个年纪可以做得更多。年龄大于80岁的法国老人中,有86%的人认为自己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所以说,这些所谓的“老年人”的压力更多地来自于外界对老人陈旧的看法,而不是年龄的增长。按照塞尔日·介朗教授的观点,从此以后,我们将不再有越活越老的说法,我们都会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年轻,这个听起来很矛盾的说法也许即将变成现实。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基因与生物部主任雨果·阿吉拉纽肯定地表示:“一粒指甲盖大小的药丸或者胶囊可能在未来帮助人们健康地活到95岁,这并不是天方夜谭。从理论角度来看,人类健康地活到120岁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不止是人类,自然界还有其他的生物也在挑战着科学法则。鼹鼠是一种丑陋、矮胖的不起眼的小动物,但它们居然能活30年。30年的寿命在鼠类中是个什么概念呢?鼹鼠在鼠类动物中活30年就相当于人类在自然界活600岁!可以说,这种哺乳动物真正地掌握了长寿的诀窍。只要它们保持一个活跃的状态,它们的生命就能一直延续下去。更奇妙的是,鼹鼠能免疫各种类型的癌症,并能源源不断地分泌透明质酸——这种透明质酸和人类用于除皱的化妆品里的酸不一样,鼹鼠分泌出的透明质酸的质量、纯度和分子量都要比一般的透明质酸高很多。
总而言之,“未来人类虽然还是会老死,但他们却能一直保持年轻的状态。”巴黎乔治·蓬皮杜医院的营养学、心脏病学专家弗雷德里克·萨尔德曼博士兴奋地说。弗雷德里克·萨尔德曼博士的书《最好的药,就是你自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销量也一路飙升。这位长寿方面的专家肯定地说:“如今,一场医学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每一位出生在21世纪的人都有幸成为这场革命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那么对于如今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说,他们是不是因为出生得太早而不幸地错过了这场革命呢?“不是的,对于他们来说也一样。与基因相比,生活方式,或者说适应能力,才是真正影响到我们寿命长短的决定性因素。基于这个观点,我将每个人的身体都比作一架钢琴,当我们按响不同的白键与黑键时,就相当于我们启动或关闭了某些基因,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篇章,这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决定!”
弗雷德里克·萨尔德曼博士还拿出了几组数据来支持他“长寿的秘诀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个观点:摄入的卡路里量减少30%,就意味着能延长20%的寿命;每天锻炼30分钟,就能避免40%的心血管疾病;小老鼠的体温降低0.5℃,它们就能增延15%的寿命。弗雷德里克·萨尔德曼博士建议人们每天早上起来洗一个凉水澡,这样做能加快体内内啡肽的分泌,还能促进免疫系统和静脉血液的循环。这些建议都很通俗易懂,“作为一名医生,我更希望我的病人通过运动的方式来降低胆固醇或者血压,而不是一味地靠吃药来解决这些问题。”弗雷德里克·萨尔德曼说。
在科学家们研究哪些好的生活习惯能延长人类寿命时,一种名为“端粒”的物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端粒是存在于真核细胞线状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DNA-蛋白质复合体,作用是保证染色体基因组的稳定性,避免细胞分裂时发生错误的“复制”。DNA分子每次分裂复制,端粒就缩短一点,一旦端粒消耗殆尽,染色体则易于突变而导致动脉硬化和某些癌症,所以端粒与细胞老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端粒就像是我们的“生命时钟”。
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都认为生命的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更是不可逆的。人们的理论寿命在一出生时就已经由基因确定,无法改变。直到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出现,这位澳大利亚、美国双国籍生物学家和她的团队颠覆了人们对寿命的看法:端粒是由端粒酶形成的,如果端粒酶的活动显著,端粒的长度就能得以保持,这样细胞的衰老也将延后,而外界条件的改变可以控制端粒酶的分泌。这项发现对生物学界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也让伊丽莎白·布莱克本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长寿”带来的商机
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长寿”生意的交易额已达到了10亿欧元以上。那些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商机。去年9月,谷歌宣布成立Calico公司,专注于研究因衰老而带来的各种问题。其他一些大型企业也相继将目光转向了这个庞大且高利润的市场。法国生物技术公司Cellectis将客户的干细胞保存在温度十分低的环境内,他们相信未来的某一天,可以用这些干细胞帮助客户重造器官。想把自己的干细胞保存在这种超低温“冰箱”内是要付出代价的,根据保存时间的不同,客户需向Cellectis公司缴纳5到6万欧元的保管费。加拿大亿万富翁罗伯特·米勒也建议他会所的会员们在死后对大脑和身体进行低温保存(保存在零下190℃的低温环境内),这样未来某一天科技足够发达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复活”。富人们想尽办法长生不老,甚至起死回生,普通人就只能了解一下自己理论上还有多少寿命了。他们将自己的唾液样本邮寄给一些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通过测量端粒的长度可以大概预测出他们的理论寿命。全世界现在大概有十多家私营企业提供这样的服务,当然都是有偿服务,费用在800到1000欧元之间。
这些寻求长寿的做法激怒了法国科学家雨果·阿吉拉纽,他愤怒地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每个物种最重要的事就是一代代繁衍下去。一味地追求长寿是一种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法,对自然界没有任何益处。”其实,延长人类的寿命从科学理论阶段到大规模实践阶段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如今要提防的是那些想要制造事端却又无能力控制的人,”伊丽莎白·布莱克本提醒道,“即使我们现在知道了端粒如何保护染色体的末端以及端粒酶如何合成端粒,但我们并没有掌握端粒保护染色体末端的原因,还有很多事没有搞清楚,如果应用不当,可能就会踏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另一方面,大部分科学家对测量端粒长度这种做法仍持怀疑的态度。“单点测量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测量方法是瞬时性的,就像照片一样,定格的永远只是一个瞬间,而我们的生命是一部电影,端粒的长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变化。”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主任玛丽·皮埃尔·穆瓦桑说。穆瓦桑将在法国启动一项实验:今年年底之前,她将招集200名60岁到70岁之间的病人,为他们提供一年的营养辅药(维生素A和欧米伽3),观察他们服药前与服药一年后体内端粒的长度是否会发生变化。如果外力真的能改变端粒的长度,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身体的工程师,用弗雷德里克·萨尔德曼博士的话说就是:“我们自己就能分泌抗老化的药物。”
“生物弹性”确实存在
美国几名生物研究员曾找了35名志愿者,测量了他们端粒的长度,然后要求他们从此按照健康的生活习惯生活5年(饮食方面要多吃蔬菜和水果,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合理减压等等)。5年后,研究员再次对他们端粒的长度进行了测量,并与另一组未改变生活习惯的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那些改变了生活习惯的人端粒长度与5年前相比增长了6%,而那些未改变生活习惯的人的端粒长度则缩短了3%。更有意思的是,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她的团队通过观察对比那些定期从事宗教活动的人与不从事宗教活动的人的端粒长度变化,发现如果规律性地做一些事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可以“拉长”端粒。诚然,2013年公布的这项研究成果只是端粒研究很小的一个方面,但它却证明了“生物弹性”是的的确确存在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弥补以往生活中的遗憾。
虽然科技进步能为我们带来积极影响,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很多事情出发点是好的,可后来往往会偏离我们的本意。如何阻止这种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最终沦为富人的特权?如何避免健康保险公司滥用端粒的概念拒绝合理的赔偿?如果他们硬要说那些不幸意外身亡的投保人是因为端粒天生就短而死亡,从而拒绝赔偿,这种情况还真不好处理。更有甚者,保险公司还可能利用这一科学成果对投保人进行敲诈:“如果您现在不改变您的生活方式,如果您的端粒未能增长,那么以后您将要支付更多的保金!”
不过,我们所说的公平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表面上的平均主义(每个人拥有相同的机会和相同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观念,在收入、文化背景以及家庭组成都不尽相同的大背景下,让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负全责本来就是件不公平的事。在法国,政府官员和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平均健康寿命相差了整整7年,但这并不是劳动者的错。除了给人们一些中肯的建议以外,我们的社会也需要对所有人负责。科技应该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无论结果好与坏,我们都应该共进退。
[译自法国《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