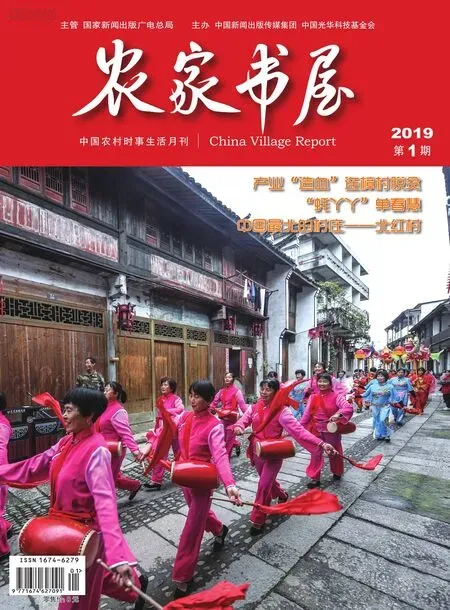密林深处鄂温克
2014-04-29马慧娟
马慧娟

“鄂温克”,本意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和桦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也称“猎民”)在森林中游牧了上千年,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辗转多处,历经多次迁徙,300年多年前进入我国境内,在广阔的大兴安岭深处驯鹿、打猎。他们尊重自然,信仰萨满,男人捕猎,女人采集、捕鱼、缝制桦树皮,一代又一代,延续着与森林相依为命的生活方式。
解放后,他们经历了四次迁移,从山上搬到了山下,逐渐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但是,他们与森林、与驯鹿的缘分没有尽,山上依然有他们饲养驯鹿的猎民点,依然有他们世代坚守的森林,与之相比,那些山下固定的“家”,更像一个交换和储存物品的地方,他们并非常年居住,也不习惯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们担心这些房子会塌下来,极少有人敢进去住。
2003年9月至2004年10月,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谢元媛,为完成她的博士论文,深入到内蒙、黑龙江交界的大兴安岭林区腹地进行田野调查,用时一年,记录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这支部落的生活现状。本期,我们就同谢元媛一起,走进这个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狩猎
在禁止打猎之前,狩猎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存的主要方式,这也是最让他们激动的事情。“有一次,我们五个人一起出去采都柿和牙各大(山上的野果子),三个男猎民都背着枪,我和王英拎着茶缸,背着铁皮水桶。走在半路上,我们遇到了大棒鸡,可惜被我和王英全神贯注的谈话吓跑了。我跟着他们几个在林子里和灌木丛中穿梭,他们脚步轻盈,行走敏捷,而我明显艰难费力,总需要他们的等待和帮助。采都柿和牙各大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两个大马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就忘了自己的疼痛。林子里的路深浅不定,我只能像熊一样迈步,而他们四个却健步如飞……我们采回来的野果子,老太太做成了都柿酱和牙各大酱,又好看又好吃。”谢元媛说。
过去,马鹿、驼鹿、猂、狍子、野猪、熊、獐、猞猁、水獭、紫貂、松鼠等,都是猎民们的猎物,猎民吸引猎物的方式有很多。鹿哨是他们一种非常古老的狩猎工具,用鹿哨模仿公鹿的叫声,完全可以乱真。
鹿哨在鄂温克语中叫“奥莱翁”,成熟的猎人都会制作自己的“奥莱翁”。找两块自然弯曲的松树根,先把树根削好,按自然弯曲的弧度从中间劈开,内部掏空,再用胶把两半粘起来,阴干,再进行装饰。光是制作这个“奥莱翁”,就要花两三天的时间。
虽说是“哨”,但鹿哨不是吹而是吸的,利用哨身弯曲的弧度发出声音,这个需要技巧,不是一般人掌握的了的。如果练习不到位,发出的声音是引不来鹿的。鹿哨分大小两头,小头,声音很悠长,“呜——呜——”的,主要用来引诱公马鹿,时间多在凌晨。大头用来模仿猂的声音,不是吸,而是轻轻叫,利用的是筒子的回音。
除此之外,还有把桦树皮剪开一个口子含在嘴里,模仿小狍子的声音,哇——哇——,引来大狍子。还有利用口技的,比如把手放在嘴边,模仿飞龙叫声。老猎民拉吉米自己还做过一种工具,把木头敲得咔哒咔哒响,模仿松鸡交配时的声音。
在猎民家庭中,狗就是家中的一员,猎民和猎犬同吃一碗饭,同用一双筷子,同睡一张床。猎犬会自觉地恪守自己的职责,在没有得到主人的允许前,不会有半点儿违规行为。吃饭前,它会静静地守候在主人的“撮罗子”(猎民住的地方)外,等待主人的召唤,晚上也会等主人熟睡之后,才钻到主人铺下休息,但时刻保持警觉。如果有什么动静,它不会先惊动主人,而是迅捷地从床下钻出,绕过地上的盆盆罐罐,走到外面判断声响来源,再决定是否叫醒主人。打到猎物后,猎人通常都会赏给猎犬食物,而猎犬决不会不经允许就偷吃主人打来的猎物。一些身经百战的猎犬,甚至可以独自出猎,为主人寻找野味。
在打猎方面,猎民有世代遵守的的“森林法则”:山上的树不能随意砍伐,只有搭盖“撮罗子”时用活树,烧柴是已经枯了的站杆;打猎也一样,在野生动物繁育的季节,为了保护怀孕的母兽和正在成长的仔兽,猎人会划定专门的猎场进行狩猎,甚至封枪养山,繁殖期和哺乳期的动物不能打,尽量不打幼兽,平时不打母鹿,除非是打鹿胎的季节。
猎民的生活中,没有明确的四季划分,对季节的划分还是沿用了对狩猎活动“时候”的把握,“到了打鹿胎的时候了”、“到了打狍子的时候了”、“到了打棒鸡的时候了”,他们至今还会这样说。小孩子大概10岁的时候,就开始漫山遍野跟着大人去打猎,能找到灰鼠,特别高兴,他们把冬天叫做“打灰鼠的季节”。
驯鹿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活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驯鹿放养。驯鹿是《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坐骑,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为“神兽”,《春秋》中谓之“麟”,即麒麟中的“麟”。驯鹿造型十分古怪,马头、鹿角、驴身、牛蹄,俗名“四不象”。生活在我国境内大兴安岭北麓森林中的数百头驯鹿,是世界上分布的地理位置最靠南的驯鹿种群,也是是全亚洲唯一的驯鹿产地,而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出现在大兴安岭北坡,就是跟驯鹿有关。驯鹿是一种生活在环北极圈苔原地带的寒带动物,喜欢吃地衣(石蕊)、蘑菇、苔藓,如果气温太高,其繁殖会出现问题,对于敖鲁古雅鄂温克人来讲,它们身材比较高大,驯化之后的驯鹿,又容易使唤,成为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在森林中迁徙的惟一的交通工具。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饲养驯鹿的方式是以自然散放为主,完全遵从驯鹿的特有习性,任其自由自在地在林中觅食,只在需要的时候不定期地将鹿群从林中撵回。
每年春季开始接羔,5、6月份,驯鹿就产羔了,这个季节,女人们都非常忙碌,虽然很忙很累,但是很开心。她们每天都要出去找鹿,看看这个鹿下了什么样的羔,是花的还是黑的,牵着大鹿走,小鹿羔子就在后面跟着,非常开心。刚生下的小鹿羔子,人不能碰它抓它,要不然它妈妈就觉得它被弄脏了。有别的味道了,鹿妈妈会不要自己的孩子。
找鹿的活儿是男女都能做。找鹿要看鹿往什么方向走了,沿着蹄印去找,一路上什么都能看到,棒鸡、熊、兔子,秋天还能看见灰鼠子。猎民带着列巴背着枪,在路上能打到啥就吃啥。打到大猎物时,就要找着驯鹿给驮回来。
驯鹿的主人在鹿崽儿降生之后,就将其拴在营地的木栅栏里,给它戴上笼头,给母鹿佩戴铃铛,让鹿崽儿熟悉母亲的声音并记住铃声,帮它有节制地吮吸母乳,同时熟悉主人的气味。因为驯鹿的习惯是晚上出去觅食,白天回来睡觉,为了确保鹿妈妈回来,所以每天晚上,猎民都要把她们的孩子关在鹿圈里,这样,晚上觅食结束她们就会回来,卧在鹿圈前面,等着跟孩子见面。
夏天的大兴安岭虾虻、蚊虫特别多,猎民每天都得用几根朽木,头对头拢在一起,采来一种潮湿的草,点着,只冒烟,不起火,给驯鹿“熏烟儿”(熏蚊虫,鄂温克话叫‘萨弥),白天驯鹿都围拢在“萨弥”周围歇息,晚上气温低了、虫子少了,才出去找苔藓吃。
兴安岭的夏季很短,到8月末9月初,天气就凉到冷的地步了,这时驯鹿开始交配,蘑菇也长成了,猎民和驯鹿都采食野生的蘑菇。驯鹿是非常聪明的动物,自己能够辨识哪些是有毒的蘑菇而避开不吃,猎民们吃蘑菇也都是从驯鹿那里学来的经验。天凉了,驯鹿不再用“熏烟儿”,白天可以跑远了。林子里的蘑菇长得分散,驯鹿为了找蘑菇吃,会到处乱跑。这时候,猎民最大的工作就是跋山涉水地寻找驯鹿。猎民说:“现在外面来的人在林子里下的套太多了,驯鹿不小心就会被套住,跑不了就会饿死,也会因为受伤而死。所以必须及时出去寻找。”
漫长的寒冬里,最低气温零下四五十度,山上的猎民回到了山下集中供暖的新居,他们在冬季最寒冷的两三个月里(12月中旬至3月中旬)基本不在猎民点居住。因为寒冷季节里,驯鹿不太需要人的照顾,它们奔散到各处,扒雪找苔藓吃。猎民只需隔上半个月左右上山看看驯鹿的踪迹,知晓驯鹿的大概位置,从而方便来年春天雪化以后找寻;同时,也看看驯鹿喜食的苔藓是否被雪压得太实,有没有“白灾”。
来年4月份,还没等到冰雪完全融化,猎民们就要上山常住,忙碌的时节就要开始了。猎民们选择水源好、苔藓丰富、背风向阳、交通方便的地方搭建大鹿圈,找回怀了小仔的母鹿,准备接羔,新的一个轮回开始了。
驯鹿长年游走于丛林之中,食物中缺少矿物质,而摄取食盐是它们获取身体所需矿物质的重要方式。而每当猎民要召唤驯鹿时,也总是手持盐盒或盐袋,轻轻敲打发出声响,丛林深处的驯鹿就会应声而来。每当主人给鹿群喂盐时,温顺的驯鹿就撅着嘴巴、伸着舌头,发出浑厚的叫声,把主人围在中间,争相在她的身上吻来吻去。
猎民与驯鹿的关系,远不止这些,他们会为自己的每一头驯鹿命名,命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通常会根据驯鹿的体态颜色、年龄特征、性格特点及特殊经历进行。鄂温克妇女能轻松地辨认出鹿群中的每一头驯鹿。
猎民们还骑着驯鹿去打灰鼠,撵驯鹿的时候骑着它,木棍朝左边指,它就朝左边拐,木棍朝右边指,它就往右边拐。驯鹿有病了,咳嗽了,猎民就会熬一锅草药,岁数大有经验的猎人都知道什么病用什么药,然后挨个喂给驯鹿们喝,不咳嗽的也喝,非常见效。驯鹿有时也能自己在林子里找草药吃,除了苔藓和蘑菇,它们也吃桦树叶、嫩草、节骨草。
驯鹿死了,老猎民会为它们举行风葬,就是病死的也都要风葬,做个架子把它搁到上面去,为的是不让它烂了或被别的野兽吃了。
“我们就是这样打猎、放驯鹿。过了一年又一年。过去,打猎、放驯鹿的地方挺大的,方圆上千里……一直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境内都去过,不管多远的路,我们都牵着驯鹿走。那时,到处都有猂、鹿、灰鼠子,现在不一样了,到处都有人,到处都有偷猎的人。这才过去几年呀…… ”被外界称为“最后的酋长”的玛丽亚·索曾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