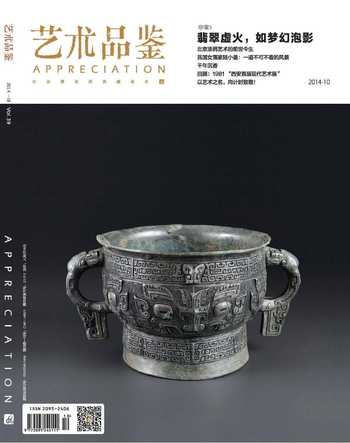宗教经典与法物包装
2014-04-29朗韵
朗韵



佛教是清代宫廷生活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王朝与佛教,尤其是与藏传佛教的渊源是久远而厚的,其历朝帝王、后妃中,崇奉佛教者甚众。无论于他们是出于纯然的宗教信仰,抑或“安抚蒙藏”的统治策略,乃至杂糅种种而成的动机,遍布禁宫内外的皇家御用佛堂的兴修;不计其数的经典、佛像、祭法器等宗教品的制作及其存留至今,则是我们在300年后仍可凭以想见当时信仰之盛况的直接依据。
清代宫廷佛教物品的包装,在具体形式上有着各种区别变化,却均以华美精工、用料考究为共性特征。这虽是一定意义上宫廷内各类物品包装极尽奢华富丽的皇家气派的普遍反映,但其对物品的装饰功用的着意强化,包装形式语汇,甚或包装材质本身所表达的深层宗教蕴意,则是普通物品包装所无法兼具的。包装的本旨原是为容存与保护被包装物的,从这一角度讲,其实用意义是重于装饰作用的,而作为佛教物品的包装,虽亦有如“佛窝”等类出于方便实用的考虑而制作的特有包装样式,而就总体而言,宗教品报装的意义,往往是以偏重彰显被包装物的宗教特性为要务的,佛教物品依种类大致可分为佛教圣物,如佛陀、活佛或高僧舍利、神佛造像、经律论典及祭器、法物等。其内容互异,本质特征却相一致,即作为宗教品的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恰是宗教品对于其信仰者的究竟意义之所在,它常常借助于宗教品包装的装饰作用得以体现。清廷主要尊崇的藏传佛教是注重形象图示的佛教教派,它尤其强调对佛教圣物、经像、法器等的崇奉供养,在达到佛教的终极目的——成佛的修为实践中的不可或缺性,这应是宗教包装皆极尽华丽精美之能的总体特征的理论根源所在。此一特征则还可与清廷崇佛之盛况相为因果,有清一代以乾隆朝崇佛为最,宗教品包装之精华也正是集中于这一时期。
清宫佛教物品的包装形式,有着地域上的横向借鉴与历史上的纵向继承两大渊源。藏传佛教是最终形成于西藏地区的,附属于它的宗教艺术,在形式上也有着明显的藏民族特征。这种地域性的审美趋向于藏传佛教一起为清统治者所接纳,并在相关的包装形式中予以借鉴和应用。如铃杵的包装、舍利盒的形制等即是。对于佛教包装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固有形式,则基本予以承袭,或稍加改进,如经籍的装帧形式即是分别沿袭汉、梵两种旧制、而对梵式略加变革的。对借鉴与继承二者的融合集成,或略加变通,乃成为清代宫廷宗教包装的又一特色。
宗教品作为一类有着特殊内涵与用途的物品,其随信仰之盛而大量造作的历史实况,必然地伴生了其包装的内容形式、工艺技法等的独特与高超。
锦缎包“梵夹式”装《白伞盖仪轨经》
清乾隆/长42厘米/宽29厘米/高1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白伞盖仪轨经》包装华丽考究。经文以满、汉、藏三体文字对照,泥金抄录于散页磁青纸的两面,共计二百六十余页。全部经页依序叠放整齐,上下各用木质护经板一块将散页约合为册,经板外均髹朱漆,戗金满饰吉祥图案。整体外包锦缎,束以丝绦。此种装帧形式源于对古印度佛经装帧形式的仿效而略作变化,称作“梵夹装”。传统梵夹装是用夹板将经页夹好后,连板带经于正中或两端钻一或两个透孔,穿绳其内,捆绕成册,此件乾隆四十五年(1780)所制的梵夹装佛经则护板及经页上都无钻孔,而代之以对护经板的精雕细绘,另以锦缎包裹,外更缠以五色绦带,这是清宫佛经,尤其是宫中御制藏传密教类经典在装帧样式上的常用形制。它着重于对佛教经典所固有的装帧形式的宗教性内涵及其堂皇的装饰性效果予以突出强化。此外还在绦带一端安鎏金铜环扣,用以束紧经册,方便实用。此件佛经包装为清宫中模仿古印度贝叶经梵夹式包装的典型实物,原藏于皇帝日常所居的养心殿内,足见其珍贵。
铜鎏金嵌玻璃彩绘《文殊赞佛法身礼经》盖盒
清乾隆/长23.5厘米/宽12厘米/高19.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经装帧为变体梵夹式。经盒内装《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礼经》,经文用满、蒙、藏、汉四体文字对照墨书于长方形金粉硬笺上,经页重重叠放,周边绘饰蓝查体梵文文殊咒,既有装饰作用,又可使页次有序,不致错乱缺失。其上下以戗金纹饰紫檀护经板相夹,上护板外面居中亦刻文殊咒以点明经题,内侧绘释迦牟尼佛及文殊菩萨像,中书四体经名;下护板内则画广目、增长、持国、多闻四天王像,以为护法神祗。上下护经板之神像上各覆3层绣八宝图案的绸质经帘。经册整体放置于一铜镀金须弥托座上,座顶四隅起与经册等高的折角护栏以固定经册,外罩鎏金铜框玻璃盖盒,玻璃内衬纸上除彩绘八宝、摩尼等密宗常用装饰图案外,还绘有汉地象征福祚的蝙蝠纹样,体现了汉藏文化在宫廷包装形式中的融合。经盒做工精到,装潢考究,通体鎏金并镶嵌青金石、松石及珊瑚等珍材,组成装饰纹样,极显精美华贵。以此类风格包装的佛经多非用于日常的诵读,而是专为陈设供养而制的,因此在包装样式、工艺及用材等方面淡化其实用性而着意突出富丽堂皇和庄重神圣的装潢效果,以显示皇家的豪华气派及其对佛教圣典的珍视与尊崇。
嵌石檀香木《无量寿佛经》莲座盖盒
清乾隆/长21.7厘米/宽9.8厘米/高1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经盒内装磁青纸泥金写本贝叶式《佛说大乘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略称《无量寿佛经》),是清宫佛堂中供养所用佛经。经文用藏、满、蒙、汉四体文字书写,每种字体各录一份,总合四体经文,上下各以檀香木护经板夹装而成全册。护板表面以青金石、松石、珊瑚等嵌为夔凤图案,内侧挖槽,底面彩绘持国、广目、多闻、增长四天王像,并题经名,上遮四层画有八宝纹饰的绢绸经帘,它既是护法神像的垂幕严饰,而其厚度刚好与槽口齐平,因此又具有保护泥金经文不为木板划损的实际功效。经文存置于一做工精致的木盒内,盒底部为须弥式,下承托泥,上为束腰浮雕莲座,莲座起檐,盒盖正好固定其中。盖上有松石等镶嵌而成的八宝图案及梵文种子字。经盒以檀香木料精雕细刻而成。檀香木为珍稀木材,选用它为装藏佛经的材料,具有多重意义:一则用料的名贵既表达了供奉者奉佛的恭敬与虔诚,也体现了御府用品的非凡与奢华;二则檀香木的馥郁香气,正契合佛教中所谓“熏香供养”的宗教要求;再有檀香的天然气味可以驱虫避秽,则使这个经盒本身具有保护经籍免生囊虫霉蚀的实际功用。
织锦插套及包袱装《心经》
清嘉庆/长30厘米/宽15厘米/高3.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册为御笔墨书《心经》一卷。五彩织锦为书衣,外护以硬纸函套,其表面亦裱装同样的织金彩锦,内外一致。经册为传统经折式装帧,这种装帧形式是隋唐佛教盛行时期,佛教徒为了唪诵经文的方便,而将佛经由以往的卷轴装改革形成的。方法是将整卷经文首末,用较厚硬的织物或色纸为书衣,折叠成册。至宋以后,大凡佛、道经典,多用折叠形式,遂称“经折装”。此册《心经》即沿其制。因其为御笔抄录,所以于函套之外更包以云龙纹锦缎包袱,束以绦带,重重包装,即为格外保护,又以示敬重。绦带上缝缀白缎子一条,上书“乾隆六十三年(1798)二月朔日”字样,这是因为清宫中如御题书册等类物品,多有相对统一的包袱包裹,外表注明可方便查找。
清嘉庆/长30厘米/宽15厘米/高3.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册为御笔墨书《心经》一卷。五彩织锦为书衣,外护以硬纸函套,其表面亦裱装同样的织金彩锦,内外一致。经册为传统经折式装帧,这种装帧形式是隋唐佛教盛行时期,佛教徒为了唪诵经文的方便,而将佛经由以往的卷轴装改革形成的。方法是将整卷经文首末,用较厚硬的织物或色纸为书衣,折叠成册。至宋以后,大凡佛、道经典,多用折叠形式,遂称“经折装”。此册《心经》即沿其制。因其为御笔抄录,所以于函套之外更包以云龙纹锦缎包袱,束以绦带,重重包装,即为格外保护,又以示敬重。绦带上缝缀白缎子一条,上书“乾隆六十三年(1798)二月朔日”字样,这是因为清宫中如御题书册等类物品,多有相对统一的包袱包裹,外表注明可方便查找。
清/长22.9厘米/宽65厘米/高6.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经为抄本藏文《长寿经》。经文以泥金精写于磁青纸两面,共计一百二十余页,仿贝叶经样式有上下护板夹装成册。护经板为木制,裱褙蓝色外皮,与经纸颜色统一。上板正面书梵文经咒,内侧呈凹形,绘画上乐金刚及金刚亥母形象;下板凹槽内彩绘贝衮占苏,四臂文殊菩萨及墓主依怙三尊为护法。画像形象鲜明,色彩艳丽,其上均覆盖三重分别绣有八宝、莲花和龙纹图案的经帘。全经存放于一青金石经盒内。经盒为铜鎏金框架,青金石为壁板,上设抽拉式盒盖。经文置于其中,既可随时取出念诵,也适于固定一处,安奉供养。从经盒的特殊选材及其制作、鎏金工艺等看,此经盒应是西藏所制,后被进献朝廷的。
织锦万寿云头《佛说十吉祥经》函套
清乾隆/长13.5厘米/宽10.5厘米/高4.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经函硬板折合式,表面粘裱万寿纹样织锦,内里黄云锦缎为衬,选料上乘。其右片与前后片函板顶端各剔挖成硬角如意云头形状,三片相互嵌合,融固定经函的实用性与美化装饰作用为一体,构思巧妙。经函内装清乾隆朝大学士于敏中所书《佛说十吉祥经》经文玉版及其墨拓,楠木夹板为书扉及封底,其上减地剔雕云水、蝙蝠等图案,正中镌刻经名。经本为方册经折式,其内金字玉版与墨拓各为一页之版心,四周以黄绫包衬。这种装帧方式,版本学上称作“袍套装”或“惜古衬”,本是指将古旧善本的书页作版心,四周重加托裱的古籍修装方法,俗又称为“金镶玉”式,这当然是比喻的叫法,而在帝王之家却有此真正将玉版镶为经册折页的实举。而此经的包装形式和材料中所频繁出现的“万寿”、“云头(如意)”、“蝙蝠(福)”等形式语汇的寓意,又暗与本经“吉祥”的旨趣相契合,由此,清代宫廷包装之考究及其高超的艺术性可见一斑。
织锦御笔《妙法莲华经》函套
清乾隆/长42厘米/宽17厘米/高3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妙法莲华经》共7册,皆经折式装帧,总为一函。经文以金汁书写于磁青纸上。每册扉页白描精绘金彩说法图,末页有韦驮天护法像,这是汉传大乘佛教经典的惯制。此经经函为硬板折合式,函板有一定厚度,故其各面相结合及折角出的边缘均剔成斜角,前后板与右板内折部分更分别剔挖成凹凸如意云头形状,这不仅有美化装饰作用,更可使函套合起来的各部分镶嵌扣合紧密,对书籍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包装整体堂皇富丽,设计巧妙,制作精细。此经经文为乾隆三十年(1765)御笔,应是乾隆为祝贺其母崇庆皇太后圣寿而抄录的。经册与经函均以蓝底团龙纹缂“万寿”字织锦为面,内外统一,除显和谐美观,更因为它有点明与烘托“祝寿”这一特定主题的吉祥寓意。此部《法华经》一直存放于乾隆为崇庆皇太后所建寿康宫内。
鞔皮描金铃杵盒
清/宽约20厘米/高2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盒为木制,随铃、杵形状做成由两个相对独立的存放单元组成的特形包装,旁安合页及插销,以利开合。盒表面鞔软皮,可起到箍紧异形木胎,免有开裂、变形之虞;皮上绘画金彩装饰花纹,外罩明漆,有美化与防潮、防蛀等实际功用;内里红云缎为衬,不至磨损法器。铃、杵为佛教密宗诸多法器中最为常见者,含有多重宗教内涵,通常分别代表一对相对对立统一的理念,如杵表摧破、铃表成就等,故实用时往往成对使用,因而其包装盒亦做成同时容纳一对铃杵的样式,以便于保存、携带及使用。此对铃杵是达赖喇嘛进献清廷的。
银簪花经匣
清乾隆/长30厘米/宽14厘米/高1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匣为装放佛经所用,纯银制成,故名。经匣为内弯的长方形状,顶面正中置翻盖,后安合页;前设别扣,锁定盖板,使内装的册页不致散失。匣左侧有一长方形带环。经匣表面錾刻七珍、八宝等宗教器物所惯用的装饰图案,做工精湛。匣盖内贴有清宫旧签,上书:“乾隆二十年(1755)十二月二十五日,达尔党阿奏进追赶阿睦尔撒纳所获银经匣一个”,由此可知此匣本属在新疆制造分裂,对抗清廷的准葛尔部落首领所有,是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期间为清军缴获而进献朝廷的。其内弯的弧形造型和表面安设的穿挂背带的钩环,都便于骑乘时携带,反映出此经匣为蒙古游牧民族所用的特点。
红漆描金缠枝莲花双层舍利盒
清/高11厘米/直径15.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盒内存放着燃灯佛舍利和迦叶佛舍利各两颗,分作两包,以绵纸及黄云缎重重包裹,外束绸带。从原存的签条记录可知这四颗佛舍利为八世达赖喇嘛分别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四十年(1775)进贡给朝廷的,其后一直被供奉于宫中佛堂内。舍利乃佛教圣物,为各宗派所尊崇,故其安置十分讲究,以存放于瓶、棺、函、盒等器皿内,再起塔安放供养为常例。此四颗舍利以盒存放,盒木胎,内外均髹红漆,外表描金绘缠枝莲纹。盒体呈宝瓶状,初看似只有盒盖与盒体两部分,实则其上半部分又独立为一圆盖盒,构思奇巧,用以将两尊古佛的舍利分别安放。盒的造型及装饰特征都带有浓郁的西藏风格。
紫檀雕御制诗札布札雅碗盒
清乾隆/高9厘米/口径2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铁鋄金碗套,亦称普修碗套,即“藏式碗套子”。这种鋄金工艺,主要是手制,将金砸成金皮,制成金箔錾于铁铸镂花的碗套之上。碗套嵌有提梁耳,可以系带背携。在罩盖套壁和盖面上镂空有勾莲、缠枝花卉和螭龙纹。花卉精细,螭龙灵透活泼,而且铁的外表包有一层金箔并嵌有松石珠,更使盒体显得玲珑剔透,金碧辉煌。
盒内盛有根瘤碗,藏语为札布札雅碗。木碗撇口,呈墩形,有清晰自然的纹理,持于手中滑润精巧。碗底足圈内可看到阳文楷书“乾隆御用”四字。在平底的外圈上,还有用银丝嵌成的隶书诗句。据说此种器皿有防毒作用。这种精美名贵的套具是西藏上层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忠诚敬意,特意配制的。乾隆对此木碗也十分重视,在木碗上题款嵌诗,还另配上刻诗的紫檀罩盖匣,作为上等物品珍存。
鞔皮圆嘎布拉谷盒
清/高约15厘米/直径约20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盒内装噶布拉鼓,又称人头皮鼓,是一种常用于驱鬼伏魔等类密教仪式中的宗教法器,据称还具有息灾增益的功能。鼓盒木制,圆形,内膛大小与鼓相合。顶为带合页的翻盖,其前端安有搭钩两个,用以扣锁盒盖与鼓盒。盒里衬红色云纹缎,外表鞔皮描金,并髹明漆,既使鼓盒经久耐用,又利于内装法器的保存及携带。这是宫中密宗法器所常用的典型包装形式,尤以乾隆朝最为盛行,清宫档案中就屡见皇帝传旨,为西藏达赖、班禅喇嘛进献等类有着重要来历的密宗祭法器“配鞔皮画金套”的记载。这个鼓盒应是宫中造办处所做。
银间镀金玻璃门佛窝
清乾隆/高约10厘米/厚4.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佛窝,清宫旧档中又作“佛锅”,是一种方便携带的佛龛形制,内装佛像多是有着特殊宗教意义或较高历史、艺术价值的小型造像,以便携带身边,随时礼拜而用。此佛窝背板镌刻满、蒙、汉、藏四体铭文,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十八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大利益番铜旧琍玛手持金刚。”由此可知龛内所供佛像之珍贵。佛窝为银质,正面设上开式提拉门,便于竖立安放佛像,不致于携带过程中意外滑脱,乃至失损尊像。龛门正中镶玻璃,透过玻璃可见内装的持金佛像。佛窝内随造像形状做成卧囊,起到固定及保护尊像的作用;选用织金红锦为衬,以象征金刚类造像所常用的火焰背光,有着装饰与庄严的双重意义,由此亦可见宫廷宗教包装考究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