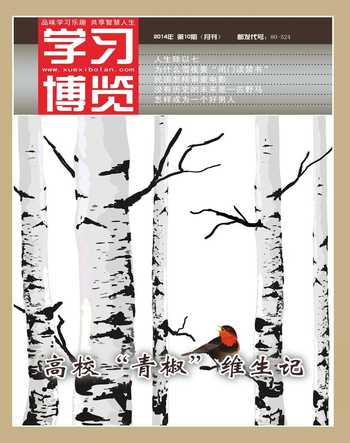挥之不去的怀乡病
2014-04-29雪堂
雪堂
如果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曾经是一种思潮,眼下它远未退烧,相反,越来越多的“回乡记”仍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俨然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社会心理的流露。
《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一书的撰稿人群体是一批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年轻人,曾经真切地在乡村出生、成长起来,来到城市求学、生活,并且有过在故乡之外的中国农村田野调查经历,这些一直在观察和思考今天“乡土中国”问题的人,再次回到那些越来越陌生的中国乡村,“家乡”在一个疾驰的变革时代变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
怀旧病人的集体乡愁
由于是讲述自己家乡的情形,无论是对传统还是对现状,撰稿人复杂的情绪中往往更多的是批评和内省。当代中国的社会公众评价有其极为特殊之处,即人们对变革并不见得有多大的真实歌颂,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的疑虑;相反,他们对那些对传统的顽强捍卫则从来不吝啬自己的掌声和带有共鸣的叹息。
书中所有撰稿人都是怀旧病人,无一例外对儿时乡村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价值给予了高调的确认,对家乡当下的问题和现状则深表遗憾,提出无休止的质疑。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私人观察和判断,择取的样本容差同撰稿人本身的样本容差同样不足以支持其观点的“回乡记”,在网络上公布后竟然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同,引起了讨论。最终整理结集成书,来到一个更广阔的接受与言论环境。不能不说这反映了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之下都郁积着某种深刻的焦虑。
天真烂漫的旁观者
费孝通先生曾说:“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但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当我们用一个时间跨度提取出某个“中国问题”并最终找到答案时,你会发现那个问题早已经过一场变化,变得更复杂、更不可逆转。当人们终于无法适应剧烈变革带来的眩晕,“回乡”不再仅仅是追寻记忆的物化存在,更像是一种文化寻根之旅,但就其实质来说,这种文化寻根的本能与诉诸“传统”存在明显的区别。
以《回乡记》的撰稿人来说,他们显然并非思想完全成熟的观察者,有的甚至还比较天真烂漫,只是想回到从前。进一步说,他们回到家乡后,更多的是成为整个乡村原住民通过礼仪人情扼守传统的旁观者,是那样一场自觉的集结在传统之下的本能运动的访问人。
然而,也正是从这批人之中,将来会诞生真正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对城乡二元世界的改造”进行全面评价的人物,因为这是他们这代人真正的需求。而现下他们的观察所得,不过是上一代人用传统麻醉自己、挣扎求生存罢了。
回不去的“熟人乡土”
在许多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和困惑中,“乡村公共品的困境”这个题目下的一组文章涉及农村社会转型的细部,尤为引人注目。传统的乡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微观说是生产耕作时的互助,站远一点说直接指向乡村的公共生活,包括交通(修路)、灌溉(农业设施投入)、医疗(乡村医生)等公共设施或公共服务的供给,都要依赖内生的组织结合道德礼法来运作。一位撰稿人回顧了故乡村庄当年引水灌溉中村民自发合作、互相提供公共服务的故事。从集体时期的公共“垄沟”,到近邻几家合资合作投入灌溉设施,直至私家购置的水泵、水管,灌溉作业从自发寻求乡村公共服务到可以独立完成的演变正是一个缩影。
今天农村的社会分化越来越大,纯农户所占比例减少,“农业生产合作几乎无从谈起。日常互动逐步减少了,社会关联也日渐式微。”在市场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与乡村衰落同时,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理性、私人观念依仗着新技术的推广,在乡村微生态环境中完全驱逐了叫做“农业生产合作”的公共品,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
一篇题为《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悖论》的文章,归纳了这种供给的悖论: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依赖于集体的“公共财政”能力;然而,当集体有了资金进行公共设施建设的时候,村民小组们又期望把这些钱收入个人腰包,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村庄的平静。
变革中的故乡与人心
《回乡记》文章的选录颇具心思,对应的题目深度显然超越原文:有日渐消散的“年味”和淡薄的乡村人际关系,原先作为大家庭感情枢纽的长者逝去后,产生了所谓“核心家庭”和“丧家犬”情结久久挥之不去;有转型时期农村治理与公共服务缺失的悖论;还有传统传宗接代观念在时代冲击下形成的新的代际关系,“城乡分住”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今天城乡关系的反映,新版的“城镇剥夺农村”正在成为现实……都令人感受到一种贺雪峰教授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浓烈气氛。
面对乡土中国的急剧变迁,每一个有“故乡”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不适应,都会生发出自己的“乡愁”。无论你现在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还是二者间的“摆渡客”,或者是进城不归但内心深处仍然渴望获得故乡血缘和传统安慰的新“城市人”,可能“谈论”这些问题都显得空泛,但记录下这些一手的观察绝对值得。这或许就是本书未来的历史价值吧。
我们现在或许可以看出,所有围绕着“回乡”所不断带来的新的痛苦,都来自于变革。人,也确实有美化以往事物的不自觉。当下面对的这种,过去西方把它叫做“现代化的阵痛”,城市和乡村都要经过这种必要的试炼。又或者,变的不是故乡,而只是人心。痛苦只是源于“家”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