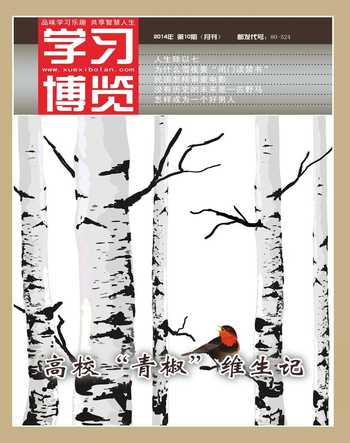沈从文:大道无言
2014-04-29史飞翔
史飞翔
1923年秋,一个土得掉渣的年轻人从前门站走下火车,望着偌大的一座城市,他说:“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这个年轻人有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叫沈岳焕,后改名沈从文。
1929年,在胡适的关照下,沈从文谋到一份差事——在中国公学做讲师。第一次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沈从文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为的是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校门时不至于显得太寒酸。登上讲台时,沈从文紧张得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为了上好第一堂课,他准备了好久,可是走上讲台后,他竟足足站了十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1930年,沈从文在武汉大学做助教。他很不满,写信给大哥说:“我还是要坚持创作,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将来是希望一本书拿五千版税的。”
1933年,沈从文和张兆和喜结连理。沈从文说:“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许多年后,沈从文的内心深处却萌生了一种隐隐的遗憾:自己结婚太早,为家庭所累,以致没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而她,好像也不曾用心地对他说过那个“爱”字。
1938年,沈从文南下昆明。一次,一位学生问他写作的经验,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趁着二十来岁有写的冲动时尽可能多写。”几十年后,又有人问他小说怎么写得那样好,他答曰:“一辈子都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那才奇怪了。”他告诉施蛰存:“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1948年,天玄地黄。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沈从文写道:“就时代发展看工作,我已成为过时人,与现实不甚配合得来也。我工作自视还停滞在学习阶段上,要再摸十年八年,才望有点结果。可是时代变化大而快,要求作家又太多太切。我因为性格内向,埋头努力易,活动应变难,所以近年在此教书用笔实有和全面发展脱节之势。一个湘西乡巴佬的长处和弱点,由此可以充分见出。”他对大哥说:“既不想做官,也不拟教书,所以很希望一个人能回来住住。”当然,这只能是希望。
1949年,有学生来探望沈从文。他送给对方五本书,其中一书的题字为:“与瑞蕻重逢,恍如梦中,赠此书,可作永远纪念。”在《边城》后题写:“什么都不写,一定活得合理得多。”尔后,他写信给丁玲说自己“因为心已破碎,即努力黏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但最后他又决绝地表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怎么惋惜”。
1956年,时在湘参观的沈从文写信给妻子:“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沈从文选集。他在信中感叹道:“我实在是个过了时的人。目下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员,或四十岁以上的大学教授,还略略知道沈从文是个什么人,做过些什么东西,至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因为我写的都是大家一时用不着的,等到大家需要时,我可能已不存在了。”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重新被人提起。有人调侃:“沈先生行情正在看涨。”对此,沈从文波澜不惊。对所有的恭维,他总是轻轻地摆手说:“那都是些过時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1985年,有人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打扫女厕所的事,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不想,这位83岁的老人抱着她的肩膀,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像个饱受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涕泪俱下。所有人都惊呆了!
1988年,沈从文长眠了。临终前,家人问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摘自《阳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