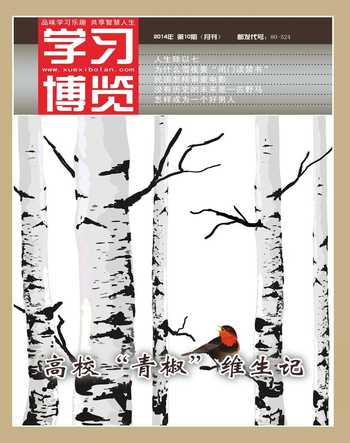高校“青椒”维生记
2014-04-29本刊编辑部
本刊编辑部
“五一之前我很受打击,从没想过会离开园子,也有一种很丢人的感觉。但五一之后看到学生的反应,我觉得自己12年来过得很奢侈。”最终从教师岗位调任为职员的方艳华略有感伤。
2014年5月5日,两篇名为《请求清华留任方艳华老师》和《清华,请留下方艳华老师》的人人日志开始流传于网络,将清华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方艳华是谁?她的去留
又怎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非升即走”惹不满
方艳华,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师,2004年开始一直任讲师。
2014年4月初,37岁的方艳华按照系里要求,做3年一次的述职答辩。主管外文系教学工作的张为民副主任的评语是:“教学效果优异,深受学生欢迎。独特的英语写作教学理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答辩结论:继续聘任,上报清华大学人事处最终核定。但是,校方根据“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则‘非升即走”的规定,判定方艳华科研考核不合格,不符合续签要求,由校务委员会下达不再续聘的决定。
5月初的一天,外文系2011级毕业生庞博偶然得知方老师被解聘的消息,在班级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方老师因为学校的一些政策关系,不得不离开了。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可以给她写一封信,把我们眼中的方老师是怎么样的还原一下,写完之后给学校。”5天内,庞博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等地共计50余封毕业生来信4万余字,洋洋洒洒几千字者不在少数。
这些信件被贴到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清华学术大牛越来越多,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却是越来越少,老师忙发论文,忙拉课题,忙培养研究生,真正能在培养本科生上花这么多时间而且又如此优秀的老师,很少很少了。”
“我们不是要给学校施压,只是用学生的记忆向学校全面展示老师的面貌、为人、教学和师道……学校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应该听学生的声音。”
“大学是为学生完成高等教育而开设的,评价一个老师是不是优秀,是不是应该留下,学生们没有发言权,只有论文说了算,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连学生的授课需求也无法充分满足的学校真是好学校吗?哪怕发表了成吨的论文,可无法教好学生、教会学生的老师真是好老师吗?在这种目的性、功利性极强的氛围里,培养出的学生真的是好学生吗?当一所大学失去了包容性,不以尽心尽力完成对学生的教育为首要目的,而是只汲汲于名与利时,还是我们向往的大学吗?”
清华在1993年开始人事制度改革的探索,提出“非升即走”实施方案,通過末位淘汰制优化师资队伍,实现人才流通。
1999年,校方实行有限期与长期聘用相结合的聘用制度,将“非升即走”制度化。新制度强调:对新聘人员实行连续合同聘用,规定初级职务最多两个聘期,中级职务最多三个聘期,如不能晋升高一级职务则不再续聘;副教授以上经过一至两个聘期后可长期聘任。至此,合同制逐步替代“铁饭碗”意识,在清华推广开来。
根据现有制度,方艳华“合同到期不再续聘”符合正常程序。
“非升即走”并非清华原创。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美国大学协会联合通过了《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的原则声明》,提出广为人知的“Tenure-Track”制度(又称“up-or-out”,“不升即离”制)。为了获得终身教职,美国大学专职教师往往要经历获取博士学位、博士后研究(2-3年)、助理教授(至少5年)、副教授(3-4年)和正教授的发展“流水线”。在助理教授试用期内,若无职位晋升,则必须走人;若达到评定标准,则有永
久或继续任职的资格,除非某些不可抗因素干扰。
“失去这份热爱的工作,是让我很痛心的”
“我觉得有些想法如果能影响到一些学生的话,价值不比几篇论文差。”
方艳华在清华外文系教授本科专业英语写作课,自2007年开设以来,至今“不可替代”。“大家都不愿意教这门课,都嫌它难,推来推去就到我这里来了,一直以来都只有我一个人教。系里也希望我再带一个老师,但是找不到。”
方艳华的学生王蕾,在请愿书中写道:“……在课上,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考量每一个标点符号、选词是否切合语境,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小方老师让我们一次又一次修改自己的作文,结成对子相互修改,并留下每一次底稿制作自己的‘作品集。她教给我循序渐进的写作方法,更重要的是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的行事态度。”
在方艳华的教学理念中,英语写作教师跟体育教练一样,需要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写作是很个性化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犯的错也不一样。我肯定得课下跟同学一对一交流。” 曾经有人说,这样一门“没什么大不了”的课,随便找一个外教就可替上。但在方艳华眼里,“课可以上得很水,也可以上得很重。”
办公室里,方艳华拿出两摞厚厚的作业批改记录,这是学生为她整理出的申诉材料,也是她教学工作的见证。一线教学占用了方艳华绝大部分时间,自2007年开设写作课以来,方老师批改每份作业平均耗时30分钟,每周总计25小时。
方艳华并没有太多遗憾,“我一直在按自己的理念、梦想生活。学生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也实现了我想让他们学到的东西。职称和金钱不是我看重的,但教书育人这份工作我很珍惜。失去这份热爱的工作,是让我很痛心的。”
方艳华仅是当下中国高校中年轻教师生存矛盾的一个缩影。在第30个教师节过后,我们不得不正视高校“青椒”的生存状态。
“青椒”=“夹心层”+“不上不下”+“境遇尴尬”
“青椒”,是网络上对88万(教育部截至2011年年底的统计)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这是一个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比例高达62%的庞大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读20余载终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
或许,这数以万计的高校青年教师普通、平凡,没有太多骄人业绩,也没有显赫名声。三尺讲台,对这些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年轻人委以千钧重任。可是,当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赚钱养家……这些词语在现实中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之后,种种欲说还休的困顿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脚步趔趄、心生乏意,也让“夹心层”“不上不下”“境遇尴尬”成为挥之不去的标签。
生活就像“赶地铁”
曾几何时,供职高校,成为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杏坛授业,桃李天下,为这份职业平添几分光环。更羡煞旁人的是,能带薪坐享寒、暑两个假期,不用天天坐班,免受“朝九晚五”之痛——这也经常是“青椒”在承受巨大精神、物质压力之外,聊以自慰的安慰剂。
事实是,“青椒”们确实免受“朝九晚五”之痛,可是,为了如期赶上第一节课(早八点),避开交通早高峰,“青椒”们六点多就得从昌平、大兴、良乡向学院路出发。春夏尚可,秋冬时节,真是披星戴月。如若不幸遭遇交通拥堵,当白领们纷纷致电公司解释迟到之时,“青椒们”却心如刀绞。因为,迟到哪怕一分钟就会被定性成“教学事故”。面对学生和教务处,你百口莫辩,“既然知道北京堵,谁叫你不早点出门呢?”或有人言:谁让你不住在学校或者在学校附近住呢?答:学校家属区“青椒”根本没资格“染指”,周转房早已人满为患,成为学校这个“房东”安排下的“合法”群租,想租还得“排号”等。学校附近属于学区,房租尚且无法承受,更遑论买下它。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在六环外“蜗居”。
33岁的“青椒”刘老师工作3年半以来,一直过着一成不变的“一日生活”:早上6点多起床,看书、查资料、写论文和投标书,再抓紧完善由老教授或教研室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中午“随便搞点吃的”后花一个多小时辗转抵达学校,完成下午3个课时的教学任务,下课后还得赶在财务、人事下班前“把提前在家贴好的发票送去报销”;晚上回家也是片刻不得闲,上传教学课件、回复学生邮件,真正能坐下来看看书、写写字已是深夜。甚至,没有双休日和假期,“不去参加学术会议的话,就抓紧多写点论文,还得准备PETS-5考试(评职称时的必要条件)。”“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如此满满当当,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这段时间很忙,忙完就好了”,这是他对女朋友说的最多的口头禅。刘老师未婚,尚没有家庭琐事的打扰,在他身边,已经成家、有小孩的“青椒”更是焦头烂额,“可我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信步走进任何一个大学校园,很难再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惬意闲暇的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口中的“赶地铁”:“现在的状态,即便是在北大校园,大家都急匆匆赶路,像在赶地铁。”
教学科研难平衡
在一项关于“青椒”的调查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发现,有72.3%的青年教师认为工作“压力大”,且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科研。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受访者觉得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
李旦任教于沪上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系。他所在的大学对教师评职称设有一些“最低门槛”,比如有几篇代表作,承担过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负责人,拿过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工作6年的他曾两度向“老板”提交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但均未获批准。“写申请书很费时间,短则两个月,长则半年。因为我要介绍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既要与以前的研究关联,也要找出创新点,很费脑筋。”
今年是曹东勃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的第三年,除了承担公选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外,他还为研究生讲授专业选修课《经济哲学》。“青年教师多半是想把课上好的。没有哪个青年教师一进校就说,‘我根本不在乎学生的评价,只搞研究就行了。因为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站住讲台,把课上好,一个教师的大后方就稳固了。”
曹東勃还记得工作第一年的情景:80%时间用于教学,20%时间做科研。他2010年7月毕业,9月就要上讲台,同时讲授本科生和研究生两门课。除去到山东农村调查的15天,两个月的暑假只剩一个半月可以备课。“第一次备课时间不够用,当时只搞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课件、教案,勉强做完一半。最紧张的时候,这一周的课刚上完,就要马上制作下一周的内容。”
过去这一年,曹东勃在农村驻村调查了60天。他坦陈,以前教学压力大的时候,根本抽不出这么多时间,现在投入教学的时间逐渐减少,但学生评教的分数却在逐年提高。曹东勃授课的四个班,前两年每年只有一个班的评价在90分以上,今年,四个班的评教分数都超过95分。
“容不得”
十年一剑的科研
从入校培训的第一天起,“青椒”王老师就不断地从人事处、科研处和学院其他老教师那听到论文、课题的重要性,“按学校规定,要想评副教授,至少需要1部专著、3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收录的论文,同时须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项目两项,其中主持纵向项目(含国家各部委及省级政府正式委托项目)1项,或主持到校经费20万元(理工科)、10万元(人文社科)的横向项目。”
短短一个学期,王老师就完成了将近300个课时的教学任务、申报课题6项、投稿9篇、还兼职新生班主任。“成果”累累,可他却觉得这更像一种“戕害”。甚至,他还给自己和同行下了个“知识民工”的定义。
“现在要鞭策、要急功近利地把最好的资源投入到最好的大学,想要有高收入、高薪水,就必须竞争、急于求成。”这种量化的考评管理,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看做是“GDP主义”,“这整个儿是一个指标系统,大到一个学校,小到一个老师,都是用一套指标系统衡量。人只是为了挣工分,创造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的环境,哪还容得下你十年磨一剑?学问本就需要‘慢工出细活,现在倒好,‘大干快上,天天逼着你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而不是出好活儿。”王老师也曾想过以一种不屈服的姿态对抗这种评估方式,不过没出两年,就败下阵来,“五年内不能从讲师升为副教授,就得离岗走人,不再续聘。连饭碗都保不住,这是大问题。”
上课是最不重要的
“良心活儿”
教学是 “立校之本、生命源泉”,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云南大学“70后”副教授尹晓冰的惊人之语:“教师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就是自我毁灭。”
“我觉得,教学上只要使三成力就够了,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到科研上,和评职称挂钩,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法宝。”王老师直言,他越來越品出同门师姐传授的“高校生存法则”的味道:“很多学校的教学任务都主要由年轻人承担,又要逼着你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还要上够课时量,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上课自然会被最先舍弃。”他的身边,越是大牌的教授,越不愿意去上课,“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乐意自己做课题出文章”。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十分反感这样的言论:“我认为文章只应该占所有素质的十分之一,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教育方面的关怀、口头表达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与学生交流的能力、能不能把知识传给下一代等。”
但这一切,因为和现有的利益导向机制不相匹配,能真正听进去的人实在寥寥。每个人都很忙,忙着结项、写标书、发论文,甚至是找发票报销、和期刊编辑拉关系。上课,已经成为最不重要的“良心活儿”。
无奈之下,萧功秦选择用另一种路径说服学生:“不去争取那些课题,不去发表那些东西,就默默地自己搞自己的东西。你可能得不到很多的褒奖和奖金,但是你们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将来可能做出重大的成就。”没过多久,学生们说,无助感却更加强烈地袭来,这条路并不轻松。
“传道授业解惑”,这本是三尺讲台赋予这些“青椒”们最神圣的使命,也是让“教师”不仅仅只是一份职业的价值所在,可如今,一些“青椒”坦言无法体悟这样的境界,因为他们心中的困惑也“无处可诉”。
廉思把这种在高校青年教师中极为普遍的状况称为“自我认知下行”。在他发出的5138份调查问卷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当“催人奋进的压力”遭遇功利的评价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已在高校工作六年。他觉得,青椒压力不小是事实,但压力也有类型之分。比如,青年教师在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但在工作岗位上,除了教学和科研重担,上有学问渊博的教授,下有渴望知识的学生,这些也应该算是“催人奋进的压力”。
瞿骏曾赴国外访学。他说,欧美学术界实施的是精英化教育,拿博士学位要苦学,尤其在美国,用五六年甚至七八年的时间拿一个学位是家常便饭,同时,大学教职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可一旦获得教职,特别是终身职位后,教师基本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学术研究了。在我国,青年教师相对而言基数庞大,入职后的竞争特别激烈。
几乎每一位接受采访的青年教师都认为,现有的考评体系和方式过于功利。本想安于治学,做些“良心活儿”,但这些若以量化指标来衡量,都显得是在做无用功。
在中文系任教的林晓东最近半年埋头点校,整理古籍,为其添加标点、校正文字。很多人一听,觉得他傻。一方面,做这类基础的工作无法获得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点校是“雕虫小技”,点对了,应该的,稍微错一点,就是水平能力有问题。眼下,一本古籍刚点校完,林晓东没拿到一分钱,换来的只是自己心头一乐。
“不考核肯定不行,缺少外部约束机制,高校会堕落;但是,不能让考核把人考得烟熏火燎,把大学考成一个速生鸡的养鸡场。”做一名大学教师,应该是“发现兴趣、呵护理想”的过程。可青椒们也感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教书、做学问不仅要耐得住清贫,还要有一些“投机取巧”应对考评的能力,让自己“活”下去对很多人来说,这真是太难了。
难耐清贫
学校是个清静之地,有时,李旦躲在办公室里,也像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学校里,大家的收入差别不是太大,可走出去看看,和我一样年龄的,那差别就大了!”
李旦初略算了一本账:因为要养孩子,一家人每月开销少说5000元,一年就是6万;养车去掉2万,其他杂七杂八加一起,年支出大约10万元。
今年是李旦参加工作的第六年,根据目前的收入,养家糊口勉勉强强,手头若再要有一些积蓄,实在艰难。为孩子积攒来日的教育费用,乃父亲职责所在,但眼下也成了一桩隐隐心事。同事中,有人已为了高薪而跳槽,投奔企业去了。
林晓东来沪9年,如今拿到手的薪水4000元左右。他也有一本账:每顿饭在学校食堂解决,花费10多元;平时很少添置新衣服,除掉交通费、通讯费、买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的结余大概2500元,一年下来能存下3万元。“学校提供的房子能居住11年。11年之内买不起房,那么唯此一途,离开这里。”
尽管如此,想进入高校体制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多,每年积压着大把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即使一个待遇很低的辅导员岗位,也都有上百人竞争。于是,“愿赌服输”成为那些在基础学科勤奋耕耘的青年教师们的默默选择。并且,除了那些想在教学和学术领域有所作为的教师外,大部分教师只是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当成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
当然,不是所有老师都辛苦,都清贫。一些教授,凭借着自己的行政权力,四处拉课题,分包给底下的博士、硕士去做,然后在他们的科研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甚至有些教授,一年能发五十几篇“学术论文”——这往往是一些教师一辈子所有文章的总和!在一切“向钱看”的政策指引下,项目经费可以折算成绩点。比如,南京某高校,按照不同论文等级,折算教师发表的论文分数,一篇学术论文,根据等级,3到10分不等。而每一万元课题经费,就能折算成1分。那些动辄有几百万项目的教授,仅仅课题这一项,就有几百分。于是,就看到这样的马太效应:那些“学霸”们,不管是在行政上还是在学术上,都牢牢掌控着一切权力,动辄几千分的绩点,而那些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在“重项目,重科研,轻教学”的评奖机制面前,只有寥寥几十分的绩点。
新闻中报道:“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表示,要在今年消灭大学教师课时费低于30元的现象,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 熟悉南京教育市场行情的人都知道,一个高校老师只要口才过得去,随便到一个教辅机构谈谈价,课时费很容易达到80元以上。于是,很多青年教师,出于生计考虑,不得不拼命在外兼职代课,无法安下心来教学、搞学术。
当以“学术为业”的教师们,在为基本的生计发愁,并且悬殊的收入分配,很多时候是被垄断的行政权力与扭曲的学术权力所左右的时候,他们心中,真的是连一张平静的课桌也放不下了。
编后:学者廉思将高校“青椒”比作“工蜂”。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的群体,被自嘲成“学术民工”。本来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这样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他们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心态。这样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今日中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
高校“青椒”们未尝不知这样的悖论,面对这样的环境,他们只能借用张鸣老师的一句“学有病,天知否”作为自己内心深处最痛苦且挣扎着的哀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