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洛神赋图》中山水画法对山水画创作的启发
2014-04-29孔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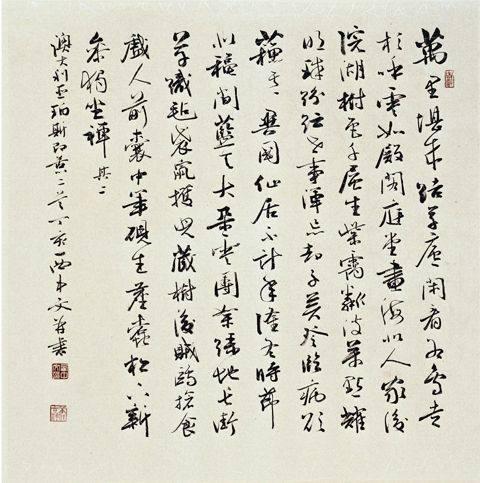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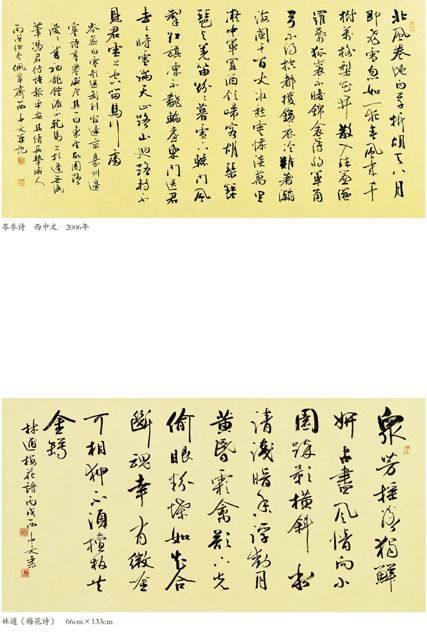
摘 要: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画家根据曹植那篇婉转动人的《洛神赋》而创作的,以人物为主,画面中洛神和诗人曹植置身于美妙的自然山川中,山水作为人物的背景,并没有独立开来,是早期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这种古老的画法非常典雅,勾勒填彩,青绿着色,虽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正是这种不成熟才显得这幅名作更加稚拙可爱、曼妙无比,给我们山水画创作提供许多借鉴空间。
关键词:顾恺之 《洛神赋图》 山水画法 创作
一、山水中的线条之韵
《洛神赋图》用圆润匀称的线条勾出山石和树木的轮廓,造型质朴可爱,具有浓重的装饰趣味。山水画中的线条是人物画线条的衍生物,春蚕吐丝,质感柔滑,没有变化。这时期的山水画还没有形成皴法,只是对山体简单的勾勒。纵观中国山水画史,其形式语言之一的皴法变化很为突出,并随着山水画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从自然造化里汲取营养,留其精粹,并最终程式化,皴法成为山水画独特的语言,在表现山石结构和意境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成熟的皴法,是绝不可能出现如董源、范宽、李唐、郭熙等人的宏伟巨制;没有皴法,也较难表现出或迷离,或崇高,或幽远的山水画境。可以说,皴法的发展显现出不同的山水画形态,我们今人亦是从各家特有的皴法用笔上辨识出各家面貌,并由此研习山水画。“勾、皴、点、染”中的“勾”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在许多画作中,勾法与皴法相交织,并没有泾渭分明。《洛神赋图》中的山水画法纯以勾法,造型简洁,线条从容不迫,如音乐一样缓缓流出,给予我们不同的美的享受,展示了山水画勾法的美妙,这为晋唐青绿山水画的发展提供了范本,同样也给后世的许多画家以诸多启发。
比如赵孟頫,他的《吴兴清远图》是张简淡且极富神韵的佳作,整幅画面呈平远式构图,画幅中水与天占的比例很大,只在画幅的居中位置有一抹山痕,山体空勾无皴,造型洗练到含有一种抽象的意味。山体的轮廓线很淡,非常柔美,显得很轻盈,仿佛溶入到天光水气中。此图描绘的是一种理想、一重境界、一场迷梦,深得《洛神赋图》中山水画法的神妙,色彩古淡凝练,构图上较之更为洗炼、意境上则更为清远,是赵孟頫师古山水画的典范之一。整幅作品极淡极远,虽是师古的杰作,但画面构成却给人一种十分现代的感觉,这种画法与现实中的山水既近又远,禅味十足,有一种日本枯山水园林艺术的风味,值得观画者深深品味。赵孟頫的另一佳作《幼舆丘壑图卷》也是“托古改制”的作品,相较《吴兴清远图》更加古雅厚重。这是一幅中景山水,赵孟頫用朴素的线条柔柔地勾出山石的轮廓与结构,似真似幻,没有复杂的皴法,没有对真山水的逼真描摹,但线条如诗如歌般地婉转着,这种柔韧的线条描绘出坚实的山石,显得山石有种内敛的力量,柔与刚之间透显出微妙的平衡,使得冷硬的山石有了活泼泼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随着线条的韵律跃动,形成了心中的丘壑,与真山实水相交融,晶莹剔透,如在镜中,静穆中有活力,纯净中透高雅。
赵孟頫的次子赵雍受其父师古的影响,他的《狩猎人物图》(传)中的山水更富有装饰意味,其线条如人物画中衣纹的表现,繁复严谨,方中带圆,一根根线条本身较少变化,如行云流水一般流动翻卷成山石的形状,山石的结构亦是用勾法,线与线之间的疏密对比较弱,整个山峦如可见的乐章,忽而舒缓,忽而疾驰,内敛中有张力,读画者的心境也随着线条的起伏而波动。
又如陈洪绶的《停舟对话图》,山石同样是以勾勒为主,特别是近景处的山石,奇肆高古,与《洛神赋图》中的山石勾勒造型非常相似。陈洪绶山水画的用笔造型是从他的人物画中派生出来的,这一点也与《洛神赋图》如出一辙。
从这些画作中就可以看出,勾法对后来青绿山水画的绘制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勾法在水墨山水画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例如黄公望《九峰雪霁图》,就是一幅以勾勒为主的水墨山水画作。此图中近景用起伏变化的线条勾勒出嶙峋的山石,并用淡墨渍染,较少用到了皴法;远处山峰简洁空灵,只是勾勒出外轮廓线,与中近景山石的线条形成繁简的对比。水与天用浓墨渲染,烘托出晶莹的山体,仿佛整个山体都映着雪光,这种洗练的画法十分贴切画题和其意境,整幅画面就像笼罩在剔透冰清的琉璃世界中,肃穆静谧,宏大深远。
单纯的勾法是对物象的高度提炼,势必会带来山水画的装饰性与抽象性,如当代卢辅圣的山水画,画面单纯、抽象,富有音乐性,却只用勾染,这样,画面中线是柔的,色是淡的,线条流淌出山石,甚至没有树,没有一切繁杂的事物,有着晋人的风韵,虽然不能“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却是心中弹奏的山水之音。
二、山水中的色彩之丽
《洛神赋图》中山水以青绿着色,单纯雅致,后世青绿山水画的色彩都是沿袭此法,发展到唐代形成了李思训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画,色彩十分绚烂。《洛神赋图》却没有那种华丽的贵族气象,它所显出的是与洛神和诗人性情相契合的诗意之美、朦胧之美,它的青绿色是柔和的,几乎融入太虚之境里,没有李思训的大青绿那么有存在感。这种若有若无的青绿山水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存在感,但它却永恒地略带淡淡的忧伤感动了我们,由此,我们体会到了色彩的纯净柔雅之美。在后世画作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其影响,如钱选的山水画作《秋江待渡图》、《幽居图卷》、《山居图卷》等,都是以墨线勾勒山石轮廓,再施以或淡或柔的石绿或石青色,明快澹静,富有古韵,温润得如玉一般,使得山石仿佛从内里散出光来。卢辅圣的山水色彩亦是清雅朦胧,仿佛罩着一层纱。中国山水画的色彩处理是取法自然,并最终抽象化与纯粹化,因此它可以发展成纯水墨,甚至可以是其他色彩,如卢禹舜的山水画作《老子观道》与《八荒神通》,整幅都是鲜亮的红色,反而显得空蒙与神秘。
三、山水中的时空之错
《洛神赋图》中的空间感较弱,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远大近小”的现象,这种空间上的“错位”感带来了不同的韵律和视觉享受,也极好地烘托出画的一个主题氛围,把缥缈的、亦人亦神的一个真实与虚幻相结合的空间表现了出来。在同一画面里洛神与曹植出现了多次,表现了不同的时空,这种表现方式与《韩熙载夜宴图》颇为相似,山水在画面中起到了连接的作用,随着情节的发展或疏或密。从另一方面看,《洛神赋图》中的山水则是一种永恒之境,顾恺之用人事的无常衬托出宇宙的永恒。
我们可以从《洛神赋图》中山水时空的处理方法上感觉出,中国山水画的时空维度是很宽广的,可以无限延伸。例如贾又福的画作,并不局限于某时某景,他“以石观化”,表现的是更为壮阔,更为抽象的超时空精神境界。又如卢禹舜的“静观八荒”系列作品表现的则是梦幻、深邃、静谧的宇宙情怀。他们都挣脱出了时空的局限,其实这与古代山水画家的宗旨并不相悖,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一直都是“象外之象”,通过山水进行哲学性思索。
四、山水中的抽象之思
甲骨文中“山”的写法为“”,这种象形的写法就是古人对山的直观与整体的感受,概括简练,是一种提炼抽象的造型,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造型与之有相通之处,《洛神赋图》中的山石造型基本上是由不同形状的“△”组合而成,又如唐时的敦煌壁画《舟渡图》中的山水背景。这些都是对山石的整体抽象性的宏观把握,而不是对山石具体造型结构的描摹,在艺术表现力上有其独特性。
钱选的山水画就有着这样的抽象之思,他喜用方折的硬线勾勒出稚拙古朴的山体,与《洛神赋图》中柔性的山石不一样,形成了一种刚性的美。但同样的,钱选的山不是复杂的具体的描山摹水,而是一种抽象概括,特别是《山居图卷》,画幅中央的几座山峰恰如甲骨文“”,可见钱选并不执着于复杂多变的物象,而是追求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核。米芾与米友仁的云山墨戏中的山也多是这种造型,满纸烟云,恍惚迷离,画的就是文人的一种情思。当代新锐画家黄红涛的《无名山》系列中山的造型亦是如此。这种抽象的山体造型可以剥离出现实,不是具体哪儿的山,而是一种泛指,一种本质,更为贴近世界本源、亘古洪荒。
综上所述,《洛神赋图》中的山水画作为早期山水画让我们看到了山水画最为本真的源头,为我们研习山水画带来了诸多灵感,提供了诸多可能性,提醒我们不能囿于程式化的思维之中。中国画的艺术精神就是写意的,就是抒情的,有着生命的跃动与喜悦,古往今来的山水名作其实都是把握了山水本身的生命韵律与节奏,不仅仅是对技法的肤浅追求,更为重要的是对自然最深层的感动,这对我们山水画创作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简介:
孔翎,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