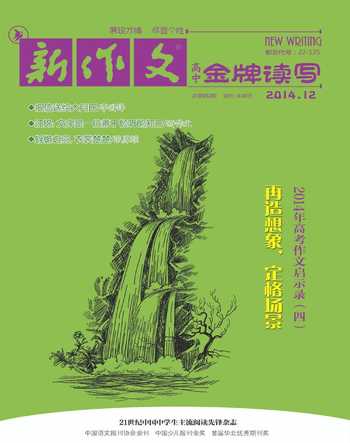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2014-04-29张勇耀

【文前小语】
伤春悲秋,这是人类共有的情绪,人类把它们唱在歌里,写在诗里,千百年来咏叹不尽。其实在这共有的情怀里,潜藏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咏叹。时间的无可挽系,让生命变得匆匆,花谢犹有花开时,人生却无再少年。生命是一场单程旅行,一旦上路就不会再回到出发的地方。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伴着这样的咏叹,我们变得凝重,也更感到了生命中时光的珍贵,而这样的咏叹经典,同样出自《诗经》。
张勇耀,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会员,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出版有散文集《会唱歌的蝴蝶》,散文小说集《风中飘过村口的影子》等。现居太原。
自然总是给我们以无穷启示
我们看天的浩渺,看地的沉厚;看水的流动,看山的坚韧;看树的挺拔,看花的绚丽;看鸟的欢快,看鱼的自由……看着看着,我们就看到了自己,或者说,它们都变成了我们的镜子,折射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天空说:心胸要宽阔呀;大地说:为人要厚道呀;水说:要刚柔相济有智慧呀;山说:要抬头挺胸不屈服呀;树说:要向着阳光生长呀;花说:要趁着恰当的季节开放呀;鸟说:要珍惜自己的天空呀;鱼说:要享受自由的美丽呀……是的,它们都会说话,而这些话我们什么时候能听得懂,却全在于我们自己的悟性。
《诗经》时代,一位诗人看到了一只漂亮的蜉蝣,那种有着透明得如同薄纱一样羽翼的小虫子,突然感到了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惊惧。因为他从这美丽得令人心碎的小虫子身上,陡然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所有人类的宿命。他情不自禁地吟咏: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蜉蝣啊蜉蝣,你有着薄纱一般并且泛着生命光泽的羽翼,就好像我们人类,穿着自认为能够让自己以最佳形象出现在这世间的最华贵的衣服。然而我的心是如此的忧伤啊,因为你和我,将有一样的归宿。
说衣裳“楚楚”,是因为在《诗经》时代,只有楚国人能够织出那样一种薄如蝉翼的华丽丝织物来,穿着那样的华贵衣裳,美女们自然“楚楚动人”。然而穿着这样的衣服又能怎样呢?最后的结局也还是死亡。诗人如此感叹,是因为他知道,蜉蝣这种昆虫,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到一周左右,常常是“朝生暮死”。长着精美绝伦的翅膀又能怎么样呢?生命短暂,人和蜉蝣都终将归于尘土,那是一样的归宿啊。
诗人接着反复咏叹: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采采:光洁鲜艳的样子。归息:意思同“归处”一样,都是指归宿,即死亡。这一节与上一节意思完全相同,只是强化了咏叹的效果。
第三节意思略有改变: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掘阅:挖穴而出,“阅”通“穴”。麻衣:白色的衣服,指蜉蝣的翅膀是白色的,就如同古代诸侯、大夫等统治阶级日常穿的衣服。说(shui):住,居住。蜉蝣挖穴而出,就如人生命的开始。雪白的翅膀扇动着一个生命全部的渴望和喜悦,正如我们出生后穿上了代表着人类尊严的各式衣服,开始我们短暂的一生。然而蜉蝣以极快的速度死亡了,那曾经的渴望和喜悦都像一阵风消融在空气之中,仿佛它从来不曾来过。我们人类呢?我们拥有如此短短几十年的生命,死亡之后,又会有什么留在这世上,证明我们曾经来过的痕迹?
诗人的千年之叹,穿越时空,直抵我们的内心。
事实上,几千年来人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叹息。在我们无力阻挡时间的河流从我们身体里穿过的时候,死亡的阴影就时时在我们的身边徘徊。活着是美好的,而且我们人类可以活出比其他生物更高的质量,我们懂得以人的方式来装饰自己,懂得追求美的姿态,懂得寻找让自己幸福和丰富的方式。然而放在死亡的阴影下来看,我们曾经精心的装饰、爱美的姿态、追求幸福的过程,都显出一种巨大的无奈与哀伤,有时甚至显得有些讽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消费自己的生命?——是的,消费,我们的祖先或者说就是父母,是为我们买过在这世间暂住的票的。
这就是一只朝生暮死的蜉蝣,给予我们的启示,向我们提出的最高级别的问题。
漫漶在《诗经》中的生命意识
两千多年来,人类一直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诗经》中到处都充满了这种生命意识,我们的古代先民们早就在时光的流逝中思考人生的意义。
阅读整部《诗经》,我们会发现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时间名词与时间副词,“岁”“年” “月”“日”“春”“夏”“秋”“冬”“夙”“宵”“夜” “晨”“昏”“朝”“夕”“蚤”“早”“晏”“昼”“旦”“莫(暮)”“肇”“自”“今”“昔”等等。这里代表的是先民对时间概念的明晰,以及先民对时间的深切感受。时间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先民从对时间的感受中体悟了生命的存在。日月出没,四季轮回,花开花落,其中都有时间的影子在游走。在现代科技手段下,我们可以使用慢镜头,用半个小时看一朵花开放的过程;然而也可以使用快镜头,十几秒就历尽日出日没、春夏秋冬,甚至可以让一张婴儿脸迅速老年。但我们的先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科技手段,他们以最原始的纯朴心性,从真实的日月轮回、生死契阔中感受时间的消逝、生命的无常,于是发出了深沉的感叹,当然也有美好的感叹。《诗经》中“怊”“逝”“迈”“除”“永”“就”“将”等描写时间的词汇,就包含着迅速、消逝或长久的意思,我们的先民已经认识到时间是漫长无尽的、永恒的,同时也是易逝的。时间的漫长越发反衬出个体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易逝又促使他们思考如何增加生命的密度,提高生存的质量。
《诗经》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关于如何消解生命短暂带来的悲剧因素,得出了两种思考结果:一种是“乐”,即立足当下,及时行乐,以乐消忧,正如《秦风·车邻》中所说的,“今者不乐,逝者其耋(dié,指年老)”,“今者不乐,逝者其亡”;另一种是“戒”,即时光易逝,生命有限,人类要利用有限的生命,职思其居,兢兢业业。
第一类的代表诗作是《魏风·山有枢》。这是一首很有趣的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贴心”的数落,让我们既感觉亲切,又觉得这其中的悲凉: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
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枢、榆都是树名,枢即刺榆树。“隰”指潮湿的低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山上长刺榆,洼地长榆树(物都各从其类)。你有华贵漂亮的衣裳,为何不穿在身上?你有精美的车马,为何不乘又不坐?到你死去那一天,别人占有尽享乐。
这首诗还有两节,和这个意思大致相同。第二节中间两句是“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第三节中间两句是“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 廷内:庭院和房屋。考:敲击。你有宽敞的庭院和华美的房屋,为何不洒不扫使其更舒适亮堂?你有钟鼓这些精美的乐器,为何不击不敲享受音乐的美好?你有美酒有佳肴,何不天天弹琴鼓瑟以作宴饮之乐?生命短暂,姑且用它寻欢作乐,姑且用它消遣时光吧。而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则更点明了这样做的意义:“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等你死了,你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就都会归于他人,哪怕这些人是你的亲人,但他们不是你。
这都是大实话呀,钱财皆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生命有限,一旦你死了,你没有享受过的,别人就替你享受啦。这劝人者是如此清醒,时时把死亡看成被劝者生命享受的参照物,强调对生命中“物”的运用和对生命本身的愉悦。在古人看来,包括在绝大部分的当代人看来,及时行乐,确乎是增加生命密度的有效办法。
第二类的代表诗是《唐风·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聿(yù):语助。莫:古“暮”字。除:过去。无:勿。已:甚。大(tài)康:过于享乐。居:处,指所处职位。瞿瞿(jù):警惕瞻顾的样子。蟋蟀在堂屋鸣叫,一年匆匆又到了岁末。如今我是如此忧伤,因为时光流逝得是如此快疾。寻欢作乐可不要过度啊,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职责。行乐不能荒正业啊,贤士一定要时刻警觉。
这样的劝勉,让我们感到一种正能量。我们无力留住时光的流逝,但我们要在享受人生的时候有所节制,要乐而有度,乐不忘忧,时时忠于自己的职守。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在《诗经》时代,我们先民的理性精神即已初步觉醒,某些先知先觉的人士已经在探寻摆脱时间焦虑困扰的合理途径。这首“劝人勤勉”(金启华、蒋立甫之说)的诗,代表的是我们的先民在跨迈了及时行乐门槛之后所达到的全新的境界,因而更有意义和价值。
《诗经》之后关于生命意识的思考
可以说,《诗经》中所表现的时间意识,对后世诗文有着深远的启示。孔夫子从黄河滚滚东去不舍昼夜领悟到时间的永恒,庄子以“白驹过隙”喻指人生的短暂。这种对时间的诗性感受方式,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哲学的诗意与情趣。《诗经·唐风·蟋蟀》等诗对于时间的那种隐隐焦虑,到了《离骚》中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对国事充满焦虑的屈原,对时光的流逝、人生的无常同样充满焦虑。他担心的是,时光流逝,人生易老,而理想抱负却不能实现。我们看他的几句诗: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其他还有如“及荣华之未落”“恐高辛之先我”“及年岁之未晏”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讲,时间意识流贯《离骚》全诗。如果说《诗经》中的时间意识开启了后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那么《离骚》则进一步将伤逝主题与功业意识联系起来,从而对时间的思考更为凝重。
而到了汉乐府时代,诗人们依旧纠结在这样的“生命意识”中。可以说,人生无常、生命短促引发了诗人们无穷的深沉感伤。创作于汉代,大多佚失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这样的思考就比比皆是。“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累累坟墓与萧萧白杨更是加深了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如何消解这种恐惧?如何让生命更有意义?针对此类人生最大的问题,提出的方案,依然秉承了《诗经》中的两句。生命短暂、及时行乐,如: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生年不满百》)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青青陵上柏》)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上东门》)
另一类则是劝戒建功立业的,而且在建功立业之外,还多了对“荣名”留存于世的希望: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长苦辛。 (《今日良宴会》)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回车驾言迈》)
人仅仅只是天地间的一个匆匆过客,正如《青青陵上柏》中所表达的意思:柏树生命长久,千年万年依旧可以苍翠如新;而人类的生命却如此短暂,甚至比上不它的一个零头;石头坚硬如斯,千年不化,而人却是那样容易便化为尘土。作者用柏树和石头来托物起兴,反衬出人不如物的可悲遭遇,表达了诗人对生命永恒的期盼以及对生命必然死亡的无可奈何的悲哀之情。再如《今日良宴会》,用“飙尘”比喻人生,既以飙风的旋起旋止暗喻人生的短暂,又以飙风卷起来的尘土旋聚旋散暗喻人生意义的空虚。在这种情况下,是将有限的生命沉醉在感性的享乐之中从而获得暂时的解脱,还是建功立业留名后世,可以说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诗人们的纠结可以说一路下行,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远不老的主题。但诗人们的思考似乎更趋于理性,也有了更为现实的思考。即使提出“行乐”,但背后隐藏的也还是建功立业的大情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操《短歌行》)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曹植《薤露行》)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
(曹植《箜篌引》)
○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
(张华《壮士篇》)
○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
(陆机《猛虎行》)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杂诗》)
而因为在现实中不能施展抱负,又不愿与时代同流合污,不少人选择了寄情山水,隐逸乡间,在看似闲适的吟哦中,思考着人生的意义。“竹林七贤”以及陶渊明等人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阮籍曾写过82首《咏怀》诗,其中有不少就表达了对时光易逝的伤感。比如“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愿为三春游,朝阳忽蹉跎”“逍遥未终晏,朱阳忽西倾。蟋蟀在户牖,蟪蛄号中庭”“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等。在阮籍笔下,人和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是倏然而逝的,从年轻到衰老、死亡的规律谁也无法抗拒。既然如此,生命的意义何在?人们一切行为的价值何在?诗人于天地之间久久徘徊。
到了唐诗宋词中,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丝毫没有减弱,反而因为时代的原因,对这种思考呈现出了更为生动的意象、更为精美的表达。常见的意象如“日月”“白发”“花”“流水”“更漏”等等。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物的长久不移与人生换代的迅疾,道明了时间于物于人的秘密。再比如: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李白《将进酒》)
○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
(李白《古风》十一)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四时如逝水,百川皆东波。青春去不还,白发镊更多。
(孟郊《达士》)
○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
(晏殊《破阵子》)
甚至有的直接就用了“蜉蝣”的意象。如苏轼《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时间的变迁在自然景物上留下的痕迹相对说来并不显著,若干年过去了,树木衰而复荣,山川面目依旧,但人事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放眼历史的长河,天地悠悠时间无尽,自己的生命不过是那长河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浪花。时间的无穷与自身的渺小,构成了人生的大悲恸。
没有人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增加生命的厚度和密度。珍惜时光,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便成为诗人们对抗时光易逝、人生易老的积极呼吁。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汉乐府《长歌行》)
○人生贵壮健,及时取荣尊。夏禹惜寸阴,穷治万水源。栉沐风雨中,子哭不入门。
(苏舜钦《夏热昼寝感咏》)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杂诗》其一)
此类诗句还有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从《蜉蝣》出发,中国的文人们一直试图通过内心的追问,得到关于生与死、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答案。然而这终究是一道难题,因而人类就不免常常笼罩在一种彻骨的悲凉之中。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对死的忧伤、困惑、追问,归根结底是表现着对生的眷恋,这也是人心中最自然的要求。正如阮籍《咏怀诗》其七十一所写:“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也谨以这句诗,送给那些还在挥霍生命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