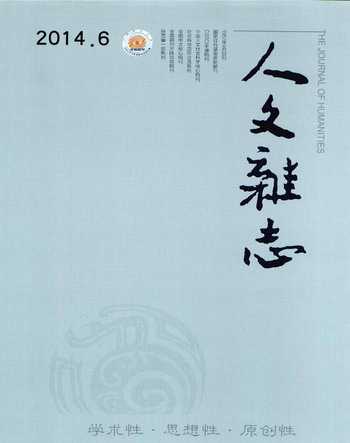汉字革命”派语文知识的“选择性错误”
2014-04-29朱晓梅赵黎明
朱晓梅 赵黎明
内容提要近代语文运动特别是五四“汉字革命”运动,是一场“将语文还给大众”和“语文现代化”的文化革新运动,其对中国语文乃至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立下的功绩,理应得到充分肯定。然而,宣传革命理论的同时,运动中也时常出现有意无意的“知识性错误”,主要表现在对“言文一致”的错误认识、将文白之争比附为拉丁方言之争、将教育落后之责诿过于汉字等方面。“东方文化”派曾一一指出上述错误之所在。这些常识性错谬,反映了“汉字革命”论者的“意图伦理”。如今重新检视这些问题,有利于对新文化运动得失的深度反思。
关键词“汉字革命”语文知识选择性错谬“东方文化派”“意图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6-0059-06
1922年,在“国语研究会”会刊《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号”上,钱玄同第一次祭出了“汉字革命”大旗,胡适、黎锦熙、蔡元培、周作人、沈兼士、赵元任、傅斯年等,从汉字存废、字母化以及国语建设方向等层面,分别提出对汉字加以“彻底改革”的意见。其实,作为一场语文运动,它的时限可以延长很多,上可溯及1892年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的发表甚至更早,下可延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代甚至更晚。清季民初以来,凡是旨在对中国语文进行大众化、通俗化、拼音化改造的文化活动,都应摄入“汉字革命”的范畴。
“汉字革命”运动敏锐地感应了时代潮流,准确地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客观地讲,它是一种进步的语文还原运动;其所秉持的理论依据有它的真理成分,其所欲追求的目标如今也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其对中国语文乃至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立下的功绩,理应得到充分肯定。然而,正如其历史功绩不可忘记一样,其理论错谬和实践偏颇也同样不可忽略。特别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宣传策略,只要效果不管事实的学术态度,尤其应该反思与警醒。特别在语文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带有“意图伦理”色彩的常识错谬,即语文知识的“选择性错误”。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他们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不少“证据”,那些曾经迷倒了无数革命追随者的言之凿凿的所谓事实,原来不过是或子虚乌有、或人为杜撰、或张冠李戴的一次次“乌龙”。本文重新检视“东方文化派”的相关质疑,拟对“汉字革命”派有意的“知识错误”进行一次系统清理,对其学术精神进行再一次考量。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东方杂志》(1911-1932)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研究”(11XZW014)
一、“言文一致之实安在乎”
近代以来,文字改革者发动大众语文运动的一个最大理由,就是中国文字“言文分离”,不利于启蒙兴国。基本逻辑是:语言与文字分离,造成学习困难、识字率低;而识字率低,民智不开,又成为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欲强大必自语文改革始,而改革语文必走文言向白话、汉字向拼音转化的道路。如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指出言文不一的弊端:“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黄遵宪:《日本国志•文学志》,选自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1898年,裘廷梁进一步指出言文不一的危害: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愚民”,而且“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两千年来文字一大厄也”。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近代史资料》(1963-2),中华书局,1963年,第120页。而到了五四时期,不论废汉论者还是白话文论者,都异口同声地把“言文不一”视为了汉字野蛮,文言落后的最主要证据。“言文一致”成了语文改革家判断语文优劣的理想标准。
“言文不一”果真是中国文字的致命弱点吗?“言文一致”果真是一种语言的最佳境界吗?中国语文“言文不一”有没有特殊的文化原因?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辨析的。
2014年第6期
“汉字革命”派语文知识的“选择性错误”
首先,语言与文字不能混为一谈。比较而言,文字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语言的变化性较大,因此语言与文字不一致是语言文字生存的一种常态。这种语言文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固然带来诸多不便,但相对而言,其便利性可能更多,如保持时间上的连贯性、地域上的统一性等,因此“言文不一”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杜亚泉说:“其文字不至随语言而改变,于学术上及社会上之便利殊多。”④⑥杜亚泉:《译者前言》,见[日]山木宪《中国文字之将来》,《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因而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上,他认为宁可“改变语言以就文字”,而不是相反,“理想之文字,必简略于语言,但能有一定之规则与语言相对照斯可矣。且欲使语言与文字,有对照之规则,亦惟有改变语言以就文字,使言语渐归于统一,不能改变文字以就语言,致文字日即于纷歧。”④显然,在他眼里,改变文字以就语言,反而会造成混乱的结果。
其次,文言白话各司其责,各擅其长,不能强归一致,也不能强分轩轾。胡先骕认为文言与白话所用场合不同,口语多用于写实,文言多用于抽象,所以二者不必混为一谈,“夫口语所用之字句多写实,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即敷陈其义,亦不易领会也,且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今试用白话以译Bergson之创制天演论,必致不能达意而后已,若欲参入抽象之名词,典雅之字句,则又不为纯粹之白话矣。又何必不用简易之文言。而必以驳杂不纯口语代之乎。”⑦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2、5页。杜亚泉则坚持,文言白话作用于人的器官不同,效果不一,不能“强令一致”,“至于文字语言,不能强归一致,语言发于口而感于耳,文字作于手而触于目,器官既异,作用自殊,强令一致,则便于口者不便于手,利于耳者不利于目,无两全之道也。”⑥
再次,“言文不一”反而有利于传统的继承。胡先骕曾举例说,英国诗人乔叟五百年前之诗之所以“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就是因为英语“谐声”和“言文一致”的缘故,因此他认为言文分离,对于典籍的保存、文化的传承功莫大焉,“向使以白话之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之为劣,岂不谬哉?且盘庚大诰之所以难于尧典舜典者,即以前者为殷人之白话,而后者乃史官文言之记述也。故宋元语录,与元人戏曲,其为白话,大异于今,多不可解。然宋元人之文章,则于今日无别。论者乃恶其便利,而欲故增其困难乎,抑宋元以上之学,已可完全抛弃而不足惜,则文学已无流传于后世之价值。”⑦杜亚泉也设想,假如文字随语言而转,拼音以代中国汉字,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必定陷入不能读不能传的境地,“若我国亦用标音文字,则不但春秋战国之文,将无从索解,即汉唐宋明之文,亦将不能卒读矣。四千年之中,至少有三四种专门之文学,承学之士,虽白首不能尽通。今则历朝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沧桑屡易,而文字则亘古如新,其便利二也。”④杜亚泉:《译者前言》,见[日]山木宪《中国文字之将来》,《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因此,他们认定,“言文分离”既是特殊国情造成的,也是文化传承的需要。
最后,欧西言文,何尝合一。他们批判大众语文的倡导者,动辄以欧西为法,而实际上并未了解欧洲语文的实际。杜亚泉曾这样批评言文一致的“无谓”:“言文一致者,彼派之所倡导者也,以为言文一致,则学问易于进步,又以欧美诸国为言文一致之过,是皆无稽之说也。欧美之国民,非尽能读其文字,其不受教育之人,虽无不能言语,而亦不能解文字。”⑤[日]山木宪:《中国文字之将来》,杜亚泉译,《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胡先骕批评新文化运动时也说:“且言文合一,谬说也。欧西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即以戏曲论,夫戏曲本取于通俗也,何莎士比亚之戏曲,所用之字至万余,岂英人日用口语须用如此之多之字乎?”⑦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他们不仅注意到泰西文字“言文不一”的现象,而且认识到中国文字“言文不一”的特殊地理原因。“欧洲各国,区域较小,而各国之文字不同。若我国亦用标音文字,使言文一致,则一国之中,将有数十百种文字出现。”④
综上所述,他们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言文一致”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理论的基础,它是中国大众语文运动家对西方语言传统的有意“误读”,“言语自言语,文字自文字,言文一致之实安在乎?”⑤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批评固然有不少真理的因素,但其立足于“精英”的文化立场,跟面向大众的整个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的声音显得不合时宜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文言、白话之争岂可等同于拉丁、方言之争
为了取得白话文运动的合法性,加快白话文运动的进程,大众语文运动家往往喜欢将中国的文言、白话与欧洲的拉丁文、方言进行有意的比附,并以乔叟创造英国文学、但丁创造意大利文学、路德创造德国文学为楷模,把当下中国发生的白话文运动,自比为中国版“文艺复兴”的一部分。胡适就是这样的典型,他断定文言和西方的拉丁文一样是已死的文字,白话跟各国的方言土语一样是活的文字,死的文字必须让位于活的文字,“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文字也。”胡适:《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第79页。胡适极力建构白话的出发点当然可圈可点,可是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他犯了包括事实错误、逻辑错谬等在内的多重错误。拉丁文并不等于文言,英德法文也并不等同于白话,二者乃是“不相类之事”,胡先骕非常详细地指出了这一点:“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德法、外国文也。……夫今日之英德意文固异于乔塞、路德、但丁时之英德意文也,则与中国之周秦古文也,与今日之文字较相若。而非希腊拉丁文与英德意文较之比也。”⑦也就是说,拉丁文对于各国通俗文来说,乃是一种外国文字,跟汉文化圈里汉字之于日韩文字颇有些相似,将拉丁文等同于汉字,这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不仅是一个事实错误,更是一个不可原谅的“淆乱视听”。梁启超也认为“将文言比欧洲的希腊文、拉丁文,将改用白话体比欧洲近世各国之创造国语文学,这话实在是夸张太甚,违反真相”,因为“希腊拉丁语和现在的英法德语,语法截然不同,字体亦异,安能不重新改造?譬如我中国人治佛学的,若使必要诵习梵文,且著作都用梵文写出,思想如何能普及,自然非用本国通行文字写他不可”。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九),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30-4931页。
那么,西方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才能跟中国的文白形成正确的对应呢?只能跟有关国家的古语今语相对应,比如英国通俗文只能对应于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古文,“绝不能拿现在英、法、德文,和古代希腊、拉丁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现代英国人,排斥希腊、拉丁,是应该的,是可能的,排斥《莎士比亚集》,不惟不应该,而且不可能。因为现代英文和《莎士比亚集》并没有根本不同,绝不能完全脱离了他,创成独立的一文体。我中国白话之与文言,正是此类。”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梁启超全集》(九),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30-4931页。所以人文主义者一致认定,“他们将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了解为拉丁与各国土语文学的关系则是一显然的错误”③余英时:《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第63-65页。这种错误之所以发生,跟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对欧洲语文的事实了解有关,也跟其强烈的宣传目的有关,“近人引用拉丁文与土语文学之例证来推广白话文运动的确收到了宣传的效果,但就事论事,却是出于对近代西方文学发展的曲解或误解。”③概括起来,这里的错误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将欧洲各国土语文学的兴起,简单地理解为代替拉丁文;第二,将中国的文言白话之争,简单地比附为拉丁与方言之争;第三,绝对化地将拉丁文与文言理解为“死的文学”,土语与白话文学理解为“活的文学”;第四,将拉丁文与方言土语、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关系绝对化了。
三、“废除汉字”能否成就“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五四时期,大众语文论者比其前任(如吴稚晖等)多了一条“废除汉字”理由,就是汉字是“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记载符号;要想废孔,必先废汉,这是新文化运动者的通用逻辑。钱玄同说:“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钱玄同文集》(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0页。他将此种剿灭汉文的行为称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对此意见,陈独秀极力附和,发誓一定要废除汉字这“腐毒思想之巢窟”,“中国文字,既难传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15日。废汉就等于搬掉了孔教之根基,就等于铲除了沾满腐朽思想病毒的载道之器, 表面看起来,这样的文化行为真可谓釜底抽薪,彻底而又彻底了。但实际上疑问多多,很多问题是似是而非的。
第一,废除古文甚至汉文,能不能确保废除腐毒思想?显然不能。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周作人,对于废汉的片面行为曾提出过委婉的批评。他说,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固然道出了某种事实;将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可是这并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具有“荒谬思想”的人,无论他用古文,还是白话文,无论是德文,还是世界语或其他什么文,“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仲密:《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11期,1919年3月2日。周作人此论的重点固然是强调“思想改革”的重要,但这里实际上也击中了废汉论者的要害。
第二,即使真的废除了汉字,能否根本废除中国文化?当然也不可能。任何一个民族一定有它的基因谱系,文字是其中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一系,废除了它的文字,也许可以改变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甚至可以部分地改变这个种族,但是不能从根本改变它的基因。“汉字革命”口号提出后,有人致信《新青年》,调侃地质问钱玄同:“我想钱先生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毁了,廓而清之。我想这却不是根本的办法。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的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任鸿隽:《致新青年》,见《钱玄同文集》(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读者的质疑,活活勾勒出了废汉论者意欲“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滑稽姿态。
第三,汉字文言果真如废汉论者所言一无是处吗?其实非也。大一统中华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字文言的稳固性。从时间维度上来说,前面言及的周秦汉唐之文,之所以能代代相续,“亘古如新”,古老的汉字实在立下了汗马功劳,“四千年之中,至少有三四种专门之文学,承学之士,虽白首不能尽通。今则历朝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沧桑屡易,而文字则亘古如新。”杜亚泉:《译者前言》,见[日]山木宪《中国文字之将来》,《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所以汉字担负了一种文化接续的重任,“言文分离”成就了一种文化的统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③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5、212页。而不是相反。
另外,汉字特有的“认形不认声”优点,不仅使其历经数次异族文字入侵而巍然不变,而且能够不断同化异族语文,这对保持中国文字的向心力,保存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可谓功莫大焉,“至吾国之文字,以认形故,不易随语言之推迁而嬗变,虽吾国家数为异族所征服,然吾国之语言,属单音之中国语系,与入主中国之民族之多音系语言大异,且虽偶用其字与辞,必以认形之字译其音,如巴图鲁、戈什哈之类,故文字语言不受外族之影响……彼入主与杂居之民族,但有舍弃其语言文字以同化于吾国,故吾国能保存数千年来文学上不断之习惯与体裁直至于今日。”③
为了最大效能地改变中国文化,新文化运动者使用了“废除汉字”这一釜底抽薪之招,其眼光之独到、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得不深为佩服。的确,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非比寻常。高本汉说:“中国不废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的或顽固的保守性。……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文化基础之时。”转引自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伊斯特林也说:“妨碍中国汉字过渡到字母-音素文字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一过渡会中断同中国多少世纪以来用汉字体现的古老文化的联系。”《伊斯特林论汉语和汉字》,《汉字文化》1994年第2期。两位汉学家的论说,揭示了照搬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可能,也可以看成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家的严重批评。废除汉字不仅不可能,而且不能够,汉字废除之日,也就是中国文化沦丧之日。
四、教育落后之责该不该由汉字来承担
废汉论者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把教育落后、文化落后乃至中国文化不能与现代文化并列的根源都统统罪于汉字。首先,汉字太过繁难,普通百姓不易掌握,即使掌握也太浪费时日,不利于教育普及。清末文改人士感叹:“尝念中国文字最为完备,亦最为繁难,……字典所收4万余字……士人读书,毕生不能尽识……童子束发入孰,欲尽其业,慧者亦须历十余年,……缘文字与语言各别,读书识字,兼习其文,记诵之功,多稽时日也。”蔡锡勇:《传音快字》,《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4页。钱玄同等悉数照搬,“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⑨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1卷7期汉字改革号,1922年。其次,汉字造成中国“自绝于世界文化”,致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格格不入,傅斯年列举的“最祸害”现代世界文化普及的两大元凶之一,就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这种语言文字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它使中国文化远远落后于世界文化:“不特妨害知识的普及,并且阻止文化的进取。”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初步谈》,《国语月刊》1卷7期汉字改革号,1922年。钱玄同也说:“汉字的罪恶……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⑨中西文化平等地位的建立首先必须从文字平等开始。钱玄同说:“中国文字,断非新时代所适用。”钱玄同:《答陶履恭论Esperanto》,《钱玄同文集》(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9-100页。如此推理,他们的结论是汉字不灭不足以立足于世界。
教育落后之责该不该由汉字来承担?“东方文化派”的回答是坚决否定的。杜亚泉曾如此反问:“吾国中若清文、若蒙文、若藏文,皆标音文字,何以吾国民之通识清文者亦不多见,而蒙藏之民,通文识字者亦不能多于行省之民也?”所以他得出结论,“国民通文识字者之少,由于教育之制度未备,不能归咎于文字”。杜亚泉:《译者前言》,见《中国文字之将来》,《东方杂志》第8卷第8号。也就是说,“汉字革命”论者错因为果,因果倒置,把教育落后之责加于语言文字之上,是一种不公平的责难。章太炎也有类似看法:“今者,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体,岂有优于中国哉?合音之字,视可识者徒识其音,固不能知其义,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栗,故俄人识字者其比例犹视中国为少……是知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章太炎:《驳中国宜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7页。在他们看来,仅仅凭此就对中西文字强分轩轾,结果不仅会颠倒黑白,而且会进一步掩盖中国教育的落后腐败,“或谓欧西各国言文合一,故学文字甚易而教育发达;我国文言分离,故学问之道苦,而教育亦受其障碍而不能普及。实则近年来文学之日衰,教育之日敝,皆司教育之职者之过。”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2页。据此,胡先骕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今日最要之急务,在提高国民程度,同时并介绍真正西洋文化以补吾之不足焉”,遗憾的是,“今新派不此之务,乃以文字就国民程度,造成一种支离破碎不全之文学,养成一种盲从浮薄鄙夷国学之心理”。唐庆增:《新文化运动平议》,《甲寅周刊》第1卷第34号。
上述四个方面的“常识性”错谬,有的是拘于时代识见的知识“硬伤”,有的是未加深思的信口开河,有的是倒因为果的张冠李戴,有的则是不择手段的宣传策略,个中透露的学术精神大可怀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普遍有一种被称为“意图伦理”的理论冲动,用王元化先生的话说,这种思维模式就是,“在认识论上先确定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页。为了引起足够的注意,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可以违背现代舆论规则制造一场“双簧戏”;为了造成宣传奇效,达到废除汉字的目的,当然也可以生出更多的“历史事实”。对于这种倾向,杜亚泉当时就有深刻批判。在跟《新青年》斗法不得不“下野”之后,杜氏曾借蒋梦麟《何谓新思想》的“附志”,总结了整个西方文化的“根柢”:“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想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与要的缘故,此是西洋现代文明之根柢,亦即西洋现代文明之病柢。”杜亚泉:《对蒋梦麟〈何谓新思想〉一文的附志》,《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年2月。以“现代文明”为法的五四“新青年”,当然无法免此“病柢”。如何避免此病?杜亚泉提出了一种救治方法,即“以理性率领情欲”的理性药石,根治“以情欲率领理性”的现代文明“病”。笔者以为,这种诊断是切中病害的,开出的处方也是对症下药的。如今,包括“汉字革命”在内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传统”,在继承这一现代遗产的时候,哪些应该舍弃,哪些应该保留,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合乎科学理性的理当发扬,违背科学理性的必须摒弃,对于孔教问题的评价应该如此,对于语文运动的臧否当然也应该如此。
作者单位:朱晓梅,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赵黎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静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