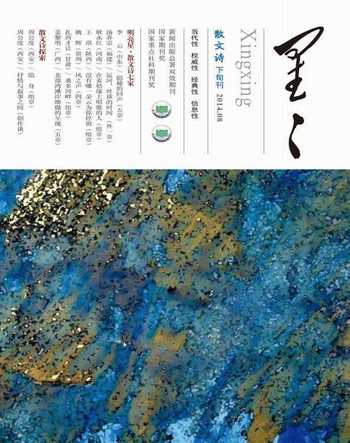母亲
2014-04-29周冬梅
周冬梅
印象中,母亲一直像个男人一样活着
——题记
她用外婆嫁接给她的勤劳,劈材、挑水、喂鸡、犁地、插秧、打谷。就连一直被男人牵着鼻子走的老水牛,也不再回头质疑母亲的身份。可以说,抬、担、挑、扛、打、割、磨、推,十八般武艺,母亲没有一样不精通。
很多的时候,她像门前自留地里命运悬乎的苦瓜,什么都装在心里,从不轻易说出。为了活着,她常常把黑夜熬成白天,把苦难熬成汗水和泪水,把自己熬成一罐毒药。很多时候,她一肩挑着过去,一肩挑着现实,两只脚在上坡路上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但她还是像大树一样站着。扛着鸟巢,扛着风雨,扛着一片天空,扛得不能再扛的时候,还是咬牙切齿地扛着。
很多时候,她翻晒着黄豆,也翻晒着光阴。事实上,她的硬伤比黄豆还多。很多时候,母亲握着镰刀的把柄,割断青黄不接的阳光,又把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斩草除根。很多时候,母亲用打铁匠的女儿这个身份,举起铁锤,像生活捶打她一样,捶打另一块铁,直到变形、服帖了为止。
弯腰、屈膝、鞠躬、叩首,这些重复的动词,指挥了母亲一生。可以说,这一生,母亲的汗水和泪水,比谷子的产量还高。无论怎么吹糠,见不到五斗米,无论怎么拔节,我也从没见过母亲超过100厘米高的幸福。
推磨的时候,母亲觉得自己就是一颗,被石磨软磨硬泡的豆子。在一个名叫日子的磨心里周旋,慢慢地,磨去棱角,磨去青春,磨损健康,磨掉生命。先磨圆,再磨成粉,灰飞烟灭的那种,零落成泥的那种。打水的时候,她会投下另一个自己,打探生活的深度和厚度。她的一生像水桶,被水欺压或者别离,谁也无法饮干她的痛苦。
偶尔没事,母亲也喜欢铺开大地这张稿纸写诗。写春暖花开,写炊烟掐不断的情感,写田埂踩不弯的思念。写着写着,玉米走成了七律或绝句,南瓜花形而上学,苦瓜越来越现实主义,红薯充当标点符号,麻雀踩着韵脚。写着写着,一首诗,被打磨得比镰刀还亮。写着写着,锄头成了母亲手里的笔,要么深入,要么浅出。写着写着,一首诗就老了,半截在外面,半截在土里,像极了一棵庄稼的模样。
不过,她还是保持着形而上学的姿势。但,她的头发,下垂着,她的乳房,下垂着,她的脚深深陷入泥沙俱下的日子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