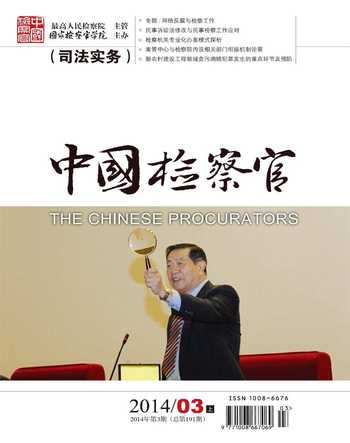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
2014-04-29韩大元
韩大元
自1954年宪法以来,在一院制下设置常设委员会的我国人大构造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地位问题一直颇受关注。虽然宪法文本一直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然而,大会的这种最高地位在现实中有时越来越难以体现,特别是在1982年宪法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后,全国人大构造在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背离。
首先,立法是全国人大最重要的职能,对立法权的配置也集中体现人大构造的特点。目前,全国人大立法权的规范与现实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冲突。1982年宪法后,常委会不仅享有了立法权,而且在立法数量日渐膨胀;常委会立法对现实的控制力日臻发达;常委会的立法界限渐趋模糊。其次,在决定权方面,同样存在着大会权力式微、常委会权力膨胀的现象。分别体现在组织建设的决定权、人事的任免权、财政预算的决定权三个方面。最后,在监督权方面,根据宪法的规定,人大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其他国家机关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然而,大会一年一次的短时间集会,其监督权在很大程度上被虚置,其监督的实效性有所削弱,而常委会的监督权出现超越宪法界限的现象。
目前,全国人大的内在构造——大会与常委会的关系已发生结构性的变革,由大会的实质最高地位逐渐转变为形式最高地位,由常委会对大会的从属性逐渐转变为常委会的主导性。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大会与常委会具有一体性。第二,宪法文本规定的权限不清,宪法解释虚置。第三,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组织建设有很大的差异,大会效率较低。
正确处理全国人大与常委会关系直接关系宪法体制的稳定与宪法实施的过程,需要从“依宪治国”的战略高度认识和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了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应当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完善人大制度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大会的职能,加强大会对常委会的制度性监督,保证全国人大的民主正当性与合法性。
(摘自《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3-17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