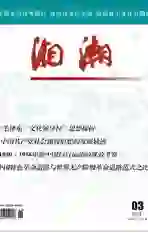我所知道江青迫害秘书的一些情况
2014-04-29杨银禄


阎长贵是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1968年1月江青诬陷他是“坐探”,把他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了7年多。我曾和阎长贵共事3个多月(共同任江青的机要秘书),他出事后,我接着任江青的第二任机要秘书。江青诬陷、关押阎长贵的情况,我亲眼所见。
成为江青秘书后与阎长贵相遇
1967年1月6日,我从中央警卫团调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工作,主要任务是收发、整理、保管文件资料,值班,接打电话,会议准备等工作。10月3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找我谈话,说:“你在主任值班室的工作干得不错,领会领导的意图较快,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你的家庭成份、出身和社会关系都是好的,政治思想表现也是好的,群众关系融洽,經组织考察研究,决定调你去江青同志那里工作,任务是收发和保管文件,也就是担任江青同志的机要秘书。”他接着说:“江青同志现在的秘书叫阎长贵,这个同志有文化,是个大学生,会写文章,是个笔杆子,人很老实,厚道,组织纪律性强。江青同志想把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去工作,发挥他的特长,所以叫你去接替他。请你今天准备一下,明天就到钓鱼台11号楼去报到,我亲自送你去,你明天上午10点钟到我这里来。”
我对汪东兴找我谈话及内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那时,我对江青的脾气、性格、为人等一概不知,只是认为她政治地位很高、名声很大,她的秘书工作很重要,不容易做好,像我这样资质极平凡的人到她那里做秘书工作,实在不可想象,于是忙推脱说:“我文化水平低,能力差,不能胜任如此重要的工作,干不好对不起组织。”汪东兴看我不想去,耐心地说:“杨银禄同志,你知道吗?你是从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中精心挑选的,调你给江青同志当秘书的事,我是报告了主席的,主席明确表示:调中央警卫团的同志干秘书工作,当江青的秘书,我信得过,我放心。况且,我把你的情况、介绍材料和照片,也已经送江青同志看过,她表示同意你当她的秘书。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不就为难了吗?”他还承诺说:“你去试一试,积极工作,认真负责,尽快适应那里的环境,适应工作,干好了就干下去,实在不行的话,再回警卫团。”
经过汪东兴这样耐心诚恳地说服、劝导,我想通了,不应该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不应该为难领导,组织上如此信任、器重我,不要不识抬举了。况且,按照组织原则,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我是个军人,服从是天职,按当时流行的说法,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样我就同意了。
我又说:“我没有做过秘书工作,特别是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心中没有底、发怵,请汪主任多帮助。”汪东兴说:“对于没有做过的工作,发怵是可以理解的,等干了一个阶段,熟了就好了,熟能生巧嘛。”
10月4日下午1时左右,我由汪东兴陪同,来到国宾馆——钓鱼台11号楼。进楼后,汪东兴带着我径直来到阎长贵的办公室。看样子,阎长贵是刚刚起床,被子还没有来得及叠。他揉了揉多日没有休息好的疲倦的眼睛,有礼貌地说:“汪主任来了,请坐。”
汪东兴指着我对阎长贵说:“这就是杨银禄同志,今天我把他带来了,请你首先把这里的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及需要他做的工作向他好好介绍一下。江青同志起床以后,请你把杨银禄来这里工作的事报告她,有什么事,你再打电话给我。从今天起,你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你要抓紧时间带他,使他尽快熟悉情况,熟悉工作。”汪东兴说完后就走了。
阎长贵当时的年龄是30岁,由于操劳过度,用脑过度,工作劳累,长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看上去好像40左右的人。他个子不太高,腰也不太直,面色憔悴,双眼布满了血丝,一副近视眼镜挂在鼻梁上。他强打精神,用嘶哑的声音对我说:“已经知道你的大名了,欢迎你来这里工作,我早就盼着你来了,你来了我很高兴。”我说:“你的情况汪主任已经向我介绍了,你是大学毕业生,我是个初中生,你是我的老师,我要向你虚心学习,你在这里工作有了经验,请你好好教我、带我,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请你批评教育。”他说:“这没有说的,请放心好了,互相学习,互相学习。”他介绍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特别怕声音,怕风,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咱们在楼里说话、走路、开关门窗等各种动作都要特别轻,千万要注意;因为她怕见生人,所以在短时间内你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了,你也不能跑,在原地站着,不要紧张,一跑就坏了。她不跟你说话,你别主动跟她说话,今天我不跟你说得太深了,以后你慢慢体会吧。你先在我这里熟悉情况,和我一起整理文件,等她主动要求见你时,我再带你去见她。”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阎长贵耐心地教我如何给江青挑选文件资料,怎样签收,怎样分类登记,怎样发送,怎样保管文件资料。他讲得很细,教得很认真,我也虚心学习。他像一位兄长教一位小弟弟,毫无保留,十分耐心。从第一天起,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有知识,有修养,对组织忠诚,对同志诚恳,对工作认真负责,生活艰苦朴素,作风谦虚谨慎,性格内向,不善言谈。那时我就暗自下了决心,在我们相处的时间里好好向他学习,以利于今后做人、做事。
我和阎长贵相处了3个月零5天。在这段时间里,我按照他教我的工作方法,试着签收、挑选、分类登记、发送、保管文件资料。一开始,每做完一道工序都请他过过目,检查检查有什么差错?过了大约两周的时间,他对我的工作基本上满意了,放心了,大多数工序他就不过目了,只对江青必看的文件夹内的文件看看,把把关。因为江青还没有正式和我见面,所以江青打铃叫秘书,还是由阎长贵去。他平时谨言慎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除了谈工作,基本上没有聊过天,拉过家常,更没有谈论过江青的脾气性格,是是非非,他即使受了什么委屈也没有在我面前透露半点不满情绪。他容人、容事、容言,我对他非常佩服。
1968年1月3日晚上,我接到“父病故速归”的加急电报。噩耗传来,我悲恸万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阎长贵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建议我请假回去,但此时江青已睡觉,他立即打电话请示汪东兴。当时汪东兴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东兴批准我回去料理老人的丧事。阎长贵派人替我买好火车票,第二天,即4日一早又派车把我送到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我就这样急急忙忙地离开北京回到了老家——河北定县,回家当日下午就将父亲掩埋了。父亲的去世,使我极度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由于劳累、悲伤,火气太盛,我患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本想掩埋了父亲就立即回北京,可是,我病得不能动弹,只能躺在土炕上养病。
8日,汪东兴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干部科的干事毛尚元,到我的老家接我回北京,并带去汪东兴用毛笔写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杨银禄同志,你的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马上回京。”当时,我上吐下泻还未止住,高烧未退,身体十分虚弱,老母亲也不愿意叫我马上回京,想叫我再守她几天,我和毛尚元耐心地做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那时地方较乱,毛尚元干事怕出事,从三十八军要了一部吉普车,还有一位干部,一位战士持枪护卫,把我们送到定县火车站,迅速回到了北京。毛尚元干事把我从北京站直接送到汪东兴的住地——中南海南楼(南船坞)。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见我发烧,昏迷不醒,立即找来医生给我打针、服药,经过医生的有效治疗,我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轻松多了,睁开眼一看,汪东兴坐在我的身边。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父亲的后事处理完了吧?按照常理说,你父亲刚刚去世,应该让你在家里休息几天,为什么叫你马上回来呢?因为关锋出问题,被隔离审查了,还有别的情况,江青同志怀疑她身边有不可靠的人,所以才叫你立即回北京,这是她的意思,你如果觉得身体好些了就赶快回钓鱼台工作,她现在急切地等待你回去呢!”
我那时年纪轻,没有斗争经验,头脑简单,又不知道关锋和阎长贵原来是一个单位的,更不知道他们是师生关系,根本没有想到江青怀疑的那个不可靠的人竟是我几个月来朝夕相处,并且很要好的阎长贵,至于还有别的什么情况,我没有多想。
我于8日深夜回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已经上床休息。阎长贵见到我以后,问寒问暖,楼里的其他同志,如厨师、警卫员、护士、司机、门卫兼做服务工作的都围过来安慰我,劝我节哀。大家都表情如常,没有任何异样,谁都没有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之兆。
借“出差”之名把閻长贵关押起来
9日,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完毕,吃完早饭,到办公室看文件,阎长贵带我去见江青,他说:“杨银禄同志从老家回来了。”江青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那天,江青没有在办公室继续看文件,要车到外边去了。究竟到哪里去了,我和阎长贵都不知道,后来才听警卫员孙占龙说,江青到中南海丰泽园暂时躲了起来,怕阎长贵“伤害”她。
江青走了以后,隔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陈伯达、姚文元来到11号楼大会客厅,找阎长贵和我谈话。陈伯达说:“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需要阎长贵出一次差,秘书工作暂时由杨银禄同志接过来。由于时间紧迫,交接工作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还要交接清楚,不能出任何差错。”姚文元接着说:“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了,不需要我解释什么了,抓紧时间交接文件,我们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楼)等你们交接工作。”我和阎长贵表示,一定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办。
他们走了以后,阎长贵带我到二楼江青的办公室清理登记文件,他读文件号码,我登记,工作态度还和平日一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生怕搞乱了,将来说不清。江青办公室的文件不算多,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登记完了。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办公室继续清理登记文件。大概还没有登记到十分之一,跟随江青出去的警卫孙占龙打电话给我,他说:“江青同志叫我问一下文件交接完了没有?她叫你们抓紧时间,快一点交接,越快越好。”我说:“我们尽量抓紧时间。”我不解地问:“老阎出差还回来,交接文件干什么?多麻烦!”孙占龙批评说:“咱们不是有一条规矩嘛,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叫你们交接就交接,叫你们快点就快点,啰嗦什么?”又过了半个小时,孙占龙又来电话催促说:“江青同志叫我再次催你们快点交接,她说她等得不耐烦了。”第二次的催促我才觉得可能出什么事了,“老阎怎么啦?”孙占龙第三次来电话讲得就更明白了,我在电话里听得出他紧张得喘着粗气,他说:“江青同志说你们别交接了,她说阎长贵不离开11号楼,她不能回去。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你可看住阎长贵,别叫他跑了!”我心里很纳闷,很别扭,又不能说……
不一会陈伯达、汪东兴来了,找阎长贵谈话。时间不长,阎长贵回到办公室拿了牙具和一些东西,汪东兴和警卫团的两名战士把阎长贵送到钓鱼台西北门内20楼警卫连部,暂时关押在那里。
这就是阎长贵的“出差”。我甚感愕然,全身冒冷汗!
“这是戚本禹、阎长贵玩的圈套”
1968年1月9日,阎长贵不明不白地“出差”了,江青再打铃叫秘书只有我去了,那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害怕极了。1月10日下午2时,江青起床以后,打铃叫秘书。我听到铃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她头也没抬就说:“我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保险柜,柜子里有一个档(一格)文件,等我明天休息的时候,你给我取回来,那些文件很重要,不能搞丢了,也不能搞乱了。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我回答:“江青同志,我记住了!”
1月11日,江青正在吃早饭,打铃叫我,我听到铃声,立即走到她的饭厅,见到她女儿李讷坐在饭桌的南边,我没有注意看江青的表情,就小声问道:“江青同志,您叫我?是不是让我在您午休的时候去中南海把那些文件取回来?”我站在旁边大约等了一分钟多的时间,也没有听到她说话。这时,我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不说话呢?就注意了一下她的表情,发现她的下巴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咬牙切齿地喊道:“谁叫你取文件?我问你,你前几天回老家干什么去了?”我说:“我父亲去世了,经汪主任同意,回去料理我父亲的丧事。”她听了我的回答,喊叫的声音更大了,吼道:“你父亲去世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他们好干坏事,是戚本禹、阎长贵玩的圈套,你老实交代清楚!”我忙解释:“别人做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我父亲真的是去世了,您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的毛尚元同志调查,是他把我从老家接回来的。我父亲是真的去世还是假去世,他是清楚的。”江青听了我的解释,认为有失她的威严,恼羞成怒,气极败坏地叫道:“你在撒谎!我现在就派人到你老家把坟墓扒开,看看尸体是不是你父亲,如果不是,看你作何解释,如果不是你父亲,你就犯了欺君之罪!”她一边撒泼一边站起来,把一双筷子狠狠摔在桌子上,筷子反弹起来落在地毯上,她双手叉在腰间,用更高的声音狂叫:“你刚刚来我这里,就敢跟我顶嘴,以后还了得?你给我立即滚出去!”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难过极了,气愤极了,心想:“身在高位的江青,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父亲去世,非但不表示任何同情,不予以安慰,还扬言派人扒坟验尸,来她这里工作是走错了路,进错了门,认错了人,我真后悔。”缓了半个小时以后,我打电话给汪东兴,要求回中央警卫团,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待了。汪东兴很快来到11号楼,他这样向我做思想工作:“批评是动力嘛,要经得起批评。看样子她的气是撒到你的身上了,实际上不是对着你的,这叫迁怒吧,她不但怀疑是戚本禹和阎长贵把你支走,还怀疑我把你支走。算了算了,在她面前有什么道理可讲呢。江青怀疑是戚本禹、阎长贵把你支走的,作为抓阎长贵的一个理由,这是个不成理由的理由。你回老家办丧事是我批准的嘛。你今后说话、办事,要十分谨慎,在工作上千万不要出差错。要把别人的教训当成自己的教训,别人吃了堑,自己要长智。”他沉思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不说那么多了,你在这里再工作一段时间,再试一试,如果实在不行,江青同志明确表示不再用你了,你再回中央警卫团。”汪东兴这样一说,我基本上明白了,理解了,难过的心情也平和多了。
江青解释为什么要抓阎长贵
为什么要抓阎长贵?江青跟我这样说:“关锋原来是《红旗》杂志社的,阎长贵也是《红旗》杂志社的,关锋是一个野心家,阎长贵肯定是关锋的小爪牙,抓阎长贵是理所当然的。据说阎长贵和关锋是师生关系,这还得了?一日从师,终生为父呀!他知道关锋的问题是不会少的,他能忍心主动揭发他老师的问题?我们把他关起来,不愁他不交代问题,到那时,关锋的所有问题,将大白于天下。”当她谈到阎长贵和戚本禹的关系时,又说:“阎长贵的关系多,且复杂得很,他不但和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和戚本禹的关系更不一般,他刚来我这里时,竟然听戚本禹的吩咐。人各有其主嘛,可阎长贵听他的,不听我的,搞颠倒了嘛。有一部电影叫做《一仆二主》,你们要看一看(她叫我们与她一起看了这部电影)。党内斗争很复杂,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阎长贵知道戚本禹的问题太多了,也知道的事太多了。”
江青后来还跟我说:“我会相面。”她说:“我身边经常有坐探和钉子。阎长贵就是关锋、戚本禹派来的坐探、安插的钉子。……发觉了坐探需及时清理掉,发现了钉子就马上拔掉,心慈手软是搞不了政治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嘛!小杨,我告诉你,你在我这里工作,就得和我一条心,绝对对我不许三心二意的。我叫你办的事,你要专心致志地办,并且办好。办好了是本分,办不好是失职,我要拿你是问。不是我要你办的事,你绝对不能办,你不能当别人的枪使用。否则,你没有好下场!”江青说得出,做得到。她除了诬蔑阎长贵是“坐探”外,后来又说她的护士周淑英是林彪、邱会作、叶群派来的“坐探”,她的护士赵柳恩是黄永胜派来的“坐探”,等等。1973年她还说我是挑拨她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关系的“反革命”,要不是毛主席、周总理、汪东兴保护我,我和阎长贵的下场是一样的。
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不断地把秘书当“钉子”拔掉
阎长贵“出差”后不久的某一天,叶群给我打电话说:“我想去看看江青同志,是林彪同志叫我去看江青同志的,如果江青同志有时间,精神好的话,我现在就去。”我把叶群来电话的内容报告江青时,她痛快地说:“请叶群同志现在就来。”半个小时以后,叶群来了,把她引进到二层江青的办公室,我就马上出来了。
她们谈的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但叶群下楼后,把我叫到大客厅跟我谈话。她说:“杨秘书,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冲锋陷阵的,是立了大功的,可是,有的人恨她,要陷害她,其中就有‘王、关、戚,关锋和戚本禹把阎长贵安插在江青同志身边,阎给他们搜集材料,通风报信,妄图制造事端。江青同志政治敏感性很强,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也早就想把姓阎的端出来,因为时机未到,怕打草惊蛇,现在时机到了,所以才把他端出来,这叫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可以说是一锅端了,除恶务尽嘛。从江青身边拔掉了一颗钉子,林彪同志知道后,很高兴。杨秘书呀,你的工作很重要,责任很大,很光荣。你是部队派来的,阶级立场要坚定,为江青同志服务,就是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不要辜负组织的信任。”我向葉群表示,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叶群为什么跟我谈话?我和她没有隶属关系。我想不是叶群向江青表忠心,就是受了江青的委托。
1973年6月11日是我落难的日子。我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赶出钓鱼台以后的当天下午,江青提出让10号楼值班室值班的刘真担任她的机要秘书。汪东兴根据江青的意见,从中南海来到10号楼找刘真谈话。汪东兴对刘真说:“江青同志让你当她的秘书。”刘真一听吓了一跳,因为他亲眼看到江青的前两任秘书都被她毫无根据地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赶走了,阎长贵还被她关进了监狱,所以他表示坚决不干。他急忙说:“我不行,我可干不了,绝对不行,请汪主任另选别人吧!”当时汪东兴很为难,极力说服刘真。但是,刘真还是说干不了,执意不干。这时,汪东兴不得不下命令了:“刘真同志,你说行得干,说不行也得干,我不要求你思想服从,但我要求你组织服从,不干不行啊!”刘真是一位训练有素、忠诚老实、服从命令、通情达理的好同志,非常理解领导的心情,虽然内心不同意,但还是组织上服从了。他就是江青的第三任秘书。
疑则不用,用则不疑,这是作为领导人所具备的起码素质。但是,江青这个人疑心特别大,与平常人不一样。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江青就污蔑刘真偷看她的文件。同时,江青对刘真当时结婚一事非常不满,气极败坏地说:“在这关键时刻,正当我集中火力向林彪、孔老二猛烈开炮的时候,你刘真竟然结婚,拱掉了我一个炮腿!”她一气之下,把刘真赶到了农场劳动。
刘真走后,组织上又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挑选了刘玉庭去当江青的秘书。刘玉庭也是坚决不干。但是,他认为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同意了。他就是江青的第四任秘书。
后来,江青又污蔑刘玉庭把她的文件偷出去让人家拍照了。她命令工作人员立即开会,妄图整刘玉庭,遭到全体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她还威胁说,她有许多文件找不到了,其中还有毛主席给她的亲笔信。还说此事王振荣也有责任(因为王振荣代替干了几天收发工作),如果找不到这些文件,要一起算账(后来这些文件都在她自己保存的保密柜里找到了)。她还硬逼着刘玉庭为她写整新华社记者杜修贤的假证明。遭到拒绝后,她大骂刘玉庭出卖了她,为此,停了刘玉庭20天工作责令他写检查。有一天,刘玉庭家因为邻居的下水道堵塞进水了,他利用江青睡觉的时间赶回家中进行了处理。当刘玉庭急急忙忙赶回去的时候,江青声色俱厉地质问:“你出去干什么去了?”刘玉庭如实地回答了她,她不但不安慰几句,还大声伤感情地说:“我还以为你家死了人呢!”
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而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江青的第三任和第四任秘书刘真、刘玉庭,可能遭遇与我和阎长贵同样的厄运,因为我太了解江青这个人了。
江青和林彪、叶群这类“大人物”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江青迫害的工作人员的这些“小人物”也都早已平了反。江青在“文革”中,动辄怀疑这个工作人员是“坐探”,说那个工作人员是“反革命”,随心所欲,信口雌黄。我作为担任过江青五六年(1967年10月~1973年6月)机要秘书并且担任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党支部书记的人,负责地讲,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苦出身,共产党员,对党、对社会主义有深厚感情,工作勤勤恳恳、细致周到、任劳任怨。一句话,不论他们的思想,还是行为,都是无可指责的。历史无情,历史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