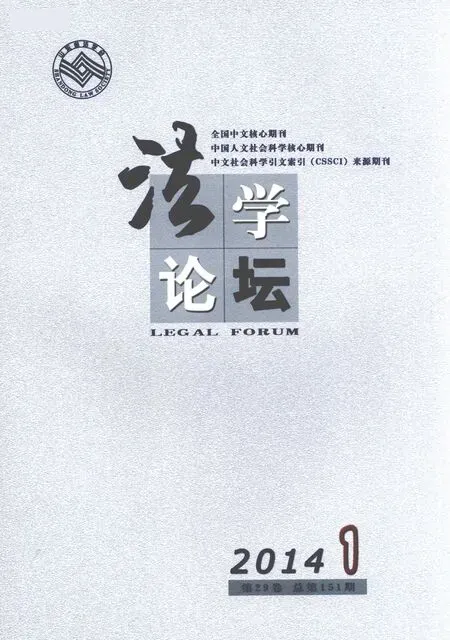论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的应然归属
2014-04-18杨显滨
杨显滨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240)
【学术视点】
论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的应然归属
杨显滨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240)
法律本质作为法律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一直倍受我国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不但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但时至今日仍无定论,主要有阶级论、社会论和无本质论三种学说。前两种学说,对法律本质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仅击中了法律本质问题的一个侧面,不能有效地反映法律的应然本质。后一种倾向于对不确定性的追求,不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当扬弃。而公平正义的特质反映了法律诸多属性的共同性,决定着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彰显司法公信力,增强公众对国家强制力的认同感,最终实现良法之治,达到法律的应然状态。因此,应当把公平正义作为当代中国法律的本质。
法律本质;当代中国;公平正义
一、法律本质探究之基本问题考察
(一)法律本质探究之价值审视
自从法律产生以来,人类就开始了对法律本质的探究,虽然同时代的法律也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但人们始终相信其具有某种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就是法律的本质。人们之所以认为法律具有这种共同性本质,原因在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都是对社会矛盾的直观反映,也是时代的一般要求。同时,每一个时代的法律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特定的,决定着作为法律的上层建筑,那么,这就决定着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其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存在多大差异,其必然存在一定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体现在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反映时代精神的、具有共同性的法律观点,这种法律观点就形成了该时代的法律本质。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律本质体现并反映着时代的法律精神,也是该时代法律的灵魂,对了解和研究一个时代的法律至关重要,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法律不同类型进行分类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参见谢程鹏:《法律本质论的历史发展》,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可见,法律本质是一个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重要法律问题,也是法律研究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吉林大学第一任法学院院长张光博教授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法的本质问题是法学研究的逻辑开端。特别是法学专业的课堂教学中需要尽快作出定格的解释,以免使青年学生长时间莫衷一是。”*张光博:《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导法学沿着正确道路向前发展》,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也就是说,如果想研究法律问题,必须先了解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很好地从事法学研究,因为它是法学研究的起点问题。无独有偶,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张文显教授也有过相关的阐述,他认为:“法的本质问题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变迁而不断被重新思考与解答的古老话题,是法学理论中的基石性、原点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如何解析法的概念、法的作用、法的起源、法的更替与继承、法的未来、法的消亡等问题,进而涉及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法的本质和作用等问题。对法的本质问题的不同回答,历来也是划分不同法学流派的基本标准。”*张文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不难看出,张文显教授对法律本质问题的阐述更加详细,强调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很好地回答法律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就不能合理地解答何为法的作用、法的概念、法的起源、法的消亡、法的未来、法的更替与继承等问题。此外,法律本质是划分不同流派的标尺,对法律本质的不同认识,决定着不同流派的归属。由此可见,对当代中国法律本质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探讨和研究至关重要,这关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贯彻和实施,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参见彭中礼:《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研究重述》,载《时代法学》2009年第4期。
(二)法律本质探究之现实困境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法律本质如此重要,为什么多年来法学界并没有对法律本质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理由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复杂性,且变化多端,对其本质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可能是完全或彻底的真。同理,对于法律本质的探索也是一样,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持续的、充满荆棘的漫长过程。更甚的是,法律作为人造的对象,由于受到人的理性的限制,增加了认识其本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圣·奥古斯丁曾经用“什么是时间?如果无人问我,我知道。而如果我要对一个问者解释时间,我不知道”的例子来阐述解释法律本质、界定其内涵是多么的不容易。简言之,我们通常对一些事物的感知是清晰的,但如果真正地让我们对其进行解释或阐述却显得尤为困难,法律本质亦是如此,看似简单,但很难定格。*参见谢晖:《法律本质与法学家的追求》,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基于此,有人认为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人类探求法律本质并得出一个定格的结论是不可能的。虽然每个时代对法律本质的认识有不同的法律观点,但每一种观点都只是探求到了法律本质这座冰山的一角,无法看到其全貌。即便是某个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法律本质观,也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被超越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是永远的霸主,立于不败之地。*参见赵雪纲:《关于法律本质的认识论探讨》,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忽略了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共同性,只要共同性的存在是客观的,法律本质在客观上也必然存在。特别是在同一时代,由于其经济基础是特定的,那么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法律上层建筑必然具有共同性。因此,虽然探知法律本质的过程极其漫长和复杂,且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其公平正义的共同性决定了对法律本质进行定格是可能的。
二、法律本质探究之应然路径
(一)透过法律现象揭示法律本质
所谓法律现象是对法律本质的反映,虽然现象有真象和假象之分,却都是对法律本质的反映。法律本质存在于法律现象之中,通过一个个的法律现象表现出来,为我们所感知。透过法律现象我们可以揭示法律本质,从而把法律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因此,谢晖教授认为,法律现象是法律这一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外在表现,是法律各种外部联系的总和,具有表象性和直观性的特点。*参见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辩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可以这样说,只要从法律现象出发,通过对法律现象特征的认识,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窥探法律的本质。可见,把握法律现象是定格法律本质的基本方法之一,应当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二)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法律本质
法律本质虽然不像法律现象那样变化多端,既有多种存在形式,又有真象和假象之分;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作为客观事物的一种,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那么它的本质也应该随着法律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必然受到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建筑的影响,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作为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总和的经济基础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是一个活跃的、革命的因素,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受生产力制约的经济基础也是不断运动发展的,与此相适应,作为法律的上层建筑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反应,新的法律本质因素不断产生,旧的法律本质因素不断灭亡,新的法律本质不断取代旧的法律本质。此外,上层建筑的种类繁多,除了法律之外,还有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组织、设施等,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家族中的一员,不可能完全脱离其他成员而存在,彼此之间必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他成员的变化发展必然带动或促进法律的变化发展,法律本质也必然作出相应的调整。所以说,法律本质不是永恒的,永远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参见季金华:《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的研究范式》,载《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三)用联系观把握法律本质
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没有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法律也概莫能外。法律往往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法律的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受到国家的影响,法律本质必然带有国家的某种属性,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为统治阶级服务。同时,法律本质存在于法律现象之中,法律现象是反应法律本质的现象,只有透过法律现象才能把握法律的本质,那么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状况,也会影响我们对法律本质的把握。另外,一些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也会影响我们对法律现象的认识,因而在揭示法律本质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些基础性因素对法律现象的影响。因此,在探求法律本质的漫漫征途中,我们要知道联系是普遍和客观存在的,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注意把握各种因果联系及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用联系和整体性的观点整体地、系统地、综合地看待问题,不能用孤立、片面的观点看待问题,从而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视角,力求概览法律本质的全貌,否则会以偏概全,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歪曲法律的本质。理由在于,无论在法律本质的哪个视角,都只能窥到法律本质的一个角落,不能总览全局,最终会对法律本质进行不合理地定格,导致极端化倾向,不能自拔,不利于人们认识、理解和把握法律的本质。*参见王章来、王天成:《法律本质正解》,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1期。
(四)通过媒质作用研究法律本质
法律通常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处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如果想要揭示法律的本质,必须理清法律与政治国家的相互作用关系和法律与市民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使政治国家通过法律实现与市民社会的互动,把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搜集、整理和提炼,形成政治国家的意志,然后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立法,最终上升为法律意志。如果法律能够很好地起到媒质作用,架起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桥梁,把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传递给政治国家,政治国家经过权衡进行回应并上升为政治国家的意志,进而诉诸立法,提升到法律层面,对市民社会的法权进行有效地保护,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良好互动,这时法律的本质就是公众意志的体现,真正地达到了公平、正义的理想状态。总而言之,把握好法律的媒质作用,掌握好其运行机制,可以比较容易地揭示法律的内在规律,透视法律的本质。*参见季金华:《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的研究范式》,载《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三、当代中国现有法律本质理论解读
(一)阶级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阐述是针对资产阶级法律而言的,虽然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对于我们了解和揭示各种类型的法律本质都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一切类型的法律都应当具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我国也不例外。*参见吴祖谋、李双元:《法学概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阶级论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法律应当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为了调整社会关系才出现的。在阶级社会里,充满了阶级矛盾和斗争,也许这时有些法律带有一定的阶级性,甚至阶级味比较浓,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带有阶级性,有的阶级性强一点,有的弱一些,有的甚至没有阶级性。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革,阶级斗争早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法律的阶级性早已褪色或即将褪色,只有很少一部分法律规范还带有阶级色彩,总有一天阶级性会完全从我国法律中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紧紧抓住我国法律的阶级性不放,固守我国法律本质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那么,就会歪曲法律的本质,造成人们对法律的误解,不利于法律的贯彻和实施,使法律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大众,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参见刘升平:《近年来法理学研究述评》,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1期。
(二)社会论
社会论认为法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坚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回顾法的历史发展过程,法律的职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最开始的社会公共职能为主转变到阶级统治职能为主,再转变到社会公共职能为主。因此,他们坚持法律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客观需要和客观规律的反应,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不是由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决定的,也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和国家没有直接关系。即便在充满阶级斗争的阶级社会里,法的社会公共职能同样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统治阶级需要借助法律的社会公共职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以达到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目的,也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适当的借口。总而言之,他们主张法律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法律是社会的产物,贯彻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参见郑成良、宾凯:《法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6页。客观来说,社会论比阶级论更有说服力。但法律的属性有多种,比如阶级性、社会性、规范性、强制性、确定性等等,社会性只是其中的一种属性,和我们讨论的法律的本质属性不是一回事。它不是所有法律属性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属性,而是一个贯穿于始终的、起统领作用的、具有共同性的属性。如果轻率地认为社会性就是法律的本质属性,难免过于偏激,等于永远把法律本质埋藏在千里冰层之下,永无出头之日,我们对法律本质的探寻就会变成幻想,法律也就无进步可言。
(三)无本质论
无本质论不承认法律本质的存在,表明人们对不确定性追求的渴望,是与阶级论和社会论完全对立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国内最早是由朱苏力教授在1995年提出来的,当时引起法学界的广泛争论,批评之声络绎不绝。他认为“法律”之所以给人一种共性的感觉,原因不在于“法律”具有一种共同的本质属性,而是为了使用的方便而使其具有“家族相似”性,是人为的结果,其实它们所指向的对象未必相同。且“法律”可能指的成文法典、习惯法、判例法、民间法等等,本质上不是一回事,只不过都打上了法律的烙印,给人造成一种误解,既然都是法律,就应当具有共同的本质。事实上,只是名字相同而已,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客观存在的本质属性,只不过是使用法律的人把“本质”这个词强加到“法律”这个对象中来的。因此,朱苏力教授认为,“法律”的“本质”是人造的,应当抛弃,把人们从形而上学的“基本主义”的桎酷中解放出来,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虚构的东西而自寻烦恼。*参见朱苏力:《法律的本质:一个虚构的神话》,载《法学》1998年第1期。从客观上来讲,朱苏力教授的观点代表了部分学者的心声,其合理性的一面毋容置疑。但法律既然存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其固有的内在规律,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因为对确定性的追求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就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我们有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因此,我国现有法律应当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只有这样我们的法律才能稳定,才能具有确定性,对我们的行为才能具有预测性和指导性,才能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大局服务。
(四)综合评述
综上所述,法律本质问题是法学研究的重点也是法学研究的难点,对此西方各个法学流派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一直争论不休,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因为他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探求法律本质,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那么,各个流派对法律本质的定格存在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在国内,我国法学界对此已经形成了几种主要观点,包括阶级论、社会论和无本质论,其中,阶级论占据主导地位,也是我国法学界比较认同的一种观点。笔者认为,无论是阶级论还是社会论,都仅仅是法律的一种属性,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法律本质,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法律本质也会有所差异。即使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永恒的、不变的,它们也只不过代表了法律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性,却不是法律的根本特性。理由在于,它们不是对法律的各种属性的提炼和升华,没有共同性,不能概览法律的全貌,难免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至于无本质论,倾向于对不确定性的价值追求,忽略了法律的稳定性,需要给人们提供确定性的指引,使人们能够预测到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可以想象,如果一味追求法律的不确定性,法律条文本身及对我们的教育、指导和预测作用也就变得虚无缥缈,不可捉摸,这样法律也就失去应有的含义,我们就不能再称之为法律了。
四、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的应然归属——公平正义
(一)公平正义——法律其他属性的价值统摄
当代中国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的阶级性已黯然失色,不再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即使其法律仍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其宗旨和价值取向也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法律作为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至少应该在权利义务的分配上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就社会性而言,法律的确是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并最终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但这仅仅是一个表象,是法律本质属性的一个外在反映,正是因为要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在调节的过程中,如果想取得人们满意的效果,必须体现公平正义,让各个利益主体和义务主体心服口服,这样的法律才是“良法”,才能得到较好的贯彻和实施。无本质论虽然看起来有点荒唐,主张追求法律的不确定性,但其仍然要秉持一种法律理念,那种理念仍然应当包括公平正义的内容,且公平正义在这种理念中应当起主导的、决定性作用。无论一个社会的法律多么可行,法律的设计多么巧妙,逻辑多么紧密,一旦失去了公平正义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因此,公平正义才是法律的本质属性,是各种法律现象的真正归属,对法律的其他属性起统领作用,即法律的本质归属应当是公平正义。
(二)如影随形——法律与公平正义的历史渊源
公平正义也有人称之为正当、合理、合情、公正,它是人类对法律的一种追求,也是人类期待法律应有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就理想状态而言,“良法”应当具有正义性,否则就是“恶法”。在立法阶段,我们认为法律是对相关利益进行第一次分配,要满足和符合公平正义的条件。同样,在法的实施阶段,作为对相关利益进行的第二次分配,也要满足和符合公平正义的条件。*参见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人民比较喜欢的一种说法是:‘法即是公平、正义。’这一点,无论在古今中外的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背背景的人群之中,都是一种长久而热切的期盼。而世界史上,第一次表达了这种人类普遍心声的人,据我所知,却不是什么法学家,而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但他所留下的、极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法律正义’的演讲,其声音,却穿越了数千年的时空,至今仿佛回响在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下。”*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记——从古埃及到美利坚》,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不难看出,早在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就有了法律的本质是公平和正义的呼声,且与当代中国追求公平、公正的法治理念是一致的。可见,尽管古老的西方社会也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法律也曾经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镇压人民的工具,但法律始终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从未改变过,公平正义始终是法律的根本属性。*参见白向勇:《关于“法律本质”概念的中西方比较》,载《华商》2008年第15期。
西方法学家曾经给法律下过很多定义,比如“法律就是公平正义”、“法律是一种良好的秩序”、“法律是一种公平正义的习惯”等等,但不约而同地把公平正义与法律紧紧相连,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他们探知了法律的本质属性就是公平正义。希腊人认为,法律是公众的合意,是由人民制定的、正义的和有理性的,不是因为它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也不是因为它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是因为它与公平正义具有相同的品质,反映了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呼声。柏拉图宣称,人的灵魂之中,有好的部分,也有坏的部分,如果好的部分占主导地位,人就处于正义状态;反之,则处于非正义状态,人就是自己的奴隶,失去了应有的理智。这时就需要法律进行调整,使人回到正义的状态,由此可见,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也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6-161页。亚里士多德继承柏拉图的正义观点,他认为,法律不是对别人的压迫和奴役,而是当不公平、不正义出现时,来“拯救”世人的。因此,法律的本质在于公平正义,而不在于压迫与奴役。*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9页。罗马人进一步发扬了希腊人的正义观,西塞罗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坚持,判断法律的标准不是看它是否出自国家的制定和认可,也不是看它是否来自公众的制度习俗,而是看它是否与公平正义相符,是否满足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自然情感的追求。很明显,西塞罗同样认为,法律的精髓在于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才是法律的真正本质。*参见[古罗马]西塞罗:《法律篇》(第1卷),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5-72页。即使在中世纪,人们仍然认为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本质。虽然托马斯的神学观不否认法律的强制性,但更强调法律的正当性,始终把法律的正当性放在首位,认为公平正义才是法律的根本属性,是评价一项法律好坏的根本标准。可见,公平正义在托马斯的神学观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当代学者对法律本质的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奠定了法律本质理论研究的基础。*参见周永坤:《论法律的自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165页。
更值得关注的是,提到公平正义,必然会想到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尔斯教授,他花了20年的心血完成了他的法学名著《正义论》,接着又为这本书辩护了20多年。罗尔斯教授认为,一部法律不管其可操作性多强、设计如何合理和巧妙,只要不满足和符合公平正义,它就不应当具有权威性,应当被人们推翻,也就是我们说的“恶法”。此外,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他们对于自己的利益十分敏感,力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时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便产生了。公平正义的观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利益(权利)和负担(义务)在个体之间的合理分配问题,这与法律的目的和职能是不谋而合的。况且,只有首先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解决社会的稳定、和谐统一、效率、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罗尔斯还宣称,公平正义还应当具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不能为了满足他人的利益而牺牲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利益,即便是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对象也不可以。*参见何勤华、严存生:《西方法理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3页。虽然这个观点有些极端,在社会利益大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当代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它却深刻地揭示了法律与公平正义的关系,法律离不开公平正义,否则法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对其他属性起统领作用。
(三)公平正义——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的应然归属
1、公平正义的特质决定了其作为法律本质的价值归属。公平正义可以归结为我们常说的“理”、“公理”、“天理”、“常理”等,其不断内涵丰富,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且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所谓公平正义不是指绝对平等,而是指公平正义因素在社会分配上的平等,简言之,一个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可能在某一事件中获得的公平正义因素多一点,而在另一事件中获得的公平正义因素少一点,但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公平正义的。这与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体现并践行着法律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也不是神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或国家的意志,而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公平正义不是国家、某个政治团体或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其阶级性不是永恒的,当然在阶级社会里其必然具有阶级的内容,被统治阶级用作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公平正义的内涵必然受到政治、经济、宗教、法律文化、艺术、哲学等因素的影响,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综上所述,公平正义的特质与法律的诸多属性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特质,体现了法律的价值追求和本质特征,从而决定了其作为法律本质的价值归属。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公平正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把公平正义定义为法律的本质,那么,法律本质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法律本质是不能定格的。其实,并不矛盾,公平正义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不断地放弃不合时宜的成分,吸收合理的、先进的成分,吐故纳新,不断地改变公平正义的内容,但公平正义作为与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相适应的法律本质的事实不会改变,它仍然用新的公平正义内容体现并反映新法律(随着公平正义的发展变化,现有法律的内容也会随之变化,形成具有新内涵的新法律)的本质属性,所以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永恒本质无容置疑。
2、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呼唤公平正义的法律本质归属。张文显教授认为:“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律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过程。”*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由此不难看出,权利和义务对法律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但其与公平正义的自然法观念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德沃金教授已经给了我们肯定的回答,他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这样写道:“罗尔斯的理论在深层意涵上是以权利为基础的”,*[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4页。乍一看,这似乎和公平正义没有什么关系。但读过《正义论》的人们都知道,公平正义是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基石和主要论调。既然罗尔斯以公平正义为基石和论调的理论是以权利为基础,鉴于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和不可分割性,也可以说罗尔斯的理论是权利和义务基础。由此可见,罗尔斯坚持公平正义是以权利义务为基础的,没有权利义务的适当分配是实现不了公平正义的;同时,公平正义对权利义务分配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如果分配不适当,满足不了公平正义的标准,这样的权利义务分配结果将会受到公众的质疑,甚至被推翻。法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解决权利和义务的分配问题,而分配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实现公平正义,故而,权利义务分配过程决定着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取向,呼唤公平正义的法律本质归属。
具体而言,权利是由公平正义决定的应当享有的利益和自由的范围和幅度,义务是由公平正义决定的应当负担或承担的行为、给付或责任。权利与义务处于公平正义的统一体中,公平正义决定着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承担着什么样的义务,即一项法律之所以称之为法律,是因为其符合和满足“理”、“公理”、“天理”、“常理”的标准,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也就通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归根到底,法律离不开公平正义的理念,公平正义决定着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决定着法律的权利义务内容。所以,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本质属性,是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的应然归属,也是一种必然选择,符合我国目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参见张新奎:《法律本质新探》,载《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也许有人会对公平、正义的法律本质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如果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本质,就无法解释法律生活中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现象。其实,这是一种对权利义务平衡观念的错误解读,因为权利义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等的,不对等是权利义务平衡的一种特殊表现,但从社会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来说仍然是对等的。而且我们也不能任意限制一些人们放弃自身的权利,比如民法中的赠与合同、无偿借贷合同、无偿保管合同、无偿委托合同等,因为这是契约自由、意志自治的表现,是人类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此外,正如前面叙述的那样,公平正义也不是绝对的公平,容许特殊情况出现,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公平正义的。因此,把法律的本质定格为公平正义,并没有违反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参见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170页。
3、法律权威性的维护和国家强制力的公众认同期待公平正义的法律本质归属。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维护这种权威,法律只有与国家强制力相结合,借助国家的力量保障人们享有的合法权利得以实现,负担的义务得以履行,以达到公平正义的最佳状态。而这种状态反过来会增强公众对法律权威性和司法公信力的认同,从而对法律产生依赖,形成一种坚定信念,有利于彰显法律的权威性和贯彻实施。这就从另一方面表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司法公信力需要法律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应然状态,通过这种状态树立法律在公众中的权威性和认同感。基于此,把公平正义定位为法律本质的应然归属是一种必然。然而,法律的权威性需要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否则,公平正义的法律状态是无法实现的。如果离开国家的强制力,权利与义务仅仅是抽象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因为没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法律就得不到有效地贯彻和实施,人们就可以恣意妄为而无需担心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谓的权利与义务也就变成空中楼阁,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公平正义的法律应然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公平正义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永远不可能实现。法律也只有与国家强制力相结合才具有权威性和威慑力,迫使人们去服从,以维护法律的权威,保障法律的贯彻和实施。简言之,光凭人们公平正义的观念来定格法律本质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定的保障措施,以保证这种公平正义理念的贯彻和实施,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把公平正义的法律本质属性落实到实处。*参见[德]赫尔曼、康特洛维茨:《为法学而斗争法的定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71-84页。一旦公平正义的法律状态在人们生活中呈现,并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人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受到法律的约束,认可法律所采取的各种合法的强制力。理由在于,公平正义是每个社会的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长久期待,如果能够实现公平正义,受到合理的强制力约束是值得的,更有利于维护人们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因此,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增强司法公信力,促进人们对国家强制力的认同和接受,迫切需要法律实现和达到公平正义的应然状态,把法律的本质定格为公平正义。
总之,法律本质决定法律现象,法律现象是法律本质的反映,我们可以透过法律现象来把握法律本质。对法律现象起决定作用的基本要素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国家的强制力,而权利义务的分配是否合理是由公平正义的理念来决定的和衡量的。权利和义务不是完全对等的,也存在不对等的现象,但仅仅是权利义务对等的一种特殊表现,就社会总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而言又是对等的,依然没有脱离公平正义的法律本质轨道。至于国家强制力,必须与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相结合,以保障法律沿着公平正义的道路前进,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本质。如果国家强制力没有公平正义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国家很有可能利用强制力作为压迫人民的工具,胡作非为,实施暴力统治,最终使法律偏离公平正义的轨道。公平、正义与国家强制力结合的结果就是为了实现权利义务与国家强制力的结合,也是法律的应有之意,也就是说,权利义务在法律上本身就是权利义务与国家强制力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保障,以实现法律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目标。一句话,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决定着权利义务的分配,但需要国家强制力的参与和保障,最终实现良法之治,达到法律的应然状态。*参见陈皓:《卡多佐:司法传统的革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1页。
[责任编辑:王德福]
Subject:On The Ideal Attribution Of The Law Na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uthor&unit:YANG Xianbin
(Koguan Law School of Shang 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China)
The nature of law, as one of the basic problems of the legal research, has been causing widespread concern from the jurisprudence field in China,which is not only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 but also the most divisive issue, but the conclusion still isn’t made by anyone today, the main ideas include three theories : the class theory,the social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no essence . The former two theories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law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and only hit one side of the problem of the legal nature,which can not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essence the law ought to possess. The latter tends to the pursuit of uncertainty,which doesn’t suit to the n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o that we should abandon. However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reflect the commonality of many legal attributes, determin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s beneficial to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law, highlighting the credibility of justice, enhancing the identity which is from the public towards coercive force of the state, so we could achieve ultimately the rule of good law and reach the ideal statement through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refore, we should think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as the essence of the law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legal nature; Contemporary Cina; fairness and justice
2013-11-01
杨显滨(1981-),男,河南潢川人,扬州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11届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民商法学。
D90
A
1009-8003(2014)01-006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