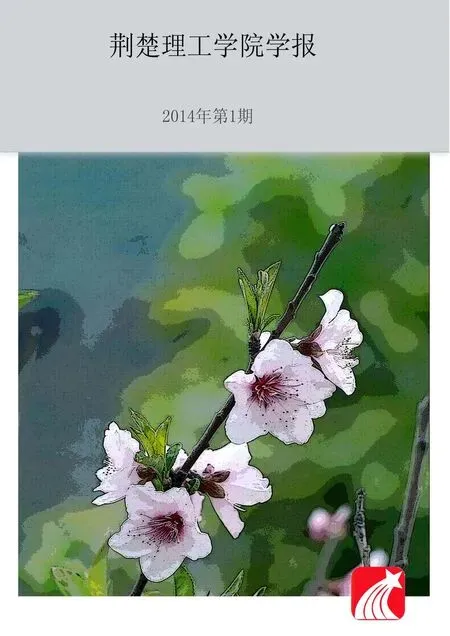彰显自然教育思想的机制、特点和本质
——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2014-04-17刘黎明
刘黎明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彰显自然教育思想的机制、特点和本质
——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刘黎明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有着极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性善论、自然权利和自然状态学说、经验论哲学、心理学,它们制约着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的机制、特点、本质和规律,使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呈现出丰富的意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理论基础;机制;特点;本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宏观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方面的著作有张斌贤、褚宏启等著《西方教育思想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王天一,方晓东编著《西方教育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单中惠主编《西方教育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李明德著《西方教育思想史:人文主义教育之演进》(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代表性的论文有:郭法琦的《重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历史研究》(《教育史研究》1990年第2期)、钟昱的《浅析自然教育理论的历史演进》(《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王小丁,高志良的《西方自然主义儿童教育理论的历史演变》(《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2期)、张二庆,耿彦君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3期)、肖丹,赵万祥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根基与脉络》(《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黄英杰,王小丁,张茂恩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嬗变与和合》(《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刘黎明的《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武陵学刊》2011年第3期)、刘黎明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现代意义的追问》(《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刘黎明的《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研究的四个范式》(《教育史研究》2011年第3期)、刘黎明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历史嬗变的动因探析》(《当代教育论坛》2012年第4期)、刘黎明的《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2年第3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从宏观上探讨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动因、研究范式、基本观点、历史功绩和当代价值,但缺乏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系统研究。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主题。
在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史上,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是与性善论、自然权利和自然状态学说、经验论哲学、心理学紧密相联的,后者是前者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它们制约着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自然教育家对自然教育思想的建构。本文就此作些学理上的探讨。
一、人性本善的思想
性善论是卢梭和裴斯泰洛齐自然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卢梭认为,正确地认识人的本性是说明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前提条件。然而,关于人的知识是一切知识中最有用而最不完备的。更不幸的是,人取得的所有进步都使人更加远离原始状态。我们的新知识积累得越多,就越是没法抓住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人的不断研究,使得我们无法认识人。卢梭对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性善论”的学说。他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纯洁善良的,具有爱心和怜悯心,“一个人对别人的义务不只是靠后来的智慧的训诫来规定的,而是只要他不抗拒同情心的内部推动,他就永远不会伤害别人,甚至不会去伤害任何有感觉的生灵。只有在涉及他的自我保护的正当场合,他才不得不先考虑自己。”[1]79-80他“发现了两种先于理性而存在的人的本性:一种本性使人对自己的福利和自我保护极为关切,另一种本性使人本能地不愿意目睹有感觉力的生灵(主要是人的同类)受难和死亡。……人的精神能够使这两种本性协调并结合起来,并且仅仅由此便产生所有自然权利的法则,而没有必要让人的社会性介入。”[1]79-80关于人性本善的思想,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诠释得更为清楚: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本性的最初的冲动始终是正确的,因为在人的心灵中根本没有什么生来就有的邪恶,任何邪恶我们都能说出它是怎样和从什么地方进入人心的。对此,卢梭强调这是“不可争辩的原理”。他的整个《爱弥儿》就是围绕着这个原理来论述自然教育思想的。他在《致博蒙特的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根据我所著述的推论,根据我在最近的著作(即《爱弥儿》)中尽可能阐明得更完善的推论,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人类是天性本善的生灵,热爱公正与秩序;人类心灵中本无邪念,最初遵循本性的活动总是正当的。……我已经表明,所有归咎于人类心灵的不道德行为都不是人类心灵本来所具有的;我已经表明了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可以说我追溯它们的渊源,已经表明,由于不断改变他们善的天性,人类最终变成现在这样。”[2]就性善论的内容而言,卢梭认为,它主要包括自由、良心和理性三个方面。
(一)自由
卢梭认为,自由是人宝贵的天性,人是生而自由的。这种自由就是指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凡是真正的意志都具有自由性,因而人在他的行动中是自由的,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体现了人的主动性和自由。“一切行动的本原在于一个自由存在有其意志,除此以外,就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解释了。”[3]404这种自由的意志是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人能以自由施动者的身份参与他自己的活动,其他动物则不能。“构成人类与兽类之间的种差的不是人的悟性,而是人的自由施动者的身份。大自然支配所有的动物,兽类服从支配,人同样感受大自然的影响,但人自认为有服从或不服从的自由,而主要就是由这种自由的意识显现出人的灵魂的灵性。”[1]95在卢梭思想的视野中,“天性的自由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并不完全被动地服从自然,具有通过自由意志对自然进行取舍的能力;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存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意志的强迫及依附关系。只有这种自由状态下的人才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4]。自由是个崇高的字眼,以至卢梭说:“我愿意自由地生,也自由地死,”[1]62,放弃了自由,也就放弃了做人的权利。
(二)良心
如果说自由代表了自然的意志,那么良心体现了自然的情感。卢梭认为,在人的各种天性(自然语言、自然情感、自然意志等)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欲念,因为它关涉到人的生活和生存。我们的欲念是我们保存的主要工具,欲念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我们的生存离不开它。然而,我们的自然欲念是很有限的,它们是我们达到自由的工具,它们使我们能够达到保持生存的目的。这些有限的欲念就是保存生命和自由所需要的基本限度。此外,还有一种与自然欲念相对应的人为欲念,它超过自保的限度而奴役和毁灭人,是违反大自然“本意”的,是卢梭所反对的欲念。
而区别自然欲念与人为欲念,依靠于良心。如果说欲念是肉体的声音,良心则是灵魂的声音。他热情歌颂了良心: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他还指出了良心的合乎自然的向导作用:良心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们,它是人类真正的向导;它对于灵魂来说,就像本能对待肉体一样;按良心去做,就等于服从自然,就用不着怕迷失方向。所谓良心就是道德的先天原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尽管我们有自己的准则,但我们在判断我们和他人的行为是好或是坏的时候,都要以这个原则为依据,这个原则就是良心。
良心就其内容而言,它包括自爱和爱人。人的种种欲念的本源,惟一同人一起产生而且终身不离的根本欲念,就是自爱。自爱的内涵,就是对自己的生命有最大的兴趣,热爱自己的生命。自爱始终是很好的,始终是符合自然的秩序的。因此,人的重要责任就是学会自我保存,学会自我关怀。我们爱自己要胜过爱其他一切东西;从这种情感中将直接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同时爱保持我们生存的人。也就是说,良心不只是自爱,而且还会爱周围的人。小孩子的第一个情感就是爱他自己,第二个情感就是爱同他亲近的人。因为,在他处于幼弱的状态,他对人的认识完全根据那个人给予他的帮助和关心,并由这种认识养成了爱他同类的习惯,养成了道德,即把自爱之心扩展到爱人。
(三)理性
卢梭认为,与有感觉而无智慧的其他动物相比,人是一个主动的有智慧的生物。他之所以不会消极被动地反映自然,因为人的天性中有自由有理性。在卢梭看来,感觉和理性是有差异的。感觉只是被动地表面地感知外物的形象,而理性则对外物进行比较、归纳、分析、判断、辨别,对众多繁杂的印象进行思维加工,力图帮助我们发现事物间的内在联系,知晓事物的道理,获得观念和知识。
卢梭的性善论构成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影响着他的整个自然教育思想的建构,具体体现在:在自然教育的内涵上,强调教育即儿童天性的自然发展,通俗地说,就是让儿童根据自己的性情率性发展,教育的过程就是儿童追寻自身天性发展的过程。在教育目的上,培养身心调和发达,既有运动员的身手,又有哲学家的头脑的自然人。在教育的过程上,强调人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育要服从于自然的教育,按照儿童的天性展开教育的过程。在教育内容上,反对18世纪流行的文字教育和书本教育,主张从自然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从活动中学习。在教育路径上,强调消极教育,自由教育,研究性学习。
裴斯泰洛齐受卢梭的影响,也持性善论,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和向善的。他说:“我十分热切信奉的信念是:人类是可以改善的”[5]62,因为“人心向善,人人都情愿做个好人”[6],有些人之所以有不善的行为,是因为通行向善的道路被堵塞了:“人是善的,而且愿意向善;他愿意在这样做时是愉悦的。如果他不善,那准是向善的路堵塞了。堵塞这条路是件可怕的事情,但这种事情却是那样的普遍,以至眼下好人少。但一般说来,我永远相信人心是善的”[7]339。“我的所有著作中,并以我能达到的最清晰的方式所说明的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人是本性为善的存在者,他热爱正义和秩序;人心中没有原初的堕落;自然的原初运动总是正确的……,一切加诸人心的邪恶都不出于人的本性。”[8]正是在“性善论”的影响下,裴斯泰洛齐建构了“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理念,提出了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二、自然权利和自然状态学说
自然权利是17-18世纪在欧洲广泛流传的思想。这一思想着重强调自由、平等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人的自然权利。卢梭认为,凡是出自自然的要求,所有的儿童都是相同的。他们都生来就有自由发展的权利。“自由”是儿童最重要的自然发展权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深刻地诠释了“自由”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每个人生而自由、平等。孩子们生来就是自由的人,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无权加以处置。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放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9]可见,他把自由等同于德性。在他看来,自由是比生命更高的善,“自由就是服从于个人对自己的立法。这首先意味着,不仅是对法律的服从,而且立法本身都必须源自于个人。其次,这意味着,与其说自由是德性的前提或结果,不如说自由就是德性本身。……尤其要紧的是,他提出要以一种新的对人的定义取代传统的定义,在新的定义看来,不是理性而是自由成为了人的特质。”[10]由此,卢梭开创了自由哲学。
基于这种自由哲学观,卢梭要求教育者首先应遵循儿童的自然本性,创造儿童主动发展的条件,让儿童自由地率性地发展。因为自然教育即儿童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也即儿童天性的发展。儿童的内在的自然本性决定了儿童在教育中的中心地位,也构成了确立儿童主体地位的内在依据。其次,应尊重儿童的特点和需要,体会儿童的所思所想所做,一切以儿童为出发点。因为儿童具有与成人不同的特点,具有“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因而,他反对把小孩子当大人看待,而主张“把孩子看作孩子”,做到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作出或好或坏的评判。让特异的征象一再地显示和确实证明之后,才对他们采取特殊的方法。让大自然先教导很长的时期之后,你才去接替它的工作,以免在教法上同它相冲突。按照大自然的教导,就是要让儿童自由地活动,尽情地玩耍,培养他们可爱的本能,使他们的童年充满恬静、喜笑颜开。再次,要依据儿童的自然进程和儿童的年龄特征施教。因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总之,要保障儿童的思想自由、个性自由和活动自由,因为在卢梭看来,“自由是最大的善,那就是我的基本准则。把它应用于儿童和童年,而且所有的教育原则皆来自于它”[11]。
与卢梭自然权利学说紧密相联的是他的自然状态学说,它直接为自然人的概念的提出以及自然教育思想的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卢梭的笔下,原始的自然状态是恬静和自由的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处在这个时期的人虽然没有某些动物那样强悍凶猛,也没有另一些动物那样灵巧敏捷,但他的身体构造却是所有动物中最合理的、最完善的。“他所关心的首要事情是自我保护。大地为他提供生活必需的东西,本能驱使他去利用它们。饥饿和种种欲念使他相继采取各种生存方式。”[1]126因而,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它既存在于个体身上,也存在于全人类。
更为重要的是,人在精神上有意志自由和自我意识。如前所说,“构成人类与兽类之间的种差的不是人的悟性,而是人的自由施动者的身份。大自然支配所有的动物,兽类服从支配,人同样感受大自然的影响,但人自认为有服从或不服从的自由,而主要就是由这种自由的意识显现出人的灵魂的灵性。”[1]95由此,他得出如下结论:“野蛮人在丛林中漂泊游荡,没有技艺,没有语言,没有栖所,与人无争也不与人交际,既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无害人之念,甚至可能从未能够对人进行辨认。他们没有什么情感,并且自给自足,只具有与其状态相应的意识和智力。他只感到实际的需要,只留心他认为必须注意的东西。他的悟性也只是发展到了有点自负的程度。如果偶然有所发现,他也不能与别人交流感想,因为他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即使有所发明,也将与其发明者一同消亡。没有教育,也没有进步。一代一代毫无进展地繁衍下去。每代的出发点都相同,那混沌初开的蒙眜时代不知过了多少世纪,人类已经老了,而人依旧是个稚童”[1]120,但他有灵性和自我意识。
卢梭之所以赞美自然状态和自然人,并非要人回到远古,重返森林,而是包含了他的人文理想,这就是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和向往。在他看来,“自然使人幸福和善良,而社会使人堕落和不幸”[1]134,他在《爱弥儿》一书中更是赞美了大自然的“和谐”、“匀称”和“有序”:“大自然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匀称,而人类是那样的混乱,那样的没有秩序!万物是这样的彼此配合。步调一致,而人类则纷纷扰扰,无有宁时!”[3]400可以说,卢梭“对当下混乱社会的鞭笞,对导致人类不平等的私有制的批判,恰恰是为重建以自然状态所蕴涵着的人文理想和社会秩序张本。对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的追求,构成卢梭自然状态的真正本意”[12]。
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在教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强调教育目标是培养“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想”的、身心自由和谐发展的自然人;其次,强调教育的本真内涵是回归儿童的自然状态,使儿童在活动中、在游戏中接受教育;再次,强调自由教育,让儿童拥有活动的自由、探索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唯有如此,儿童才能“在获得他那样年纪的理智的同时,也获得他的体质许可他享有的快乐和自由”[13]209。
三、经验论哲学
经验论哲学成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康帕内拉非常重视感觉、经验的作用,他“把‘感受’看作最高的认识形式,无论是解读《圣经》,还是观察大自然,感受不仅仅是指当下的感觉,而且也包括对外在的、未知的事件的觉察,甚至连预见也有感受的依据。”[14]西班牙人文主义者维夫斯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从各种感觉到想象,再由想象到理解,它是学习过程的生命和本质。所以学习过程要由个别事实到大批事实,由个别事实到一般事实,这是在儿童学习中必须注意的。”“因此,各种感觉是我们最初的老师,理解则源于感觉”[15]。意大利的达·芬奇坚信“我们的一切知识,全部来自我们的感觉能力”,“智慧是经验的产儿”,“在经验的指导下读书,价值要大得多,因为经验是我们老师的导师”[16]。
而奠定经验主义哲学基础的是英国哲学家、教育家弗兰西斯·培根。他认为,人若要支配自然,改造自然,首先必须认识和服从自然的规律,因为如果我们不服从自然,我们就不能支配自然。而认识自然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感官感知实现的。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这乃是认识事物的基本原则。当然感觉也有其局限性,补救的办法是给感官提供工具和帮助,但主要依赖于科学实验。培根“对于教育思潮上所贡献的,非他自身的教育论,而是他的学风。即其尊重经验,重视自然的观察研究的思想遂成为产生拉特克、夸美纽斯等的教育思想的源泉。……严格的说来,他虽然不是经验主义的鼻祖,但因了他的影响而产生出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教育学说,那是无可见逃的。……16世纪的实学的教育思想,只是经验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教育说的先声,且如代表感觉的实学主义者马卡斯特的思想,其所传布的地方并不广大;及至17世纪受到培根的影响,才渐加有力起来,发达起来,致造成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潮”[17]。可见,培根对经验论哲学的形成功不可没。
17世纪的夸美纽斯受培根的经验论影响很大,对培根的《新工具》赞美有加,把它看作刚出现的新世纪的灿烂之光,并认为“归纳法是研究自然的一种方法,这个归纳法真正包含着探索大自然奥秘的途径”[18]。受培根的影响,他也强调,知识的开端永远必须来自感官,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基础。因此,教学应贯彻直观性原则,要求教师在可能的范围内,一切事物都应放到感官跟前。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应放在视官跟前,一切听得见的东西都应放在听官跟前。假如事物本身不能得到,便可以利用它们的模型图像,制造范本和模型以供教学之用。这种感觉认识论为他的自然主义教学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感觉经验论色彩十分浓厚。感觉经验论是他自然教育思想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在卢梭的语境中,感性认识是人的认识过程的起点。因为“人的最初的自然的运动是观测他周围的一切东西,是探查他所见到的每一样东西中有哪些可以感知的性质同他有关系,因此,他最初进行的研究,可以说是用来保持其生存的实验物理学”[13]148。由于所有一切都是通过人的感官进入人的头脑的,所以人的最初理解是一种感性理解,正是有了这种感性理解作基础,理智的理解才得以形成。所以说,我们最初的哲学老师是我们的脚,我们的手和我们的眼睛。它们是我们智慧的工具,要学会思想,就得锻炼我们的感觉和各种器官。因此,卢梭主张1至12岁的儿童进行感觉教育,要尽量用可以感觉得到的事物去影响他,则他所有一切的观念就会停留于感觉;使他从各个方面都只看到他周围的物质世界。他反对理性教育,因为这个时期是儿童“理性的睡眠期”,在人的一切官能中,理智这个官能可以说是由其他各种官能综合而成的,因此它最难于发展,而且也发展得迟。
在卢梭看来,经验学习是儿童最重要的学习方式。只有经常同自然界接触,在感觉经验中学习,才会获得对事物可靠的认识。他举例说,如果儿童经常去黑暗的地方,他就不会对黑暗感到恐惧。如果他经常看见蜘蛛,他就不会害怕蜘蛛。因为经验使他熟悉和习惯了看蜘蛛。
卢梭还认为,与经验学习密切关联的是“实践”。由于一个人亲自取得对事物的观念比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观念要清楚得多,因此,他倡导“从实践中去学习”[13]109。如果儿童要获得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就需要在感觉活动中去学习。儿童什么东西都想去摸一摸,什么东西都想去弄一弄。他这样动个不停,你不要去妨碍他,因为这可以使他获得十分需要的学习。正是这样,他才能学会看、摸、听,从而通过这种办法了解事物的冷热、软硬和轻重,判断它们的大小,它们的样子和能够感觉出来的种种性质。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科学知识,应使儿童从生活和实践的切身体验中去学习。“从对爱弥儿的教育和获得知识的过程来看,爱弥儿首先在大自然中学习天文、地理知识,他的化学、物理学知识也是通过亲自实践获得的;待他进入青年时代,便要到手工工场做工,了解人类互相依赖的物质关系,同时还要到其他各行业特别是农业中去了解它们的作用,从而正确地认识到农业生产是第一位的社会观念;此外,他还要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得到关于商业、交换的尺度、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等社会观念。卢梭的这种生活实践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实践与实践之间的联系,这无疑是对实践理论的一个贡献”[19]。
卢梭对感觉经验论的见解,在西方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强调从感觉经验中,从实践中学习,既丰富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经验论哲学思想,又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下旧的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为后世的活动教学思想和“从做中学”的理念提供了思想源泉。卢梭以后的近代和现代的诸多教育思想都可以从卢梭这里找到踪迹。
心理化自然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也很重视感觉经验论。他把感觉印象看成一切知识的绝对基础,“是人类教学的唯一真实的基础。因为它是人类知识唯一真实的基础。继感觉印象之后的一切都是感觉印象的结果,都是对他加以抽象的过程。因此哪儿的感觉印象不完善,哪儿的结果就既不会明确、可靠,也不会有把握;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感觉印象不精确,虚假和错误就会随之而来”[5]200。然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好像波涛起伏的一片混乱的感觉印象的海洋。假如仅仅通过自然,我们的发展还不够迅速和不是没有阻碍的话,那么教学的任务,就在于消除这些感觉印象的混乱现象;把各个物体一一区别开来;把相似的或是相互有关的印象在想象中集合起来。这样使所有的东西对我们清楚起来,并且由于对这些东西有透彻的认识使我们形成了明确的观念”[20]。
尽管裴斯泰洛齐也赞成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但是他强调仅仅依靠个人亲身获得的感觉经验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感觉经验常常带有偶然性,必须诉诸于符合儿童本性的、心理学的、循序渐进的方法。教育者施加人为影响时,必须符合儿童本性(心理活动)的规律。因为“施加人为影响的规律是从研究本性发展过程中推演出来的,本性永远是施加人为影响最重要的基础,人为影响和本性之间的关系犹如一座房子和岩石地基之间的关系:只要这座房子同岩石地基结合成一体,就还可盖几间厢房;但是一旦这座房子同岩石地基结合部出现了裂缝,这幢房子终有一天会倒塌,变成断墙残垣”[7]340。这样,他的感觉经验论就和心理学密切关联起来,为近代西方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学依据。
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对经验论的阐释也十分精彩。经验在杜威的生长论自然教育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他相信,一切真正的教育是来自于经验的,感官是知识的门户。“在全部不确定的情况当中,有一种永久不变的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即教育和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21]317。因此,他力图建立一种经验的理论,以便使教育能够在经验的基础上合理地进行。在杜威的语境中,经验是教育的内在蕴涵,离开了经验的改造,也就无所谓教育。“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愈是明确地和真诚地坚持这种主张,对于教育是什么应有一些清楚的概念就愈加显得重要”[21]319。正因为如此,他把教育定义为:教育是经验继续不断的改造,使得一方面能操纵经验,一方面能使经验日益丰富。他要求教师应做的是,不仅要知道儿童经验的性质和源起,更重要的是将儿童现有的经验与前人已经组织好的经验融合起来,变成科目,使学生“从经验中学”、“从做中学”。这是教师的重大责任之所在。由于他的“教育哲学是属于经验、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21]320,这使他的教育哲学充满了经验论色彩,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经验论教育哲学。
四、心理学
尽管自然主义教育家的自然教育思想都有心理学的视野,但在这里,我们主要论及几种比较成熟的心理学思想。
(一)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说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是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质料”是构成事物的最初本源,是形成事物的原因,说明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形式”是事物的本质,说明事物为什么这样构成。两者相互依存。具体就人而言,人是由质料——躯体和形式——灵魂所构成,形式是主动的,质料是被动的。由此出发,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灵魂论,提出人的灵魂由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所构成。其中植物灵魂的表现形式为营养和繁殖;动物灵魂的表现形式是感觉和欲望;理性灵魂的表现形式是理解、判断和沉思。理性灵魂是最高级的部分,促进人的理性的发展也就成了教育的终极目标。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的灵魂如同一块白板,没有刻上任何东西,所有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感觉进入人的意识的产物。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心理学思想为他的自然教育思想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其积极意义,“首先,他对人的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论述为教育必须包括体育、德育和智育提供了人性论上的依据;其次,他的‘灵魂白板说’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教育在人的理性发展和知识获得等方面的作用”[22]。
(二)心理化自然教育家的心理学思想
裴斯泰洛齐通过自己的教育实验和探索,长期寻找一个所有教学手段的共同的心理根源,力图把教育教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他在《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孩子》中断言:“我感到我的实验已经证明民众教育可以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可以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建立起通过感觉印象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可以撕掉肤浅的,装腔作势夸大其词的伪装。我感到我所能解决的是那些具有洞察力、没有偏见的人的问题”[5]22-23。这个心理根源首先是指向感觉和直觉的。他认为,人们是通过感官活动如看、听、触、闻等,来感知事物特性的,从而形成了模糊的直觉,再通过思维活动对直觉加以整理、解释和命名,最后用言语表达出来。感觉和直觉构成了人们认识、思维和能力发展的基础。其次是指向各种教育的简单要素,如语言、外形和数目。他指出,“最复杂的感觉印象是建立在简单的要素的基础上的。你对简单的要素完全弄清楚了,那么,最复杂的感觉印象也就变得简单了”[5]83。这奠定了他的要素教育论的思想基础。
裴斯泰洛齐对能力的分析和论证,也构成了他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裴斯泰洛齐看来,人的能力是由脑、心、手三个部分组成。脑即“精神”,包括感觉、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和语言,是人的所有内在精神的官能;“心”主要指道德情感;“手”是指人的实践活动能力。这三种能力应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为他的“教育心理学化”思想和人的和谐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赫尔巴特进一步发展了裴斯泰洛齐的心理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心理学——主知主义观念论。赫尔巴特认定观念是人的心理活动最简单最基本的要素,是人的全部心理活动的基础。各种观念的出现、活动、集聚、分散、增强和减弱,构成了人的全部心理活动。因此,他强调,心理学就是研究观念的科学,重点研究观念的出现、结合和消失。
赫尔巴特还提出了“意识阈”和“统觉”两个重要的概念,用来阐明有关观念的问题。他认为,一个概念若要由一个完全被抑制的状态进入一个现实观念的状态,便需要跨过一道界限,这些界限就是意识阈。他强调,意识阈的概念表明,心理学不仅要研究意识现象,而且要研究超出意识之外的现象,这些现象就是“无意识的意识”。而统觉是指新旧观念的联系,意即把分散的感觉刺激纳入意识的核心,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新旧观念结合得越多,学生获得的知识就越广,越容易理解,越牢固。
赫尔巴特为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结合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认定教育者的首要科学是心理学,第一次把心理学作为阐明教育学问题的理论依据。他是最早宣称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的人,最先将心理学与哲学分开,认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应建立在形而上学、数学和经验的基础上。他把心理学运用到教育研究中,探讨了教育目的心理化、教育内容心理化、教学程序心理化和教学方法心理化,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化自然教育思想的发展。
(三)杜威的机能论心理学
杜威的机能论心理学是他的生长论自然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一般认为,杜威在1896年发表的《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是美国机能心理学诞生的标志,也是心理学著作对教育学产生深刻影响的最重要的里程碑。杜威在这篇文章中反对把心理分析为各个元素或分解为各个部分,强调心理活动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心理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有用工具,有机体是通过反射弧这个器官的协调来适应环境的。由此出发,他强调本能的意义,认为儿童心理学内容基本上就是以本能活动为核心的习惯、情绪、冲动等天生心理机能不断展开生长及与周围环境协调的过程。教育的任务就是发现本能生长的规律,促进儿童本能的不断生长。
综上所述,自然主义教育家们从性善论、自然权利和自然状态学说、经验论哲学、心理学等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为自然教育内涵、自然教育目的、自然教育路径以及自然主义儿童观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的机制、特点、本质和规律,使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呈现出丰富的理论意蕴,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1]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高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普拉特纳Plattner等.卢梭的自然状态——《论不平等的起源》释义[M].尚新建,余灵灵,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67.
[3] 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下)[M].李平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 于书娟.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卢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4.
[5] 裴斯泰洛齐.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M].夏之莲,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 裴斯泰洛齐.林哈德与葛笃德(上卷)[M].北京编译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358.
[7] 阿·布律迈尔.裴斯泰洛齐选集(第一卷)[M].尹德新,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
[8] 余中根.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64.
[9]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2.
[10]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84-285.
[11] 吴式颖,任钟印.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206.
[12] 赵立坤.卢梭浪漫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52-153.
[13] 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M].李平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4] 吴国盛.自然哲学(第2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46.
[15] 威廉·博伊德,埃德蒙·金.西方教育史[M].任宝祥,吴元训,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80.
[16] 李武林.西方哲学史教程[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264.
[17] 蒋径三.西洋教育思想史(上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87.
[18] 夸美纽斯.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M].任宝祥,熊礼贵,鲍晓苏,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07.
[19] 于风梧.卢梭思想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1.
[20] 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80.
[21] 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22] 张斌贤.外国教育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86.
[责任编辑:王乐]
2013-09-19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其当代价值研究(2013YBA216)
刘黎明(1964-),男,湖南茶陵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G40-09
A
1008-4657(2014)01-00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