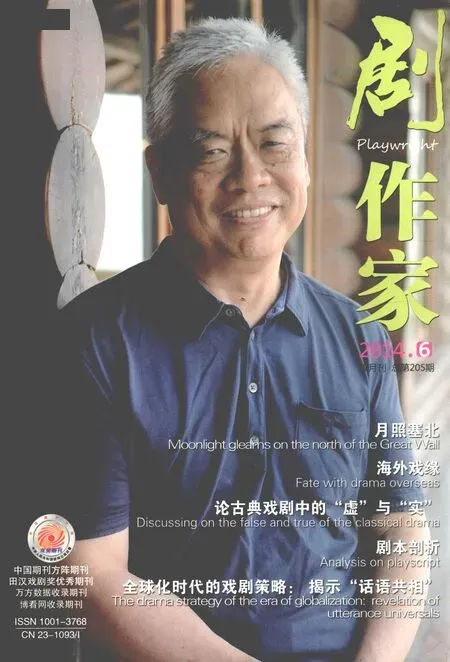《我爱桃花》——精妙绝伦的剧本结构
2014-04-17陈俊
陈 俊
《我爱桃花》——精妙绝伦的剧本结构
陈 俊
《我爱桃花》是一部探讨情感问题的后现代剧。故事的由头源自小说《醒世恒言》第五回的一个小故事,用戏中戏的方法巧妙地将古今如一、永远也无法说清的人类情感困惑展现在舞台上。
该剧是担任过《铁齿铜牙纪晓岚》《倾城之恋》等电视剧编剧之一的邹静之先生的舞台剧处女作,自2003年首演,就引起了轰动,连演400场,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境况。2014年,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了这出戏,我看的是福建人艺的演出版本。
大幕拉开,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醒世恒言》第五回“淫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里截取唐代人冯燕与渔阳牙将张婴之妻偷情的故事:
唐时,渔阳燕市少年冯燕,与牙将张婴之妻通奸。某夜,张婴醉归。张妻忙将冯燕藏起。不想张婴醉卧时压住了冯燕放在椅子上的巾帻(类似帽子)。待冯燕想逃开时,发现自己的巾帻被张婴压在身下,怕第二天张婴醒来,奸情败露,于是示意张妻将那巾帻拿来。张妻悄然到张婴身旁,彼时巾帻压在张婴身下,张妻会错了意,以为冯燕是要张婴腰间的刀,而要杀自己的丈夫。于是,悄然将刀抽出,递给了冯燕。冯燕见刀感觉这女人心狠手辣,想这女人如此心狠,此时能如此对待老公,彼时便也会如此狠心对待别人包括自己,便一刀将张妻杀死。
如果《我爱桃花》仅仅以这样一个三角孽恋为核心铺陈剧情,它能释放出的戏剧魅力是非常有限的,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有戏没戏,显然,这样处理的话,起码戏是很有限的。
作为戏剧的内核,剧作者邹静之采用“戏中戏”的结构方式,演绎剧情。作者将“戏中戏”编排得独具匠心,将古代与现代、戏里与戏外进行穿插和融合。一边是演员排演《醒世恒言》“冯燕与张婴之妻偷情”戏,而另一边,扮演冯燕和张婴之妻的演员(英子)恰巧也是一对现实生活中各自有家室的情人,他们在排戏中不断的内心矛盾冲突体现为对戏中人物处理方式的不同意见。围绕偷情与杀人情节,戏剧凭借“会错了意”与“杀谁”这两个焦点,排比铺陈出多头叙事维度和多种不确定结局:
结局一:冯燕杀张婴妻。
结局二:冯燕杀张婴。
结局三:冯燕自杀,张婴杀妻。
结局四:刀还回鞘,谁也不杀,情人不再做情人。
结局五:刀还回鞘,退回原来生活:夫妻继续做夫妻,情人继续做情人。
故事在舞台与现实生活二维空间里,在过去和现在时间交替中演绎困扰了人类千百年情感纠葛问题:一会儿是唐代张婴的家里,一会儿是现代的舞台上。时空的交替昭示着戏剧探索的是人类自古至今无法说得清道得明的“情惑”两难。
这致命的一刀要落在谁身上是个难解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不该死的理由。适才耳鬓厮磨如今就要痛下杀手这转折不能为张妻接受。张婴是无辜的,他一直装聋作哑如此隐忍的一个人不该突然间不明不白死去。他死了观众不干。这戏就落了俗。
思来想去冯燕只能挥刀自杀。演着又出问题了。用张婴的话来说:“……听着你在我这儿接了刀不忍杀我也不忍杀她自杀了那你就变得对她有情对我有义。情义两个字都让你占上了。那你还不是英雄吗?你是英雄我算什么了,那我算什么东西。”
冯燕自尽了他就成了义士了。偷朋友妻的前罪一笔勾销。张婴觉得不值。无论谁死,这戏都无法演下去。讨论出来最自然的结果就是将抽出的刀插回去将饱满的杀机用冰冷的刀鞘包藏住。张婴昏沉睡去,冯燕带着肌肤上的温存走回,深夜张妻怀着来日的期盼入梦。妙人儿明夜再来相会。天下无事皆大欢喜。
冯燕第二天来到张家。经过日常走惯的那条小巷入眼是如此陌生。他怀疑往日的一切是癫狂的梦。情怀不再。枕边人也陌生如路人,隔着千山万水的路人。他敲门居然恭顺守礼。只说自己是来还个借的话本。
附着在桃花上的幻境消失了。一夜之间两人生分了。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昨夜那一刀已经斩下。宝刀一经出鞘不见血不回。他们不能重新开始。一切都回不到最初了。不管取舍是多么不易,人心有多么不甘。
剧终,三个人回到各自的生活轨迹中。像现实中许多寻常夫妻出轨了再回来。彼此都心知肚明也都若无其事。和这个人游戏一回与另一个人白头偕老。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经过类似的波折,或大或小,于是剧情能引发如此多的感慨和共鸣。彩虹总出现在风雨之后,可风雨之后却不一定有彩虹。就像本剧的最终,张妻还是张妻,和张婴相敬如宾,对冯燕以礼相待。这样的结局对三个人而言是好的吗?现实的选择往往如此,大多数人的选择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最不坏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也是最为社会规范所认可的选择。
五种叙事方向,每一种叙事向度都指向一种不同结局,但五种向度都指向同一种人生状态: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活在自我的欲望里,自我的本能欲望才证实了他存在的真实;一方面人又离不开他人,人是在他人的目光中生活的,人无法认识自己,只能通过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他人的评价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有的人能冲破这个约束,有的人一生就束缚在这个评价里,或“杀”人或被“杀”或自“杀”。如《桃》剧中张妻说:“你一直想以一种杀戮的方式,把我从你心里除掉! ”冯燕对英子说:“你编的这个谎言把天下的桃花都给杀灭了。”张婴、妻、冯燕互为他人的地狱。从法律上看,冯燕与张婴之妻偷情,但从情感的真实冲动看,张婴假借婚姻凭证占有对他没感情的妻,这是合法的公开强奸。冯燕杀张婴妻,表面上看是冯燕嫌张妻狠毒,内在则源于审美疲劳,要彻底摆脱掉她对自己生活的干扰。张婴杀冯燕与妻,表面上合情合理,事实是出于人类自私与占有欲的劣根性。张婴妻杀夫,表面上看她忠于自己情感,不愿与冯燕做露水夫妻,实际上源于她的欲望得不到正常发泄。张婴好杯中之物,常酩酊大醉,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偷情者名不正言不顺,除遭受巨大心理压力不说,还要担惊受怕。正是在这一点上,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而对你身边的人来说,你也是他们的地狱。这个地狱是人人都要经历的地狱,是个必经的地狱,冲破地狱,你就得到自由。安于地狱,也可以生活一辈子。只是个选择问题,选择不同,人生道路不同,人生结局也不同。
“选择”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哲学命题,也是一个在戏剧舞台上历久不衰的冲突要素。从莎剧的“生存还是毁灭”到“我爱桃花”的杀还是不杀。
要么,你有大智慧,参透人生玄机,超越选择的尴尬。你永远不必急于作出选择,只是让偶然带着你奔跑,信马由缰,任其自然。情来偷情,情去分手。 一切麻烦的事、难办的事、头痛的事都悬置起来,任其发展。如《桃》剧第五种叙事与结局:刀入鞘,情冷却,冯燕与张婴之妻各自退回原来的生活轨道,生活一如既往地平淡,无惊涛骇浪,无欲死欲仙。平平淡淡才是真。
福建人艺版的《我爱桃花》是以第五种“大团圆”的方式作为结局,但我看的原剧本处理却是回到第一幕开场场面,以张妻吟诵词曲为收尾。“桐叶惊飞秋来到,芭蕉着雨,隔着那窗儿敲。听天边一声一声的雁儿叫,明月高,杵砧声中盼郎到,盼郎到,郎不到,害得俺对银灯独自斜把那鸳枕靠。薄命的人啊,可是命儿薄,自己的名字,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自己叫。”本人觉得,原剧本的处理更有意味。人们大都选择最大众认可的结局,但每个人难道没有“意淫”过,生为尽兴、死为尽情?
从演出整体性来说,不管是舞台设计还是演员表演,福建人艺的年轻演职员已经体现了很高的水准。到目前,已经演了50场,场场爆满。
责任编辑 姜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