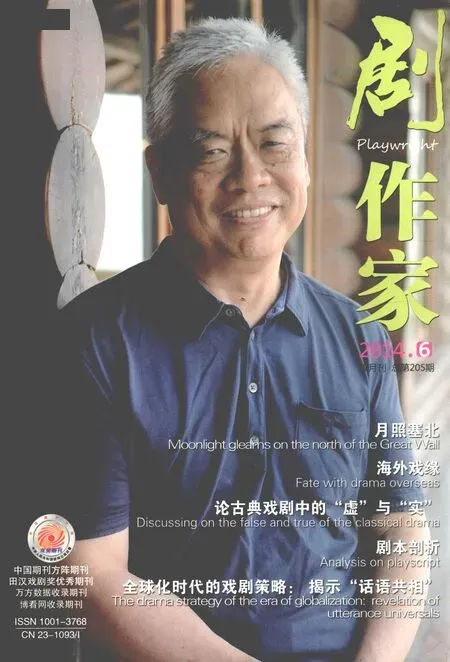论古典戏剧中的“虚”与“实”
2014-04-17李晓
李 晓
论古典戏剧中的“虚”与“实”
李 晓
“虚”与“实”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对范畴。源出《战国策》“本末更盛,虚实有时”,是古代哲学“有”与“无”的关系在美学中的反映,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后就成为创造形象的美学理论。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曰:“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在文学创作中要求以实秀显虚隐、以虚带实、虚实相生的“虚实论”的根本特性。六朝以后,文学艺术各门类都在发展着这个理论,在文学中讲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主要是讲究文学形象的空间观念和意象观念,即在创造形象中要讲“虚”与“实”的互补。如明李日华《广谐史序》云:“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实者虚之故不系,虚者实之故不脱。不脱不系,生机灵趣泼泼然。”[1]古典美学的“虚实论”在文学创作中有它的宽泛性,无论景物描写、人物描写和营造意境、编织情节等方面都有着艺术的体现。在戏剧文学中,明清的曲论家讲得更多的是编织情节中的“虚”与“实”的问题,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情节之“实”,指历史事实之“实”;情节之“虚”,指艺术虚构之“虚”。在戏剧理论中,这是剧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事件与人物)的认识问题,同时又是如何描写的技巧问题,在认识和描写中更多地带上了剧作家的主观意识和情感。
兹从四个方面来看明清曲论家对“虚”与“实”的认识:
(1)“谬悠而亡根”,这是明胡应麟在《庄岳委谈》“戏文非实”条下提出的基本观点,曰:“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亡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反是而求其当焉,非戏也。”[2]胡应麟认为“戏文非实”,作传奇亦当如此,否则就不是“戏”了。在这里很明确地说作传奇要“谬悠其事”。“谬悠”一词,语出《庄子》卷十“天下篇”,谬,虚也,悠,远也。晋郭象注曰:“谬悠,谓若忘于情实者也。”“谬悠”即“虚”,与“实”相对,凡传奇的情节,其事可“谬悠而亡根”,其名可“颠倒而亡实”,如果欲去求其事实,那就不是戏了。“谬悠”,即虚构之技法也。胡应麟认为,凡戏如《荆钗记》、《香囊记》等,“咸以谬悠其事也”。[3]清焦循评《铁邱坟》时亦说“假《八义记》而谬悠之”,指《铁邱坟》“观画”一出徐勣教薛子的情节,生吞《八义记》程婴教赵子的情节,“以嬉笑怒骂于徐勣”,因其虚构的情节“妙味无穷”。故曰:“彼《八义记》者,直抄袭太史公,不且板拙无聊乎?”[4]在评《雌木兰》时,因徐渭写了“王郎成亲”,则曰:“而所传木兰之烈,则未尝适人者,传者虽多谬悠,然古忠孝节烈之迹,则宜以信传之。”[5]清李调元亦云“元人有《关公斩貂蝉》剧,事尤悠谬”[6],貂蝉嫁吕布,本属虚构,关公斩貂蝉更属谬悠其事了。王国维在《曲录自序》“追原戏曲之作”,总结戏曲创作的语言与情节时亦说:“语取易解,不以鄙俗为嫌,事贵翻空,不以谬悠为违。”[7]自元以降关于戏曲情节的“虚”与“实”,以“谬悠其事”为戏曲创作的一条规律。然而,所谓“虚”者,也并非一味地“虚”,须在“实”的基础上“谬悠其事”。明谢肇淛曰:“凡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8]戏曲情节以“虚实相半”为“游戏三昧”,对于虚构的情节亦须要描写得“情景造极而止”,使人信其有,即为“戏”之原则。
(2)“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汤显祖的这句话正是他戏剧创作的主张。从创作理论上来分析,亦可以说是对“虚”与“实”的认识问题。汤显祖《牡丹亭》以“情”反“理”,当“情”与“理”发生矛盾时,为“常理”所不容,就可以突破“常理”的桎梏,按“情真”的逻辑,按作者之意,虚构情节创造出惊世骇俗的情景。汤显祖曰:“嗟乎,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9]茅元仪对此极为理解,曰:“如必人之信而后可,则其事之生而死,死而生,死者无端,死而生者更无端,安能必其世之尽信也……临川有言: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我以为不特此也,凡意之所可至,必事之所已至也。”[10]如果以现实生活之理“格”杜丽娘之情,那么《牡丹亭》生而死、死而生的情节就不成立了,艺术之精神荡然无存。然而,《牡丹亭》终究以它的艺术精神成为不朽之作,世所“信”者并非是生而死、死而生之“事”,所“信”者乃是生而死、死而生之“情”,“理之所必无”,然在“情之所必有”,这就是艺术的伟大的力量。虚构之情事可以超脱现实之常理,凡是作家思想意识所能到达的境界,其孕育的虚构的情事亦能到达这个境界。此即谓“凡意之所可至,必事之所已至也”。所以梅孝己说:“况夫钟情之至,可动天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将何所不至哉!”[11]
但是,这等虚幻的情节虚构,于情于理皆不合常情常理,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戏剧中便会受到责难,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先听听清凌廷堪如何说的,曰:“元人关目,往往有极无理可笑者,盖其体例如此。近之作者乃以无隙可指为贵,于是弥缝愈工,去之愈远。”[12]凌廷堪的话里表达了倾向性很明确的观点。元剧的体例,亦即“戏”的体例,容许“极无理可笑”的情节;明末清初的剧作家却重视起戏剧情节和细节的合理性,“以无隙可指为贵”;于是有人改作、重定旧剧,弥补失实与不当之处。笔者认为,这里出现的两种不同观点,都无可指责:从“戏”的本质来说,虚幻的情节超乎常理,若有助于作者立意的表达,则是作剧的一种技巧和风格;而追求情节与细节的合理性,如李渔所说的“密针线”、“戒荒唐”,合乎情理和生活逻辑,亦是作剧的基本要求。可以批评旧剧在情节上的失实和不当之处,然以封建伦理观念改窜旧剧情节的不合伦理或荒诞不经,则大可不必。正如凌廷堪所说,愈是精心修订,离原本之意愈远,结果流行的仍是已经深入人心的原本。李渔曾对人们熟悉的名剧《琵琶记》批评甚多,曰:“若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诸如此类,皆背理妨伦之甚者。”[13]李渔对《寻夫》一出最不满意,非议甚烈,曰:“赵五娘于归两月,即别蔡邕,是一桃夭新妇。算至公姑已死、别墓寻夫之日,不及数年,是犹然一冶容诲淫之少妇也。身背琵琶,独行千里,即能自保无他,能免当时物议乎?张大公重诺轻财,资其困乏,仁人也,义士也。试问衣食、名节,二者孰重?衣食不继则周之,名节所关则听之,义士仁人曾若是乎?此等缺陷,就词人论之,几与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无异矣。可少补天塞地之人乎?”[14]李渔批评赵五娘只身上京于伦理不合,难保名节,恐有非议,甘当“补天塞地”之人,借张大公家仆人小二伴赵五娘去京,改写此出。不料遭非议的却是李渔自身,清梁廷枏曰:“笠翁以《琵琶》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因作一折补之,添出一人为伴侣,不知男女千里同途,此中更形暧昧。”[15]梁廷枏亦从伦理上批评了李渔的改本,又妨伦理更甚矣。
(3)“古戏不论事实”,这是明王骥德对古戏情节在“虚”与“实”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但是戏剧发展到王骥德时,情节的虚实关系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出现了不同的倾向,曰:“古戏不论事实,亦不论理之有无可否,于古人事多损益缘饰为之,然尚存梗概;后稍就实,多本古史传杂说略施丹垩,不欲脱空杜撰;迩始有捏造无影响之事,以欺妇人小儿者,然类皆优人及里巷小人所为,大雅之士亦不屑也。”[16]王骥德认为“古戏不论事实,亦不论理之有无可否”,与“谬悠其事”、“情”可超越“理”而虚构其事一样,同为“戏”的体例所容,无论“谬悠”也好,虚构也好,都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造,古之戏“大抵真假相半”,“大抵多虚少实”[17],大多对“其事”“损益缘饰”,尽管虚构修饰的情节很多,但须“尚存梗概”,即“其事”的大关节目总须与“事实”相近。如昆曲演唱的元关汉卿《单刀会》于事实“损益缘饰”很多。据《三国志•鲁肃传》,孙权向刘备索还长沙、零、桂三郡,元剧改索荆州;鲁肃邀请关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元剧改鲁肃暗藏甲士于壁衣之后;鲁肃因责数落关羽无归还之意,元剧改为关羽按剑震慑鲁肃;刘备以割湘水为界罢军,元剧改为关羽浩荡而归。戏剧情节颠倒为之,塑造了关羽气贯长虹的英雄形象。惟为索郡事,“肃邀羽相见”,“单刀俱会”,实有其事,所谓“尚存梗概”也。明胡应麟评曰:“元词人关汉卿撰《单刀会》杂剧,虽幻妄,然《鲁肃传》实有‘单刀俱会’之文,犹实于明烛也。”[18]
明吕天成《曲品》卷上在品评“旧传奇”之前曾就戏剧情节说“有意驾虚,不必与事实合”,[19]与王骥德的观点是一致的。如评《彩楼记》曰:“且是全不核实,古人好诙谐如此,然亦古质可取。”[20]而后明代的传奇,“稍就实”,“不欲脱空杜撰”,
也就是说基本“就实”,在史实的基本上虚构情节,所谓“本古史传杂说略施丹垩”。如明梁辰鱼《浣纱记》,写吴越争霸事,关于这段史事在《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传》和《吴越春秋》、《越绝书》、《吴地记》都有记载,作者在“古史传杂说”的基础上,进行虚构想象,以范蠡、西施的爱情故事贯穿始终,完善戏剧的情节。所谓“略施丹垩”,即虚构的成分并不很多,因为有了必要的虚构,情节就显得生动有致,正如明张琦评《吴越春秋》(《浣纱记》原剧名)所说“善述史学而不平实”。[21]其中虚构和想象的内容也大多取于稗史、传说,因此范蠡、西施、伍子胥、伯嚭的形象较之正史丰满得多,性格更且鲜明。又如张凤翼的《虎符记》,敷写明将花云守太平城事,根据《明史•花云传》城破花云遇难,作者却将花云夫妇遇难改写成“以存易亡”的团圆结局,乃是传奇“体裁应尔”。作者写城破花云被擒,押监武昌,并突出描写其妾孙氏携虎符带幼子花炜逃出城去,历尽艰险,抵达南京。后花炜出师,破武昌,以虎符为证,与父相会。吕天成评曰:“前半真,后半假,不得不尔。女侠如此,固当传。”[22]“女侠”指孙氏,作者借鉴民间的讲史演义,虚构了孙氏训子、花炜救父的许多情节,倍为感人,所以吕天成说“固当传”。至于舍实取虚,全凭想象编织情节,“捏造无影响之事”,迎合当时尚奇的风尚,出现了一些纯属虚构的“戏”,在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有不少这类作品。如《新金印》:“此俗优所演者,较原本十改五六。一经抹涂,色泽大减。”[23]这类戏大多采自传说,情节虚幻,演出热闹,观众欢迎。然而,这类戏并非全是优人、巷人所为,文人作家聊出戏笔者亦有,其中大多含有讽刺意味。如孙钟龄的《睡乡记》“聊出戏笔,以广《齐谐》。设为乌有生、无是公一辈人,啼笑纸上,字字解颐”。[24]而史槃的《樱桃记》则“凿空出奇,大可捧腹”。[25]明末著名的阮大铖创作的《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其情节全属虚构,曰:“其事臆出,于稗官野说无取焉。盖稗野亦臆也,则吾宁吾臆之愈。”[26]王思任称阮氏传奇“不谱旧闻,特舒臆见,划雷晴里,不架空中”,[27]此亦成为阮氏传奇的风格。不过,这类作品并不很多,大部分传奇是虚实相半、虚多实少的居多,因其最符合戏剧的创作规律。如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28]如此,“若良史焉,古意微焉”。[29]
(4)“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明王骥德曰:“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明珠》、《浣纱》、《红拂》、《玉合》,以实而用实者也;《还魂》、“二梦”,以虚而用实者也。以实而用实也易,以虚而用实也难。”[30]关于戏剧情节的虚实结合的问题,古代剧作家和曲论家基本取得一致的认识,如何运用虚实结合的规律,即虚实结合的方法论,王骥德的体会是“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是非常正确的。戏剧的大体情节是事出有本的,或本于史籍,或本于小说、传说,或本于现实的故事,如此还不足于构成戏剧情节,在创作过程中还须凭借生活的积累和经验,遵循戏剧的结构规律,进行艺术的虚构和想象补充完善戏剧情节,尤其是细节的描写。在艺术价值上,虚构和想象的创造力显得尤为重要。王骥德认为大体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实而用实”,一种是“以虚而用实”,这话就概括得不太正确了。因为《明珠》、《浣纱》事出有本,也并不是“用实”描写,其中有很大程度的虚构情节;《还魂》、“二梦”(即《南柯》、《邯郸》)事属虚幻,亦有本于小说、话本和传说,其虚构描写的成分虽然很多,终究也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生活而进行必要的提炼、加工。因为戏剧是表现社会生活的,戏剧表现社会生活有自己的规律,在情节构成中“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即为“剧戏之道”,是符合戏剧的本质和表现规律的“金科玉律”。在明代的大多数传奇作品,运用的便是此法,不如此,不足以言“戏”也。
清李渔对于戏剧情节的虚实关系的方法论亦多有阐述,著名的言论有:“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虚则虚到底”,“实则实到底”。此等语似是而非,然而实在是李渔的创作经验之谈,问题是该如何去理解它的真义。李渔曰:“传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随人拈取。古者,书籍所载,古人现成之事也;今者,耳目传闻,当时仅见之事也。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31]李渔将“传奇所用之事”分为古、今和虚、实,“随人拈取”,然其戏剧观念则尚虚,认为“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李渔既重视用“实”,更重视用“虚”,在方法上有其一家之言。如说“虚”者为“空中楼阁”,“无影无形”,与吕天成所谓“有意驾虚,不必与事实合”同理,然更形象化,重点在“随意构成”之“意”,即随作者的立意想象虚构的情节必须得符合戏剧创作的规律,“空中楼阁”必须建筑在作者的立意之上,虽不合事实,然必须符合情节发展的规律,其人其事须在戏剧的情理之中。李渔在论述古今事的虚实关系中又有自己的观点。首先否定“古事多实,近事多虚”的说法,以《西厢》、《琵琶》为例说道:“莺莺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饿莩其亲,五娘之干蛊其夫,见于何书?果有其事乎?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即使古事,亦有实有虚之谓也。然而又说“作者秉笔,又不宜尽作是观”。因为流传的古事之“虚”者,已在观者、读者的心中既成戏剧故事之“事实”,不宜尽作虚妄之事而改之。所以当魏贞庵相国给李渔看“崔郑合葬墓志铭”,命作《北西厢翻本》“以正从前之谬”,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道:“谓天下已传之书,无论是非可否,悉宜听之。”[32]李渔拒绝改作。
李渔曰:“要知古人填古事易,今人填古事难,古人填古事,犹之今人填今事,非其不虑人考,无可考也。”“今人填今事”宜从“虚”,因为“目前之事,无所考究,则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以凭空捏造,是谓虚则虚到底也。”李渔的意思是,今人今事仅靠“耳目传闻”,所见所闻皆有片面性,无可求其全,亦无可考其实,为求形象丰富、情节合理,以虚构想象为主要的创作方法。所谓“虚”写,亦属现实的提炼加工。因此,若写孝子,“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记,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若写恶人,“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其余表忠表节与种种劝人为善之剧,率同于此。”“今人填古事”宜从“实”,“若用往事为题,以一古人出名,则满场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载籍,班班可考,创一事实不得。”所谓“创一事实不得”,应该是说基本事实和大关节目求实,为求古事的真实性和情节的合理性,须描写“满场脚色同时共事”之历史的人际环境,描写“本等情由贯串合一”之艺术的真实性。还必须遵从古事的“既成事实”,因为“传至于今,则其人其事,观者烂熟于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据,是谓实则实到底也。”因为往事可考,须求其“实”,即使原本是“虚”者,“观者烂熟于胸中”,亦视作为可据之“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李渔提出的要描写“满场脚色同时共事”、“本等情由贯串合一”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的问题,是十分可贵的真知灼见,丰富了历史题材的创作理论。今人需要深刻领会其义的两点内涵:“虚则虚到底”是在“耳目传闻”的“目前之事”的“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创作的;“实则实到底”讲究古事“班班可考”,但并不排斥为求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的必需的虚构想象的描写。
最后附带说说所谓的“实录”。在晚明清初时期,出现了一批称为“实录”的传奇,如明朱濑滨的《鸾笔记》,吕天成评曰:“记江陵夺情,郑、赵诸公廷杖时事,语多凿凿,可称实录。”[33]又明王应遴的《清凉扇》,祁彪佳评曰:“此记综核详明,事皆实录。”[34]吴伟业评清李玉的《清忠谱》曰:“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35]又有影响更大的清孔尚任的《桃花扇》,作者在“本末”中亦道:“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并专附“考据”一文,表示事出有据。然而,孔尚任在“本末”中亦道:“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又在“凡例”中说:“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笔。”可见,作者在写作中也杂取宏光遗事,因其新奇而加渲染成戏,为了戏剧情节的需要也可以在细节描写中加以点染。作者在主要情节和大关节目上尊崇史实,而在李、侯爱情的描写和宾客穿插的言行上进行了必需的虚构描写。无论是前者或后者,作者皆倾注了个人的爱憎感情和寄寓着感叹兴亡之意,作者并未用史学家笔法实录,而是用戏剧家笔法构造戏剧。作者的好友顾彩说得很在理,曰:“斯时也,适然而有却奁之义姬,适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适然而事在兴亡之际,皆所谓奇可以传者也。彼既奔赴腕下,吾亦发抒其胸中,可以当长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吊零香断粉,可以悲华屋邱山,虽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无所避忌者,然不必目为词史也……而桃叶却聘一事,仅见之与中丞一书,事有不必尽实录者。作者虽有轩轾之文,余则仍视为太虚浮云,空中楼阁云尔。”[36]此类概称“实录”的传奇,实际上乃是“实多虚少”,以“实”“尚存梗概”,大关节目“班班可考”,以“虚”“略施丹垩”,或有“损益缘饰”;从作法上讲,乃与李渔所谓的“实则实到底”的原则是一致的,亦并不排斥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原理。
注释:
[1] (明)陈邦俊编:《广谐史》,《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6辑。
[2] (明)胡应麟:《庄岳委谈》,《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明万历刻本。
[3] 同上。
[4] (清)焦循:《花部农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第226页。
[5] (清)焦循:《剧说》卷五,同上,第192页。
[6] (清)李调元:《剧话》卷下,同上,第52页。
[7] 王国维:《曲录自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页。
[8] (明)谢肇淛:《五杂俎》,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
[9] (明)汤显诅:《牡丹亭题词》,《汤显祖集》二,诗文集,第1093页。
[10] (明)茅元仪:《批点牡丹亭记序》,明泰昌朱墨刻本《牡丹亭》。
[11] (明)梅孝己:《洒雪堂小引》,明末墨憨斋刊本《洒雪堂》。
[12] (清)凌廷堪:《论曲绝句》自注,《校礼堂诗集》卷二。
[13] (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第16页。
[14] (清)李渔:《闲情偶寄·演习部》,江巨荣、卢寿荣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5页。
[15] (清)梁廷枏:《曲话》卷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第268页。
[16] (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47页。
[17] 参阅(宋)灌圃耐得翁:《都成纪胜》,其论皮影戏之情节“大抵真假相半”,论傀儡戏之情节“大抵多虚少实”,清初曹寅《楝亭藏书十二种》。
[18] (明)胡应麟:《庄岳委谈》,《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明万历刻本。
[19] (明)吕天成:《曲品》卷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第209页。
[20] 同上,卷下,第226页。
[21] (明)张琦:《衡曲麈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270页。
[22] (明)吕天成:《曲品》卷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第231页。
[23]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第80页。
[24] 同上,第12页。
[25] 同上,第45页。
[26] (明)阮大铖:《春灯谜记自序》,明末刊本《十错认春灯谜记》。
[27] (明)王思任:《春灯谜记叙》,明末刊本《十错认春灯谜记》。
[28] (明)谢肇淛:《五杂俎》,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
[29] (明)胡应麟:《庄岳委谈》,《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明万历刻本。
[30] (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54页。
[31] (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审虚实”,《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第20页。以下李渔语皆出于此节。
[32] 同上,“音律第三”,第35页。
[33](明)吕天成:《曲品·新传奇》,清抄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未著录。可参阅吴书荫《曲品校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3页。
[34]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能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第48页。
[35] (清)吴伟业:《清忠谱序》,清顺治年刻本《清忠谱》。
[36] (清)顾彩:《桃花扇序》,别署梁溪梦鹤居士,清康熙年刻本《桃花扇》卷前。
责任编辑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