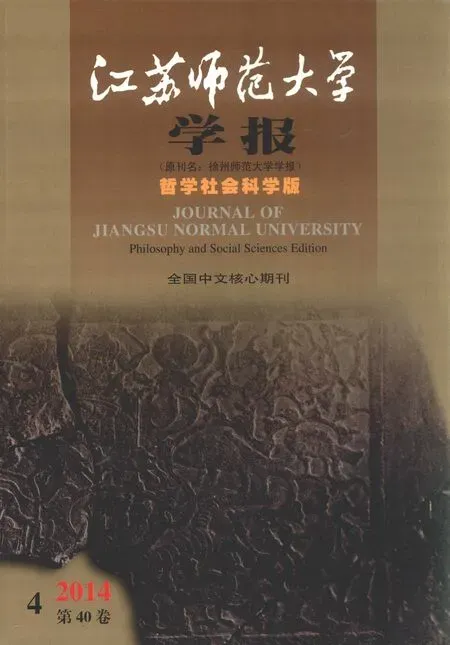论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
2014-04-17朱庆葆刘
朱庆葆刘 霆
(1.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 210093;2.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38)
论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
朱庆葆1刘 霆2
(1.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 210093;2.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38)
国民政府;中华国民拒毒会;禁烟运动
禁烟是近代涉及公众利益的一项事务。1924年,中华国民拒毒会的成立,体现了民众对于公共事务的结社自由。该会以《拒毒月刊》作为舆论调节机制,营造出政权系统之外的立言空间,并以拒毒运动周作为发动群众、领导禁烟运动的平台。就国民政府而言,无论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还是领袖孙中山的“拒毒遗训”,都必须承担肃清烟毒、建设国家的任务。随着统治的稳固,国民政府亦逐渐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组织控制。毫无疑问,中华国民拒毒会成为其必须谨慎面对的公共力量。但平衡禁烟与财政的关系却并非易事。由于党国体制的设计,国民政府须以主角的身份控制禁烟运动的规模与节奏,故其一味强调领导权,极力控制民众行为,而忽视社会的禁烟需求与动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的失范。而中华国民拒毒会在与国民政府短暂合作之后,亦以解散而告终。
近代中国,鸦片泛滥成为国家衰败与民族耻辱的象征。在“亡国灭种”的民族主义语境之下,民众始终是禁烟运动中最基本的社会力量。由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国人政治参与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因此民众对禁烟运动的参与、监督便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众广泛参与的背后,始终未脱离禁烟社团的组织发动与推波助澜。1924年,中华国民拒毒会(以下简称拒毒会)的成立是民间禁烟资源的一次成功整合,它利用日益发达的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渠道和交流平台,迅速掌握禁烟的话语霸权,营造了独立于政权系统之外的立言空间,成为民间禁烟运动的领导组织。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无论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还是领袖孙中山的“拒毒遗训”,都必须承担彻底清除烟毒、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因而,拒毒会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公众力量。但双方的价值诉求显然存在着历史滞差。国民政府希望将拒毒会纳入政权体制之内,加以引导和控制。拒毒会亦希望在政府的领导之下推动禁烟工作。但社会监督的角色定位却使其与政府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而终致解散。国民政府的禁烟运动亦因此失去与基层的紧密联系,难以实现全面的社会动员和整合。而民众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一旦被堵塞,也就失去了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若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分析拒毒会的命运,则尤显历史的耐人寻味。
一、拒毒会的成立及主要活动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鸦片成为国家分裂与军阀混战的渊薮。日益严重的烟祸使得民间拒毒运动不断发展,晚清以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地禁烟组织开始呈现出规模化的联合趋势。当其时,毒品问题亦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1923年12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成立“鸦片及其他毒品顾问委员会”[1],作为国际间讨论共同限制毒品生产、分配和输出的主要机构。该委员会决定于1924年召开国际禁烟会议,讨论远东鸦片及世界毒品问题[2]。为有效整合国内禁烟力量,并向国际社会表示中国民众的禁烟决心,1924年8月5日,中华高等教育会、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中华教育改进会、环球中国学生会、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卫生教育会、男女青年会、上海总商会、日报公会、律师公会、红十字会、全国医药会、世界佛教居士林、万国拒土会等30余家民间团体,以“肃清国内鸦片之种植、国外鸦片及一切复制毒品之输入”为宗旨,在上海参与发起组织拒毒会。此后,上海图书馆协会、上海留美同学会、上海理教联合会、中华妇女协会、国民对英日外交大会、救国联合会、基督教救国会等组织亦先后参加进来[3]。
拒毒会的活动以舆论宣传、毒况调查及组织拒毒运动周为主。就宣传而言,1926年之前,拒毒会尚没有自己的舆论阵地,一切通知、公告、宣言等均利用《申报》、《大公报》等已经较为成熟的报刊发出。1926年,拒毒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拒毒月刊》。该刊发行后,其销量不断增加,三年内即达到20万份[4],成为拒毒会“发挥言论宣传事业的先锋”[5]。除此之外,拒毒会还出版英文《拒毒新闻周刊》、《拒毒季刊》、《中国烟祸年鉴》等,其宣传声势及影响极为广泛。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力量对国家或政府的调节作用恰恰是通过公共舆论来实现的。从《拒毒月刊》等刊物的发行数量可见,拒毒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公共舆论这一调节机制。毒况调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利用各地的拒毒分会、同志社及其他民间团体,向群众广发调查表格,调查各地流毒实况[6];二是派员亲自到各地调查。如拒毒会干事戴秉衡曾独自前往东北,深入日租界,完成《东北烟况实祸》的报告[7]。持续的毒况调查,使得拒毒会掌握了充分的数据,权威的信息成为其凝聚公信力的基础。拒毒会最有影响力的活动是“拒毒运动周”。从1926年开始,其将每年的10月1日至7日,定为“拒毒运动周”,以此宣传拒毒主张,造成拒毒舆论。在运动周内,拒毒会积极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参与其中。如《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等中西报馆均响应运动,发行拒毒特刊;各游戏商场亦特编拒毒戏剧等节目;各影戏剧院加映拒毒幻灯影片;各大中小学校亦纷纷进行拒毒宣传及演讲比赛等[8]。“拒毒运动周”为拒毒会提供了发动群众、增强影响力、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舞台,拒毒会亦始终以主导者的角色控制着运动的规模及步骤。
随着全国禁烟形势的发展,拒毒会的组织规模日益扩大,从1924年的188个分会发展到1930年的450个分会[9]。在组织关系上,该会成立之初,各地分会与上海总会是一种合作关系[10]。而1930年,总会对各地分会及拒毒同志社进行了整合,将原有同志社一律改组为“拒毒宣传会”,置于总会的领导之下。同时,总会还派员赴南洋开展拒毒运动,并先后在新加坡、爪哇等地组织分会[11]。可见,20世纪30年代的拒毒会是在海内外均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团体。
禁烟运动是近代中国涉及公众利益的一项事务,故拒毒会始终以“督促政府严厉禁烟”为己任[12]。1925年4月,北京政府内务部提议鸦片公卖。拒毒会通电号召全国各界一致反对,并致函国务总理顾维钧,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13]。10月,鸦片公卖之说再起,拒毒会又电请段祺瑞“明令遏止”。压力之下,北京政府终于“取消是议”[14]。凭藉舆论与政府博弈而取得的胜利,为拒毒会的进一步参与政治集聚了资本。善后会议期间,拒毒会应邀派代表赴京,明确要求政府允许其对禁烟工作“贡陈意见,俾资采择”[15]。而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亦在南方日趋崛起,并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进行着一场北伐革命战争。无论是党国体制的设计,还是政权合法性的建设,国民政府都必须有效地控制全国的民众运动及社团组织,务求成为禁烟运动的领导者,而非以配角的身份追随着运动的方式与节奏。
二、短暂的合作
1924年11月,孙中山赴京参加善后会议。12月4日抵达天津,次日与各团体代表举行茶会[16],并向参会的拒毒会成员表达了其对于禁烟的态度:“鸦片营业绝对不能与人民所赋予权力之国民政府两立,中国之民意,未有不反对鸦片,苟有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鸦片之恶势力表示降服者,均为民意之公敌。对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苟负责之政府机关为自身之私,便对鸦片下旗息战,不问久暂,均属卖国之行为。欲达禁烟之目的,必须由国民政府采定全国一致遵守之计划,但在军阀未经打倒,民治政府未能统一全国以前,拒毒团体须奋斗不懈,千万不可放弃坚忍与不妥协之奋斗决心,永远抱定彻底不降服之政策。”[17]此即所谓的“总理拒毒遗训”。这是国民党领导人与拒毒会的第一次接触,并就禁烟问题首次交换了意见。不容忽视的是,孙中山在代表国民党表达禁烟态度的同时,亦婉转地表明:待国民党统一全国之后,自应由其来主导全国的禁烟运动。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拒毒会设宴招待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特务处长杨虎等人,明确表达了“青天白日旗所到之处,拒毒事业即开新局面”的希望[18]。对于拒毒会的盛情款待,国民党持谨慎的态度,陈群、杨虎及上海市党部等机构仅派出代表赴宴。尽管代表们均表示愿尽力赞助拒毒运动[19],而实际上,此次宴请中拒毒会并没有得到新政府关于禁烟的任何承诺。
1927年4月及6月,拒毒会分别向武汉及南京政府呈递请愿书,表达其彻底禁烟的主张,并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推行禁政[20]。此后,国民政府虽然出台了三年禁烟计划,但是负责相关事宜的禁烟处却隶属于财政部[21],此举有着明显的财政意图。8月,拒毒会召集上海各团体开禁烟联合会,禁烟处处长李基鸿在会上成为被抨击的对象。会议通过了针对国民政府的宣言,指责其鸦片专卖政策是违背民意、违背三民主义的祸国、卖国之行为,与旧军阀官僚无异。而拒毒会所凭藉的利器正是“总理拒毒遗训”,这使得国民政府十分被动。宣言还认为,在禁烟问题上“人民苟坐视而不顾,是人民失其为国民之天职。苟政府置民意于不顾,是国民政府已失其为人民所赋予权力之政府矣”[22]。显然,拒毒会对政府发难的法理依据来源于公民监督政府的现代政治逻辑。
此时,国民政府甫定南京,内部矛盾重重,对民众的驾驭更是力不从心,故其对待拒毒会这样的团体是十分谨慎的。11月24日,履任才1个月的财政部部长孙科[23],虽然为筹款之事焦头烂额,但还是电邀拒毒会派代表赴南京参加禁烟政策的讨论,拒毒会藉此再次提出组织禁烟委员会的建议,并要求将禁烟与财政分离[24]。拒毒会的要求,对需财孔亟的政府而言并不容易。12月6日,财政部次长郑洪年在与拒毒会代表钟可讬、黄嘉惠的商谈中道出实情:“目下禁烟计划,仅为筹款之计……本部屡思修改,因军费紧急,未遑计及。”[25]然而,此政府“苦衷”,并未见谅于拒毒会。
1928年1月,拒毒会再次敦促政府成立禁烟委员会,并召开全国禁烟会议。2月,又致函新上任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谓“以党治之政府,而征款及于鸦片,将留万古莫涤之恶名”,规劝政府“禁烟事业应认真从禁入手”[26]。3月,拒毒会又两次发动上海各社会团体召开禁烟促成会。国民政府在压力之下,派员赴上海与拒毒会会晤。显然双方并未达成一致,4月,国民政府新出台了禁烟法,拒毒会依然指责其为“寓禁于征”[27]。而此时禁烟当局又被暴出用“土贩之巨魁、漏网之毒犯”从事鸦片征税业务的丑闻[28]。拒毒会遂于5月1日再次发表宣言,要求“当局诸公,遵从总理遗训……采纳本会主张,切实禁烟,努力除毒”[29]。6月,拒毒会草拟了禁烟方案[30],并派出钟可讬、李登辉晋京与国民政府再次商组禁烟委员会[31]。钟可讬向全国经济会议提出拒毒会的禁烟方案。6月底,在舆论及民情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经过犹豫和观察,终于基本采纳了拒毒会的建议。此后黄嘉惠再次赴京,与内政部长薛笃弼及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会面,双方就今后的合作基本达成了共识[32]。7月18日,国民政府宣布撤销禁烟处,并颁布了《全国禁烟会议组织条例》及《禁烟委员会组织条例》。8月25日,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成立,拒毒会成员钟可讬及李登辉皆进入委员会的权力核心,钟可讬被选为常委,李登辉则任委员会副主席[33]。
禁烟委员会的成立为国民政府与拒毒会的合作提供了组织机制。国民政府藉此将拒毒会纳入体制内,从而便于管理和控制,同时亦获得拒毒会所拥有的道德合法性及民众的支持。此后,国民政府对拒毒会的各项活动都尽可能地给予方便和支持。如对拒毒会之宣传人员及所贴之宣传品,皆“通令所属一体保护”[34]。在“拒毒运动周”中,各地方政府及党部,或对拒毒会成员“妥为保护”[35],或召集当地各公团举行拒毒运动,以资响应[36],或训令税捐各局卡,对于拒毒会所制之拒毒影片一律免税放映[37]。此外,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拒毒会之普及拒毒教育亦积极配合[38],并多次饬令或发函要求各学校支持拒毒会举行的拒毒论文比赛[39]。对于《拒毒月刊》,国民政府更是支持订阅。拒毒会曾函请各省政府通令所属行政机关一律订阅[40]。此后,中央各部委、江苏、浙江、福建、云南等大多数省份皆通令所属各机关按月订购[41]。这不但扩大了《拒毒月刊》的影响力,同时亦在经济上给予拒毒会大力支持。
拒毒会亦希望通过加入禁烟委员会,强化其政治力量,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政策影响力。因此,其亦尽可能地与政府保持一致。在政府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若涉及禁烟禁毒的宣传,拒毒会总是派出代表到场演说,显示出对国府的拥护和支持[42]。在国际会议及外交纠纷中,拒毒会亦始终积极地利用其国际影响力为国民政府的政策进行宣传。如1927年,拒毒会向国联请愿,请国联顾问委员会采用中国政府禁绝鸦片的原则,责成各国政府限期肃清烟毒[43];1928年,拒毒会致函外交部长黄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为政府提供了日内瓦禁烟大会上极为需要的资料。对此,黄郛亲自给李登辉及钟可讬回信表示感谢[44];在日内瓦禁烟会议上,“远东鸦片调查团”禁止中国代表参加,且不调查鸦片以外的其他麻醉毒品。为抵制这一不公平的调查,拒毒会公开发表《反对调查远东鸦片宣言》,与政府几乎在同一时间采取了抗议行动[45];1929年,国联副秘书长艾文诺来华,拒毒会设宴欢迎,积极宣传中国的禁烟政策,并指出治外法权及租界对中国政府禁政的影响[46]。拒毒会还拟具了对国联的说帖,请艾文诺转交国联秘书厅。经过艾文诺的努力,该说帖被西方各大报刊转载,国际舆论开始同情中国,支持中国政府的禁烟主张[47]。但国民政府难以真正摆脱鸦片利税的诱惑,且随着其统治的稳固,亦开始加强对民间团体的组织控制。这些均构成了国民政府与拒毒会合作的潜在危机。
三、拒毒会的解散
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控制禁烟运动的努力。禁烟委员会成立后,即明确其为“督理全国禁烟事宜的机关”[48],并试图以规范化的方式对民间禁烟运动进行管理。1929年6月3日,乃虎门销烟90周年纪念日。为了继承该事件所赋予的民族主义象征,树立政府权威,行政院规定每年6月3日为禁烟纪念日,但要求全国在政府的指导下统一活动。为此,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拟具了宣传纪念日办法,并经国务会议议决通过。作为全国必须遵循的规范,该办法对禁烟日当天全国党政军机关、各团体、学校、工厂、商店等的纪念仪式、程序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典礼仪式分为11个步骤,其细致程度甚至包括国旗、党旗的悬挂,默念及奏乐的时间等[49]。此外,由于焚毁毒品始终是禁烟运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项程序,禁烟委员会于1930年会同内政、卫生、工商三部拟定了焚毁鸦片及麻醉毒品条例草案,并经行政院议决通过,使得“这项最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最易失控的活动在政府所容忍的社会秩序内进行”[50]。对于民间个人及社会团体所筹设的戒烟所,国民政府亦试图加以规范及领导,规定:凡个人及社团创设戒烟所均须先呈由该管市县政府呈请主管机关核准转禁烟委员会备案方准设立;在该管市县政府指导监督下办理戒烟事务;一切设施悉依照市县立戒烟所章程之规定办理;应有三千元之准备基金;每日戒烟人数、性别、年龄、职业、所用药剂,及戒除结果应每三个月终列表汇报该管市县政府呈送主管机关转禁烟委员会备案[51]。该规定于1930年11月经行政院核准公布。值得注意的是,“六·三纪念日”虽经行政院明定日期,但并未列入正式纪念日程之内。当时国民政府的正式纪念日有识字、造林、筑路、卫生、保甲、合作、提倡国货等七项运动,均处于中央党部的有效指导之下。禁烟委员会于1930年2月呈请中央党部,要求于此七项运动外加入禁烟运动一项,将每年6月3日列为正式纪念日[52]。但此项建议未获批准。或许国民政府并不想给禁烟运动以更高的政治地位,亦或许国民党中央党部对能否有效控制禁烟运动亦缺乏信心。
在国民政府加强对禁烟运动控制的同时,鸦片公卖的主张又开始抬头。1931年年初,禁烟委员会委员、拒毒会成员伍连德发表《流毒已极之鸦片问题》,公开呼吁实行鸦片公卖,用15年的时间完成鸦片禁绝,并认为这才是一条根本现实的道路,否则于事无补,反而会将烟祸愈演愈烈[53]。伍连德是公共卫生专家,又是拒毒会的高层骨干,其公开鼓吹鸦片公卖,使得拒毒会极为被动。在就此事函询禁烟委员会,并得到否定答复后,拒毒会发表宣言,认为鸦片公卖“乃政治、道德之总破产”,必将导致政治退化、政权混乱等严重后果。拒毒会在宣言中指出:“伍连德不但违反本会整个之主张,亦违反其个人素来之主张”,并郑重声明“对伍氏个人之言论,绝对不表同情也”[54]。之后,拒毒会浙闽津哈各分会亦发表反对鸦片公卖意见,并请政府宣布禁烟政策,彻底肃清烟祸[55]。而此时国民政府却派出李基鸿赴台湾调查鸦片公卖制度。显然禁烟委员会的答复并不可靠,鸦片专卖亦非空穴来风。拒毒会再次发表宣言,谓“今苟自行施行专卖,则前之反对外人纵毒牟利以割国人者,今乃取而自行之以残杀同胞,是不啻自挝其颊,可耻之事,孰甚于斯”。2月13日,拒毒会名誉主席唐绍仪召集常务委员会,讨论应急方案,14日发表公函,谓“财政部近竟派员驰赴台湾,调查当地公卖制度,意在仿行……敝会本总理遗训,抱拒毒决心,对此祸国殃民之鸦片公卖政策,议决反对到底”。并决定19日下午“假天后宫桥堍上海市商会,举行各界联系会议,妥筹应付良法”[56]。在拒毒会的号召下,上海各团体呈请中央制止鸦片公卖,认为政府种种之事实,“实与决心禁烟有背道而驰之现象,不但多年烟禁费于一旦,而国际禁烟之条约、国民党禁烟之党纲、总理拒毒之遗训、第一次全国禁烟会议议决,均将完全违反……用敢集合公意吁请纠正,对于鸦片麻醉药品之毒害,雷厉风行,彻底禁绝,全国人民愿为后盾”[57]。
在拒毒会引导的强大舆论攻势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否认鸦片公卖的说法。但随后发生的“白案”成为双方关系的转折点。1931年3月中旬,黄嘉惠与其妻白芝英赴台湾考察鸦片专卖制度。当他们到台湾时,上海媒体却报道了香港海关发现白芝英的行李夹带毒品的事情。3月21日,拒毒会常委会举行会议,电召黄回沪申明真相。在真相未明之前,由王景岐、李登辉、钟可讬等人代理黄的事务[58]。4月3日,黄氏夫妇抵沪[59]。4日,拒毒会常委会听取黄的报告后发表声明:“经本会各委员详细查询,多方研究之结果,认为白女士事件之谣言无据”[60]。随后,黄嘉惠亦发表声明,认为“此事全无根据。予等此次并未赴港,有护照上基隆警察署印章为证……鄙人从事拒毒多年,触忌各方,树敌甚多,被人陷害,早在意料之中……谋我者之处心,其目的非仅在内子及鄙人已也”[61]。白芝英亦公开表示现已获得诬陷之证据甚多,在必要时将择其公表,以明真相”[62]。与此同时,禁烟委员会派员赴香港调查,并由外交部照会英使,饬令香港海关将查获经过详细答复[63]。而黄嘉惠亦委托上海古沃公馆海礼思律师及香港威更生律师向香港政府调查此案。4月15日,香港海关证明,“近来并未查获任何私运吗啡案件与中国妇女有关系者”。而威更生的调查结果亦显示“并未得有白芝英医师私运吗啡之任何证据”[64]。事情至此已经真相大白,由于黄本人为国民党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十八分部的预备党员,该党部亦认为黄系被诬陷[65]。此后拒毒会的职员全体声明,要求政府查办诬告人[66],并致函各组织团体,要求公众主持公道,施以援手[67]。辽宁、天津、太原、福州、兴化、杭州、苏州、新加坡、巴达维亚、金华、溧阳、济宁、哈尔滨、西安、成都等地拒毒分会,纷纷要求当局查办诬陷之人[68]。
此案的结局最终不了了之,但拒毒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却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似乎“白案”的发生并非一个孤立事件。之后,拒毒会的财源及黄嘉惠本人的安全均受到威胁[69]。由于党政机关不再积极支持《拒毒月刊》的订阅,1932年后该刊的发行数量明显减少。此外,“拒毒运动周”亦改称为“拒毒宣传周”。显然,该运动的地位开始降低。且各地国民党党部在运动中逐渐取代了拒毒会的主导地位。如1935年1月,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拒毒宣传周。宣传周的活动与拒毒会所主持的拒毒运动周的形式十分类似,亦由拒毒标语、电影、传单、演讲、集会等项组成,但运动的主角已经不再是拒毒会[70]。1936年4月20日至26日,上海市党部亦完全主导了拒毒宣传周的开展。宣传周的形式亦仿照运动周,但筹备会却由市党部、市政府、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市禁烟委员会等11个部门组成,拒毒会仅是其中1个,且筹备会的地址亦设立在市党部[71]。可见,即使在拒毒会最有影响力的上海,国民政府对禁烟运动的控制亦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但拒毒会毕竟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及强大舆论力量的民间社团,故国民政府始终希望其能够与政府合作,支持政府的“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抗战前,双方似乎有过接触,国民政府承诺向拒毒会提供资金,但要求其活动只限于拒毒教育及调查日人在中国的毒品犯罪[72]。双方的沟通过程虽不得而知,但1937年6月,《拒毒月刊》停止发行,拒毒会最终以解散的方式表达了其坚决不向政府妥协的态度。
四、结语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将党纲中群众运动的内容作了调整,使其地位大为降低,并通过了“改组中央党部案”,将“民众运动委员会”改名为“民众训练委员会”[73]。可见,随着国民政府统治的稳固,其逐渐加强了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及控制。就禁烟运动而言,国民政府希望将其作为一项最高决策自上而下地推行,因此其设定一系列的范畴,以便将禁烟运动的方式标准化、规范化,使得全国任何团体、组织的纪念活动都必须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国民政府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前,禁烟运动就已经是一项成熟且影响广泛的社会运动,其得以存在的活力正在于广大民众的认同和参与。一方面,拒毒会固然承担着运动的领导角色,使得国民政府在驾驭社会力量时面临着不小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拒毒会亦成为沟通基层民众与政府政策的一个桥梁。此种作用,国民政府本可更好地加以整合和利用。遗憾的是,国民政府一味地强调禁烟运动的领导权,而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影响和需求,在打压拒毒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一整套严密、自控型的禁烟管理机构,希望以此来控制运动的开展,并自上而下地建构政府与社会的沟通渠道。此种模式,使得基层社会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活力,从而限制了禁烟运动的社会基础。
[1]罗运炎:《国际禁烟沿革》,《时事月报》,第13卷第1期,1935年7月,第33页。关于该组织的名称,国内报刊译为“国际禁烟会议”,而官方文件一般译为“国际禁烟顾问委员会”(见孟鞠如:《国际禁烟与中国》,《外交评论》,1937年第4期)。
[2]夏奇峰:《国际禁烟大会之筹备及其草案》,《东方杂志》,第21卷第20号,1924年10月25日。
[3]罗运炎:《中国烟禁问题》,兴华报社,1929年版,第112页。
[4][12]《拒毒会发行月刊》,《申报》,1929年10月27日。
[5]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26年创刊号。
[6]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26年第3期。
[7]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30年第42期。
[8][22]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27年专号。
[9]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31年第41期。
[10]《中国国民拒毒会分会组织大纲》,《真光》,1924年第11期。
[11]黄嘉惠:《最近一年之拒毒运动》,《时事年刊》,1931年第1期。
[13]《拒毒会反对鸦片公卖》,《申报》,1925年5月8日。
[14]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25年第5期,。
[15]《中华国民拒毒会提出善后会议关于禁烟问题之建议案》,《时兆月报》,1925年第9期。
[16]《中山大学学报》编委会:《孙中山年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128页。
[17]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孙中山全集》(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2页。
[18]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27年第11期。
[19]《拒毒会欢宴政治部代表》,《节制》,1927年第5期。
[20][24]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27年第16期。
[21]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23]刘寿林等:《中华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24页。
[25][27]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93、198页。
[26]《拒毒会概呈禁烟计划》,《兴华》,1928年第6期。
[28]《拒毒会宣言》,《卫生报》,1928年第21期。
[29]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28年第22期。
[30]《拒毒会的禁烟议案》,《财政旬刊(汉口)》,1928年第9期。
[31]《李登辉钟可讬晋京商组中央禁烟委员会》,《申报》,1928年6月4日。
[32]《五中全会之禁烟提案——拒毒会提出十大纲领》,《申报》,1928年7月1日。
[33]行政院禁烟委员会:《全国禁烟会议汇编》,1928年,第1-32页。
[34]《令民政厅饬属保护拒毒会宣传人员由》,《河北省政府公报》(命令),第123期,1928年12月1日。
[35]《民政厅训令第208号》,《浙江民政月刊》(卫生及禁烟),第28期,1930年3月20日。
[36]《令各县长召集各公团举办拒毒运动》,《河北省政府公报》(训令),第395期,1929年8月30日。
[37]《财政厅训令》,《河北省政府公报》(指令),第476期,1929年11月19日。
[38]《教育厅训令第681号》,《云南教育周刊》,第1卷第20期,1931年8月12日;《教育部令饬各校学生参加拒毒论文比赛》,《湖北教育厅公报》(中央消息),第2卷第6期,1931年3月31日;《暨南校刊》,1933年第83期。
[39]《暨南校刊》,第184期,1936年;《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164期,1936年。
[40]《请各省推销月刊》,《真光》,1929年第11期。
[41]《按月订购拒毒月刊》,《江苏省政府公报》(杂述),第290期,1929年11月18日;《民政厅训令第二六九号》,《浙江民政月刊》(公牍),第25期,1929年12月20日;《厅令拒毒月刊应径向订阅》,《福建省政府公报》(民政),1933年第354期;《饬令各机关订阅拒毒月刊》,《云南民政月刊》(民政),1936年第25期。
[42]《市党部举行国耻纪念会》,《上海党声》,1929年第26期。
[43]《中华国民拒毒会向国联请愿》,《申报》,1927年10月10日。
[44]《函中华国民拒毒会一件》,《外交公报》(文书),1928年第2期。
[45]行政院禁烟委员会:《全国禁烟会议汇编》(一),1928年,第49页;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28年第25期。
[46]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29年第29期。
[47]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1932年第59期。
[48]《禁烟法施行条例》,《北平市市政公报》(法规),1928年第4期。
[49]《禁烟公报民国十九年汇编》,1931年3月,第32-33页。
[50]《训令第三一九五号令》,《行政院公报》(训令),第184期,1930年9月10日。
[51][52]《禁烟公报民国十九年汇编》,1931年3月,第38-39、45 -46页。
[53]《流毒已极之鸦片问题》,《医药评论》,1931年第52期。
[54]《拒毒会反对鸦片公卖》,《兴华》,1931年第6期。
[55]《拒毒会反对伍连德》,《公教周刊》,1931年第96期。
[56][57][64]《中华国民拒毒会反对鸦片公卖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
[58]《常委会对白案之议决案》,《申报》,1931年3月22日。
[59]《黄白赴台湾查烟返沪》,《申报》,1931年4月4日。
[60]《常委会对白案之声明》,《申报》,1931年4月5日。
[61]《黄嘉惠之声明》,《申报》,1931年4月8日。
[62]《白芝英不承认贩毒物》,《申报》,1931年4月7日。
[63]《禁烟会调查贩土案》,《申报》,1931年4月4日。
[65]《白芝英贩毒系被人诬陷》,《申报》,1931年4月15日。
[66]《拒毒会职员要求查办白案诬告人》,《申报》,1931年4月29日。
[67]《拒毒会致函组织团体》,《申报》,1931年4月24日。
[68]《各地拒毒会对白案之表示》,《申报》,1931年5月29日。
[69][72][加]卜正民、若林正编著:《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弘侠译,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86、288页。
[70]《市党部主办拒毒宣传周》,《卫生月刊》,1935年第6期。
[71]《拒毒宣传周》,《上海党声》,1936年第8期。
[73]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19页。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
ZHU Qing-Bao1LIU Ting2
(1.History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jing 210038,China)
National Government;the 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anti-opium campaign
In modern history,the anti-opium campaign involves the public interest.In 1924,the 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This reflected the people'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It used the media and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anti-opium movement.A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whether the ruling party's ideology,or the leader Sun Zhongshan's"anti drug teachings",it must take the tasks of eliminating opium and building the comtry.But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i-opium and the public finance ws not easy.The national government emphasised leadership trying to control people's behavior,but ignored the social demand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anti-opium campaign,resulting in the twis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the society.The 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 also ended in dissolution.
K262
A
2095-5170(2014)04-0065-07
[责任编辑:刘一兵]
2014-03-16
朱庆葆,男,江苏句容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霆,男,江苏如东人,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