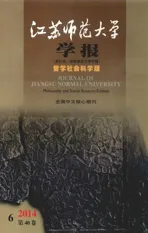可选择现代性与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道路哲学逻辑之论
2014-04-17曹典顺
曹典顺
(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江苏徐州 221116)
可选择现代性与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道路哲学逻辑之论
曹典顺
(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江苏徐州 221116)
现代性;可选择现代性;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道路;哲学逻辑
现代性不是一个既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可以有多种内涵,在本质上具有可选择性。正因为现代性具有可选择性,现代性也才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现代性依然可以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哲学原则之一。可选择现代性本质上是一个具有辩证发展逻辑的现实存在,其辩证发展逻辑在本质上表现为现代性的差异性和时代性。现代性的差异性是指现代性本质上是可选择现代性,现代性的时代性是指现代性具有与所表征时代相一致的绝对性。中国道路的哲学确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现代性两个基本特征的诠释,即可选择现代性奠定了中国道路的现代性前提,中国新现代性表征了中国道路的哲学逻辑。
近年来,尤其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建设问题(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被视为最重要的国策。之所以如此,与中国哲学家们的努力是不可分割的。比如,早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联合主办的第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就是以“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为主题。这就是说,在中国哲学家的思想深处,中国道路与现代性密切相连。那么,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左右中国道路呢?谈及现代性,人们无法回避笛卡尔和卢梭两位哲学家。因为,笛卡尔被人们视作现代性的发现者,卢梭则被视为开启现代性批判的著名哲学家(注: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著名哲学家)。那么,为什么说是笛卡尔发现了而不是说笛卡尔创造了现代性呢?
众所周知,现代性已经成为了一个哲学概念——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原则。这就是说,人们已经普遍认可,现代性是社会发展中的内在逻辑,只能被认识而不能被创造。那么,既然现代性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什么卢梭、黑格尔、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鲍曼等哲学家还要前赴后继地批判和反对现代性呢?尤其是齐格蒙·鲍曼,还要把现代性视为导致奥斯维辛大屠杀这种惨剧的根源呢?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道路还不可回避现代性呢?要想阐释清楚以上这些问题,只能从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和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的理解中寻求答案,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既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即在本质上可以有多种内涵,或者说是一个“可选择性”的事物——“可选择现代性”。从此种意蕴上理解,现代性可以分为可选择现代性和传统现代性,中国新现代性只是诸多可选择现代性形式中的一种,是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哲学逻辑。
一、现代性: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原则
从19世纪中叶或更早时期起,伴随着启蒙运动兴起的现代性理念和现代性思维,在持续的鲜花以后,不断承受着激烈或强烈的批判。从鲜花层面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即使不知道笛卡尔及其现代性思想,但有相当多的人都知道表征笛卡尔现代性思想的名句——“我思故我在”。从批判层面看,人们把对社会发展的不满,主要归咎为现代性的后果,最为经典的一个事例是,人们认为现代性带来了火车,但火车带走了儿子。不论批判者如何批判,甚至批判者将自己视为后现代性哲学家——以表达自己对现代性的不满,但后现代性依然不能摆脱现代性,它的内涵超越不了现代性所能蕴含的边界。当然,人们现在论及的现代性,除非特别说明,已经不再指代传统现代性,而是指代可选择现代性,即现代性可以存在不同的范式,包括各种后现代范式(如建设性后现代,等等)。正是因为可选择现代性的边界宽泛,所以现代性依然可以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哲学原则。
现代性反对蒙昧,而反对蒙昧依然是当下时代的任务。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是一起成长起来的两个社会发展意蕴上的范畴,现代社会以反对蒙昧为开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社会开始于17、18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时。当然,这是指欧洲意蕴上的现代社会,而中国的现代社会则开启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日本的现代社会则开启于明治维新运动时期,等等。也就是说,从时间意蕴上看,现代社会开启于17世纪,从空间意蕴上看,现代社会则没有同一的开始时间。现代社会的开启,是以作为哲学原则的现代性为理论前提的。在现代社会以前,社会处在封建的蒙昧状态,欧洲称之为中世纪。因此,现代性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要启蒙,即引导人们摆脱黑暗的时代。至于当下时代,显然是现代社会。那么,处于当下时代的现代社会为什么要反对愚昧呢?众所周知,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许许多多愚昧的东西都通过书籍等具有文字和图画标记的传承物记录了下来,这就使得许多人因受教育的方式及其程度的影响不同而陷入不同的蒙昧状态。这即是说,虽然整体意蕴上的当下时代已经摆脱了蒙昧,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不再蒙昧,从现实生活世界看,许多人依然蒙昧,甚至十分蒙昧。比如,据美联社报道,在中非共和国2014年1月19日的一场抗议中,自称“疯狗”的基督徒聚众围殴落单无辜民众,并向对方身上泼洒汽油点燃烤肉吃。当然,在中国也不乏愚昧的事件,既有人们熟知的邪教组织和邪教活动,也有打着传统文化幌子的封建迷信活动,尤其是一部极具哲学意蕴的《周易》,被诸多现代人解读为能够占卜的灵异之物。
现代性提倡自由,而追求自由依然是当下时代的主旋律。从哲学内在逻辑看,现代性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崇尚主体性,因此,甚至可以称现代性哲学为主体性哲学,“说到底,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挥”[1]。在黑格尔看来,与主体性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自我意识”。现代性通过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即现代性通过借助对未来自由的许诺,为自己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存在找到了根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把自由原则列入了基本国策,许许多多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都不能与此原则相冲突,更不允许与之相悖离。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从国家层面看,中华民族为了争取自由、独立与尊严,坚决抵抗任何国外势力的欺凌和压迫;从个人层面看,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人们,都强烈地渴望自由的生存方式。从时间意蕴看,现代性自由经历至少有三大阶段,即追求精神自由时期、追求肉体自由时期和追求生存自由时期。在追求精神自由时期,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自我精神体验,即感受自由;在追求肉体自由时期,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肉体欲求,即对象自由;在追求生存自由时期,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人格平等,即尊严自由。当下时代,尽管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观明显不同,但对自由的态度没有改变,总体上属于从追求肉体自由向追求生存自由的过渡时期。因为,当下时代社会发展的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生存需求,生存意蕴上的尊严自由阶段远远没有到来,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的政府把能够让国民过上更为体面、尊严、舒适的生活,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比如,与信息化特征相适应的网络时代,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引导人们关注网络的言论自由,而不是限制人们的网络自由。
现代性相信理性,而崇尚理性依然是当下时代的思维方式。在文艺复兴的先驱们看来,社会之所以不能发展和进步,是因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具备也不相信理性及其力量。之所以如此,或许是遭受非理性统治的时代太过于长久,人们特别想呼唤一种发展和进步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人们想换一种生存方式。在哲学的帮助下,确切地说,是在主体性哲学的帮助下,经过思想、科学和技术的逐步联姻,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被催生并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这种意义上了解的启蒙就是理性主义的启蒙,或者说,理性是现代性的本质诉求。既然如此,科学和技术就不能停止发展,否则,社会就不能进步和发展,而不能进步和发展的社会是不符合理性主义要求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理论,因为,“在技术和科学这两种积累性的、发展进步的制度中,没有什么仍然是坚固的。新的技术应该不断取代老的技术。从一个方面说,合理化要求不断地用新的东西取代老的东西。‘进步’一词也意味着不断用新的东西取代老的东西。如果科学和技术停止发展,现代世界将会崩溃”[2]。当下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刻也不能停止发展。为此,经济哲学中发明了一个专门概念——滞涨。所谓滞涨又称滞胀,即经济停止发展、增长停滞。事实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不能停止发展,因为每一个领域都属于一个“社会消费”环节,如果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社会发展就将中断。邓小平在概括现代社会时曾经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是在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生产能力,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属于生产力的要素。邓小平之所以要把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看到了现代社会不能停止发展和创新的方面。或许会有人提出,当下中国发展阶段,已经不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初级发展阶段,而是“可持续发展”阶段。在我们看来,可持续发展阶段,本质上依然是“发展”阶段,而发展就是要用新的科学技术和思维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治理环境污染,应该通过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而不至于回到远古时代,即不能退回到没有工业文明的时代。所以,理性的发展理念应是当下的思维方式,当然,此理性已经发生变化,它已经在走向反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途中。
二、可选择现代性:中国道路的哲学可能性
既然现代性依然是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原则,那么,为什么诸多哲学家一方面反对现代性,另一方面又非常关注现代性呢?我们认为,齐格蒙·鲍曼从现代性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的关系中道出了该问题的本质。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现在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3]。鲍曼的观点很明确,现代性本身具有辩证的性质,后现代性哲学家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是现代性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否定整个现代性。劳伦斯·E·卡洪对现代性的辩证性本质给予了极高评价。在卡洪看来,“现代性不是拿一种目标或价值和另一种目标或价值做交易;它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要达到的目标或要获得的价值,在眼看着唾手可得之际,被暗中破坏了。转变成了对它自身的空洞的模仿。这个主张强劲有力。这个主张充满了真知灼见”[4]。在辩证现代性的理解下,对现代性的历程有着多样性的概括,有人将其称为流动的现代性,有人将其称为可选择的现代性或建设性现代性。我们认为,建设性现代性适合表征同一个实体国家的现代性历程,而不同的实体国家之间,最为恰当的表征还应该是可选择现代性。中国道路是相对美国道路、俄罗斯道路、德国道路等不同实体国家的发展道路,阐释其哲学可能性必然要从不同的实体国家角度,即从可选择现代性角度进行。而从可选择现代性的视角理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必然具有存在的哲学可能性。
可选择现代性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强调社会发展道路的差异性,这就为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中国特色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从一定意义上理解,传统形而上学亦可称之为独断论哲学,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有一个“同一性”的终极价值和终极目标。现代哲学的发展,尤其是后现代性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蕴上就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质疑。对这种研究成果,伽达默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甚至认为,20世纪哲学研究的最大成果就是对一切独断论所持的批判态度。哲学家们在反思形而上学,尤其是在反思现代性哲学时发现,“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5]。这就是说,在许多哲学家的哲学观念中,现代性并不像决定论者所预言的那样——会按照相同的发展方向产生、发展和变化,因为,它会受到主导文化观念的主体的制约。无论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还是从主体能动性的视角看,或许只能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才能感受到历史决定论的意义,但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中,主体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人决定的,而不同的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是极为不同的。比如,当今美国,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施政理念就有所差别;当今中国,既有坚持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流派,也有否定改革开放的左派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右派。既然作为社会发展道路确立者的主体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么,具体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必然因主体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中国道路的根本特征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世界价值,中国特色只是它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差别所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归根结底是要走向世界价值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道路将成为世界道路,而是指无数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最终会趋向于世界道路。
可选择现代性最为重要的本质是强调对传统的批判性,这就为中国道路所具有的创新本性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追溯哲学史,现代性不是开始于笛卡尔,而是开启于古希腊时期。按照阿格尼丝·赫勒的理解,“现代性的动力首先出现在民主鼎盛时期雅典城邦的欧洲自传里。苏格拉底和智者是重要的演员,他们在行动和思想两方面体现了这种动力。传统受到质疑。被认为真实、神圣、理所当然的信念如今被质询和检验。曾经被认为真实的东西如今被认为是不真实的;曾经被认为正确而加以接受的东西如今被认为是错的”[6]。事实上,此后开启的现代性依然秉承着这种反传统的现代性。也正因如此,可选择现代性不可超越现代性,但可选择现代性却又与传统现代性理论的确不同。即使在反对传统的问题上,可选择现代性也有着三层意蕴上的特点:其一,可选择现代性坚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反传统道路,而不是彻底意蕴上的反传统;其二,可选择现代性坚持人本意蕴上(或称文化意蕴上)的反传统,而不是科学技术意蕴上的反传统;其三,可选择现代性坚持可持续发展意蕴上的反传统,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意蕴上的反传统。可选择现代性的这些特点,恰恰与中国道路的创新本性相一致。众所周知,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学界并不能完全达成共识,所谓的“北京共识”,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反对中国道路观念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认为中国道路还只是发展中的道路,没有可以推广的意蕴。但我们不认可这种看法。中国道路的确是发展中的道路,但没有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固化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相同的本性,即保持旺盛的创新能力是其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可选择现代性最为重要的信念是坚信社会发展道路的价值逻辑,这就为中国道路所具有的道路自觉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信念本来是指主体对某一问题坚定不移的态度,本文喻指现代性想要实现的目标。从这层意义上理解,现代性最为重要的信念与可选择现代性最为重要的信念明显不同。虽然现代性也认为社会发展道路是进步的,但发展进步的逻辑是技术逻辑,而可选择现代性最为重要的信念是价值逻辑,即强调社会、政治、伦理等的协同发展,或者说,人们坚信自己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积极价值。那么,社会发展道路的事实如何呢?赫勒对此有专门的概括,他认为:“只有技术的逻辑实际上变得(经验地)普遍了。有各种社会力量为一种或多种‘可选择的技术’提供模型。但迄今为止它们仍然只是模型。技术中发展趋势的多元化并没有到来。相反,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发展趋势却远不是齐一的或线性的。而且在将来也很难期望它如此。”[7]众所周知,邓小平针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多次阐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我们看来,邓小平所指称的“发展”并不是技术逻辑意蕴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指价值逻辑意蕴上的社会的协同发展。因为,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是指发展策略层面意义上的发展,并不是发展战略意义上的发展。当然,社会的协同发展必然包含科学技术的发展,只不过它消解了技术逻辑下的科学技术所具有的霸权思想。那么,既然中国道路秉承价值逻辑,人们就没有理由怀疑中国道路的自觉性,即中国道路不可能是自发的行为,它是人们在总结社会发展经验和理论基础上的自觉选择。中国道路的自觉性表现为多个方面,比如,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这诸多的自觉体现在价值逻辑的层面就是自信。
三、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道路的哲学逻辑
马克思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8]按此理论理解,中国道路的理论必须彻底,而中国道路理论的彻底,离不开对中国道路哲学逻辑的研究。从语义学的角度看,既然可选择现代性是现代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概括性哲学表达,那么,中国道路的哲学逻辑就应该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可选择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
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建设是逐步走向现代性之路的,即人们熟知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之路。而本文或当下所指代的中国道路,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所选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此相一致,中国道路的哲学逻辑应该用中国新现代性予以表达。可选择现代性包含一般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两个方面的本质规定性,可选择现代性的一般性原则是各种具体社会发展道路的共性原则,特殊性原则则是指各种具体社会发展道路所具有的个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中国新现代性既要具有中国特色,还要具有世界价值(前文已经论及)。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人们(尤其是中国学者)更为关注的是中国特色,并不注重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视域研究,而根据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得以实现之后,全世界只有一条发展道路——共产主义道路,这就是说,通向共产主义的中国道路必定包含有世界价值的意蕴。换言之,作为中国道路哲学逻辑的中国新现代性,必须具有既能够表征中国道路个性特征的元素,还必须具有世界价值的共性原则。或者说,要准确把握中国新现代性,就必须深入探讨中国新现代性的本质特征。限于篇幅和当下的认知能力,本文并不合适从概念的范畴阐释中国新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只是从中国新现代性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视域分析中国新现代性本质特征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中国新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涵将另文阐释。
中国新现代性应该蕴含能够向世界各国推广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元素,即中国新现代性能够表征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坚定不移地信任中国道路。自信本是一个心理学词汇,被运用到政治哲学视域来理解中国道路,应该用最为宽泛的世界历史眼光来回应,也就是说,应该从中国道路蕴含的世界价值或世界意义来理解中国道路。否则,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就很容易沦落为自我欣赏或自我膨胀式的自大,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自大式的社会发展道路自信,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都不乏存在者。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新现代性能够表征中国道路的道路自信,那么,中国新现代性中就应该蕴含有能够向世界各国推广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元素。具体而言,之所以认为中国新现代性中蕴含着敢于向世界各国推广的世界价值,是因为中国新现代性中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
其一,中国新现代性拥有影响世界社会发展道路的国际视野。中国新现代性是构筑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社会发展逻辑,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左右着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理念和建构视野。从这种意蕴上理解,中国新现代性能否拥有影响世界社会发展道路的国际视野,关键看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眼光。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社会发展道路的理念和秉承自我创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理念,或者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是不具有国际视野的。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道路依然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自我创新理念进行,即没有社会发展理念的国际视野。但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之后,中国道路就不能不注重国际视野,即不能偏离世界文明的大道。
其二,中国新现代性拥有超越当下世界社会体制的共性原则。中国道路只有具备当下世界社会体制的共性原则,才可能不被世界历史潮流所淹没,当然,能够在满足当下世界社会体制共性原则的基础上超越这些原则,才是中国新现代性的本质所在,或者说,这才是敢于向世界推广中国道路的重要原因。从当下的世界社会发展体制看,一个国家不论是采取共和制,还是采取君主制,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封建时代的绝对君主制体制,即君主至高无上的君权体制被取代或削弱。也即是说,当下世界的社会发展体制的发展趋向是共和制,或者说,当下世界社会体制的共性原则就是共和制政体。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形式上即是共和制政体。在我们看来,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在总结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等政体基础上构筑的政体形式,如果能够不断地创新该体制的内涵和规范民主的形式,就一定能够逐渐被全世界认可并超越当下世界普遍社会体制水平。
其三,中国新现代性拥有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除了人们熟知的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十字军东征等。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观冲突时有发生,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理解,这些冲突归根结底在于物质利益的冲突。但从冲突的直接原因看,并不直接反映在具体的物质利益之上(物质利益是隐藏在背后的最终原因)。比如,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国也参加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进行过珍宝岛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但都不是根源于直接的物质利益。也正因为此,许多国家试图掩盖冲突的真实原因,只是把冲突的原因归结为思想意识,比如,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被日本等国家视为中国霸权意识的发展。如果从思想意识的角度理解,不仅习近平明确向世界阐明,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时期的外交政策都是以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为核心价值。这就是说,从思想意识的角度看,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表明,中国新现代性拥有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
中国新现代性应该蕴含具有中华文化意蕴的中国价值元素,即中国新现代性能够表征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谈及埃及人们会想到金字塔,谈及印度人们会想到佛教,谈及法国人们会想到埃菲尔铁塔,谈及美国人们会想到自由女神像,谈及中国人们会想到瓷器。也即是说,尽管其他民族和国家也有类似内容的文化,但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别的文化符号。有社会哲学史家认为,世界文明中唯有古老的中华文明没有断裂过,但在我们看来,断裂只是相对的,文明通过它特有的文化符号传承了下来。在此意义上理解,不论人们怎样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说“不”,但都无济于事。因为,从唯物主义的视角解释就是,人们的基因图谱记下了人们的文化和习惯;从意识能动性的辩证法思维解释就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书籍等内化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那种故意地或破坏性地让人们忘记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曾经向传统的儒家文化说“不”的“文化大革命”。从现代性的视角理解,究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据,或许是因为人们试图用现代性的理念快速和彻底地取代传统理念。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外部力量还是内部力量,中华文化或中华文明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尤其是那种试图消灭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努力是徒劳的。
当今中国,对待中华文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态度,一种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另一种认为,中国文化是最糟糕的羞于启齿的文化。这两种极端态度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精神的,贬低中华文明的实质是没有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热情与豪放精神;把中国文化理解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成果而不是最优秀的文明成果之一,容易带来藐视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后果。
在我们看来,如果中国新现代性能够表征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那么,中国新现代性必须蕴含具有中华文化意蕴的中国价值元素。
其一,中国新现代性应该继承传统文明表征的优雅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从一定意义上理解亦可称生活习惯,正是从生活习惯的视角理解生活方式,每个民族在既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每个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并不存在统一的生活方式,从自然环境的角度看,在中国南部红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与在中部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以及在北部黑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生活方式明显不同;从人文环境看,中国人群中既有喜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也有羡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有希望饮茶或品茶等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总之,不论是在哪里生活,早年时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被完全改变的,即“乡音无改鬓毛衰”。所以,中国新现代性中必然要包含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就像基督教为了能在欧洲得以广泛传播而改变了不允许基督徒吃肉那样(吃肉是欧洲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新现代性要得到中国人的支持和认可,必须融入传统文明表征的中国人自己认为优雅的生活方式。
其二,中国新现代性应该继承传统文明表征的优良社会传统。社会传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既包含政治要素,也包含伦理要素等。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形成了诸多的优良社会传统,比如,从政治要素看,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胸怀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政治信仰;从伦理要素看,有“孔融让梨”、“郭巨埋儿”等感人至深的道德传统。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道德状况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有知识分子不再信任中国道德状况可以改变。之所以应该引起关注,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这些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许多优良社会传统受到冲击;另一个原因是,应该让这些知识分子理解,马克思辩证法讲得很清晰,任何东西都能改变,中国道德滑坡的现象也必然会改变。也正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他认为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9]。
[1][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2][6][7][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9、64、98—99页。
[3][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4][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94—295页。
[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9]习近平:《不赞成课本去掉古代经典诗词》,《新京报》,2014年9月10日。
Selectable Modernity and Chinese New Modernity:On the Philosophy Logic of Chinese Road
CAO Dian-shun
(Research Cente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Paradigm Innovation,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Modernity;Selectable Modernity;Chinese New Modernity;Chinese Road;Philosophy Logic
Modernity is not an established static thing,it can have multiple connotations with selectable nature.Because modernity has selectivity,modernity has the legitimacy of existence and modernity can still be one of the philosophy principles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Selectable modernity is essentially a reality existence of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logic,which is presented in the difference of modernity and the times of modernity.The difference of modernity means essentially selectable modernity,the times of modernity means that modernit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odernity of the spirit of the age.The establishment of philosophy of Chinese Road in a certain sense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that is,selectable modernit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emise of modernity of Chinese Road,and Chinese new modernity characterizes the philosophical logic of Chinese road.
D61
A
2095-5170(2014)06-0088-07
[责任编辑:李文亚]
2014-07-03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专题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3WTB027)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委托课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觉自信的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3SQWT01)的研究成果。
曹典顺,男,江苏沛县人,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