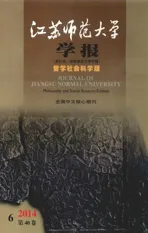西汉四皓史事的文化解读
2014-04-17王健
王 健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西汉四皓史事的文化解读
王 健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四皓史事;庙堂谋略;传奇时代;隐逸文化
“四皓史事”产生于一个由谋略主导的传奇时代,这要从战国到西汉初期的长时段来审视。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便是以政治、军事的捭阖纵横为舞台,由谋士群体为智库,以谋略为驱动,书写胜王败寇、去危图安的历史传奇。刘邦作为草莽英雄崛起,其事业处处得益于谋略。既坐天下,谋略情结依旧。对所事之君刘邦的这些特性,张良有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自信,然后才谋划了四皓的系列政治表演,不动声色地影响、进而改变高帝决策心态。从西汉后期开始,四皓话语广泛出现在传统典籍、史论和诗赋中,该话语代表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政治传统,寄托了“群辅”的东宫制度安排,承载了隐逸文化理想,对中古政治和社会生活均有久远的影响。
“四皓史事”是西汉初年围绕帝储废立斗争、由庙堂谋略演绎而成的一部传奇。它从本事开始,历经流传,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情节逐渐丰富完善的长期过程,具有明显的多义性,给后世的阐释和传播带来了多种文化取向;同时,其真实性也受到一些后世史家的质疑。如何准确把握四皓史事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合理阐释四皓影响高帝决策和西汉政局变动的内在原因,进而阐明四皓话语的历史影响,仍是有待探索的课题。本文拟立足于谋略文化的视角,以文献记载和文物线索为依据,援引历代史论精华,对上述相关问题作进一步阐释和探讨,希望有助于全面认识四皓史事及其传播史的文化意义。
一、“四皓”本事及其“层累的情节”
四皓的史料,主要保存在《史记·留侯世家》中。司马迁所记凡三事:一是张良为吕后解难立策。西汉初年,汉高祖“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张良应召,谋划邀请隐居的四位高士出山辅佐太子,经营羽翼。第二件事是赖“四人”的谋划,在朝廷出兵镇压英布叛乱时,使太子避免了“将兵”出征。第三件事,策划宫廷宴会见面,“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此番见面,使高帝放弃了废嫡立庶的打算,太子遂安。
四皓何时出山入朝?史无明载。从劝阻太子出征英布事件可以推测,起码应定在该事件之前。故司马光《通鉴考异》云:“四皓来,不得其时,今附于英布未反之前。”[1]即不晚于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年底。
四皓因安刘获得何种待遇?清人吴兆宜《庾开府集笺注》:“汉高祖以商山四皓为太子太师。”[2]按今本《史记》阙,故此说并无可靠根据。考张良时任太子少傅,叔孙通为太傅,故四皓的职位应为太子宾客,宾客的身份属于幕僚类型,这成为后世太子宾客职官化的基础。
为太子刘盈保位成功后,四皓留在长安还是归隐山林,司马迁记载亦阙。后世对此多有推测,并无定论。《前凉录》:“张重华问索绥曰:‘四皓既安太子,住乎?还山乎?’绥答未悉。重华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长安,有四皓冢,为不还山也。’”[3]四皓终老于长安的说法,除了有墓葬线索外,还有其神位刻石的佐证。赵明诚《宋本金石录》“四皓神位刻石”条:“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验其字画,盖东汉时书。”[4]故朱熹云:“但不知高后时此四人在甚处?蔡丈云康节谓事定后四人便自去了,曰也不见得,恐其老死亦不可知。”[5]
但也有四皓隐退的线索可寻。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记:“今商州四皓墓有二:一在州西三里,一在州东八十里商洛镇西。未知孰是。”[6]据此,四皓晚年又隐退到商洛山。“四皓”结局及墓葬地点记载的纷乱,反映了有关历史记忆的模糊。
“四皓”的称谓,开始于何时?严可均《全西汉文》载刘邦诏书的轶文:“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可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7]这则轶文倘属实,则四皓的说法,在事态发生时就已出现。西汉文献中最早使用“四皓”称谓的,是扬雄的《解嘲》[8]。东汉时班固撰《汉书》,也多次使用该称谓。
至于四皓姓氏及其籍贯,《史记》《汉书》均漏载,直至南北朝典籍中才开始出现具体的说法。据《史记·留侯世家》索隐引《陈留志》:“园公,姓庚,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甪里先生河内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远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对此,唐人颜师古表示怀疑:“‘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竞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9]但宋人曾著录长安存世碑刻文字,汉惠帝时所刻四皓碑所记,一曰圈公,二曰绮里季,三曰夏黄公,四曰甪里先生[10]。碑文所记圈公说法,或属可信。
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观,其总结的规律是:“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愈无征,知道的古史愈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11]时代越往后,知道的越多。拿这个规则来看四皓故事,令人有类似的认识。后人难免对四皓姓氏籍贯、行迹产生怀疑,这也是不少史家对四皓史事真实性有所保留的原因。
二、“四皓史事”的时代特征
四皓史事堪称汉代历史上的奇人奇事。明人江用世称:“前有黄石,后有四皓,皆天生此辈奇人为子房用。”[12]一语道出了史事的本质。四皓史事产生于一个由谋略主导的传奇时代,这要从战国到西汉初期的历史长时段来加以观察。
这个时代的特殊性,可以归纳为四点:
一是平民政治出现,布衣将相登场,改变了三代世袭贵族把持历史的传统。赵翼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其势不得不变。……于是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13]
二是民间智能之士的涌现。平民政治潮流推动了各类人才的涌现,其中智能之士辈出,如吴起、李悝、商鞅、鲁仲连、鬼谷子,一直到张良、陈平、郦食其、范增等,成为时代政治演变和权力博弈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尽管经过秦朝和汉初的大一统,在战国流风拂荡之下,入汉之后同样是传奇人物辈出。扬雄云:“夫蔺先生收功于章台,四皓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骠骑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名于细君。”[14]
三是谋略文化的盛极一时。在战国列强博弈到秦汉王朝更替的战乱时期,奇谋诡计各擅胜场。《管子·霸言》云:“夫使国常无患,而名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争胜之国,必先争谋。”[15]《战国策·秦策一》:“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16]《墨子·尚贤上》:“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17]谋略人才受到器重,或为帝王师,谋划推行改革大计;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战国以来的诸侯君主,盛行礼贤下士之风,对谋士以师相待,甚至屈执弟子之礼。谋略引导政治,文士组成高智能群体,智能与权力结合起来。军事谋略决定胜败,谋略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谋略书写了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
四是隐逸文化由潜流而汇成江河。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云:“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志节高蹈的隐士古已有之,但东周以来,才真正发展成为一种隐逸的社会文化现象。汉光武帝诏书:“自古尧有许由巢父,周有伯夷叔齐,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自古圣王皆有异士,非独今也。”[18]隐逸是现象,才智和谋略是内涵。隐逸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包含了人才和智慧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隐逸与谋略成为一对历史的孪生兄弟,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从社会史的视角观之,上述时代的最大特征便是以政治、军事的捭阖纵横为舞台,以谋士为主体,以谋略为驱动,书写胜王败寇、去危图安的历史传奇。异常发达的谋略文化,影响到统治集团乃至底层民众,整个社会均为这种文化氛围所浸染。自战国迄西汉,这种谋略为主导的文化现象久盛不衰,衍生出大量历史人物和事件,四皓史事便是这场历史巨变的产物。
三、四皓何以能扭转高帝决策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虽然记载了四皓护卫太子避免出征英布,但却略去四皓影响高帝废立太子意图之事。《资治通鉴·考异》称:
按高祖刚猛伉厉,非畏缙绅讥议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高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矰缴安施乎?四叟实能制高祖,使不敢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也,留侯岂为此哉。……凡此之类皆非事实,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19]
此则考异影响颇大。司马光持有否定性看法,究其根源,首先是因为他对四皓时代的历史语境缺乏深切体察,故需加以辨析。
四皓之事能够扭转高帝意志、令其放弃废嫡立庶决策的关键何在?事件中有两组关键人物,四皓只是前台人物。从谋略之道来看,事件的总导演是谋臣张良,高明的评史者也是从这里入手,来分析张良针对高帝的个性和观念的策划。
如何看待张良的谋略筹划呢?北宋程氏以睿智的眼光,抓住了事态的关键,他高度关注张良扭转帝王决策的独辟蹊径:“事君须体纳约自牖之意,人君有过以理开谕之,既不肯听,虽当救,止于此终不能回却,须求人君开纳处进说,牖乃开明处,如汉祖欲废太子,叔孙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听矣,纵使能言,无以易此。惟张良知四皓素为汉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汉祖知人心归太子,乃无废立意。”[20]从中看出了高明的事君之道。这种事君,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谋人”,是臣下采用人事之谋,来巧妙地改变君主认知的一种应对。
朱熹发挥了二程由“攻蔽”而“就明”的策略评价:“夫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处,所通者明处也。当就其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且如汉祖爱戚姬,将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争之者众矣,嫡庶之义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贤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则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与张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与周昌叔孙通,然而不从彼而从此者,由攻其蔽与就其明之异耳。”[21]
东汉王充曾作过一个著名的假设。他假定不是四皓出面,而是韩非效力,“使韩子为吕后议,进不过强谏,退不过劲力,以此自安,取诛之道也,岂徒易哉?”[22]对比之中,谋略家与法家的应对手段迥异,高下立见。
高帝作为四皓事件的另一位主体,需要加以分析。刘邦是传奇时代的产物,是传奇时代的宠儿,也是传奇传统的忠实践履者。何以见得?请看事实:
刘邦作为草莽英雄而崛起,事业处处得益于谋略。刘邦阵营中谋士群体的贡献度极高,张良、韩信、陈平乃至郦食其之徒出神入化,精心筹谋,屡操胜算,汉高祖“数赖张子房权谋,以建帝业”[23]。故既坐天下,谋略情结依旧。可见,刘邦宠信谋略,欣赏谋略,敬畏谋略,倚重谋略之士,并将能否招揽谋略之士视为帝王素质的关键。同时,刘邦又有道家倾向。这种倾向看来对他服膺四皓、赏识太子的招揽人才赢得人心起到了重要的认同作用[24]。
如何分析高帝的转变?刘邦态度的改变,有两点基础尤其值得分析,一是敬慕四皓;二是欣赏太子招揽人才的能力和魄力;进而认定太子系人心所向,羽翼已成。葛洪认为:“汉高帝虽细行多阙,不涉典艺,然其弘旷恢廓,善恕多容,不系近累,盖豁如也。虽饥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辞致之以为羽翼,便敬德矫情,惜其大者。发黄鹄之悲歌,杜婉妾之觊觎。其珍贤贵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盖有过人者矣。”[25]宋代二程指出:“盖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杰之力,故惮之。留侯以四皓辅太子,高祖知天下豪杰归心于惠帝,故更不易也。”[26]葛洪看重的是刘邦“珍贤贵如此”,二程则关注“惮豪杰之力”,两人看点略有差异。
这段历史的传奇之处在于,在秦末汉初的政治舞台上,并没有看到隐居商山的四皓施展才略的凭据,但其名声之大足以赢得高帝的敬重。进而让高帝赏识并折服于太子刘盈招纳人才、凝聚人心的能力。
对所事之君刘邦的这些特性,张良有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自信,然后才谋划了四皓的系列政治表演,“明以观色,谋以行权”,不动声色地影响进而改变高帝的决策心态。东汉徐干赞许张良云:“见变事则达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27]史实及史论均表明,四皓的出场,的确是改变高帝抉择的决定性因素。
到了宋代,相对于战国至西汉这样一个诡道流行、谋略至上、波谲云诡的时代,人们置身于儒家伦理牢笼天下、君主权威日益强化的文化朝代,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导致一些北宋史家对汉代人的思维和观念世界已有所隔膜,彼此视域难以融合。司马光有见于太史公的崇奇、好奇,却对东周至西汉历史环境的特质缺乏体认和理解[28]。
司马光对事件真实性的质疑,还在于他是用儒家伦理尺度重塑历史,这是他持否定性意见的第二个原因。宋代学者曾谈到司马光删略四皓之事的动机:“辩四皓为惠帝立党制其父,以明父子之义。”[29]今按,宋儒所强调的这种政治伦理原则,在西汉前中期其实并不为政治家所看重,不仅有汉高帝赞赏太子刘盈的招贤纳士,而且汉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汉武帝也为太子立“博望苑”通宾客。直至武帝晚年爆发巫蛊之祸,宾客制度的负面问题才暴露出来。可见,司马光否定四皓故事的真实性,其实隐含了利用重释四皓故事训诫后世的苦心[30]。
对于四皓史事中的权谋因素和四皓的身份定位,朱熹曾有精到看法:“汉之四皓,元稹尝有诗讥之,意谓楚汉分争却不出,只为吕氏以币招之便出来,只定得一个惠帝,结果小了,然观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谋之士。”透过汉初政坛上的风云变幻,朱熹抓住了智谋因素,识见颇高。
黄淳耀敏锐地揭示出四皓的身份定位及其传奇性:“彼四皓者,特战国豪杰之士,田光先生之流耳,意气刎颈,固其常也。以高帝漫骂轻士故不至,以太子卑辞安车故至,无足怪者。且以帝所至敬,无如子房,其次则叔孙通,又其次则周昌也。三人反复言之而不听,而四皓回其意于立谈之顷,此岂徒以其名哉!”[31]“权谋之士”与“豪杰之士”的定位,反映了史家解读的深度。
明人沈懋孝对事件中的曲折和人情利害因素,有深入细致的理解和推断:“人情有溺而锢也,犹疾之中结不开也,开之必有所借缘,其势之可通,则医家因治之法是已。四皓者,非帝所想闻不得见者耶,一旦从太子伟冠裳见上,将非借其明以通之乎?帝指四人者示戚夫人曰:羽翼成矣,缯缴焉施,或者无柰夫人何借以拒弄之,或者真谓四人辅太子又可无忧吕氏,或又心知孱子者不足抗太后,既已自悟其失矣,而托为之说,以安太子者耶?要之,留侯之策秘,此时必自有见,史氏不能明,遂谓招此四人之力,殆非其深指也。”[32]沈氏从心理分析角度着眼,尝试揭示出高帝利用四皓出场来表态的复杂动机,该说值得重视。
再讨论一下改变事态的综合因素。首先,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行之久远,这种传统对高帝构成了较大压力。其次,勋臣集团的立场和态度,如张良、周昌等公卿的群体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刘邦的决策。史家指出,“元勋大臣们从维护汉皇朝政局的稳定出发,坚决反对刘邦改易太子的谋划,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慎重和负责的考虑”[33],高帝不能不迁就他们的政治选择。
四、四皓话语:连绵影响及其意义
从西汉开始,四皓话语广泛地出现在传统典籍、史论和诗词歌赋中,影响到中古政治和社会生活,丰富了传统文化观念的表达模式。四皓话语的符号化,具有丰富的生成意义。
第一,四皓话语代表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政治传统。四皓事件的内在精神和正义性依据,在于它维护了嫡长子继承制传统。宋人孙明复高度评价四皓在这方面的贡献:“周道也,为国之大者,莫大于传嗣,传嗣之大,莫大于立嫡,不可不正也。……四先生将因是以行其道,故从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太子之位,此非周道绝而四先生复传之者乎?然四先生之出,岂止为汉而出哉,为万世而出也。”“万世之下,使庶不敢乱其嫡者,四先生也。”[34]点出了四皓之功在于斯,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功不可没。“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没也,惠帝为之制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赐葬人臣,恤典之始。”[35]
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征引此事,提出了“嫡庶之分宜辨”的原则,记叙了唐人做法来反映政治史上的取鉴。唐太宗任命魏征为太师:“时太子承干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上闻而恶之,谓侍臣曰: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征,我遣侍太子,庶绝天下之疑。九月征为太子太师,征表辞上手诏,谕以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亡国家,汉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定。我今赖公即其义也,征乃受诏。”[36]
第二,四皓话语寄托了“群辅”的东宫制度安排。西汉四皓辅佐太子,号称“宾客”,后世遂成为官制。据杜佑《通典》:“大唐显庆元年正月,以左仆射兼太子少师于志宁兼太子太傅,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并为皇太子宾客,遂为官员定置。四人掌调护、侍从、规谏。凡太子有宾客之事,则为上齿,盖取象于四皓焉。资位闲重,其流不杂。”[37]
《唐六典》记载:“太子宾客四人,正三品。《汉书》高祖欲废太子,吕氏用张良计,致商山四皓以为宾客。又孝武帝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则其义也。若有宴,赐诸司长官,太子宾客则皆预焉。太子宾客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而先后焉。凡皇太子有宾客,宴会则为之上齿。”[38]宋人高承云:“汉高祖欲易太子,吕后用留侯计,迎四皓以定太子,故宾客之名始起于此。……洎晋怀建宫惠帝,使卫庭、司马略等五人更往来备宾友,虽非官而谓之东宫宾客。唐显庆元年正月,以于志宁等为太子宾客,遂以名官定置四人,盖取法于四皓。”[39]元代征聘汉族贤士,取法四皓故事:“杨恭懿奉元人初,与许衡俱征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汉聘四皓故事聘之,考正历法,授集贤学士。”[40]
第三,四皓话语代表了隐逸文化理想,这是后世赋予四皓故事最重要的内涵。士大夫从高帝敬重四皓的史事中感受到隐逸之士的价值,“汉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籍叹述,以为美谈。”[41]人们普遍看重的是四皓的隐逸品格。白居易《答四皓庙诗》:“先生道既光,太子礼甚卑。安车留不住,功成弃如遗。如彼旱天云,一雨百谷滋。泽则在天下,云复归希夷。岂如四先生,出处两逶迤。”[42]宋人徐铉曰:“及太子之危,留侯不能正于是,襃然而起以救其失,若夫出处之分,高尚之名,皆不以屑意,功成不有,超然而去。”[43]在故事的多元结局中,多数论者选择了功成不居、超然而去的说法,无疑代表了四皓话语传播史上的主导价值取向。
第四,四皓故事引发谋略性评论。唐人元稹《四皓庙诗》对四皓造成戚夫人的悲剧加以指责:“安存孝惠帝,摧折戚夫人。……虽怀安刘志,未若周与陈。”杜牧《商山四皓庙诗》对四皓辅惠帝导致吕后专权的不虞性后果也有苛评:“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黄震亦看到维护嫡长子继承制与日后吕后专权的两难悖论,对谋略“未得为尽善”提出批评:“召四皓以辅太子,所能护惠帝者此谋,而杀戚夫人者亦此谋。”[44]
第五,四皓群体被后世道教所神化。《抱朴子·至理篇》引孔安国《秘记》,“言四皓皆仙人良师之尤”[45]。《说郛》卷七引葛洪《枕中书》:“广成丈人,今为钟山真人九天仙王。汉时四皓、仙人安期、彭祖,今并在此辅焉。”可知南朝时“四皓”已列入道家神仙谱系。北周武帝宇文邕敕纂的道教经典《无上秘要》在“得太清道人名品”等级神灵中,列出了“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商山四皓”,同列还有彭铿、墨翟、鬼谷先生、徐福和淮南八公等历史人物,“右件八十五人,系太清中真仙姓名事迹粗显者,今亦应进登太极者”[46]。
这些后世的解读,实际上形成了解释学上的“效果的历史”。历史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个体的存在,而是受时代的制约,即受时代文化和心理的制约而不断“重写”、不断“层累”起来的。话语内涵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了西汉历史,而四皓故事被充分符号化之后,被定格为历代所赋予故事的传奇价值、谋略智慧、隐逸理想和宗教信仰等后世的生成意义。
[1]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二引《考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2]吴兆宜:《庾开府集笺注》卷二,《北堂诗钞》引《史记·外戚世家》。
[3]陈禹谟:《骈志》卷十六,引《前凉录》,见“中国基本古籍库”。
[4]赵明诚:《宋本金石录》卷十九,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50页。
[5]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历代·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23页。
[6]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25,《商州·名山》。
[7]严可均:《全西汉文》卷一,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页。
[8]扬雄:《扬子云集》卷四,“中国基本古籍库”。
[9]宋濂赞成颜师古的质疑:“予方疑其诞妄不经,及读颜师古汉书注,果谓四人者匿迹远害,氏族无得而详,皆后世皇甫谥圈之徒及诸地里书傅会,可见古人读书精审,固有以及之者矣。”(宋濂《宋学士文集》卷第三十四,《题商山四皓图》)
[10]罗泌:《路史》卷三十五,《辨四皓》,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古史辨》第3册,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450页。
[12]江用世:《史评小品》卷八,明末刻本,见“中国基本古籍库”。
[1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王树民校正,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页。
[14]班固:《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下。
[15]管仲:《管子》卷九,《霸言》第二十三。
[16]墨翟:《墨子》,《尚贤》上,王焕鏕校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17]《战国策》卷三,《秦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18]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19]司马光:《通鉴考异》卷一,《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
[20]程颢等:《二程遗书》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21]朱熹:《通鉴纲目》卷三上,《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
[22]王充:《论衡》卷十,《非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页。
[23][27]徐干:《中论》卷上,《智行》第九,《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2、573页。
[24]王健:《道家与徐州——兼论汉初黄老政治与刘邦集团文化地域背景之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5]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逸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26]程颢等:《二程遗书》卷十八,问《坎》之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28]四皓本事的真实性,后代史家多数持肯定的立场,如宋人陈鹄《耆旧续闻》卷一认为:“扬子云尝称其美行,子云于高帝世为近,必其事之不可诬者。”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29]何乔新:《椒丘文集》,见《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第四百十六卷,《史学部·总论》。
[30]陈鹄:《耆旧续闻》卷一,刘元城曰:“此殆有深意。老先生作通鉴,欲示后世劝戒之意。”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31]黄淳耀:《陶庵全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2]沈懋孝:《长水先生文钞》,《四皓》,见“中国基本古籍库”。
[33]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9页。
[34]佚名:《宋文選》,孙明复文,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5]《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第一百七十卷,“碑碣部”,“杂录”。
[3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71页。
[37]杜佑:《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职官十二。
[38]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9]高承:《事物纪原》卷五,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第180页。
[40]释大闻:《释鉴稽古略续集》集一,《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41]桓范:《荐管宁表》,《艺文类聚》卷三十六人部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42]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卷二。
[43]徐铉:《徐公文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原文电子版,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1999年版。
[44]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六,《读诸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5]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六,见“中国基本古籍库”。
[46]周武帝:《无上秘要》,明正统道藏本,卷八十四。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about the Sihao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NG Jia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Sihao events;Politicians strategy;Legend of the era;Recluse culture
The Sihao events occurred in a period of dominant strategy.It needs to be inpected for the long period of time from the Warring State to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The major characteristic of the age,is to write of the history of The winner as the success and Losers into robbers legendary,by using the political,military manoeuvre among political groups as the stage,by using the adviser group as the think tank,and strategic driven.Liubang rised up as a greenwood hero,his career always benefitted from strategic thinking.When settled down,he still kept the strategic emotion.Because Liubang's charactors,Zhangliang had deeply recognaztion and enough confidence,therefore he planed Sihao Series Political Show,smoothly influenced and further changed his decision.Starting from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Sihao words appear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history and poetry,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It represents the lineal primogeniture system political tradition expression of the of the Orient House system arrangement,bearing the recluse culture ideal.
K234.1
A
2095-5170(2014)06-0045-06
[责任编辑:刘一兵]
2014-06-12
王健,男,江苏邳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