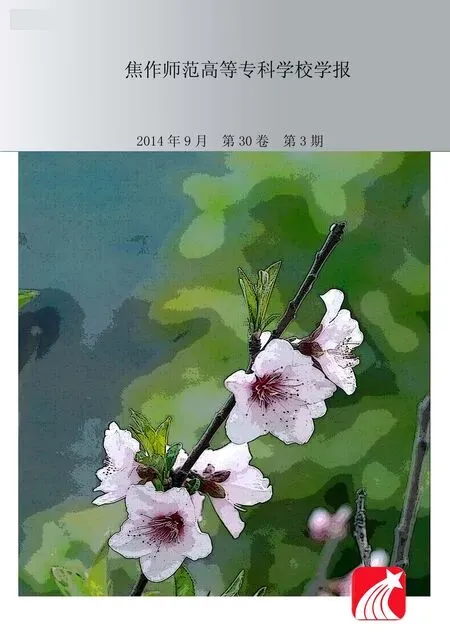山西地区蒙元壁画墓探究
2014-04-17赵俊杰
赵俊杰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450002)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地区发掘清理了一大批蒙元时期*蒙元时期,即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到1368年元朝灭亡。本文研究时限是金贞祐南迁以后,即成吉思汗八年(1213)到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之间,这期间蒙古从草原南进,逐渐控制了北方和中原地区,在1234年灭金后占据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元朝时期是从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元开始,一直到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退出中原为止。墓葬,其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好且具典型性的二十余座蒙元壁画墓的资料已陆续见诸报道。考古材料揭示,山西地区的蒙元壁画墓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壁画墓的形制与随葬品
(一) 墓葬形制
山西地区蒙元壁画墓按其主室的平面形制可分为多角形墓和长方形墓。不同类型的墓葬在建筑结构、装饰内容、随葬品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以墓室的建造材质论,山西的蒙元多角形墓又可分为多角形砖室墓和多角形石室墓。考古发现,山西地区蒙元多角形砖室墓均为单室墓,墓室分为八角形和六角形两种。六角形砖室墓有孝义下吐京元墓[1]和芮城永乐宫潘德冲墓[2],八角形砖室墓有太原瓦窑村元墓[3]、孝义梁家庄元墓[1]和平定县东回村元墓[4]等。
多角形蒙元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门一般为拱券门,个别为仿木构墓门楼,墓门处多以砖石封门。甬道为一般的拱券顶。墓顶形制有穹窿顶和叠涩攒尖顶两种。墓内普遍筑有梯形、长方形等棺床,棺床建筑形式简单。葬具多为木棺,也有的无棺,骨架直接陈放在棺床上,多仰身直肢。随葬品较丰富,有铜器、陶瓷器等。
山西地区目前发现的两座多角形石室墓是交城县元代石室墓[5]和文水北峪口墓[6],这两座墓位于吕梁市境内。两墓均为八角形,也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构成,坐北朝南。墓门有石门或以石板封门,甬道以石板铺顶,墓顶为叠涩攒尖顶。墓室北部有梯形棺床,未见葬具,骨架头向东,随葬品较少。
山西地区目前发现的蒙元方形壁画墓除新绛吴岭庄元墓[7]为多室墓外,其余的全为单室墓。以其平面形制可分为近方形和长方形单室砖墓。墓葬一般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构成。墓门多位于墓室南壁正中,用封门砖或石板封堵,有的墓门为仿木结构门楼式建筑。墓室内多有砖砌棺床,墓室四隅砌有角柱,柱上饰有普柏枋、斗拱,墓内或以壁画装饰或有砖雕装饰或两者兼而用之。墓顶为常见的穹窿顶和攒尖顶,有的墓顶装饰莲花藻井或留有方形口以砖石封堵。墓内随葬品多寡不一,器类主要有陶瓷器、木器、铜铁器、石砚台等。
(二) 随葬品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山西蒙元壁画墓中的随葬品主要有陶瓷器、铜铁器、木器、骨器、纸明器、丝绵麻制品等。山西蒙元壁画墓出土陶器有罐、盘、瓶、碟、盒、碗、香炉等。随葬瓷器较普遍,釉色丰富,有白、青、黑、绿、蓝等;瓷器器型有碗、罐、盘、碟、瓶、壶、杯等,另外还有瓷枕、瓷灯等少见器物。蒙元制瓷手工业发达,但是墓中随葬瓷器数量并不多,此或跟当时纸明器的流行有关。
铜器常见有铜发簪、铜耳坠、牌饰、铜钱、铜盆、铜钵、铜盘、铜灯、铜杯、铜香炉等。此外,还有铜镜,以圆形为主,铜镜纹饰各有不同,但多承袭前代传统纹样,常见的有海兽葡萄镜、鱼水纹镜、双鱼镜、缠枝牡丹纹镜等。随葬的铜钱唐宋元时期均有。铁器常见有铁地券、铁猪、铁牛、铁镇纸、铁灯盏等。其中,铁猪、铁牛等器物为当时丧葬习俗中的辟邪镇墓类物品,和当时的阴阳术数有关,多放置于墓内四角。
木器在墓葬中不易保存,但在山西元墓中也有发现。如山西大同市齿轮厂元墓[8]中出土有木盆架、木巾架、木桌、木榻,木器多残朽;山西大同冯道真墓[9]发现较多木器,有木棺罩、木房、木牌位、木戒板、木影屏、木巾架、木盆座、木蜡台、木瓶、木碗托、木镜架、木砚台盒等,这些木器木质有杨木、松木、榆木等。
纸明器不易保存且少有发现,但是在山西稷县五女坟墓[10]中出土有保存较好的“腊尖”和金花纸,棺内还有各色纸糊的女性衣履,这为研究山西地区蒙元时期的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外,大同宋庄元墓[11]中出土有两柄骨刷。依器物尺寸看,很可能是牙刷。在冯道真墓[9]中还发现丝织品、石枕、石砚台、龙纹墨、墓碑等。
二、壁画墓的壁画布局与内容
山西地区蒙元墓葬以壁画装饰为主,砖雕仿木构建筑装饰次之,亦有砖雕、壁画并饰于一墓者。在壁画装饰上,壁画多分布于墓室四壁,分布于墓顶部位及拱眼壁间者多为填白性质。壁画题材主要有墓主夫妇图、妇人启门图、奉酒侍茶图、出行图、回归图、山水图、杂剧演出图、孝行图等。墓室壁画从主体内容配置看,分为家族燕居系列图和多文化多宗教共融组合图两类。
(一)家族燕居系列图
北方地区蒙元壁画墓通常以墓室为一个单元,表现墓主人的现实生活情况,为研究蒙元社会习俗提供了生动可信的资料。山西地区蒙元壁画墓的家族燕居图主要包括墓主夫妇图和日常生活图。
蒙元墓室壁画中出现墓主夫妇的形象在内蒙古、辽宁以及陕西、河南地区是非常流行的,在山西地区壁画墓中出现墓主夫妇形象的壁画布局与上述地区也是十分相似的。这种壁画墓一般在正对墓门的墓室正壁绘有墓主夫妇形象,在墓室的两侧壁绘有反映墓主夫妇日常生活的图景。运城西里庄元墓[12]、平定县东回村元墓[4]、文水北峪口元墓[6]、下吐京元墓[3]等都是这种类型的壁画墓。
墓主夫妇图一般是二人并坐,男女主人分坐于椅上或榻上,位于画面左右,其身前或身后多侍立有年轻人,多数墓主人身后或上方有敞开的幔帐或屏风,例如新绛吴岭庄元墓[7]、交城县元墓[5]、孝义下吐京元墓[3]等。此外,还有墓主人三人并坐图,由一位男主人和两位女主人组成主要画面,其它内容与二人并坐图相近,例如文水北峪口元墓[6]。
以往对壁画中墓主图像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图像内涵及丧葬功能的探讨,对图像中墓主夫妇身旁侍立者的身份多以墓主人的“侍者”进行说明。任林平先生综合砖雕壁画内容、构图形式、墨书题记、遗存人骨等因素,认为一些元墓墓主夫妇对坐图中,侍立于墓主人身后的人物,其身份不是侍者,而是其家庭成员,这些墓葬均应为家庭合葬墓[13]。
在墓室的两侧壁绘有反映墓主人日常生活的图景,一般为出行图、归来图、侍从图和门卫图。例如文水北峪口元墓[6]东壁绘墓主人一男一女骑马出行,男侍随行其后,肩挑筐子;西壁大体与东壁相同,唯侍者有两人,分别随行于马后两侧,马侧尾随一犬。交城县元代石室墓[5]的甬道东壁刻鞍马人物出行图,朝向墓外,主人乘马策缰,一仆持钱幡在前,一仆担笼箱从后;西壁刻鞍马人物回归,朝墓内,主人乘马缓行,神情疲惫,二仆人随后,一抱奁,一担箱,作交耳互谈状。人物皆头戴盔帽,衣襟左衽作蒙古人装束。
侍从图主要内容有侍茶与侍酒。“奉茶进酒”题材是蒙元墓葬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题材上承自宋、下延及明,在北方蒙元墓葬中均有发现。其表现方式或由两组人物分别备献茶酒,或仅以成组的茶酒用具为符号代表备献的行为。山西北峪口元墓[6]北壁为墓主人夫妇对坐图,西壁为进茶图,东壁为进酒图。这几幅壁画内容构成了一组完整的家庭起居侍奉组图,描绘出蒙元华北农村富裕阶层或地主阶层日常的生活画卷,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和民俗化风格。通过这些壁画我们还可以挖掘其所表达的丧祭功用。袁泉先生认为:“墓室不仅作为‘收柩之所’存在,也在营造‘永为供养’的祭奠氛围,表现生者对死者的永久性祭奉。可作供养逝者之所,相当于祭礼中的‘正寝’功能。 另外,丧祭仪具在宋元时期逐渐世俗化,形成了以茶酒之器等日常‘时器燕器’为代表的祭器类型。”[14]
考古发现,一些蒙元墓葬的墓门两侧绘有门神或守卫,在此将其称之为门卫图。在中国古人看来,死者在墓葬中并不是绝对安全的,他们可能面临各种威胁,这种威胁一是来自鬼怪恶魔的骚扰,二是来自盗墓者的入侵。古人为了保护死者的尸体安全和灵魂安宁,“魏、晋、隋、唐在墓室内置镇墓兽,宋以降则作画或雕刻武士形象的门神置墓门内,意在驱邪避凶”[15]。在山西地区蒙元墓葬中经常发现有门卫图,例如山西屯留县康庄M1号墓[16]南壁墓门左、右两侧对称位置各绘有门神,左侧的门神浓眉大眼,神态威严,留络腮胡,头戴黑色展角方形幞头,身着红色袍服,脚登黑靴,腰系带,配有弓箭,手持骨朵作守卫状。这些守卫是墓葬的守护者,被画在墓室内,具有镇墓辟邪、威逼怪兽和抵御盗墓者的侵入以便佑护死者的功能。
(三) 多文化多宗教共融组合图
山西地区蒙元墓室壁画还有以孝子故事、山水人物、杂剧表演等内容为主要题材的多文化多宗教共融组合图类型。
“孝行故事图”是儒家孝行思想的生动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形式是以孝子或孝行的人物图像反映孝行故事,是中国艺术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在墓葬中创作孝行故事图旨在通过画像中的孝子所具有的道德节操,来展现说明墓主人生前同样具备或向往追求的道德节操风范,而生者通过墓葬壁画这种形式以求达到“尽仁尽孝”的丧葬目的。穆宝凤先生认为孝子图像出现在墓室中,并不单单表明孝行的思想,它作为一种图像组合模式出现在墓室中,还要结合墓室的特有环境来挖掘其深层的含义,“至孝”而可“通神”应该是其内在的功能意义所在,也是孝子图像出现在墓室中所承担的隐喻意义[17]。山西长治捉马村M2号元墓[18]为仿木结构方形单室砖墓,墓室东西壁靠近北壁一端分别绘有“王祥卧冰”“孟宗哭竹”孝子故事图,皆有红色边框围饰。墓室北壁绘有两幅“孝子”图,左侧为“丁兰孝子”图,右侧为“韩伯瑜孝子”图。山西长治南郊司马乡元墓[19]北壁绘有董永、孟宗孝子图像,南壁为墓门,东、西两壁分别绘有王祥、曹娥孝子图像。裴志昂先生认为晚唐至元代的墓葬中仿木结构和孝悌图似乎为夫妻合葬墓所专有。在他所涉及的四百多条墓葬发掘报告和专题著作中,未曾发现带有仿木结构和孝悌图的单人墓。他认为虽然单身埋葬也可以表现家族的继续性,但只有夫妻合葬墓才是家族延续、世代慈孝的纪念堂。作为慈孝遗迹,仿木结构合葬墓是根据本地的木作传统,由工匠设计规划,选择最合适、最坚固、最富有表现力的构造与装饰建造的,再加上孝子图,反映了墓主或嗣子的个人信仰与家族财力,并寄托了他们希冀家族永存不朽的强烈愿望[20]。
在山西地区的蒙元壁画墓图像构成里有一类题材尤其值得注意和研究,那就是“山水人物”图像。“山水人物”图像是“山水”和“人物”共同构成的生活图像。山西大同元墓[8]北壁绘有两幅图画,左侧为山居图,一老翁居于山中茅屋,屋旁有一株参天苍柏,树下立一童子。画面高山流水,皓月当空,雁翔天际。右侧为赏莲图,绘一山中茅屋,屋旁池中荷花吐艳,一主一仆在池边做赏莲状。西壁北端绘行舟图,一小童执篙行舟于山间河流中,主人端坐于船上,天空中雁阵成行,两岸风景如画。东壁北端绘行旅图,主人骑驴急驰于山路之上,一小童子肩负一树枝紧随其后,远处隐起高峻连绵的山峰,天空中两行大雁往山外飞去。有趣的是,墓室的东西壁描绘的却是具有写实风格的备茶图和备酒图,与北壁壁画的清淡高远形成鲜明对比。墓室的两部分壁画一方面描绘现实生活以表现墓主人丰足的家产与日常生活的豪奢,一方面似又在描写墓主人恬淡的隐居生活,颇有魏晋之风,反映了改朝换代后,在民族政策歧视下,一些深受孔孟儒学思想熏陶的汉族士大夫愤懑的社会情绪和消极的反抗心理。
蒙元是我国水墨山水画艺术的成熟期和创新期,此类绘画既老到又有创新活力。元朝取消了宋金以来的画院制度,使许多画家寄情于山水,并且很多著名的画家都是道教信仰者,有的是全真教徒,例如赵孟頫、黄公望、吴振,等等。道家崇古、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等思想,为当时的中国水墨画艺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活力。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墓室北壁绘有大幅的水墨山水图,旁有题榜“疏林晚照”,画面峰林叠翠、林木葱郁、云雾缭绕、河水清澈,有人泛舟于河上,是元墓壁画中不可多得的完整山水画卷,笔法细致,意境深远。
蒙元时期,以平阳*平阳,蒙元时期为平阳路,大德九年,改名为晋宁路,辖区包括今天的临汾、运城、长治、晋城等晋南地区。为代表的山西地区是元杂剧创作活动的中心之一。山西杂剧既有着蒙元的精神风貌和总体风格,同时由于其地域文化特色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晋南从地理位置上讲,不仅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历代商贾荟萃、贸易汇集的重要交通枢纽,各种表演艺术随着商贸的兴盛得以广泛传播。杂剧将歌曲、宾白、舞蹈动作融合在一起,是一门综合性的戏剧艺术,也是元代文学艺术的真正代表。“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都是山西人。在晋南蒙元墓室壁画中,就有元杂剧的内容。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12]的杂剧图就很有代表性,其墓室西壁为“风雪奇”的杂剧表演,由于此剧目文献上未载,该发现补充了元杂剧剧目。东壁为奏乐图,乐器中出现了琵琶,配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证明了至迟在元代晚期,杂剧演出已采用琵琶伴奏。北壁为宴飨图,南壁绘有正在舞蹈的儿童。发掘者推测,此墓壁画所展示的可能是一个杂剧与舞蹈相结合演出的场面。新绛吴岭庄元墓[7]砌有多幅杂剧砖雕——南壁中间墓门上砌一幅杂剧砖雕,帐额下面共有七块砖雕,其中间五块各雕一杂剧演员,两侧各有砖雕乐伎一块,前后二室四壁共有砖雕三十余块,生动地再现了“跑毛驴”、“狮子舞”、“双人舞”、“单人舞”的乐舞形式,清楚地展示了元杂剧中各种角色的装扮以及表演情况。这些杂剧砖雕和壁画生动地展示了元杂剧的演员行当及其服饰和表演形式等,为我们了解元杂剧的历史状况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资料。
三、影响山西蒙元墓室壁画题材的因素
(一)理学发展的影响
元代的社会思想文化与以前各朝代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兼容并蓄和“不尚虚文”,思想意识领域相对宽松自由。元代理学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是在唐代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21]。理学自宋代应运而生后,经过程颢等人的深化与发展,南宋时的朱熹己经成为儒学道统的主要代表。“理学的基本特点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化,它以传统儒家的孔、孟思想为核心,将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伦理化、系统化,与世界的本原和人的本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成为神圣的‘理’,以‘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赋予‘理’以本体论上的含义。”[22]
理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金元各代,尤其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所青睐。元初,“山西地区却受理学影响较早,且有渊源。略作溯源考察可知,宋代,程颢‘尝令晋城,以经旨授诸士子’,致使‘泽州之晋城、陵川、高平,往往有经学名家,虽事科举而六经传注皆能成诵’,乃至‘金有天下百余年,泽、潞号为多士’。‘靖康之乱,吾道(理学)遂南’。金中后期,朱熹闽学与南迁洛学逐渐北传。金末元初,北方地区理学复盛,程朱理学开始占据统治地位。金礼部尚书赵秉文便极力维护‘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主张‘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23]。元代朱学系统人物为了更好地推行理学,遂就简避繁,兼容陆学,元代始定为“国是”,成为官学,开始提倡烈女节妇、孝子贤孙。山西地区蒙元壁画墓中“孝子”图像的大量流行,无疑与北宋以来理学的发展有密切关联。
(二)宗教发展的影响
为了多民族统治的需要,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一律加以护持的政策。河东山西的佛教势力经过金末丧乱的劫难之后,在元统治者的扶持与推崇下不断增长,社会影响逐步扩大,表现在元墓装饰上为墓室饰有莲花、飞天等代表佛教的图案。全真教是在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方发展起来的道教的一个派别,它纯粹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金元之际,在统治阶级的推崇和扶持下,山西地区的全真教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元成宗之后,全真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倡服辛苦、持忍耐、勿争杀,对社会风俗影响极为深远。全真教主要的宗教经典文献为《孝经》《道德经》,与儒家理学所倡导的“孝行”思想有很多融合之处。山西地区壁画中“孝行”图和“山水”图的广泛流行,无疑与当地全真教的流行和发展有很大关系。蒙古贵族崇尚萨满教,根据萨满教的教义,其丧葬思想提倡“薄葬简俗”,这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蒙元的丧葬思想,前代的壁画墓传统也由此开始走向衰弱。
通过这些历史遗存及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蒙元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对于当时文化艺术尤其墓葬壁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文化逐渐由世俗化转向宗教化,并逐渐成为了丧葬文化的主流。
(三)社会习俗的影响
蒙元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定居文化相互混融的时期,也是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和汉族交流融合的特殊时期。一方面少数民族竭力保持自己特有的习俗不被消亡。比如蒙古族实行“薄丧简礼”和“不封不树”习俗,这一风俗尤其在拥有较高政治经济地位的蒙古族贵族群体中盛行。在这样传统风俗的影响下,这一社会主流群体的缺失使得蒙元墓室壁画艺术渐渐失去繁华的动力。另一方面则是蒙古族中下层贵族在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中原的“厚葬”等礼俗,使得其丧葬习俗里也渗透有汉民族的文化因素。汉族人民受到女真、契丹族一些习俗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开始实行火葬,例如大同市发现的元墓中就有骨灰葬。因此,蒙元的葬俗具有多元性特征,一方面实行汉化,一方面又含有浓厚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根据山西地区流行“孝子故事图”和“山水人物图”可知,处于“四塞之地”的山西地区蒙元墓葬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小,体现在墓室壁画中也有浓厚的汉族文化气息,这些图像的出现一方面与理学和道教的发展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蒙汉文化交流中,山西地区延续了汉族的传统,并且汉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蒙古文化。
综上所述,蒙元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多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多民族共存、多种文化混融的时代特征。从山西蒙元壁画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品及装饰内容来看,该地区的壁画墓可以说正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山西地区理学和道家思想的兴盛,加之山西地区独有的且较封闭的区位特征,使得当地在继承前代墓葬习俗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本地区独特的墓葬特色。对山西蒙元壁画墓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蒙元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与地域特征。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J].考古, 1960(7):57-61.
[2] 李奉山.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J].考古, 1960 (8):22-29.
[3] 戴尊德.山西太原郊区宋、金、元代砖墓[J].考古,1965(1):25-30.
[4]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孝义下吐京和梁家庄金元墓发掘简报[J].考古,1960(7):57-61.
[5] 商彤流,等.山西交城县的一座元代石室墓[J].文物季刊,1996(4):23-29.
[6] 冯文海.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J].考古,1961(3):136-138.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3(1):64-72.
[8]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元代壁画墓[J].文物季刊,1993(2):17-24.
[9]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等.山西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2(10):34-43.
[10]畅文斋.山西稷山县“五女坟”发掘简报[J].考古,1958(7):31-35.
[11]王银田,等.大同市西郊元墓发掘简报[J].文物季刊,1995(2):27-35.
[1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西里庄元代壁画墓[J].文物,1988(4):76-78.
[13]任林平.中原地区宋金元墓葬墓主图像的再思考[N].中国文物报,2014-02-28.
[14]袁泉.从墓葬中的“茶酒题材”看元代丧祭文化[J].边疆考古研究,2007(6):329-349.
[1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嵩县北元村宋代壁画墓[J].中原文物,1987(4): 39-44.
[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屯留县康庄工业园区元代壁画墓[J].考古,2009(12):39-46.
[17]穆宝凤.神秘性与世俗性的交融——元代山西地区墓室壁画的特征及墓室图像意义分析[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3(1):73-79.
[18]长治市博物馆,等.山西长治市捉马村元代壁画墓[J].文物,1985(6):65-69.
[19]长治市博物馆,等.山西长治市南郊元代壁画墓[J].考古,1996(6):91-92.
[20]裴志昂.试论晚唐至元代仿木构墓葬的宗教意义[J].考古与文物,2009(4):86-90.
[21]许凌云,等.中国儒学通论[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2):164.
[22]陈云峰.宋末元初理学北传及其影响[D].云南师范大学,2007.
[23]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