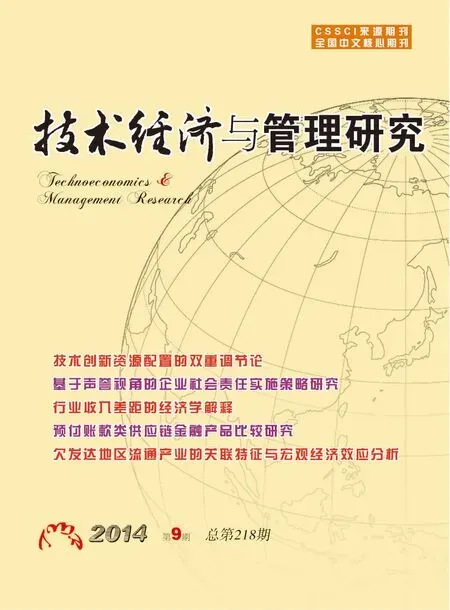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周期研究述评
2014-04-16彭欢欢
彭欢欢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北京 100086)
跨境资本流动与宏观周期研究述评
彭欢欢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北京 100086)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无法解释国内偏好(Home Bias)和资产异质性(Idiosyncratic Asset)问题,因而无法全面阐释金融危机时期国际资本流动。通过大量文献将投资组合理论引入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ODSGE)模型较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与此同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从一阶矩扩展到二阶矩,即由单独关注收益因素到关注收益因素并关注风险因素,构建了研究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周期波动一般性分析框架。这一新进展对于研究中国实施资本管制和构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对以上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重点梳理了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周期波动的相关研究并对之进行述评。
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危机;宏观周期;卢卡斯之谜;资本管制
一、引言
美国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源国,美国也是依赖其他国家资本流入为其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融资的经济体之一(Marcel Fratzscher,2012)[1]。金融危机爆发之前,Nouriel Roubini &Brad Setser(2005)据此预言,美国利用美元特权向全球输入流动性,其他国家购买美元资产为美国贸易赤字融资的全球资本循环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最终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调整贸易赤字过程中,将面临资本流入的逆转和汇率等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世界经济有可能经历硬着陆。然而事实上,金融危机时期国内和国外投资者反而大量持有美国资产,危机并未如所预言的那样出现资本外逃,尤其是雷曼兄弟破产后,即2008年7月至2009年4月之间出现资本大量涌入美国的异常现象。理论与现实的相悖启发学者们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大量思考。
此次危机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它的全球性影响,更重要的是此次危机对不同国家,包括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不同影响。从2009年开始的经济复苏,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大量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引起了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的急剧波动及其对新兴经济体国内经济、汇率和资本市场影响的担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认为大量资本流入的涌现是由于发达经济体货币和财政政策所致,发达经济体则强调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趋异所致。前者强调所谓的推动因素,即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后者强调拉动因素,即强调内部吸引力因素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的争论已经成为G20等国际论坛争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时,IMF一改金融自由化的一贯立场,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也表明立场,某些情况下一定程度对流入资本进行征税的资本管制对于开放贸易和金融系统参与国外竞争的国家是一项有用的政策工具。
金融危机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国际资本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纷纷流入美国的异常?经济复苏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什么会担忧大量资本流入的急剧增加呢?国际资本流入的急剧增加会对国内经济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后危机时代涌现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究竟是由于外部发达经济体实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实施的一系列量化宽松(QE)政策所致,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自身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稳定的增长预期吸引逐利资本的快速流入?以上现实与经典理论的相悖重新引起了学者们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研究兴趣,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各国正在积极构建资本流动管理的框架,包括是否实施为应对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实施适度的资本管制等措施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文章试图对这一系列成果进行梳理,重点对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经济周期波动的文献进行综述并进行评价。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卢卡斯之谜;第三部分为资本流动与宏观周期;最后是述评部分。
二、卢卡斯之谜
资本流动的研究源于卢卡斯之谜的提出。卢卡斯根据标准新古典生产函数测算得到印度的资本边际报酬是美国的58倍,美国资本富裕而印度资本稀缺,如果市场完全并且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资本应当从美国等富裕国家流向印度等贫困国家。然而现实中并未出现理论模型所预期的大量资本从美国流入印度。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应当从资本富裕且回报率较低的发达国家流向资本稀缺、回报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相反的是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在20世纪90年代一篇开创性学术性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该问题常常也被后续研究者们称为卢卡斯之谜或卢卡斯悖论(Lucas,1990)。
理论与现实的相悖,究竟是理论出现了偏差还是现实中存在着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真实因素被忽略了?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关于技术和贸易条件的假设是否恰当?哪些假设条件可以替代它们?卢卡斯对这一悖论从人力资本差异、人力资本外部收益、资本市场不完美和政治风险四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和扩展,仍然无法全部解释以上悖论。
随后学者们从金融摩擦理论解释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金融市场不再是完全的和完美的,存在各种形式的摩擦,导致资本不能实现完全自由流动。金融摩擦理论最初由Bernake and Gertler(1989)、Kiyotaki and Moore(1997)提出,用于研究借贷受限的宏观影响。后来学者将金融摩擦理论运用到开放经济,研究借贷合约受限对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借贷合约受限,例如投资者保护不足限制了经济体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借贷的行为,导致资本从稀缺且生产率高的国家 流 出 (GertlerandRogoff,1990; BoydandSmith,1997; Matsuyama,2004;Aoki et al.,2008)。Caballero et al.(2008)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有限兑付(Limited Pledgeability)问题。结果表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承诺有限兑付(Limited Pledgeability)限制了金融资产的供给,从而导致大量资本外流。Mendoza et al.(2007)则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能够提高预警性储蓄的保险市场使得资本大量外流。
也有学者从另一种形式的金融摩擦来解释资本流动,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首先由Bester (1985,1987)提出,后来被De Meza and Webb(1987)以及Besanko and Thakor(1987)用于解释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De Meza and Webb(1987)的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引致过度投资。Matin(2008)进一步研究了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引发经济体内生性经济周期的原因。AlbertoMartin and FilippoTaddei(2013)[2]通过将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同时强调有限承诺的作用,对近期的金融危机和全球失衡进行研究。其研究表明,国际金融一体化背景下,逆向选择通过产生大量的非生产性投资,资本的过度流入和内生性周期,有限承诺加剧了金融市场逆向选择在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开启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与金融危机关系的研究。
三、资本流动与宏观周期
在当前开放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决定资本流动方向及其结构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话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内容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第二,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现有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国际资本流动能够促进投资和金融发展(BaldwinandMartin,1999;ChinnandIto,2006)或者促进经济跳跃式发展(Murphy,Shleifer,Vishny,1989)。然而当制度框架脆弱时,国际资本流动会导致泡沫和金融危机(Prasad,Rogoff,Wei,Kose,2003)。因此经济增长、金融危机是国际资本流动这枚硬币的两面,是国际资本流动宏观经济效应的正负两个方面,综合来看,增长与危机又是宏观周期的不同阶段。资本流动与危机是文章重点研究内容,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也是开放宏观经济学中的另一重要命题,留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1.外部推动与内部拉动之争
危机时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始于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关于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的争议,究竟是新兴市场国家强调的外部推动因素还是发达国家宣称的拉动因素呢?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金融危机时期资本流动为发端,研究危机时期和危机后经济复苏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
不论是危机时期还是非危机时期,资本流动一直存在。非危机时期,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天顶、李洁,2013)[3]。危机时期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的研究成果颇多。Marcel Fratzscher(2012)[1]运用因素模型,采用50个国家证券投资高频数据分析了危机时期和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的不同驱动因素。Marcel Fratzscher(2012)[1]分别考察了三个层面的因素,包括全球共同因素、宏观事件冲击和国别因素冲击。研究结果表明,危机期间全球性因素是净资本流动的最主要因素。危机期间资本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的风险增加,导致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向发达经济体,因此出现了危机时期流入美国的资本不减反增,国内和国外投资者持有大量美国资产的异常。这一研究结论与避险天堂假说相吻合,即危机时期资本流动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尤其是当资产以国内货币计价并且名义汇率是波动的条件下,如果危机时期居民认为国外资产比国内资产风险更大,避险需求将引起资本外流的急剧减少。Milesi-Ferretti and Tille(2011)[4]同样认为规避风险冲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资本外流急剧减少的驱动因素。Broner et al.(2013)[5]的研究结果表明,避险因素在危机期间中等收入国家资本流入增加的驱动因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2009年3月开始的复苏阶段,全球性共同因素重要性递减,对于危机后的新兴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而言,国内的拉动因素成为驱动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
有些研究运用不对称理论来解释危机时期的资本流动。不对称理论认为导致危机时期的不对称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来源是国内居民与国外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外一个来源是主权风险的不对称。Tille and Van Wincoop(2008)认为危机期间国内居民与国外居民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危机加剧了国内居民与国外居民关于国内资产收益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导致危机期间资本外流的急剧减少。Broner et al.(2010)研究了国内居民与国外居民由于主权风险带来的不对称性对危机时期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国外投资者相比,国内投资者因为主权风险违约的概率较小,因此存在国外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将国内资产卖给国内投资者的动机,因此引起金融危机发生时即当违约风险增加时资本外流的急剧减少。
危机时期国内金融收紧和去杠杆化也是导致资本外流的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当国内投资者发生融资难时,将国内企业卖给国外投资者的情况增加,虽然这一点与危机时期FDI的减少事实不符,但将企业卖给外国人的行为只是存量资本总量的结构性调整,这一行为的增加并未影响到总资本流动的变化,因此不是影响危机期间总资本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危机时期国外投资者的财产权利保护恶化的模型预期危机发生时资本外流将急剧增加,但是考虑到影响国际金融资产交易的金融摩擦存在,资本外流反而急剧减少。Krugman(2000)、Aguiar and Gopinath(2005)、Baker et al.(2009)、Acharya et al.(2010)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第二阶段,将危机时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扩展到其它国际资本流动极端变化时期。
以研究金融危机时期的资本流动为发端,许多学者还研究了包括金融危机时期在内的其它存在国际资本流动极端变化的时期以及各期间相互的关系,例如突然停止(Sudden Stops)、涌现(Surges)和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等。Kristin J.Forbes and Francis E.Warnock(2012)[6]研究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极端资本运动形式,即涌入(Surges),资本流入的急剧增加;突然停止(Sudden Stops),即资本流入的急剧减少;外逃(Flight),即资本流出的急剧增加和收缩(Retrenchment),即资本流出的急剧减少。这四种极端的资本运动形式给新兴经济体国家带来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例如资本流入的急剧增加,一般会引起房地产泡沫、银行危机、债务违约、通货膨胀甚至货币危机;而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往往又伴随着货币贬值、经济增长放缓和过高的利率。新兴市场国家希望减少资本流动所导致的脆弱性并且减缓其负面效应,因此厘清并识别不同资本流动阶段尤为重要。
以往的研究将资本突然停止归咎于国内经济变量,事实上前期大量资本的流入已经引起国内许多宏观经济变量的内生性变化,例如经常账户赤字恶化,实际汇率的急剧升值,银行信贷给私人非银行部门的过度增加,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借贷外币的过度错配。这些由大量资本泡沫引起的宏观基本面的恶化无法被金融部门欠发达的经济体吸收,最终成为引发大量资本撤逃的抓手。当资本泡沫生成时期的变量融入到计量分析时,这些反映国内基本面的变量在预测能力上是不稳健的并且是不显著的。从这一逻辑出发,Manuel R.Agosin and Franklin Huaita(2012)[7]运用股票价格过度反应理论,分析了资本泡沫生成对资本突然停止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突然停止是对资本泡沫过度反应的结果,在控制住宏观基本面变量的情况下,资本流入是新兴市场国家预测资本突然停止和撤逃的最佳预测指标。同时Manuel R.Agosin and Franklin Huaita(2012)[7]还指出:这一研究结论并不意味着宏观经济基本面在预防资本突然停止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一国经历泡沫的时间越长,出现资本突然停止的概率就越大。具体来说,泡沫时间是三年的话,外逃的概率将翻番;泡沫时间是四年的话,概率将增加到3至4倍。这一研究结果与之前的关注基本面来预测资本抽逃的研究结果截然不同。
Thorsten Janus and Daniel Riera-Crichton(2013)[8]通过基于资本流动总量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全球性因素、传染因素和国内因素与资本极端运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的国内因素与资本流动的波动关系有限,并且资本管制也未有效抵御资本流动的波动;结果还表明,全球性因素和传染因素在形成资本流动的各阶段时重要性非常显著,因此只有通过全球性机构和跨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才能减少全球资本流动急剧波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三阶段,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进一步延伸至整个经济周期波动范畴。
关于获得IMF首肯的对短期资本流入征税的政策工具的实施,需要通过投资工具来识别不同的资本流动形式,例如短期债券、长期银行贷款和债券、证券和FDI等。Claessens,Dooley and Warner(1995)通过采用自相关系数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考察了以上述投资工具产生投资流的时间序列特性,研究了各种资本流动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波动性和持续性。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债券和贷款的投资比其它形式的投资表现出更好的持续性;长期投资工具包括证券投资和FDI,相对短期资本流动更具波动性。虽然这一研究结论与公共知识相悖,但是John H.Welch(1996)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John H.Welch(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便是在宏观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时期,商业银行短期贸易融资贷款被证明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稳定和重要来源;在经济形势困难时期,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动会迅速消失。
综合看来,Claessens et al.(1995)认为从宏观角度来讲,区分短期和长期资本流动形式没有意义。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讲,虽然这种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的区分意义不大,但是不同的资本流动形式(债券、投资组合、银行贷款和FDI)确实对宏观经济具有不同的效应。
2.顺周期与逆周期之争
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或逆周期性的研究来源于理论与模型的矛盾,同时依托于资本流动波动的研究。具体而言,实际经济周期即RBC理论认为,生产率冲击是资本流动的主要决定因素,该理论可以解释总量资本流入的问题,但是RBC理论无法解释国内居民的国内偏好(Home Bias)和国际投资的波动,现实中也并未出现如理论模型所预期的风险分散的安排,各国在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出现的大量分散风险的异质性经验也是理论模型所无法解释的。理论与模型的矛盾引起学者们对资本流动波动(以二阶矩度量)的研究热潮。
关于资本流动的顺周期和逆周期的问题,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Levy-Yeyati et al.(2007)研究了南北之间FDI的周期属性。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例,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和欧洲FDI外流相对于产出和利率周期呈现逆周期性,而日本呈现轻微的顺周期性;FDI和当地投资在源始国呈负相关关系。Levchenkoand Mauro(2007)采用系统性分析方法和142个国家从1970-2003年的年度数据,发现FDI是波动性最小的资本流动形式;不同的资本流动形式在不同的突然停止时期表现不同,但是FDI显著稳定;银行借贷在突然停止时期下降显著并且需要经历长时期恢复。Smith and Valderrama(2009)通过构建具有借贷限制和逆周期风险升水的小国开放模型,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各种流入资本的周期性。研究结果表明,总资本流入与国内投资正相关,资本流入的各组成部分有不同的周期属性,其中债务和证券投资组合与投资的相关程度高于GDP,而FDI与GDP的相关程度更高。另外,每种金融流动的波动性大于总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表明资本流动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替代性。Silvio Contessi,Pierangelo De Pace,Johanna L.Francis(2013)[9]分析了22个工业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各组成部分的二阶矩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总资本流入呈顺周期性,净资本外流呈逆周期,各类流入资本与经济周期呈正相关;FDI并不像债券、证券投资组合、银行贷款等纯粹性金融工具,FDI主要取决于产业政策和公司内部决策,与纯粹的金融变量间关系不大,因此FDI流入是新兴市场国家唯一非周期性资本流入形式。另外,G7国家资本账户自由化时期和其它内生性断点时期与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呈显著相关关系,而与不同资本流动类型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相关系数和协方差的系统性变化不相关。Milesi-Ferretti and Tille(2011)[4]以及 Fernando Broner,Tatiana Didier,Aitor Erce,Sergio L.Schmukler(2013)[5]研究了金融危机时期,国内居民和国外居民的国际资本流动行为。其中Fernando Broner,Tatiana Didier,Aitor Erce,Sergio L. Schmukler(2013)[5]的研究结果表明,总量资本比净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更大,总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顺周期性。
有些学者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Tille and Van Wincoop(2010)的研究模型预测总量资本流动是逆周期性的。Hnatkovska(2010)构建的模型得出总量资本流动是顺周期性的,证券投资组合和债券流入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Kaminsky et al. (2005)搜集了105个经济体的年度数据,发现大多数OECD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净流入是顺周期性。考虑到各类资本流动形式和大量国家数据不存在,因此无法推断各资本流动形式和总资本流动的结果。Pintus(2007)认为标准的新古典理论模型预期逆周期性的资本流动应当发挥国际风险分担的渠道。Kose et al.(2009)研究发现工业国能够取得某些稳健的风险分担,实际上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一体化增加的过程中经历了消费波动的增加。这是一种说明为什么观察到的新兴市场国家数据中缺乏国际风险分担的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国际风险分担与金融一体化是非线性关系,因此金融发展只有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实现有效的国际风险分担。因此Silvio Contessi,Pierangelo De Pace,Johanna L.Francis(2013)[9]认为应当谨慎地认为总资本流动具有顺周期性还是逆周期性,应当考虑资本流动的异质性,每类国家、每类资本流动形式都具有不同的周期性。
3.总资本与净资本之争
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对具体资本流动类型的关注。例如Forbes and Warnock(2011),Broner et al.(2010)等。近期多数实证研究关注具有不同发展和开放水平的国家间总量净资本流动。例如净FDI和净债务流动等等(Levchenkoand Mauro,2007)。然而,关注总量净资本的研究模糊了内流和外流资本总量之间的冲销行为,其对于国家和个体而言又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同时净资本流动反映的是国内和国外居民的联合行为,然而国内和国外居民具有不同的目标和投资动机。因此,分别研究由不同投资目标和动机下的总资本流动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净资本流动,Obstfeld(2009)认为金融危机也是与净资本流动有关,较少研究总资本流动。后来学者逐渐开始关注总资本流动。Tomas Dvorak(2003)根据数据和典型事实,运用动态理性预期模型研究了国际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总资本流动能够识别国际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本质。具体而言,国内投资者与国际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暗含净资本流动与收益间存在相关关系,而国外和国内投资者组间的信息不对称暗示着总资本流动与绝对收益间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后者的相关性强于前者的相关性,这暗含国家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强于国家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Thorsten Janus and Daniel Riera-Crichton(2013)[8]采用四层次分解方法,通过将净资本流入分解为四个组成部分,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投资性和非投资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组成成分揭示了是否需要保存现有的投资者还是吸引新的投资者需要不同的政策应对;正确区分非投资性资本的外流和具有负面效应的资本流入,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和监控资本管制的效果。研究结论还表明,总资本流动比净资本流动能够传达更多的信息,具有更好的预测性。
四、述评与启示
综上所述,梳理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的文献可以发现,国际资本流动问题是国际金融领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种问题复杂性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异质性问题(Idiosyncratic)、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
第一,异质性问题在国际资本流动领域的研究一直是困扰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理论分析和建模的技术性障碍,直到Cedric Tille and Eric van Wincoop(2010)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一技术性障碍。因为从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角度分析,随着金融一体化的深化,投资者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对资产进行投资组合配置的变化引起了资本的流动,表现为总资本和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从本质上讲存量的变化是流量,流量的镜像即存量的变化量。前人的研究多从单一资产视角研究国际资本流动,资本流动的经典理论利率一价定律或者利率平价学说,包括Lucas资本流动“悖论”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单一资产视角的分析方法。在单一金融资产视角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的驱动必然是收益因素,然而这种分析视角下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诸多资本流动现象,尤其是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现实。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认为,影响投资组合选择的因素处理预期收益外,还有风险因素。投资者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投资组合选择的变化必然引起资本的跨界流动。因而收益因素影响资本的国际流动,风险因素同样影响着资本的跨国流动。Cedric Tille and Eric van Wincoop(2010)成功地将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引入到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ODSGE)中,因而预期收益和风险的内生性变化(模型中采用二阶矩度量,概率统计上二阶矩表示变量波动情况)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驱动力量。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从单一资产扩展到两种资产,解决了理论模型中的异质性问题,提供了资本流动复杂现实的强有力的解释能力。
第二,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动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周期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1970s以后的金融危机时期。因此吸引大量学者研究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周期性行为,尤其是净资本流动的周期行为,此类文献的研究表明,净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很大并且是顺周期行为,尤其在危机期间急剧减少,以至于用Sudden Stop即突然骤停来形容金融危机伴随的净资本流入的巨量减少。2007-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资本并未大量从美国流出,反而纷纷流入美国;1909年后全球经济步入恢复期,资本又出现大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现象,引发新兴市场国家对资本大量涌入的担忧。纵观1970s至2000s,总量资本一直在增加,然而净资本流动却相对稳定(Fernando Broner,Tatiana Didier,Aitor Erce,Sergio L.Schmukler,2013[5])。总之,虽然关于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研究成果卓著,但是仍有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例如,国外居民购买国内资产时是否同时存在国内居民卖出国外资产的情况?国内居民与国外居民的资本流动是否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相关关系?我们知道,金融危机必然伴随着净资本流动的减少。但是这些减少是由于国外居民购买国内资产的减少还是国内居民购买国外资产的减少,抑或是二者共同减少的结果?与净资本流动相比,总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程度有多大?所有类型的总资本流动表现相同吗?或者是某一种资本流动类型驱动着总量资本流动呢?
虽然Fernando Broner,Tatiana Didier,Aitor Erce,Sergio L. Schmukler(2013)[5]的研究就以上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典型性事实,但是也还存在至少以下两方面的扩展:第一,将资本流动的变化分解为资产价格和数量的变化,这对于测度危机时期Fire Sales的规模尤其重要;第二,如果将资本流动数据与实物投资数据相结合,将为危机时期国内居民和国外居民的投资组合变化提供更完全的描述。
综上所述,以上研究成果有助于中国正确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涌入和波动。如果国际资本流动是由全球性因素所致,中国可以通过资本管制、外汇市场政策干预等方式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管理。如果国际资本流动的驱动是主要是由于国家异质性、国别政策和国别条件所致,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更多地通过提高国内制度质量、深化金融市场、提高宏观经济和宏观审慎监管等方式增强国内经济体的弹性,以应对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和波动。
[1]Marcel Fratzscher.Capital flows,push versus pull factor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2(88):341-356.
[2]Alberto Martin and Filippo Taddei.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A tale of two fric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3(89):441-452.
[3]张天顶,李洁.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的经验分析 [R].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峰会暨2013年国际金融研究论坛(秋季)—变化中的全球金融业:问题与选择,北京,2013.
[4]Milesi-Ferretti,G.-M.,Tille,C.The great retrenchment: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Economic Policy,2011,26: 289-346.
[5]Fernando Broner,Tatiana Didier,Aitor Erce,Sergio L.Schmukler.Gross capital flows:Dynamics and Crise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3,60:113-133.
[6]Kristin J.Forbes and Francis E.Warnock.Capital flow waves:surges,stops,flight and retrench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2,88:235-251.
[7]ManuelR.Agosin,FranklinHuaita.Overreactionincapitalflowstoemerging markets:booms and sudden stop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12,31:1140-1155.
[8]Thorsten Janus and Daniel Riera-Crichton.International gross capital flows:Newuses ofbalance ofpayments data and application tofinancial crises [J].Journal ofPolicyModeling,2013,35:16-28.
[9]Silvio Contessi,Pierangelo De Pace,Johanna L.Francis.The cyclical properties of disaggregated capital flow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13,32:528-555.
(责任编辑:JJ)
Analysis and Review on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 and Macro-cycle
PENG Huan-huan
(Centu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Finance,Beijing 100086,China)
Real Business Cycle(RBC)theory can not demonstrate home bias and idiosyncratic assets,it also can not fully interpretate the inernational capital flow especially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episode.A number of literatures emerging resolve the two abovementioned issues in appropriate approach through introducing equity portfolio theory to ope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ODSGE).What's more,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literatures have expanded from the zero or first order to second order which means researchers have shifted from only focusing on expected return factors to emphasizing not ony return but also risk factors.Therefore,they have built a general analysis framework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and business cycle.This new progress ha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importance for enforcing capital control and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ngement system for emerging economies.This paper reviews those research and literatures,stressfully reviews the literatures on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 financial crsis and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and makes remarks on them at last.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Financial crisis;Macroeconomic cycle;Lucas paradox;Capital control
F830.2
A
1004-292X(2014)09-0084-05
2014-05-31
彭欢欢(1985-),女,江苏连云港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开放宏观、资本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