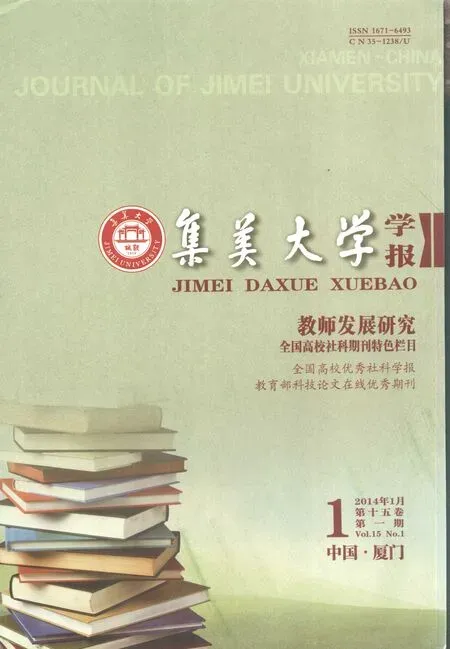新时期学习型班级建设与学生领导力研究
2014-04-14张晨
张 晨
(1.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2.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一 学习型班级的基本内涵
学习型班级是以班级成员为中心,以班级成员组织管理自治为运行机制的新型班级组织。学习型班级建设是指在学习型社会建构的大背景下,以班级组织为单位进行的创建活动。它有三个基本立意:首先,学习型班级认为每一位班级成员都有很大的潜能,但只有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才能释放出超然能力。其次,班级成员的个体利益与班级目标常常发生冲突,要使班级目标顺利实现就必须进行一定的相互协调。最后,班级成员的行为都是由其自身的某种动机驱使的,并且动机通常以人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这是学习型班级建设的三个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学习型班级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
创建学习型班级是班级组织适应新环境、新情况进行组织变革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新时期班级组织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其创建目标有三:一,创建学习型班级是为了实现班级成员之竞争力吸引聚集、契合整合。二,创建学习型班级是为了尽快实现班级目标和未来愿景。三,创建学习型班级是以期达到班级内在驱动力和班级外部推动力契合这样一种状态。总的来说,创建学习型班级是通过对班级组织形态进行变革和再塑造,对班级成员进行培训和再教育,对班级管理工作流程进行优化和再创造,对班级内部要素进行协调和重新整合的过程。其目的是要促进保持班级组织运行、运转的良性循环,使其成为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和一定范围内有效激发班级成员创造力、合理配置班级成员竞争力和科学培育班级成员想象力的班级组织模式和架构。
学习型班级不同于以往的行政控制型班级,(1)学习型班级以竞争力为主导动力,而行政控制型班级以行政约束力为动力机制。(2)学习型班级强调班级成员达到“共识”[1],行政控制型班级则强调学生个体“言行一致”。(3)学习型班级是组织管理自治,使用的纪律权威以班级成员关系为供给,而行政控制型班级是类似行政组织管理模式,使用的纪律权威源自于校规校纪的规定和教师、教辅人员的命令和授权。(4)学习型班级主张硬性纪律与柔性管理相结合,行政控制型班级则更强调硬性纪律,要求学生个体“无条件”[2]服从命令。(5)学习型班级关注的是班级成员之间关系的协调与成长,行政控制型班级则关注学生个体与纪律规范之间关系的保持与维护。(6)学习型班级注重班级成员之间情感和信息的交流,行政控制型班级则注重学生个体的行为表现[3]。总的来说,学习型班级是对传统行政型班级组织管理模式的超越与扬弃,是班级组织体制发展、模式变革和动力机制革新的统一。
二 学习型班级建设的基本路径——班级组织转型与学生领导力变革
学习型班级是开放的组织管理体系,其纪律权威和动力机制是班级成员的竞争力。学习型班级的内容架构和发展特征决定了班级组织管理运行机制是一种“竞争力匹配与调和”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型班级的建设过程就是学生领导力的创新与变革过程。
学生领导力在不同类型的班级组织模式下有着不同的本质规定。传统行政控制型班级组织视域下,学生领导力的基本内涵有以下八个方面。(1)从对象视角分析,学生领导力侧重于对“事”的治理。 (2)从功能视角分析,学生领导力注重“抑制”和“制止”功能的发挥,强调功能弱化作用。(3)从班级组织运行过程和环节分析,学生领导力强调规范规定的预先程序和事件处理的固定流程。(4)从领导力执行环境分析,学生领导力只能在封闭的区间运行,任何开放性都会对其功能发挥造成减损和破坏。(5)从领导力执行机制的特征分析,学生领导力都体现为“有序的三阶段”特征,即班级组织开展活动都经历“先声——高潮——结尾”三阶段[4]。(6)从领导力评价角度分析,学生领导力的评价标准是“数据化”指标、“细致化”量表、“精确化”统计和“静态化”分析。(7)从学生个体的认知和理解角度分析,学生领导力要求学生个体以其现阶段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水平去理解和体会各种学校纪律规定和班级领导力执行的内涵及意义[5]。(8)从领导力执行内容看,学生领导力要求学生个体对行为规范和教育教习命令的遵照和遵守。学生领导力变革要紧紧围绕上述八个方面,以实现学生领导力内涵的彻底转变与班级组织模式的完全转型。
要实现学生领导力变革与班级组织模式转型,就要建立行政控制型班级转型为学习型班级的机制体制和学生领导力变革的条件和环境。从转型过程和变革路径分析,班级组织转型过程同时也是学生领导力变革过程,它大致分为三个基本环节。
第一,重新树立学生领导力权威。确立以学生个体为逻辑起点的班级组织结构,制定能够获得学生普通接受和广泛支持的纪律规范规定,让班级管理规定和纪律规范发挥出新型班级模式的领导权威和领导效用。尊重每一位学生个体,尊重他们的发展要求和发展意愿,把学生个体作为班级组织架构中的一项功能、一个元素来对待,建立学生个体共同组成的“学生共同体”。基于“学生共同体”,实现领导权由“关注班级组织发展”到“关注学生个体发展”的转换,实现领导权权威基础即班级管理和纪律规定由“外源性授权”到“内在性支持”的转化,实现领导权权威资源由“外来性供给”到“内生性供给”的转变,最终实现学生领导权威的类型转换[6]。
第二,营造“可以犯错”的学生领导力执行氛围。学生领导权威不同于一般行政权威,它的“自下而上”的权威供给形式与行政权威“自上而下”的权威授权模式不同。学生领导力执行完全以学生个体为起点,是一个对学生个体竞争力匹配和调和的过程,它拒绝学生领导权威的滥用,主张控制和平衡,而非压制、弱化和使其不能。学生领导力执行不是中规中矩地依照纪律规定“一刀切”式的执行,而是充分考虑学生个体的发展意愿和美好想象力,促进学生之间竞争力的协调和同学关系的健康发展。在实践中,多元化的班级生活、差异化的学生类型、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进行学生竞争力的匹配和调和没有固定的标准和依据可循,只有在允许“试错”的环境和氛围下,才能保证学生领导力基本功能的实现。
第三,重新确立学生领导力执行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学生领导力建设,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行政控制型班级视野下,学生领导力目标不外乎代替教学教管人员的某些业务职能,依照现有管理和纪律规定严格执行,实施类似“法治”的管理控制模式。而新型班级组织模式下,学生领导力更加强调的是“学生自治”,是学生共同体之自治。它追求的目标是学生个体竞争力的互相吸引和聚集,最终实现学生竞争力之整合。只有在“竞争力调控”的定位上,班级组织才能履行完整意义上的服务义务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功能。而只有在新型班级组织模式下,班级文化和班级精神建设才成为现实上的可能。
三 学习型班级视野下的学生领导力发展
在学习型班级组织模式下,学生领导力的基本内涵 (同时也是学生领导力变革的基本目标)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1)从对象视角分析,学生领导力侧重于对“人”的管理。(2)从功能视角分析,学生领导力注重“疏导”和“开发”功能,重视功能强化作用。(3)从班级组织运行过程和环节分析,学生领导力关注学生之间的现实交往和日常联系。(4)从领导力执行环境分析,学生领导力要在开放状态下才能发挥作用。(5)从领导力执行机制的特征分析,学生领导力体现为“同步的三阶段”特征,即“全员参与——全员奋进——全员发展”三阶段。(6)从领导力评价角度分析,学生领导力的评价标准是“文字化”指标、“意义化”量表、“非精准化”指导和“动态化”分析。(7)从学生个体的认知和理解角度分析,学生领导力要求学生作为主体,按照其的心理意愿和主观情感去制定彼此约束的规则。(8)从领导力执行内容看,学生领导力要求学生个体在思想上有共识、情感上有共鸣、理念上有认同[1],更加关注学生个体的思想状况。总的来说,学习型班级是以激励和合作为中心的竞争力契合型组织,学生领导力的主旨内涵就是分析学生个体的竞争力结构以及匹配、调和学生之间的竞争力。
在新时期,如何提升学生领导力水平,实现学习型班级的组织转型和学生领导力的变革?
首先,树立学生自治意识是首要前提。“学生共同体”区别于行政控制型班级的重要特征就是“学生自治”,即尊重学生自我管理的权利、重视学生自我及相互管理能力的培养和满足学生自我管理在实践发展中的需要。学生自治的重要价值观是“共识”,促进学生之间达成理想和信念上的一致、态度和观念上的一致、目标和行为上的一致。基于共识基础的自治意识[1],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学生自治。学生之间的社会性交往和情感信息双向交流所产生的主流价值观、主体行为和主要动机是“共识”的延伸和扩展[7],因此,学生领导力获得了来自于学生群体的广泛合法性基础和普遍性支持。[8]
其次,维护学生领导权威是重要保障。学生领导权威容易受到多方面权威因素的影响,比如来自于班级组织外部的行政性命令和要求、来自于教育教管人员的即时性管控等等。保障学生领导权威不受外界权威的无端侵害,是学习型班级组织保持稳定架构、和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班级管理实践中,学生群体自发产生的“民间权威”亦会对学生领导权威造成消极影响,非共识意义上的团伙式权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领导力的发展。执行学生领导力的人员因素以及班级组织上的管理职权设定不再固定为班干部个人,任何学生作为学习型班级中的构成主体均有学生领导力执行监督的权威及权力。
再者,变革班级组织架构是关键步骤。班级组织运行机制是组织架构和职能设定的外化,“竞争力架构匹配及关系调和”是学习型班级组织的基本特征。每一位学生的竞争力结构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约束,都是“均等”权威基础的,即消除学生领导权单一设定模式,实现人人都有领导权威、人人都有领导权。只有在没有明显高于普通学生领导权威的氛围和环境中,单元领导权威集中现象才会消灭,“均等”权威基础才能形成。既往的信息控制模式得到彻底改变,外部信息和资源输入班级时,人人充分共享、人人普遍实施、人人自我考核。这是学生领导力的现实范围和实现空间,同时也是学生领导力发挥功能的有效边界。
最后,完善班级纪律规定是基础环节。规则是班级组织架构中的骨骼,任何价值和目标的贯彻和执行都依靠具体规则来运行[6]。规则是共识的结果,规则制定实施的有效性完全在于共识表达的完整性和共识实践的现实需要[9]。以纪律规定形式出现的规则系统,既是学生领导力执行的动力基础,也是班级文化和班级精神文明的体现。明确纪律规定的规则定位,实施规则意义上的纪律教育,改变传统“德育式”和“法治化”的教育实践方式,才能还原纪律教育的本质意义,进而实现“通过教育的纪律”、学生个体的纪律化和“美化集体的纪律”[2]。
[1]张铁勇.论以谋求共识为核心的德育理念 [J].道德与文明,2003(6):67-71.
[2]张晨,李一澜.加里宁纪律思想研究 [J].职大学报,2012(5):87-89.
[3]周毓方.丁浩川教育文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4:132.
[4]张晨.加里宁宣传思想研究 [J].职大学报,2011(5):102-104.
[5]王明方.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101.
[6]张晨.论中学生的纪律规制——兼谈中学生纪律观重塑与法治观改造 [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3(10):12-14.
[7]陈嘉明.社会规范本质的哲学解释 [J].江海学刊,2000(5):100-104.
[8]冯文敬.共识意义观:一种意义理论的雏形 [J].外语学刊,2009(2):7-9.
[9]王桂平.西方学校纪律研究的趋势与借鉴 [J].教育评论,2008(1):14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