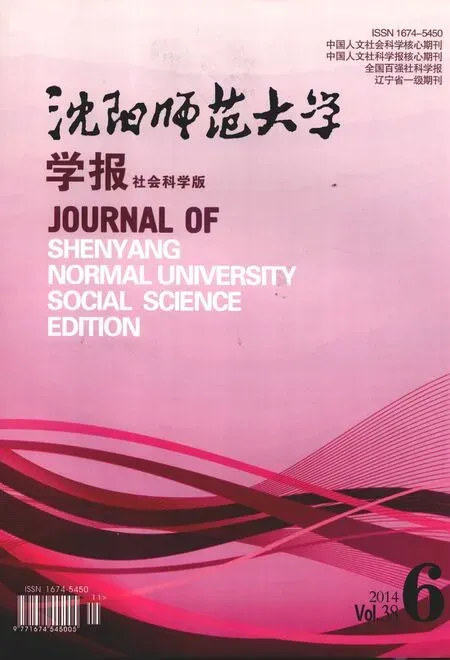论洪毅然“功用”的美感思想
2014-04-11孙殿玲
孙殿玲,刘 炜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论洪毅然“功用”的美感思想
孙殿玲,刘 炜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在中国现当代美学中,洪毅然的美感思想独具特色,不仅强调美感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性,认识到美感的历史性存在,而且对美感和快感作了严格区分,承认“有用”和“好恶”等个人利害观念对美感形成的直接影响,并大力提倡审美实践活动,主张通过美育来培养人的审美感觉、审美情趣。特别是,洪毅然把实用艺术当作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完成美感教育的有效途径,把“功用”性作为贯穿他的美感思想的主线,这与他坚持审美和艺术服务功能的观念紧紧相联。他的美感思想,于理论于实践,于过去于未来,对审美实践与理论研究都有指导意义。
洪毅然;美感;功用
我国现代美学曾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形成两个流脉:一是一般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的中国美学,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中国美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中国美学研究走出了西方思辨哲学和心理美学的形而上的圈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密切结合中国历史和当下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服务对象等问题进行研究,创立了一套别具特色的美学思想理论。作为这种美学思想理论形成的参与者之一,洪毅然的美学思想,特别是他的美感思想,立足实践,兼顾历史,强调功用,对审美和艺术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一、“美的知觉”根于社会历史
洪毅然美学思想深刻而丰富。在美感问题上,他始终强调社会历史条件对审美感受形成的制约作用。在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他就被称为“社会功利派”。在他看来,“美的知觉”的产生以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
(一)“骄傲和自豪”基于社会生活经验
任何感觉的形成都离不开社会历史环境,都与一定的生活经验有关,并表现出一定的功利色彩。这是贯穿在洪毅然美感思想中的一条主线。
首先,洪毅然认为,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美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认为,“婴儿不辨真和伪”,因为婴儿缺少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经验,所以对于真善美假恶丑,不具备分辨能力。这是美感产生于社会生活经验的证明。由于任何个人都存在于一定时代、民族、阶级之中,因此,一切个人的生活经验,也就是一定社会中的社会实践关系。正因为如此,人在所有的美感经验中,关于对象在其感性直观基础上所被唤起的、有关该事物在人的生活实践中的联想内容,都有社会功利性,因此不同时代、民族、阶级的人,对于相同事物才会有不同的美感,进而形成不同的美的观念。而这种美的观念,又必然影响人们的审美活动,指导美感向一定方向发展。
在对审美感受形成的心理过程描述中,洪毅然更加强调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认为在“美的知觉”形成的初级阶段,“联想”基于生活实践的唤起和激发。他认为,在美感形成的心理机制中,“联想”是一重要环节,这一环节是被由此物推彼物,触动回忆的
神经催生的。这个回忆,是审美主体过去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具体关系中的记忆,要受到当下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环境制约。他还举例说明了这一点。过去时代,在公共场合说起红色五星,在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下的人是胆怯的,在胆怯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美感。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公共场合再说起红色五星,自然满是骄傲和自豪,并会为自己成为共产党的一分子并拥有这样一枚红色五星而自豪。这个时候,人们对红色五星就会产生美感,红五星也因此并被认为是美的。产生这两种变化的原因,并不单纯的是人变了,而是时代变了,社会历史条件变了,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审美感受的变化。
同时,洪毅然还认为,在“美的知觉”的形成中,“受着一定时代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而存在人们头脑里的美的概念、观念、观点,也是经常起作用的。否则,不会构成对于对象事物形象作出美的或不是美的判断,即不会使一般知觉发展成为‘美的知觉’”[1]100。社会历史条件影响美的知觉形成,没有这一影响,普通的知觉就不会发展成为美的知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难免会把个人的美感绝对化,从而割裂了与社会历史乃至与整个人类社会集体审美文化生活的关系。
其次,洪毅然认为,人们对美的感受,也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对象和审美主体处于一定社会生活实践关系中,如果关系不同,那么审美主体的表现和反应也就不尽相同,“凡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所规定了的限度内,事物处于人类某种一定的生活实践关系中,所起作用如果实际有益于促进人类生活向前发展者,就好;反之,就坏”[2]43。因此,相同的事物可能因其所处时代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反映。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梵高的画,在当时,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欣赏水平有限,因此觉得梵高的画不可理喻,色彩混乱,甚至丑陋,并不受赏识,而今却价值连城,人们认为他的画充满想象,那明亮的色彩表达的正是对生活的热情和感悟,是极美的。显而易见,梵高的画本身并没发生任何变化,而仅仅因其社会历史条件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不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这已经触及到了美感的相对性问题。洪毅然能够看到美感的相对性,是唯物的,说明他对美感的认识,没有脱离社会历史,不是书斋生活里个人不切实际的空想,摆脱了以往单纯的哲学思辨。对此,穆纪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洪毅然的这一贡献,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二)“形象的直觉”是社会化了感觉
洪毅然谈美感,是在论及美的问题时涉及到的。他认为,“美是客观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1]54。秉承李泽厚的思想,洪毅然认为,美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一点并无新意。而特殊之处在于,他从论美进而讲到美感。他说,凡是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之中的自然事物,因为不具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意义,也就没有美和丑,自然也就不会产生美感。只有当事物本身具有好的自然属性,并从与人的社会生活关系中取得好的社会属性时,事物在人的眼中才是美的。在洪毅然看来,美感与丑感,不论是其自然属性,抑或是其社会属性,其实都是由人类决定的,而事物本身的属性并没有好或者不好之分。在这一点上,他把美感的本质从自然功利上升到社会功利层面,认为美感虽起于自然属性,但却决定性于社会属性。
因而,在美感内容构成上,洪毅然否认了美感是纯粹“形象的直觉”。他认为,如果美感只是单纯感官上的刺激所引起的直接感觉,没有社会内容的参与,就不存在美感和丑感。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外物的感官刺激,人有时的确能产生那种舒适的感觉,他称这种感觉为“快感”。他将快感与美感进行了区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洪毅然格外强调社会条件的作用,但同时也并不抛弃事物的自然性,他始终坚持事物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观点,认为只有两者得到统一,美感才能产生。所以,洪毅然的社会功利美感思想与李泽厚等人的思想有所不同,他在《美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与李泽厚同志商榷》中提出,将自然美融解于社会美是值得商榷的。
二、“可爱”基于个人益害观念
强调个人益害观念对美感产生的影响,是洪毅然功用美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谓的个人益害观念,与社会历史条件并不抵触。在他看来,当我们对事物产生美感或丑感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觉知事物是否“可爱”的时候,却并不仅仅是根于社会历史条件的要求,也基于个人益害观念的影响。
(一)人类觉知为美的东西源于“有用”
在洪毅然的美感思想中,总是伏着“功用”因素。他曾引用鲁迅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社会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观点的,到后才移到审美的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的分析而发现。所以美的享乐
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的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3]19洪毅然认为,人类觉知为美的东西首先是于他“有用”,这里的“有用”,便是个人过去的经验所产生的益害观念。
洪毅然认为,人们对审美对象的选择出于“有用”。他曾给美感下过这样样一个粗略的定义:“美感是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现实界事物具体形象的感性直观的感受。”[1]85主观意识,便有个人益害的成分。洪毅然认为,美感起于对象的外部直接感觉的快适,进入联想阶段辨认出对象为何物,辨认过程中并不仅仅是辨认其“是什么”,必然同时会联想到此物“有什么用”。而“是什么”和“有什么用”,总是不可分割地存在于人们过去的社会生活实践记忆中。正因为在辨认“是什么”时总要想着“有什么用”,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联想过程中重现所有与对象事物有关的种种记忆痕迹。这时候,个人益害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如果这个对象事物在过去人们的生活实践经验中所起的作用是好的、有益的,人们便会产生一种积极状态,容易形成美感。反之,便会产生一种消极状态,不易产生美感,甚至会产生丑感。与此同时,人的美感或丑感在这个时候也会一并产生,对象事物才有了可爱的或者可厌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对象物的“表现”,也会加深或者减弱人们在过去的生活实践经验中对此类事物的记忆内容。这是洪毅然的一个独特发现。他认为,如果对象事物是“可爱”的,那么它可爱的程度会反作用于过去的生活实践经验,从而加深对此类事物的喜爱。反之,如果对象事物是可厌的,那么它可厌的程度,也同样会反馈到过去的生活实践经验之中,从而加深人们对此类事物的讨厌。同样,如果此时的对象物虽在过去的经验中不那么“可爱”,但此时由于其他原因使得对象事物变得“可爱”了,那么也会减弱人们过去的经验中关于这个对象事物“不可爱”的记忆。也正是因为这样,有些事物人们才会越看越喜爱,而有些事物人们会越看越讨厌。比如现实生活中有些东西,我们开始未必真心喜欢,甚至是觉得讨厌,但因为此类东西于我们“有用”,那么很可能我们会因其“有用”而减弱心中对这类东西的讨厌感,甚至会在此类东西在现实中不断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觉其“可爱”,产生美感。
(二)“喜好”关涉美感
在强调社会历史实践对美感形成的重要性时,洪毅然也承认个人偏好对美感的直接影响。
洪毅然认为,美感产生并不仅仅因其“有用”,更多时候基于我们个人的“喜好”。在美感产生过程中,“喜好”会加强或减弱之前我们头脑中的经验,从而对事物产生美感。洪毅然以生活实例论证了这个观点。比如有的人喜欢玫瑰花,恰好又是喜欢的人送的,那么他就会因对这个人的喜爱而更加喜欢玫瑰花。同理,如果这个时候玫瑰花的“可爱”经验影响了此时他对送花人的感受,那么送花的人也同样变得“可爱”了。又如,如果有人原本讨厌戴眼镜的人,但后得知此人是因视力不好不得不戴时,忽而又觉得戴眼镜的人变得“可爱”了。就是说,由于他本人对喜爱的人的喜爱,便冲淡了他原本过去生活实践的记忆中对戴眼镜的反感。可见,美感并不一定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产生,它与个人的喜好有关。这就好比“子不嫌母丑”,这里的“母”也并非一定不丑,而决定母不被认为是丑的,恰恰是因为儿子对母亲的特殊的感情。这种条件下所产生的美的感受,往往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而更多的是基于个人的益害观念。
不难看出,在人对一切事物的审美过程中,个人益害的参与十分重要,“人们对于事物在认识思维过程所达到的益害判断,正是对当下所知觉到的那个对象事物形象产生美感或丑感的必要条件”。[1]92个人益害在美感产生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正是洪毅然美感思想有价值之处。在他看来,一切美感就其有生活的联想来看,是社会客观的,就其感性的直观来看,掺杂着个人益害观念。这是洪毅然的功用美感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兴味盎然”源于社会实践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辩论中,洪毅然是以实践美学主将的身份出现的。在他看来,美感乃至美学发展并不应无功利,而应当符合社会时代要求,自觉服务于人民群众;各种美学思想、理论及观点,并不应当止步于自身的研究发展,而应当回到审美实践中去,指导人们的审美实践活动,从而使人们“无往而不兴味盎然”[7]215,继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审美文化水平。
(一)培养兴趣是审美实践活动的目的
在洪毅然看来,追求美感,不是仅仅追求纯粹的审美愉悦和审美享受,而是通过这样那样的审美实践活动,在享受愉悦的过程中,培养大众的审美兴趣。
众所周知,洪毅然是美感教育的大力倡导者。他认为,用美学知识或美学理论、美学思想指导审美实践,有利于整个社会审美文化水平的提高;美感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端正人们的审美观点。他还认为,美感教育的任务就是促进人们的审
美实践。他本人主张普及美学,因而提倡大众美学,并身体力行,撰写了《大众美学》之作。也正是因为他在大众美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本人亦被誉为“大众美学的开拓者”。
洪毅然对审美实践的重视,颇受席勒和蔡元培的影响。他极力推崇席勒的美育思想,并加以继承发展,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原本贵在不自陷于徒有饮食男女等事”,“尤当充分发展独具之理智而富有道德意识,”才能“由‘生物人’上升为‘社会人’”,而“通过各种审美实践活动以培养人们对于一切事物的‘人的兴趣’,实为必要之途径和阶梯”。[1]208生活生产活动中处处存在审美活动,这些活动又与人们的道德品格、个人素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如何正确地引导人们的审美活动,使它有利于人类生产活动,便显得极为重要了。而美感教育作为引导人们审美活动的渠道,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看来,人只有通过审美实践活动,才能获得美的享受,获得快乐,“始而无愧于为‘人’”。他强调美感实践活动对培养审美兴趣的重要意义,但并不认为美学是无目的的活动,尤其是美感教育活动,一开始就应当有目的性;对审美活动最终效果的有效性判断标准,也是看它有没有完成当初设定的任务。他格外重视美感教育对人格完善的作用,曾与朱光潜等人联合致函党中央,建议将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同时,他还担任全国美育研究会顾问。
(二)实用艺术是美感的实践
关于美的研究对象问题,洪毅然有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一切艺术的起源,本来都是实用的”[1]34,实用艺术就是对美感的一种实践。而那些艺术品、实用艺术如果安排得当,会对生活起到非常明显的积极作用,从而指导人们在实践中更好地进行审美,进而提高审美情趣。因而,他主张将实用艺术的美归入到美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内。
首先,洪毅然强调实用艺术在实践中的潜移默化作用。他指出,在那些家具和陈设都很厚重朴实的环境中,由于吃的、穿的、用的都很朴素,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淳朴的生活作风;反之,如果人们在生活环境中接触的都是浮夸、奢靡之物,那么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人也就容易形成浮夸奢靡之风。同理,人们营造一种好的氛围,就是希望给自己一个积极影响。当今对房子的装修当属此类。对此,我们不能因某人带有主观意愿而否定所创造的美的东西,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对房子刻意的装修而否定房子装修本身所带来的美一样。洪毅然指出,实用艺术也是艺术,实用艺术的美也应当归入美学的研究对象之内。否则,将阻碍实用艺术的发展,也会阻碍美的创造。
其次,洪毅然主张通过实用艺术进行美感教育。他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凡是属于“按照美的法则而造成东西”的产品,都在艺术之内。因为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动物不同,在人类的种种活动中,不仅有需求的法则,也有美的法则。因此,广义的艺术便覆盖了所有人类参与的所有生产生活。在这里,由于狭义的艺术美育作用众所周知,洪毅然先生没有给予过多解释,而是重在阐释广义的艺术对美感教育的作用。他所说的广义的艺术,其实更多的是实用艺术。为此他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如服饰,除了有御寒保暖这种实用功能外,不同服饰还能传达出个性特征。因为有人喜欢他穿着的个性,就会愿意与之亲近。久而久之,穿衣的人和愿意与他亲近的人,会因为他们对于服饰的喜好形成某种固定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倾向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作风和习惯。“箪食瓢饮”者就容易勤俭持家,保持节约的生活习惯。这就是广义的艺术所发挥的美育的作用。与狭义的艺术发挥作用相比,广义的艺术发挥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潜移默化中。因此,洪毅然提出,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生产生活中一切“美的因素”,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其进行强化,不断提高、丰富、发展,使之有利于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从而完成美感教育的任务,实现“人的复归”[1]211。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指导实践,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洪毅然的美感思想中,实践不仅是检验美感乃至美学发展的标准,更决定了美学今后如何发展、怎样发展。我们的美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要走进生活,为生活服务,在美的生活创造中发挥它有特殊功能。因而,洪毅然功用的美感思想,在今天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创造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洪毅然.陇上学人文存——洪毅然卷[M].李骅,编选.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2]洪毅然·美学论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3]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序言[G]//鲁迅全集.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杨抱朴】
B83-0
A
1674-5450(2014)06-0090-04
2014-09-23
2012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2DZW012)
孙殿玲,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刘炜,女,山东东营人,文艺学硕士研究生。